读书《城镇交通:关于城市地区长期交通问题的研究》解读
2019-06-25魏贺
魏 贺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45)
1963年11月,英国交通部发布了名为《城镇交通》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是由布坎南领导的7人工作小组历时2年完成的,故也被称为“布坎南报告”。当时,英国正处于“赶美超苏”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和机动化革命全面推进的白热化阶段。报告开创性地探索了城市地区道路与交通的长期发展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探讨如何与机动车这一“至爱怪兽”(monster we love most dearly)和谐共存。
报告语言朴实风趣、逻辑严谨周密、图表精美细致,一经出版便家喻户晓,那些扣人心弦的技术插图和富有哲理的评述建议备受业内赞许、官员推介、媒体聚焦、全民关注,其简本在4个月内售出1.7万册,德法西日多语言译本畅销海外,第一次将交通研究由技术同行评议推向社会公众热议。
报告以环境分区与道路网的关系及街道环境承载力为切入点,以布坎南环境哲学观为理论基础,通过解析4个不同尺度的本土案例以及欧美实践经验教训,就空间结构、城市形态、历史文化保护、综合再开发、停车政策、干路网规模和投资保障等方面创造性地提出25条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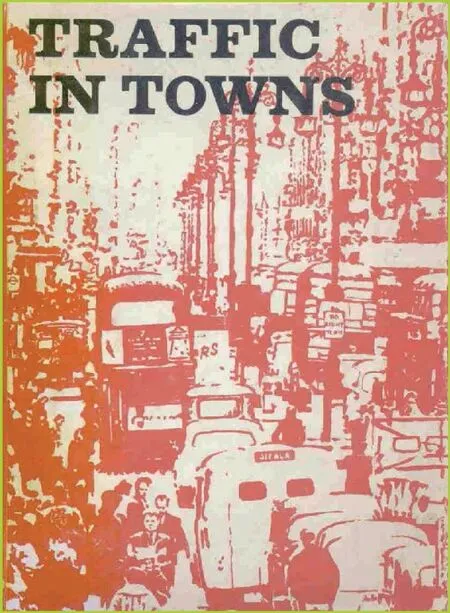
城镇交通:关于城市地区长期交通问题的研究
作 者:柯林·布坎南
出版单位: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出版时间:1963年11月
伟大思想付诸行动终成壮举
作为20 世纪60年代交通主流研究的佼佼者,报告罕见地受到执政党与在野党的一致支持。布坎南报告与同期的比钦报告(Beeching Report)《重塑英国铁路》(The Reshaping of British Railways)、Smeed 报告(Smeed Report)《道路收费:经济与技术可行性》(Road Pricing:The Economic and Technical Possibilities)具有典型的时代羁绊。比钦报告因关停支线车站以扭亏增盈的负面政治影响而臭名昭著,布坎南报告则因缺少对铁路与地铁等公共交通服务的充分论述而备受诟病[1]。Smeed报告因偏离执政党政治选择与政策偏好而生不逢时,布坎南报告则因“城市形态是静止不变”的假设被Smeed研究小组成员迈克尔·比斯利(Michael Beesley)质疑[2],又因使用由Michael Beesley所提出的成本收益分析时的语焉不详而饱受批评[3]。
作为唯一入选20世纪英国规划师重要参考文献排名的交通研究,布坎南报告位列第4位[4],与第5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形成鲜明对照,后者代表公众从社会视角对城市规划及重建理论展开深刻反思与严肃抨击,前者代表政府从社会—技术视角探索有别于美国城市交通发展模式的英国路径。伦敦大学学院迈克尔·贝蒂(Michael Batty)教授认为,报告的发布标志英国城乡规划由技术工具型规划(planning as a craft)向社会科学型规划(planning as a social science)的转变[5]。
英国法定发展规划是基于《城乡规划法1947》的一级形态规划(One-Tier Form Based Planning)体系,尚未考虑交通发展的巨大影响。布坎南报告认为大型城市法定发展规划应增设交通规划(Transportation Plan)作为强制内容,这一建议被《城乡规划法1968》所采纳[6]。报告在法定图则上的小进步有力地推动了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规划的一体化融合进程,将交通研究提升到学术、政策与政治三重属性的全新高度,是交通学科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现代交通研究的诞生[7]。经典著作《英国城乡规划》[8]认为,“任何关于交通规划(交通政策)的讨论都始于此报告”。
报告认为交通规划对应着长期发展问题,解决现状问题与近期冲突还需要实施规划(Implementation Plan)。这一建议极大地启发了于1964年成立的住房和地方政府部(Ministry of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麾下的规划咨询组(Planning Advisory Group)。规划咨询组将土地利用—交通整合规划与布坎南环境哲学观相结合形成结构规划(Structural Plan),将实施规划与地方发展规划相结合形成地方详细规划(Local Plan)[6]。两者共同构成《城乡规划法1968》中的二级结构规划体系,既有宏观引导又有土地利用控制,标志着英国城市规划体系由传统蓝图型规划向政策导向型、协商选择型规划的转变,是空间规划体系的雏形。英国科学院院士彼得·霍尔(Peter Hall)爵士高度评价布坎南对英国规划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巨大贡献,称赞其当之无愧为英国最著名的规划师,认为其影响力远超制定《大伦敦规划1944》的Patrick Abercrombie教授[9]。
布坎南环境哲学观
布坎南报告的重大贡献在于,探讨需要何种城市形态、交通模式以及如何实现,描述一种环境哲学观或者原则,并试图将其核心“将就原则”(Rough and Ready Law)应用于现实。
“将就原则”由机动车可达性、人居环境标准与物理改造投资成本三个指标组成。可达性指标代表机动车使用程度的承载水平,包含车辆安全、流线布置、停放分布和布局形式四方面权重;人居环境标准指标度量交通负外部性影响的承载水平,包含安全性、舒适性、便捷性和外观性四方面权重;两者相互作用形成环境承载力(Environmental Capacity),与考虑道路容量、停车容量的物理设施基本承载力(Crude Capacity)共同构成街道环境承载力。
任何地区都要有一个满足一定环境标准的交通承载力上限。环境标准决定可达性,可达性根据物理改造资金相应调整。地区所承载的交通量及特征需和优质的环境品质相一致,当出现反环境效应或面对历史文化保护、公共健康提升和基本住房保障等重大民生决策时,对三者的取舍应由社会民主决定(the choice is society's)。
布坎南环境哲学观在一定程度上被误解或被有意曲解。报告中提到的交通建筑(Traffic Architecture),基于人车分离与综合再开发理念形成的多层立体交通系统,被媒体形容为“激进的城市外科手术”。报告本意只是描述一种开放性选择,列举出解决交通问题从无所作为至做到极致(do nothing to whole hog)的优缺点[10]。英国《卫报》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论[11]:“布坎南从未倡导过机动化发展的极致场景,其描述的多层立体交通系统、复杂立交桥和高通行能力机动化场景却极大地吸引着新生代交通工程师,这些人将其视为一项宏伟工程和个人荣耀。而布坎南一直坚持的是城市环境品质,公共空间才是城市文明的真正宝藏”。
睿智冷静的辩证思考
在对道路网规划的技术思考中,报告认为“大规模修建环路更多的是靠直觉,而不是基于对交通流的深入研究”。“环路+放射”奴性思维化的标准格局方案,即便建成后的OD调查可以印证环路承担足够多的交通量,规划设计方案足够合理,也只是等同在浸透水的地区增设排水沟,排水沟一定陷入“果”的结论必然总是服从于“因”的先验使然之宿命。道路网规划应尽可能地摆脱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也许经过充分论证后,仍旧形成了“环路+放射”的格局,但其是自然生成的,不是直觉、经验和标准所规定的。
在对策略、措施的政策思考中,报告认为“交通问题不存在明确、最优的解决方案,不是一个问题对应一个方案,而是在一段时期内对偶尔出现的事件用政策去耐心处理”。“新建道路、拓展公共交通、拥车用车停车限制”三大对策互相依赖、互相影响,决不能随意使用,需要对实施机构、外界刺激和时间节点进行严谨论证,综合研判复杂性。如果选择与机动车和平共处,就理应重建一个不同的城市;如果无法承受大规模重建和环境品质破坏,亦理应限制机动车交通。
在对未来方向的行动思考中,报告认为“在面对机动化浪潮的严峻挑战时,若要取得比前辈(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时代)更大的成就,必须果断面对,不再困惑于目的,不再胆怯于手段,事不宜迟”。研究者要拓展视野,多专业合作,多领域协同。城市形态、量化预测、路网格局、环境管理、综合开发保障、成本收益分析、新式客货运输七个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全社会要建立一种“机动化责任”(Motorised Responsibility)的第六感,公众要对机动车的文明使用做出英雄般的自律。
时代之子,共鉴共勉
时至今日,报告中的诸多观点难免有着时代与地域的局限性,但是《城镇交通》仍不愧为时代之子[12],其哲学观、思辨逻辑与启示警示值得当下中国在机动化浪潮即将扑来之际系统性学习、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超越[13]。
反复推敲报告,脑海中不时重现智慧火花的闪耀、激发思想见解的共鸣、回荡观点异见的碰撞。谈及交通工程,交通规划的共识是关键;谈及应用技术,社会公众的支持是前提;谈及改善策略,上位政策的呼应是基础;谈及措施实施,体制机制的缺陷是瓶颈;谈及重大决策,政治政体的规则是桎梏。这一切令人情不自禁要对往事一探究竟。
在追溯历史事件、梳理发展脉络的过程中,不禁感叹整个英国交通规划与政策发展路线的曲折与不确定。即便如此,这一言难尽的不确定性中仍有着唯一的确定性,即对美好愿景的执着追求。交通本身仅是实现这一愿景的手段与方式,有悖初衷者定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所淘汰。文末,愿以报告最后一言与读者共勉:“以朝气活力、宜居宜业之方式重建城市环境,定是最为重要之事,借此英国将成为全世界最激动人心的国家,其幸福安宁与繁荣富强不可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