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电影中的科学该长什么模样
——从《流浪地球》引发的争论说起
2019-06-21西夏
西 夏
电影《流浪地球》引来的众多批评、讨论中,有一类是特别针对其中的科学问题的。这些批评和讨论无疑具有科学传播和科普教育上的正面意义,但同时很多观点也暴露出了在公众中大量存在的对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的认知盲区,归根到底,这还是一个科幻和科学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的问题。
关于对电影《流浪地球》科学内容的批评,归纳起来不外乎几种:
第一种意见猛烈抨击电影里的科学不合理,不但故事发生的基本设定、前提不科学,故事讲述过程中也充满了不科学的细节,结尾的高潮更是不具科学正当性,批评电影中的科学属于“误导公众” 的“伪科学”,进而全盘否定这部电影的价值。这方面的批评以某些科技媒体、科学传播媒体和自媒体为代表,最为突出的当然就是那篇豆瓣文章《流浪地球,不及格》,该文声称《流浪地球》彻底不及格,从而在网络引发了激烈的情绪对抗。
第二种意见只是客观分析电影中某些科学上的不尽完美,其著名代表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粒子物理学家张双南教授,凭其高级专家身份而自带权威性,他一边赞美电影带来的各种震撼,一边分析《流浪地球》不够科学之处,并尝试提出某些更好的解决方案。张教授提到了科幻电影中的科学与审美问题,认为科幻不但是基于“科学”的“幻想”,更是对科技的审美创造。不过张教授并非电影美学专家,对电影《流浪地球》中的科学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其评价还是相当于一般人所说的“瑕不掩瑜”,这类说法最不负责任的表述就是“不过一部科幻电影,大家不要太当真”。
第三种深入挖掘电影中的科学和技术细节,经过大量的分析计算,证明电影中的各种错误,从而在向公众普及很多冷门知识的同时,带着微笑与善意,指出“这是一部值得我们为之挑毛病的优秀的电影”,这类批评以地球知识局的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流浪地球〉里的杭州,为什么说没就没了?》为代表。
以上三种批评其实都依赖于基本情绪立场,即对电影的最即刻的观感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也就是说,情绪反应是该片引发激烈对抗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包含了对演员吴京及某种意识形态倾向的强烈憎恶,对此本文不作深入分析,只探讨这些批评中反映出来的某种共同的思考缺位,即它们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科幻电影的叙事结构中,科学到底居于什么地位,或者说,科幻电影中的“科学” 元素到底该如何呈现才是有效的,至少是能被接受的叙事元素呢?
电影当然都是虚构的(即使纪录片也有立场的选择和叙述建构的成分),但它之所以能被我们接受进而被欣赏,其实是基于创作者和接受者(观众)之间的一个基本的心理契约关系,这种关系借用英国批评家柯勒律治发明的一个概念“the 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可以完美描述,柯勒律治在分析戏剧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这一概念,译成中文即“姑且信之”“自愿搁置不信”“自愿中断怀疑”等,意在表达观众明知舞台上的事件是虚构的,却决定暂时放弃自己的怀疑态度,要么跟随舞台上的虚构情节沉浸其间,要么保持一种审美上的距离感静观其变。戏剧观众的这种心理状态同样适用于电影观众,否则电影的欣赏过程就没法开始。而一部失败的电影,往往是在电影叙事的过程中,因为影像语言上的种种错误而最终破坏了观众的这种自愿搁置的怀疑, 或者让怀疑、批判,甚至是彻底否定的倾向占了上风,观众“出戏”,契约关系即告破裂。
这样一种基本的心理预设机制决定了电影故事可以用一个假设(what if)来开始。作为观众,大家买票进场,一开始都是兴致勃勃,准备好了来看一个好故事,准备好了被感动、被震撼、被启迪、被逗乐。电影故事的这种假设的开场可以是某种天大的巧合,比如“两个富翁打赌,要给一个穷人一百万英镑,看他一个月后会如何收场”。故事就此展开,这就是马克·吐温小说改编的著名电影《百万英镑》。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现代人都会对这个故事的结局感到好奇,看完电影也会在会心一笑之后得出“资本主义如何如何”的结论。如果某人因为富豪不可能把一百万英镑交给穷人,或者英国没有发行过百万英镑的钞票这样的原因,就高喊“这个故事是无稽之谈”,那么我们除说他是“杠精”以外,也只好叫他们不要再看电影。
在批判电影《流浪地球》不科学的意见中,有一类是说太阳根本不会在近未来氦闪,地球也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发动机推离太阳系。持这类意见的人甚至声称“《流浪地球》宣扬的是彻底的伪科学”,他们忘了科幻就是这样一种执拗而有趣的思想试验,试验的前提条件就是:假如太阳要氦闪了,人类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看完电影,能在高高兴兴地饱受惊吓之后回家告诉小朋友不用害怕,太阳还年轻着呢,还有几十亿年的岁月静好,那么制片人和观众都会皆大欢喜。那些高喊这部电影根本就是瞎扯的朋友没有明白游戏的魅力,或许可以复习一下那个军阀和篮球的故事:一个军阀看到手下十几个兵在哄抢一个篮球,愤怒地训斥部下成何体统,为什么不每人发一个篮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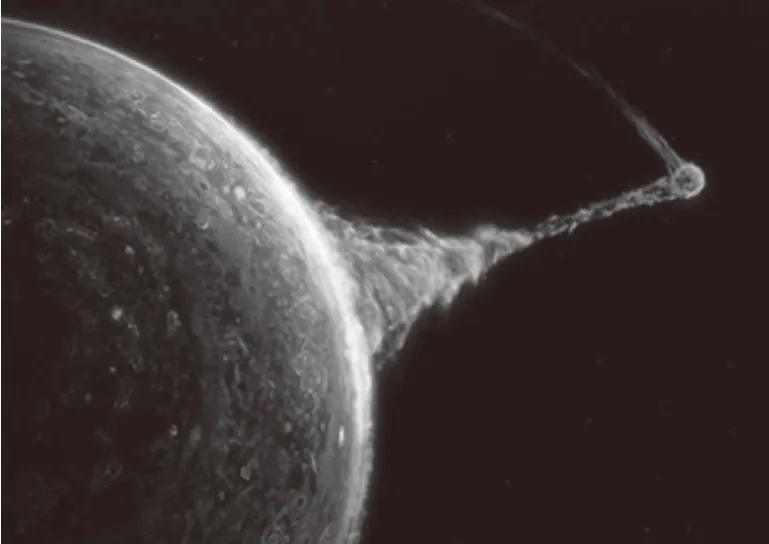
图1 电影《流浪地球》特效图
另外一些有科学背景的人经过一些数字上的推导计算后,指出电影中几十种在科学上不合理的细节,从而认为这部电影违背了“科学常识”,这些朋友或许对“常识”二字有很大的误解。他们大概忘了自己的这些推导计算需要调用各种基本数据、公式,需要使用一般人即使都学过也早就忘干净了的那些数学、物理知识才能基本正确地完成,这样的结论你能叫它们“常识”吗?即使电影的观众每人都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工作过,也不见得都能达到这样的常识标准,更别说他们大多数其实就是你的街坊邻居,是快递小哥、租房中介和股市的散户,你不能要求他们看电影的时候还做数学题。
科幻电影中跟科学有关的问题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高深的或前沿的科学理论层面,一个是现有的科学常识。所谓前沿的科学理论,肯定就不是一般人能懂得的,甚至对大众而言都是闻所未闻的,但是科幻电影要用一种大众能理解的方式生动有趣地或神奇震撼地表达出来,这是科幻电影中的科学元素需要承载的重要功能之一,即提供科学审美,或曰惊异感(sense of wonder)。正如克拉克的名言:“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初看都与魔法无异”。刘慈欣《三体》中的“二向箔”和“水滴”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们貌似背后具有强大的科学背景,但在故事中它们不需要科学解释,或者它们表现为我们穷尽现有科学体系都无法解释的东西。重点是它们要带来一种致命的毁灭美学体验,神奇而强大,让人战栗,这是一种超越日常的极端生命体验,是科幻电影所要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而BDO(巨大沉默之物)的设置以及刘慈欣的“宏细节”美学正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在电影《流浪地球》中,不但跨光年尺度的航行、一百代人的持续努力、整个地球在太空中的漂泊、木星的致命引力等都能造成这样的体验,冰封的中国城市景观、庞大的行星发动机,甚至刘启和韩朵朵走出地下城时看得目瞪口呆的巨型飞行器,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惊异感,这种惊异感最著名的例子是《2001 太空漫游》中的黑石碑,极易跟宗教情绪或崇高感联系,至于如何才能丝丝入扣地完美达成这种美学体验,不至于让人感到是不着边际的胡编乱造,那当然还得看创作者的艺术造诣,本文后面的分析会提供几点基本法则。
科幻电影中的高深理论还有另一种情形,诸如《降临》里面的语言学理论那种,虽然它的名字听起来就很高深、复杂,叫“萨丕尔-沃夫假说”,但只要解释说“一种新的语言会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我们马上就会瞪大了好奇的眼睛,准备好了迎接某种认知上的升级,这类体验是科幻电影可以提供的智慧上的愉悦,你不需要高深的教育背景,只需要抱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就能得到完美的报偿。从这个角度看,电影《流浪地球》中的科学并没有超出中学生的知识范围太多,远没有达到认知升级的程度,这也是电影被大量的科技宅吐槽的原因之一,因为里面的技术设定经不起推敲。
对于那些批评电影《流浪地球》犯了“科学常识”错误的朋友,则有必要提醒他们,所谓“科学常识”必须是普罗大众不需要经过高等教育、不需要经过系列计算即根植于心的、已知的科学真理,比如太阳是颗燃烧的恒星,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是365 天,一般情况下水在零摄氏度就会结冰等,至于地壳的厚度是多少,可以承载多大质量的行星发动机,地壳中的岩石可以提供多少聚变燃料,甚至零下八十多摄氏度的时候天上是否还会飘雪等,这些肯定不是“常识”可以解答的问题,而是需要略通数理的人士进行认真的计算才能得出的科学结论,对于数以千万计的电影观众而言,纵使他们都拥有“最强大脑”,也没有几个可以(或者愿意)一边紧跟故事情节,一边在头脑中完成这类计算,除非这些计算简单到如烧红的烙铁不能用手去摸,吃了霉烂食物就会拉肚子中毒等,这就变成是普通经验中的“生活常识”而非“科学常识”了。
在科幻电影中,我们甚至可以自创一套并不存在的“科学理论”,比如《星球大战》中的“原力”;或者明显谬误的理论,比如《回到未来》中的“德罗宁汽车加速到88 迈即可穿越时空”;以及让人感到似是而非的理论,比如《星际穿越》中的高维空间的信息是靠爱来传播等。那么,什么时候“在科学上正确”才是最重要的呢?或者回到我们文初的话题,科幻电影中的“科学” 元素到底该如何呈现才是有效的,至少是能被接受的叙事元素呢? 按照科学元素在电影叙事结构中的不同功能,我们可以分三种情形来分析。
首先是世界观设定部分。
我们知道在任何一部电影里面——不仅仅是科幻电影—— 我们都可以用一个巧合来开始:“从前有个人碰到了一件千年不遇的怪事……”就像前面我们举例的《百万英镑》那样,一般人听到这个开始就会急于知道这事有多怪,当事人会如何应对等。但我们不能用巧合来结束故事,比如你不能在人物走投无路、正邪对抗的高潮段落突然甩出一个千年不遇的巧合来收场,这会让人感觉被欺骗,或者故事冲突的解决很廉价。
对于科幻电影,我们除了笼统地说“不能出现显而易见的违背已知科学理论的情节”,具体而言应该说,你可以用任何一种假想的理论设定来开始故事,但必须遵守这样的设定,在此基础上按照普通的科学逻辑把故事推演下去。比如你可以在电影的一开始告诉大家“德罗宁汽车加速到88 迈即可穿越时空”这样的设定,然后用一系列的奇特后果来展示一个荒谬的结论,而我们的关注重点也就会始终停留在 “好吧,假如真会如此,那后来会怎么样呢”,毕竟观众要的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于是在《回到未来》中我们看到小屁孩穿越到了父母上高中的时代,帮助爸爸追妈妈,而妈妈却险些爱上他自己,我们为此忍俊不禁…… 我们知道在《回到未来》后续的故事中,主角一行穿越到了没有石油的时代,这下子他们没法回到现代了,这怎么办呢?这就是故事要讲的情理之中却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们后来找到了蒸汽机,找到了那个年代热爱科学的女教师,一起用爱情的力量加上火车的推力来帮助德罗宁加速到了88 迈,不但回到了现代完成了情节上的闭环,更把西部开发时代的美国小镇风情展现出来,给观众带来认知上的愉悦。
这就是科幻小说或者科幻电影的一个基础法则:在故事开始时定下游戏的规则,然后遵守这样的规则,带领观众一起完成游戏的历程,让他们获得情感和认知上的满足(有情人终成眷属,坏蛋终于被击败等)。对电影《流浪地球》而言,虽然现有科学共同体都认为太阳不会在近未来发生膨胀、氦闪,但是我们可以假定,万一它出现这个情况,那么人类将怎么办呢?这就是一个“高概念”故事,是电影制片人都急于寻找的“好料”。也是拜大刘所赐,我们有了一个超级大片的基本设定,包括建起一万座行星发动机、挖山石做燃料、喷射等离子火焰推动地球等,这些都是在故事叙事的基础设定之下的合理推演,如果我们去计较它们是否科学,则是缘木求鱼,跟科幻的审美目标南辕北辙了。
科幻的规则设定必须是在故事的开端。如果你中途突然又加入新的规则,而前面的游戏问题在之前的框架内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观众在情感和智慧上就可能没法得到满足,他们就会怀疑你前面讲故事的诚意。比如我们可以假定:地球环境恶化,人类奄奄一息,这时木星附近突然出现一个黑洞,于是地球科学家急于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送了一批批宇航员去探险——这是《星际穿越》的故事。但我们不能在太阳即将氦闪,地球开启流浪地球计划,遇到木星危机的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又引入一个新的科学设定说这时木星附近突然出现一个黑洞,然后地球从这里顺利地穿越到了比邻星系。这样做的问题倒不是浪费了两个高概念设定的好点子,而是用新的设定破坏了旧的设定,观众这时就会产生迷惑,不知道你到底要讲什么了,最好的结果也是“好吧,你开始了一个新的故事”。
在故事推进、转折阶段,你绝对不能使用假想的、甚至在科学上明显错误的理论来解决冲突或推进故事,如果这些元素非要不可,那也尽可能放置在叙事的前端,让其成为假定的故事设定的一部分,而不是推进故事的关键能量源泉,否则就成了显而易见的神棍瞎编和“有意误导”。比如前面提到的《回到未来》,主角们穿越到了没有石油的时代后,用火车甚至雷击的方式让德罗宁汽车加速到88 迈,从而回到了现代,故事设定的要点是这辆汽车的神奇:它是时间机器,安装有时空穿越的开关,可以定位到某年某月某日,只要速度达到88 迈就可以实现精确定位的时间穿梭。因此你不能中途让他们抛弃这辆汽车,不能出现改用马车、牛车或者加速到30 迈就实现穿越,或者突然来个外星人把大家带回了现代的情节。
对于非关键转折、非主要推动力的故事元素而言,如道具、布景、过场戏等,你可以使用似是而非、语焉不详的科学、技术,只要基本上说得过去就行,比如在《回到未来》里面的悬浮滑板,它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对于剧情的推进而言根本不重要,基本可以看成是一种未来世界大背景设定整体的一部分,只要没有明显地违反故事内的世界逻辑就行,当然这些元素最好是能创造出奇妙的新意来。《星际穿越》的故事中途引入了“虫洞”概念,这是太空航行故事中普遍使用的术语,但是这个概念可能一般人(比如非科幻迷)并不熟悉,所以电影专门设计了一个桥段来形象地解释。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电影中的几处宇宙奇观,它们都有坚实的科学依据或者推导模型,比如外星球上的巨浪,以及黑洞的形状等,它们的呈现对于故事进程而言不是关键性的,也就是说创作者完全可以换成其他的表现方式。这种似是而非的科学在《阿凡达》对潘多拉星球上的外星文明和全部生态系统的设定上是绝佳例证,虽然电影竭力显得具有一种内在精确性,但它的美和神奇已经让我们无暇追究它是否完全精确了,如反重力的悬浮山石却会流下瀑布到底是什么原理等,反正它就在那儿。惊奇美感正是科幻的终极追求之一。
在《流浪地球》里面则有火石、行星发动机等属于那种可以语焉不详的“科技”,电影对地球在流浪过程中的地质-气象灾变也做了“基本合理”的推导,这里的“基本合理”指的是如果不去仔细计算,一般人不会产生过多的疑问(南北极如何朝向,地磁是否停止,宇宙辐射如何应对等),他们将继续抱持“搁置质疑”的态度对故事静观其变。“火石”这一关键道具的出现可能并没有太深入的技术细节支撑,或者因为影片时长限制而无法在叙事中展开,总之电影中没有解释其工作原理。从叙事功能上讲,火石属于处在可以语焉不详的技术细节的模糊地带,解释清楚或许有助于展示电影的技术惊奇感,但是语焉不详也对电影的情感驱动力影响不是太大。当然在公映版《流浪地球》中,这一点带来了一定影响,因为情节关键转折处涉及了周倩为什么几枪就可以打爆它等,这被认为属于电影的硬伤,成为观众批评较多的地方。
跟故事的推进部分一样,电影的高潮、矛盾冲突的终极解决,绝对不能使用显而易见的错误理论,不能引入新的游戏规则,不能出现明显反常识的设计,否则就会让人感到被骗。电影《流浪地球》中并没有明显违背这样的原则,事实上刘启提出的氢氧混合燃烧、刘培强用伏特加酒瓶烧掉moss 等,都处于技术上似乎说得通,但可行性语焉不详的状态。这里最重要的事实是观众已经被故事的危机挤压得迫不及待,他们被人物情感裹挟着,已经决定不再关注这些科学细节的合理性,处于“宁信其有”的状态,任何一根救命稻草都愿意试一试。这也是大多数成功的好莱坞电影在高潮段落可以在科学上稍稍打些马虎眼的原因: 在《星际穿越》末尾,我们看着马修·麦康纳穿越光年来给女儿发送信息时,我们对黑洞引力是否会把他撕裂的问题已经无暇质疑。也不会在《终结者》的故事中途想起祖母悖论还没有解决,倒是电影结尾时女主角自嘲说,“该死的我一想起这个时间旅行的悖论,脑袋就大了”,非常聪明地把科学漏洞放进了或许可以解释但解释语焉不详的筐子里,反正电影到这里已经结束了。这里按重要性的级别而言,或许科学上合理的重要性要远远弱于情感逻辑上合理的重要性,所谓情感上的水到渠成,反倒不需要在科学或技术上像推理小说那般天衣无缝了。正如《星球大战4:新希望》的结尾,卢克断掉了电脑的自动导航后是如何做到准确击中死星的要害的,从技术上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时候是观众要他击中目标。
综上所述,科幻电影中的“科学”,无论是作为世界观架构设定、惊奇审美元素,还是作为叙事推动元素,都必须遵守电影叙事的基本法则,并且恰如其分地利用电影叙事的情感机制,以不破坏观众与作者达成的“搁置质疑”的契约关系为前提,才能既天马行空,又进退有据。电影《流浪地球》中的科学技术即便不是全部,至少也在最重要的层面上基本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