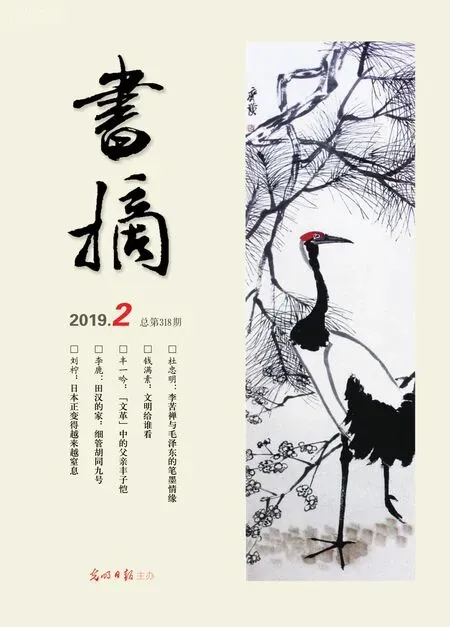日本正变得越来越窒息
2019-06-21刘柠
☉刘柠
2015年七八月间去了一趟日本。列岛溽热难当,持续逾一周的高温甚至刷新了近代气象观测史上的记录。仅东京一地,便有11672人因中暑被送医急救,死亡25人。在罕见的猛暑中,我奔波在东瀛的城乡,走在被炙烤的马路上,从关西到近畿,从关东到北关东,从东京到首都圈外的地方城市,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躁的空气。
应该说,这种焦躁感并非经济不景气所致,或者说,经济至少不是唯一的原因。经历过“失去的二十年”的日本人,对长期萧条已然具备了相当的免疫力。近年到访过日本的国人当发现,今天的日人对名牌产品并不热衷,其民族性格中原本就有的合理主义倾向越发凸显,廉价、实惠、耐用成为最高的消费标准:一些家庭主妇几乎只在百元超市(所有商品一律100日元)购买生活用品;我的一些大公司白领和媒体的朋友,多年只穿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的服装;作为世界第一的汽车大国,大排量豪车的国内市场日益萎缩,代之以混合动力的节能经济型;曾几何时,以上班族的“小跑”著称的超快节奏,开始受到质疑,媒体公然提倡“慢生活”。在“泡沫经济”崩溃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日人其实已不大会为经济而过度焦虑了。
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内阁成立以后,打出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景气刺激政策。然而风声大雨点小,据《日经新闻》2015年4月实施的民调显示,全国对景气恢复“有实感”者只占16%,而“无实感”者则多达78%。这说明经济“格差”进一步扩大,相对贫困加剧,“安倍经济学”因此被舆论批判为“对大企业和有钱人的优惠政策”。
安倍作为日本第一位战后出生的首相,在政治上有种强烈的复古趣味。从“后冷战”之初的1993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粉墨登场,到主导朝鲜绑架日人问题的调查、交涉,安倍其人一直受制于某种强烈的受害者意识。按说这种受害情结与其世代特征实难相符,甚至有些“违和感”。可实际上,这恰恰是日本政治的一个“归宿”:肇始于中曾根康弘的“向右转”,经小泽、桥本、小泉,到了安倍,“新右派”终于瓜熟蒂落,试图以“总保守化”的姿态,来收割曾几何时中曾根话语中的“战后政治的总决算”了。这一方面是近三十年来普遍保守化的国际大气候所致,另一方面,应该说也是日本地缘政治“磁力场”的变化和国民心态“形塑”的结果。
不同于以往政治家的是,对安倍来说,改宪既是手里的一张牌,同时也是世代相传的“悲愿”,源自家族的政治DNA。据悉安倍在首相官邸墙上悬挂的唯一大幅照片,不是父亲安倍晋太郎,而是外祖父岸信介。之所以把改宪作为目标,是为了继承外祖父的遗志,而博取母亲安倍洋子的欢心。这种相当私人化的情感以及国民心态的变化,构成了安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奋起挑战改宪“禁忌”的动力。
改宪动议非自今日始。历史地看,当初由美国制定的“和平宪法”落地以来,有过几次修宪运动,早期的动静甚至相当大。如《旧金山和约》刚刚缔结后的1951年9月,由《朝日新闻》实施的民调中,针对“日本签署了媾和条约,已成独立国。以一己之力保卫自己的国家计,应组建军队”的意见,回答“赞成”者达71%,答“反对”者仅占16%,“不清楚”者仅13%。翌年4月,由《读卖新闻》实施的民调,针对“你是否赞成改正宪法,日本持有军备”的问题,“赞成”为47.5%,“反对”为39%,“不清楚”为13.5%。可见,在50年代初中期,改宪派占多数,代表了某种“政治正确”。进入昭和三十年(1955年)以后,反对改宪和重新军备者开始增加,反改宪者超过赞成者是在1957年,反再军备者超过赞成者是在1956年。其后,在被称为“55年体制”的漫长岁月,改宪派始终未能再度过半。照历史学者竹内洋的说法,这是国民在鲜花(理念)与饭团(实惠)之间,优先选择了饭团的缘故。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曾致信日本首相吉田茂,要求日本修改宪法,重新武装。吉田回复道:“改宪是不可能的,因为女性们会反对。而赋予女性投票权的不正是你们吗?”正是吉田,通过有限的主权让渡(提供基地),换来美国的防卫庇护,同时以“轻军备、重经济”为路径一心谋求发展,一路做成了经济大国。而包括“集体自卫权”在内的改宪问题,则基本搁置下来。
然而,山不转水转。世易时移,随着日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迁,围绕改宪问题,国民心态和社会舆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持续萧条和中国全方位崛起的比较优势转换,包括“世界老二”经济大国易位的现实,加剧了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折射在改宪问题上,便是护宪派渐次式微,改宪派势力增强。但种种迹象均表明,日本国民在改宪问题上的态度开始松动。
那么,何以松动,日本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答案只有一个,即“总保守化”,或曰“右倾化”。表现在政治上,是执政自民党从传统的“中道保守”立场上退却,日益向鹰派位移;对外是对美追随加深,以价值观划界,公开以中国为假想敌。经济上是“新自由主义”尾大不掉,导致中产阶级萎缩,社会贫困加剧。反映在舆论上,则是原来左、中、右一应俱全的媒体“全光谱”中,中立萎缩,整体偏右。毋庸讳言,这种“地壳变动”有深刻的背景和动因。但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那就是“政治主导”,或曰“政治精英主导”。所谓“政治主导”,是与“社会主导”相对的概念,即变化不是由社会潮流推动,而是由一部分政治势力在推动、酿造。
安倍是一个具有很强议题设置能力的政治家,也不乏将议题付诸实现的行动力。应该说,这两点既是家族的政治DNA,也是其赖以成就长期政权的理由。早在安倍第一次内阁时期,尽管在位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急于“脱离战后体制”的安倍便修改了《教育基本法》,把国民养成“爱吾国与乡土”的情怀写进了教育的目标,并导入教员资格更新制,强化政府管制;进而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并制定了旨在使改宪程序可实操的《国民投票法》;紧接着,便开始着手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前提下的法律检讨……回过头来看,不啻一幅从廓清外围入手,直奔问题要害的“改宪路线图”。
如果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客观地看,首先,“和平宪法”修改与否,是日本的内政问题,外人也许不该置喙;其次,现行宪法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磨合,事随境迁,有些条文已脱离当初想定的条件,或难涵盖新形势、新变化,也并非不可理喻。如就争议最烈的第九条而言,日国内一向有一种颇主流的看法,认为第九条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日美安保条约》共同构成的“套餐”。实际上,真正对日本提供保护的并非第九条,而是“日美安保”。既如此,那为什么不能修改第九条,使其“名正言顺”地成为保护日本的法律武器呢?
但问题是,如果安倍领导的内阁认为“和平宪法”的核心条款已然过了“赏味期限”,难以适应新的现实需要,更无法继续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话,那么首先应该问信于民。而如果日本国民真的形成了改宪共识,那么尽可以本着法定的改宪程序,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正面突破。然而遗憾的是,安倍内阁的做法,有些匪夷所思。说白了,是挟政府的行政权力和执政党的强势,一味地谋求以宪法解释来暗度陈仓。如此作为,有违宪嫌疑姑且不论,更大的问题是对宪政的消解,乃至破坏。
应该承认,这种绕开改宪程序,以行政释法的战术来谋求侧面突破的“偷梁换柱”式玩法,非自安倍始,而是伴随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降,日本政治“总保守化”进程的始终。彼时彼刻,发生在日本周边或其地缘关系延长线上的个案事态(地区冲突或局部战争),则被拿来充当了“酵母”或“砝码”,为政者借力击球,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出台了一系列在过去难以想象的法律,不仅洗刷了作为“战败国”的“耻辱”,客观上也拓展了战后日本的国际生存空间。如借海湾战争,1992年出台了“PKO法案”(全称为《协助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实现了战后日本海外派兵的“零的突破”;借“9·11”后美国展开的反恐军事行动,出台了“有事关联法案”,海上自卫队的军舰在后勤补给的名义下,开赴印度洋,自卫队官兵甚至踏上了战斗的戈兰高地。
安倍第二次内阁成立后,目标更加明确,一切工作围绕改宪主题,相关程序全面提速:先是出台了《特定秘密保护法》;继而,为集体自卫权松绑;紧接着,企图强行在国会一揽子安保法案;而终极目标,无疑是改宪。这终极目标最终能否达成,另当别论,但无论如何,过去二十多年来的行政释法,特别是安倍先后两届内阁所做的功课,事实上导致“和平宪法”被掏空,自卫队的足迹将无远弗届,日本坚持了七十年的“专守防卫”路线面临实质性的改道。难怪安倍在国会发言时,不止一次把自卫队随口说成“我军”。这种对战后日本领导人来说,绝对是“大不韪”的“失言”,其实倒未必是真“失言”,也许应看作内心的“誓言”,或测试舆论水温的“试言”,也未可知。
安倍是一个高度实用主义的、不折不扣的目的论者,为了达成改宪的“悲愿”,不惜手段。某种意义上,就连“安倍经济学”也是手段,旨在提升内阁支持率,以为自己赢得推进宪改的时间,遑论历史认识。
在这种情况下,确保双方各自社会的健康发展便尤为重要。而日本作为发达邻国,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成熟的市民社会文化,及应对从自然灾害、环境问题到老龄社会的丰富经验,理应在多个领域成为中国之师。可遗憾的是,日本深陷于自身的种种问题之中,不仅难有从容,而且在一部分政治精英的主导下,越来越走向保守化,舆论空间萎缩,社会缺乏活力,令国民特别是年轻人感到窒息。这种状况,在战后七十年的今天,伴随着安保法案的躁动,变得空前严峻,甚至可以用“危机”来形容。就笔者个人的体察,大致说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忧虑:
一是国家主义与“历史修正主义”的双重变奏。以安倍为代表的政坛新右派势力,主要有双重面向: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前者标榜“自由经济”,后者则以“强盛国家”为圭臬。经济上,所谓“安倍经济学”的构造相对单纯、透明,实效也有目共睹;政治上,则相对混杂,也比较隐晦。但一个总的方向,可以用安倍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所打出的一个口号来概括——“收复日本”,即不满足于靠扩充后的行政权力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而是要在从市民社会到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收复失地”,实际上是谋求“保守复权”。所有这一切,端赖国家主义的强化。而战后日本国家意识之空前弱化,皆源于“战败国”的国体。因此、“脱离战后体制”,遂成安倍念兹在兹的迷思。而“脱离战后体制”,有两条最有效的路径:一是改宪(包括最终的自主制宪),二是颠覆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建立在“东京审判”基础之上的国际规约。前者正在锐意推进,我们且静观其变;后者则须建构一整套自己的历史叙事,而其价值内核(或曰历史逻辑),就是“历史修正主义”。对此进程,务须关注。尤其当警惕国家主义与“历史修正主义”充分勾兑后,在外界相应的条件下,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性。
二是操纵媒体,侵犯言论自由,损害公民权利。如借《朝日新闻》的慰安妇不实报道问题,发动《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保守媒体大肆攻讦,刻意给国民造成仿佛连慰安妇问题本身都不存在的错觉,导致《朝日新闻》发行量大幅下滑,被边缘化;整肃、改组NHK,任用亲信,选择性报道,乃至对2015年8月30日12万人包围国会的反“安保法制”抗议示威行动都视而不见,不予报道,被国民奚落为“犬HK”(“N”在日文中,与“犬”谐音);因对“安保法制”持批判立场,冲绳两家主要地方报纸——《琉球新报》和《冲绳时报》遭政客恫吓,扬言要“封杀”,甚至威胁将通过“经团联”等机构阻止大企业投放广告。

战后日本的科学、文化、艺术成就有目共睹,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仅次于美国,这不仅意味着科技与教育的发达,更是切实保障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权利的表征。文化创造力的前提是自由。对国民自由的钳制,必危及文化。
三是践踏法治,破坏宪政。对不惜以行政释法为集体自卫权松绑,并付诸国会强行表决一事,著名宪法学权威学者樋口阳一于众院通过的第二天(2015年7月16日),在《朝日新闻》上撰文,斥之为“三重侮辱,罪孽深重”:第一是对国会的侮辱,第二是对最高法院判例的侮辱,第三是对历史的侮辱。不仅如此,樋口还进一步指出,7月15日,众院的强行表决通过,还构成了“对民主主义的侮辱”和“对国民的侮辱”,深刻触及了一味谋求“脱离战后体制”的首相历史认识的危险本质。
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在众院特别委审议时,连自民党推荐的宪法审查会的三名宪法学者都明确表示“违宪”;表决时,在野党议员集体退场,旁听席上的市民代表悲愤呼号,举牌抗议,但法案却被强行通过……“违宪”“违反判例”不在话下,为了能通过法案,甚至到了罔顾宪法及国家法律体系的关联性、整合性的地步。法案起草班子的一位重要成员、首相辅佐官礒崎阳辅在面对民主党代表关于安保法案与既成法律体系稳定性的关系的质询时,竟然脱口而出“与法律的稳定性无关”,致舆论大哗,被呛下台。结果又为自己的“失言”道歉,却拒绝辞职。最后,连安倍也不得不出来“擦屁股”,但明显前恭后倨,暗中力挺。
“安保法案”是一场深刻的危机,不仅是日本政治的危机,也是宪政的危机。能否渡过这场危机而不重创宪政,是对日本民主主义和法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