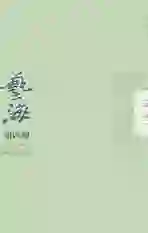《捣练图》形式美感探析
2019-06-13杨文丽
杨文丽
〔摘 要〕《捣练图》构图匀称精当,线条细密灵动,色彩绚丽雅致,纹饰精致,大到画面整体把握,小到一把扇子的精心设计,无不体现出动人的形式美感。
〔关键词〕构图;线条;色彩;形态动态与发展
《捣练图》是唐代张萱所绘的仕女图,此画构图匀称精当,线条细密灵动,色彩绚丽雅致,纹饰精致,大到画面整体把握,小到一把扇子的精心设计,无不体现出动人的形式美感。不同的人物形象其年龄、身份、分工、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反映了不同的特征。颜色以矿物颜料为主,看似简单实则无一重复,由色彩的微差调配而成,以其独特的方式呈现了一种美妙的色彩关系,使画面形式美感得到无限丰富,显示出作者对画面独具匠心的经营。
一、形式感浅析
所谓形式感,就是指我们对艺术作品在造型方面的抽象构成的主观感受。就绘画这方面来说,是构成画面的表现物体本身以及线条,色彩等方面相互融合,相互衬托、相互呼应达到的整体美感和感染力,激起观众的审美情感。
形式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绘画作品表现的物体或者人的造型,还有那些特定的线条等本身自带的美感,在造型艺术里,还包括笔墨、笔触等技法以及物质材料、物理属性的美。另一方面是,这样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带来的独特的韵律和节奏,这些要素交织在一起,不仅可以整体表达画面效果,还可以很好地传达作者想要抒发的情感,并期望引起共鸣。节奏这个词不仅会出现在音乐领域,在绘画领域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线条的长度和宽度、色彩的明暗程度、冷暖属性,形体结构的大小、方向及各种穿插关系,所有这些的交替出现,都会形成节奏,提升画面美感,调动欣赏者的情绪。
二、《捣练图》中具体呈现的形式美感
《捣练图》由唐代画家张萱所绘,是比较偏重写实的、情节性较强的一幅作品,它主要靠对情节和人物的再现来表达画面。形式感在画面中的体现并不那么直接,但仔细分析后发现,看似写实的画面中隐藏了作者独具匠心的对画面形式的布置与设计。这也是这幅作品被人们认同和极具感染力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就探讨一下形式感在《捣练图》中的具体体现。
(一)《捣练图》中富有形式感的构图 西方的传统绘画讲科学,中国的传统绘画则更加注重精神的表现,而构图正是绘画中反映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张萱对《捣练图》构图的设计十分匀称,布局精当,画中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各尽其态。仿佛让我们穿越回唐代,看到了妇女们挽着衣袖,手持木杵,身披月光,两两相对在捣衣的情景,此作以“中国传统长卷轴”的形式,再现了捣衣劳作的唐代宫廷妇女工作场景。这件作品可分为三个部分,即捣练,缝纫,熨烫三个场面。当我们在赏画的时候,应从右到左依次展开,也就是说画中是包含着时间线索的,细心地观看者或许会发现场景的次序问题,就制衣服的步骤来说,应当是先捣练,再熨烫最后是缝衣,可画家却把‘缝衣安置在了‘捣练和‘熨烫中间,打乱了传统的劳作次序。张萱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画面呢?在我看来,作者很可能就是出于对构图的考虑,第一部分中捣衣的四个女子是站立的,她们手里拿的木杵,突出了画面垂直的动感;第二部分,手拈金针坐在板凳上缝衣的人物形象却正好与第一部分形成对比,丝线的纤细与捣杵的沉重也相互对照;第三部分‘熨烫的场景中则又出现了四个站立的女子,与第一部分相呼应。如果按照日常生活中正常的劳作顺序来说的话,三组人物应当是站、站、坐,作者为了画面能够有这种高低错落的视觉效果,便调整了制作的工序,使得三组人物的姿态变成了站、坐、站。
画面安排还有一个巧具匠心之处,在捣练一组中,一个女子回过身来挽衣袖,顺着这位女子的视线,自然地便把缝衣一组中正在理线的女子带出,而画面中央蹲在地上煽火的小姑娘,在为熨烫者煽火的同时看向正在缝衣的妇人,通过人物的视线不动声色地起到过渡的作用。画中正在熨烫的新练下方有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在快乐地玩耍,为画面增添乐趣和色彩,为这张相对无聊枯燥的画面注入了生机。
(二)《捣练图》中线条的形式感 线条在传统工笔人物绘画中属主要的一种造型手段。《捣练图》中线条很细,虽细却十分健劲飘逸,疏密自然,形体准确充实,行笔起落有序,线出于体,不漏痕迹,使作者要塑造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准确地反映了人物的体态与内心世界,例如捣练的女子。作者用准确的线条把女性的身姿动态勾画得优美含蓄而安详,再如缝纫的两个人衣服纹理的勾勒也充分发挥了线条的表现力。
虽然《捣练图》中人物众多,形象复杂,动态各不相同,但在他们的主题形象的外轮廓中总会存在一个或明显或隐晦的主体形态,这就是“基本型”。线条在中国画的表达里是十分重要的,它在视觉感受、艺术形式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捣练图》中弧线、水平线、垂直线等线条的运用,给人一种经过精心布局的整体划一的印象。这些线条以一种柔和、平稳而优美的节奏组合在一起,加强了整幅画面中优雅华贵的氛围。
虽然作者对《捣练图》的创作一直没离开过模仿和写实现实人物,但张萱并不在描绘光影的技巧上着意,不像西方绘画一样,从光、影、块、面、空间等问题着手。它从最基本的线条表现要素来表现中国古代艺术鲜明而有特色的形式美感。一点一线都包含了作者的意志情感。
富有表现力的线条贯穿整幅画面之中,具有加强形象感染力的作用,严谨的造型和布局的统一,随着缓和的线条所做的无限反复的韵律感,使人仿佛穿越回唐朝,看到一群女子正在秋风下劳作的场景。
再看《捣练图》人物衣裳上的衣纹,他们是衣纹,又不仅是衣纹,这些线条劲键飘逸,经过作者无休止的反复后,有一种酣畅的流动感,衣纹虽布满衣服,但多而不乱,繁而不杂,疏密有致,这本身就充满了一种装饰韵味的形式美感,通过对衣纹的研究我们还可以判断出由于唐代对丝绸图案的不断革新,已经从只有动物纹样的图案转向动植物并重的纹样,对历史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
(三)《捣练图》中色彩的形式感体现 某些色彩、声音或形态引起的独特快感,便是最简单的对形式美的体验和感受。在《捣练图》中,作者非常注重环境和色彩对画面气氛的烘托和渲染,此画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人物身上。把人物丰腴的容貌,华丽的发饰,艳丽的衣着烘托得淋漓尽致,体现出大唐盛世雍容华贵的时代特征和当时的审美特点。
《捣练图》的设色以橙黄、白、朱红、花青等较为明亮的颜色为主,张萱喜欢以朱色渲染仕女的耳根,以此突出女子的妖媚,颜色看上去不多,但细细观摩,竟没有一处完全相同的色彩,作者经过对颜色明度、纯度等方面的独特经营,使整幅画面显得格外绚丽、高贵与雅致。站在远处眺望,冷暖色调的色块分布在画面上,再加上些许的黑白颜色又添了许多平稳和谐的感觉。而且唐代对外来文化其实也有很多好奇和兴奋,在画面中也有所体现。画中人物所穿的衣服上图案很多其实是从印度,甚至阿拉伯引进,在唐三彩的瓷器中我们也能见到。唐代不断引进这些艺术文化,于是形成了当时独特的艺术风格,张萱的画与其说是染上的,不如说是洗出来的,这样的画法可以让颜色很好地沉淀在绢布上,正反赋色,渲染浸泡,程序严格,使其色薄而质厚,人物鲜明突出。这种洗的上色法,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用。
(四)人物形体动态的形式美感 《捣练图》中女子的衣着十分抢人眼球,唐代时期经济高度发达,思想观念相对开放。从束胸长裙,不同纹理装饰的披风及长的袖上衣和高高的发髻,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描绘的都是很华贵的宫廷妇女,她们性感开放,穿着缤纷尽显“薄”“透”“露”的时代风尚,但可能受到汉代儒家思想的影响,画风虽露,却恰到好处,令人心情愉悦,欣赏赞美,却不会有一丝杂念出现。
在时代特征的带领下,作者又把自己的主观经营加入画面中、比如在缝衣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背着身体侧坐在碧毯上的理丝者,略显丰盈的身体被作者用线条把背部、臀部、到大腿小腿以及其中的空间表现得淋漓尽致。线条越简练,对形体把握的要求越高。肩膀上压下来一条红色的披帛,这条披帛刚好跟地上的那条绿色的毛毯压在一起,用颜色对比的关系和简练的线条以及精心处理的空间感,把造型方面人物的形体美感表现出来,充分展现出大唐盛世中华贵的宫廷女性之美。
(责任编辑:杨建)
參考文献:
[1]韩玮.中国画构图艺术[M]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11)
[2]丁建顺.中华人文艺术史[M].第一版.古代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