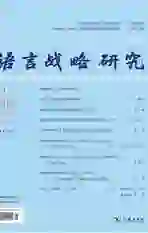海外语言与贫困研究的进展与反思
2019-06-11方小兵
提 要 受20世纪60年代美国“向贫困宣战”运动的影响,国外学者开始探讨语言与贫困的关系,分别从语言能力与贫困、语言地位与贫困、语言权利与贫困、语言多样性与贫困4个方面分析了语言与贫困的相关性,并从语言地位规划、母语教育、语言资源开发、语言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和对策。相关研究促进了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公平正义,但仍存在“惜语不惜人”(如为保护语言多样性而牺牲讲话人的权益)、“重母语轻通用语”(过于强调母语教育在减贫中的作用)、理念缺乏可行性(如试图通过将土著人的语言提升为官方语言而解决其贫困问题),以及未能区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未考虑可感知的贫困对母语人口流失的作用)等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 相对贫困;语言能力;语言地位;语言权利;语言多样性;母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1-0022-12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102
Overseas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Poverty: Origin, Core and Some Reflections
Fang Xiaobi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review of studies of language and poverty conducted b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Influenced by the US “War on Poverty” movement in the 1960s, international scholars began to explore the relevance between language and poverty. The focus of the studies are generally placed on four aspects: language capacity and poverty, language status and poverty, language rights and poverty, and language diversity and poverty.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language diversity protection, language status planning,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language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diversity conservation. However, despite their promotion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LPP)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their encouragement of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such studies also feature some problems in their argumentations. Among them, issues that are prominent and deserve attention include outweighing languages over human beings (e.g. sacrificing the rights of the speakers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advocating mother language while despising common language (e.g. overemphasizing the role of mother-tongue educ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feasibility in proposals (e.g. proposing to reduce indigenous poverty by means of upgrading their languages to official status), and failure to distinguish absolute poverty from relative poverty (e.g. attaching little importance to the effect of perceptible poverty on the loss of native speakers). This review will inform LPP studies in China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olicymaking regarding language and poverty.
Key words relative poverty; language capacity; language status; language rights; language diversity; mother-tongue education
2018年1月5日,教育部、國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制定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了“语言扶贫”的重要举措。近一年来,国内学界,尤其是从事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脱贫与推普”话题,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例如,语言可以扶贫,源自语言与教育、信息、互联网,以及与人的能力和机会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李宇明 2018);在精准脱贫中应该重视语言因素的基础性作用,因为语言作为资本,有助于改观落后地区的就业和经济劣势(王春辉 2018);语言和贫困之间枝附叶连,不可分割,语言扶贫是新时期普通话推广的重要使命(史维国,杜广慧 2018)。
然而,由于国内此类研究开展较迟,话题主要集中在推广普通话对脱贫的意义上,对国外的相关研究不甚了解,对西方学者在该课题研究中采取的视角、采用的方法、倡导的理念、提出的对策还缺乏足够的梳理,为此本文将回顾近60年来国外有关语言与贫困之间关系的研究,归纳总结语言与贫困相关性的具体表现,从研究缘起、作用机制、社会影响、干预措施等方面,综述国外在本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期为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并为中国贫困地区开展儿童语言教育和制定相关社会救助政策提供参考。
一、西方语言与贫困研究缘起与概貌
1959年,美国联邦政府首次对国内贫困状况进行调查,统计数据表明,美国有22.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这意味着当时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仍有约400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Sharp 2012)。该数据使人们感到震惊,贫困也就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约翰逊总统发出了“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的号召,许诺要把美国建成“伟大社会”,推行包括发展教育、兴建住宅、增加营养、扩大就业等在内的社会福利计划,以根除贫困。为回应美国民权运动和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的诉求,联邦政府在1964年颁布了《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和《经济机会法》(Economic Opportunity Act),并在1965年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法》,包括联邦援助城乡贫困儿童的第一部分计划;同年,《高等教育法》授权为贫困大学生提供财政援助。1968年出台的《双语教育法》(BEA)规定学校应该向孩子(主要是土著和移民家庭儿童)提供借助其母语学习英语的项目,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1974年《平等教育机会法》(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ct)颁布后,联邦政府又推出了一些针对特定贫困群体的具体项目,如“领先”(Head Start)项目为贫困儿童提供学前教育,“向上跃进”(Upward Bound)项目资助贫穷的高中生进入大学,“就业工作团”(Job Corps)为贫困青年举办职业训练。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美国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数量显著减少。
在“向贫困宣战”运动的带动下,许多学者和一些智库开始关注语言与贫困的相关性,包括种族语言(如美国黑人语言)、移民语言(如西裔和亚裔移民语言)、阶层语言(如劳工阶层家庭语言)。美国智库“贫穷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在经济机会办公室(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的资助下,通过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为解决美国贫困问题提出政策制定基础。作为该研究所的核心成员, Williams主编了论文集《语言与贫困:同一主题多种视角》(1970),将语言和贫困相关的一系列观点汇集在一起,综合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智慧,从语言视角观察反贫困计划中的紧迫实际问题。该文集在西方学界影响巨大,但也引起了许多争议。2005年10月,美国康奈尔大学举行了题为“语言与贫困”的会议。在康奈尔大学“贫困、不平等和发展”项目的资助下, Harbert等学者基于会议提交论文,编撰出版了《语言与贫困》(2009)一书,对语言与贫困的相关性进行探讨。与40年前的同名文集相比,该文集研究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美国的贫困问题,而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贫困群体面临的发展赤字和社会边缘化问题。
虽然上述两个文集都使用《语言与贫困》的名称,但内容有很大的不同。1970年出版的文集讨论了贫困与语言能力、语言地位、语言权利之间的关系,而40年后的同名文集更多采用语言生态学和语言经济学的视角,讨论贫困与社会资源获取、贫困与语言多样性等方面之间的关系。前者的作者大多来自英美;而后者的作者来自全球,包括印度、南非等国家的学者,视角更为开阔,案例也更为
豐富。
除了这两本影响较大的文集,以及围绕这两本著作发表的一系列书评(如Mufwene 2010; Dobrin 2010)之外,还有不少文献在不同程度涉及语言与贫困的关系问题,主要包括一些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著作,如Cobarrubias(1983)的《语言规划进展》、Tollefson(1991)的《规划语言,规划不平等》、Ferguson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2006);一些社会学和经济学文献,如Bernstein(1971)的《阶级、语码与控制》、Sharp等人(2012)的《社会问题经济学》。另外,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暑期语言学院(SIL)等智库和民间组织,都对语言与贫困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倡议不同类型的语言政策。
二、观察语言与贫困关系的四个视角
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4个视角对语言与贫困的关系进行讨论:(1)语言能力与贫困;(2)语言地位与贫困;(3)语言权利与贫困;(4)语言多样性与贫困。当然,这4个视角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的,仅仅是侧重点的不同。下面分别概述。
(一)语言能力与贫困
多年来,国外有众多学者对贫困儿童的语言特征(有的称为“语言缺陷”)进行描写,探讨贫困孩子语言能力欠缺的原因和对策。
语言学习环境论者认为,家庭贫困会从不同侧面影响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甚至在学龄前就已十分显著,进而影响后来其学业成功和终生发展。贫困家庭儿童语言能力之所以欠缺,是因为家庭不能为儿童早期语言习得提供质量高、数量足的语言输入,从而限制了儿童模仿的语言参照,进而导致其语言能力发展低于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儿童,主要表现为语言学习能力低下、语音意识不足、词汇和句法习得较慢等。贫困家庭父母与孩子交谈使用语言的数量与质量(如词汇量大小;解释性、描述性、引导性句型种类多少)远远低于非贫困家庭(Gruen,Ottinger & Zigler 1970)。
英国社会学家Bernstein(1971)通过“语码理论”(code theory)首次系统阐述了劳工家庭儿童与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在语言习得与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别。他指出,由于家庭环境差异,劳工家庭的儿童通常只能接触到结构简单、需依赖背景信息才能理解、适合小范围群体间交流的语言表达方式,可称为“局限语码”(restricted code);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则不仅能习得局限语码,还能接触到结构复杂、语义抽象、不需太多背景信息就能理解的“精致语码”(elaborated code)。Bernstein认为,由于学校教材、课堂教学、升学考试等使用的都是精致语码,结果导致劳工家庭孩子在学校里语言能力相对较弱,成绩常常不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存在挫败感,辍学率高,考取好大学的概率也更小,影响其向上流动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美国黑人儿童的语言能力之所以普遍“低下”,是因为黑人英语是一种“有缺陷的语言”,逻辑混乱不清,不适宜在学校和许多正规场合使用。一时间,美国黑人语言与其较低的社会地位之间是否存在共变关系成为许多学者关心的话题。社会语言学家Labov(1970)认为,应该避免将语言差异与语言缺陷相混淆,他通过调查黑人英语中系动词“BE”的省略现象,证明黑人英语和其他英语变体一样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能满足各种交际需要。因此,判定美国黑人儿童语言能力必然低下是一种语言歧视和社会偏见。真正导致黑人群体贫困的是既存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其语言。
也有学者认为,贫困会减缓认知能力的发展,从而影响语言能力的发展,因为语言机能(language capacity)是认知能力的一部分(Duncan & Magnuson 2012)。神经认知科学实验证实,贫困对认知的影响要远甚于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贫困家庭的营养供给、教养方式、家庭氛围对儿童大脑的语言系统、执行系统、记忆系统等神经认知系统的功能都会产生影响,进而不同程度妨碍语言发展(Lipina & Posner 2012)。通过图片词汇测试、语义场聚焦测试、语法接受测试、多层级的语义自上而下加工测试,学者发现视觉词解码神经区域活跃程度、语音敏感度、阅读推理能力、句法加工能力,都与社会经济地位呈正相关。相对于工作稳定、社区安全状况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贫困家庭疲于生活压力,生活焦虑程度高,过滤无关信息的能力低,因而记忆系统发展缓慢;同时,贫穷劳工家庭孩子的生活大多是物质的,缺乏诗歌吟诵表演、旅行、结社、开读书会的机会,没有“诗和远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想象力的发展。
(二)语言地位与贫困
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语言享有不同社会地位这一角度,讨论了语言与贫困的相关性,认为某些语言群体之所以贫困,不是因为其语言能力不行,而是因为其语言社会地位低,群体被边缘化,有效获取并利用社会资源和福利的手段和途径少,结果导致贫困。
經济学家Jacob Marschak(1965)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概念,认为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具有成本、收益、价值和效用,语言与讲话人的收入存在相关性。基于语言人力资本理论,Vaillancourt(2009)在加拿大魁北克调查了母语既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的居民,通过多变量分析,确定在导致居民贫困诸因素中,语言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由于教育、就业、医保等信息基本上都是以社会主导语言发布,导致社会机会不均等,小语种群体难以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有的甚至被排挤在大经济圈之外,而且在行政、司法、科技等方面难以平等获取社会资源,不能平等地参与社会发展。作者建议,虽然这些居民的语言不能成为官方语言,但政府应该在公共场合(如语言景观)强制使用多语制,在就业方面为各语言群体建立配额制(Vaillancourt 2009:158)。
为了消除在歧视小语言群体方面的指责,美国联邦政府在1963年颁布了《同酬法案》(Equal Pay Act)。法案规定,雇主对相同的工作支付不同的工资是非法的。但是由于《同酬法案》只适用于工资歧视方面,因此该法案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许多高收入行业是黑人和少数民族根本就无法进入的,谈不上有工资。为此,美国政府在1964年又颁布了《公民权利法案》(Civil Rights Act),以保证在教育、就业等方面不因语言、种族、性别等因素产生歧视,但是一些隐性的歧视仍然存在。Lambert等人(1960)最早通过“变语配对”的心理语言学实验,证实了“语言刻板印象”(linguistic stereotype)的真实存在,即人们往往会仅仅凭借一个人的语言来判断其性格和能力。“以语取人”的结果就是,社会地位低的语言在各个方面被边缘化。在美国,隐性语言歧视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家长追求“同学效应”。父母不希望其子女与非英语家庭孩子在一起,即使本身就是非英语家庭。这样一来,留给那些“失败”公立学校的只能是社区内相对贫困的学生,他们大多数都是非裔美国人和家境贫困的移民家庭学生。
在一些国家,人为制造出的语言地位不平等用来为特定阶层利益服务,并成为贫困固化机制。例如,虽然卢旺达95%以上的人都说卢旺达语,但是该国在独立之后,仍然选择前殖民语言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全民通用的卢旺达语无法进入行政、司法、教育和媒体层面。De Swaan(2001)指出,这是因为官员们自己就希望继续用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卢旺达独立之际,政府和社会精英垄断了法语教育,使其成为“神秘”而“雅致”的语言。虽然人人知道法语是通往财富权力和声望的语言,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卢旺达人来说,法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法语只能通过书面语言课程习得,而卢旺达的文盲率非常高。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看到更多的人学习法语,因为那样会影响他们垄断职场上高级职位的机会。按照联合国相关标准,卢旺达属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民众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懂法语,没文化,不够格,所以只能安于贫困。就这样,未能获得社会高等级语言成了贫困的“合法”理由,语言不平等成为固化社会不平等的隐形武器。
Tollefson(1991)从批评语言政策的角度,分析了现代社会中基于语言的制度性约束,认为这种隐性约束导致语言少数群体无法顺利进入社会和政治制度,从而产生不平等和不公正,造成结构性贫困。例如,自独立以来,印度的语言等级制度已逐渐固化,印度宪法第八附表最初列出了14种语言,称为“表列语言”,后来增加到18个。到2003年,表列语言数量达到22个。多年来,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团体一直在进行游说活动,希望其语言能够进入表列语言名单,因为不同等级的语言可以获取不同等级的行政职业、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社会地位最高的是英语和印地语,其次是区域性的邦语言,如乌尔都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等,地位最低的是一些部落语言,主要位于中南部山区。调查显示,仅仅掌握部落语言的民众,无法获得现代技术,不会使用ATM机,人均收入低,而且难以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来摆脱贫困;同时,由于政府在这些地区的公共资源投放也远远少于城市地区,当地民众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存在被现代社会抛弃的失落感和失败感(Mohanty 2009)。
有学者从话语权层面分析了语言地位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小族之所以常常与贫困挂钩,甚至一部分人陷入贫困循环,是因为社会地位低的语言群体不仅社会资源受限,更缺乏提出社会诉求的话语权。语言小族即使有减困脱贫的有效方案,但只能借助“他者语言”(社会主导语言)的媒体、渠道和平台为自己的利益发声,否则其声音就不会被听到(Ammon 2012)。这里就存在一个悖论:因为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必须借助别人的喉咙。如果贫困群体不想借他者语言发声,而是想诉诸自己的语言,那么,要么不被社会所关注,久而久之沦为默认的现实;要么出现“灰犀牛”效应,转而诉诸各种形式的暴力活动,让政府和社会感知其诉求——对此,学者们喜欢冠以“语言冲突”之名,但其实质并非语言之间的冲突,而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
(三)语言权利与贫困
西方学者所谓的语言权利在本质上是指母语权利,包括母语习得和母语使用的权利。这类学者最喜欢采用的一个理据是:母语教育更有利于扫盲和职业发展,从而有助于消除贫困,并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
Skutnabb-Kangas长期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组成员,是母语权理念的坚定维护者,她认为语言权是一种人权,母语教育是每个人都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有利于儿童成长(Skutnabb-Kangas 200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了这一观点,通过发布与母语教育相关的专家报告、宣言、倡议书和设立“国际母语日”等活动,在全世界宣传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例如,“儿童通过母语比通过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媒介学习得更快”(UNESCO 1953);“如果一个孩子最初几年的学龄教育是在母语环境中进行的话,他的学习就会更顺利”(UNESCO 2010);“我们倡导母语教学,因为它有助于更好地开展扫盲和提高教育质量”(UNESCO 2013);“母语教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要素,它有利于学习并增强读写算技能”(UNESCO 2015);“儿童用母语学习的效果是其他方式难以企及的”(UNESCO 201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二战之后成立的,那时在亚非拉出现了许多新独立国家,这些国家迫切需要消除殖民者宗主国语言的影响,并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上推广国家通用语,配合扫盲运动,消除国家贫困。因此,教科文组织最初的母语教育观念,实际上是与殖民地宗主国语言相对应的本地语(vernacular),是一种潜在的国家通用语。这一母语教育观念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欢迎,也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左翼知识分子思想逐渐占据西方学术界主流地位,与此同时,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席卷美国和西欧诸国,主要诉求是对外反对越战,支持民族独立,对内反对基于语言、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一切因素的歧视,要求权利平等(陈平 2013)。在此影响下,整个西方世界在社会思潮、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内外政策方面经历了重大变化,追求社会正义和族群平等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旋律。与此同时,母语概念从集体层面转向个体层面,母语权讨论开始面向那些原先被忽略的小族语种,在一些国家还包括土著语言和移民语言。然而,按照结构语言学的划分,一些贫困国家的语言数量动辄200到300种,基于语言平等和社会公平的原则,政府需要为每一种母语印制教材、培养师资,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母语教育理念的可行性就成了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让境内所有的语言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平等。如果一个国家同时使用着100种官方语言,那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肯定非常之低下,因为全体国民之间沟通成本太高,而难以沟通肯定有碍社会发展(Sharp 2012)。
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Fasold(1992)在《本地语教育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母语的优越性并没有在各地得到证实,接受过双语教育的讲英语的爱尔兰儿童在解算术题时,使用爱尔兰语不如用英语好,而且他们用爱尔兰语阅读的时间比用英语长。绝对意义上的母语教育可能会增加学生的负担。Gupta(1997)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通过母语教育来脱贫的局限性。他认为语言不平等只是更大社会不平等结构的一部分,母语教育解决方案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不平等,如果社会不能提供必要的语言服务来打破语言障碍,社会不平等将继续存在。期望每个国家为所有儿童提供母语初等教育,这不但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在后勤方面也是不切实际的,教师培训、教材编写、教学组织等方面的问题会堆积如山。
與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母语教育权不同,世界银行支持的是语言教育权。世界银行积极参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减贫部分,向贫穷国家提供贷款、援助和培训项目。世界银行的多份报告指出,在当今的信息饥渴社会,即便最基本的工作也要求劳动者能读能写,而大多数的工作要求更高,一个年轻的成年人如果缺乏坚实的语言教育,那么他很有可能生活在一种贫困或接近贫困的状态。世界银行认为,个人的生存权、工作权和发展权,与母语权一样重要。基于通用语的早期教育会产生最大的收益,对家庭最有价值。因此,要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解决贫困的代际传承,“必须努力改变受援助者的语言”(Alsop 2005)。世界银行在对不发达国家开展教育类投资开发项目,建立校舍和培训师资,进行就业激励和援助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家通用语教育,而不是母语教育,因为如果仅仅是母语教育,孩子上了学后可能仍找不到工作(World Bank 1980)。
(四)语言多样性与贫困
国外关于语言多样性与贫困的相关性研究,主要从国家、区域和个体3个层面展开。
就国家层面而言,Fishman(1966:146~158)认为“语言上同质的国家往往在经济上更发达,教育上更先进,政治上更现代化,政治意识形态上也更稳定和牢固……具有统一语言和多种语言的国家所表现出的许多差别似乎也体现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别”。美国学者普尔(Pool 1972)进一步指出:“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Nettle(2000)将此称为“费希曼-普尔假说”(Fishman-Pool Hypothesis),即语言多样性与国家贫困之间存在正相关,并进一步指出,语言多样性之所以会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因为它阻止专业人员流动、增加管理成本、妨碍新技术传播。
Fasold(1992)总结说,“规划者如果坚持保留文化语言上的多元化,就要准备牺牲经济进步……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成为未经语言同化而取得经济成功的样板,这至少应该使我们有理由对那些关于语言多样性照样发展的言论表示足够的怀疑”。卡林顿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煽动革命可能超出了语言学家应该做的范围,但是如果认为促进地方语言发展能够带来社会平等和保持语言多样性,那么只有拆解国家了”(Carrington 1997:89)。
就區域层面而言,Romaine(2009:135)认为,生物多样性、语言多样性与贫困三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即贫困地区通常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自然环境的生物多样性未受破坏,人类社会的语言多样性也保存较好。但是许多以脱贫为目标的开发工程和发展项目使得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破坏了当地的经济模式,迫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导致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的退化,并伴随着语言多样性的摧毁。罗曼提醒人们,不要狭隘地关注经济增长而忽视了这些行为对语言和文化构成的威胁,忽视了人类福祉的其他方面。
井上史雄对世界各个地区的夜晚照明情况进行了考察,他发现,从人造地球卫星俯瞰夜晚的地球,有3个地方比较明亮:北美、西欧和东亚。这些地区经济实力强,人口密度高,人们可以晚上聚在一起,方便地进行互相交流,这样就会发生语言的单一化。另外3处,即南美、非洲和南亚,夜晚较为黑暗,那里有众多比较贫穷的农村地区,交际密度稀疏,语言多样性保持较好。换言之,在地理分布上,富裕地区语言多样性低,贫困地区语言多样性高(井上史雄 2018)。
还有一些学者从个体层面讨论了贫困与语言多样性的关系,认为贫困会影响个体语言选择,造成语言转用,诱发母语人口流失,最终导致语言多样性减少。人类学家Whiteley(2009)研究了被纳入美国国家脱贫计划的霍皮人的生活状况。像其他美洲原住民群体一样,霍皮人往往很穷,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其他经济机会匮乏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对于霍皮族来说既是物质的、社会的,也是精神的,霍皮人的语言实践也不能脱离社区的生活环境。人们被迫放弃原有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以便不再穷困潦倒,凸显了经济发展与语言活力之间的紧张关系。霍皮语(Hopi)濒临消亡只是北美土著语言多样性减少的一个样本。
也有少数学者论证了语言多样性的益处,认为语言多样性有其经济和文化价值,可以使社会可提供的产品数量与类型得到有效增长,有助于减少贫困发生率。例如,民族主题的餐馆可以提升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方言形式的文化产品可以促进旅游经济。Ottaviano 和 Peri(2005)对过去20年里欧美160个大城市的语言状况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关联研究,为语言多样性的经济收益提供了定量证据。该研究发现,语言多样性与城市平均工资之间存在正相关。Taylor(2013)的研究更加聚焦,他发现,纽约和伦敦都位于全球最发达城市之列,但也是语言多样性丰富的城市。其中,2010年纽约市区有817万人口,来自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家庭语言和小社区语言种类众多,仅每天发行的报刊就要使用40多种语言;伦敦一直被视为欧洲最具吸引力的金融中心,而伦敦的交流语言数量多达233种,是世界最具多元化特色的大城市之一。可见语言多样性不仅不会导致贫困,反而是经济发达的表征。
Grin(2003)则从反面论证了语言多样性对于遏制贫困发生的机制作用。他指出,语言多样性固然会增加社会负担,妨碍底层民众获取公共资源,但是如果把资源投入保护语言多样性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就不但能够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稳定、可预期的社会经济环境,而且可以带来社会和谐,有助于避免因语言冲突和政治危机引发的民众流离失所和大面积贫困。现有的证据表明,维持语言多样性的货币成本非常有限(吉尔斯·格雷尼尔 2018),社会动荡的代价肯定大大高于维持语言多样性的成本。如果说维持语言多样性有可能让少部分人处于贫困,那么不尊重语言多样性则有可能造成社会上大多数人贫困。
三、评论与反思
下面将从语言资源、母语教育和语言多样性3个方面,对国外学者关于语言与贫困的研究进行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通过开发语言资源来减贫尚未真正实现
Williams(1970)从两个层面绘制了语言因素导致的贫困循环图。社会文化层面的贫困循环路径为:贫困→教育劣势→发展劣势→贫困。社会经济层面的贫困循环路径为:贫困→就业劣势→经济劣势→贫困。无论是哪个层面,语言都被视作一种资源,只不过前者是文化资源,后者是经济资源。
语言资源倡导者常常怀着良好的愿望,相信通过开发语言经济资源能够使该语言的贫困群体脱贫,通过宣传语言文化资源达到保护语言多样性的目的。然而现实生活中,语言资源往往难以在语言市场上实现其价值。Pennycook(2002)指出,“语言资源”隐喻有时会被特定社会政策话语所利用,目的是将“当地人”圈禁在保留地和种植园中,以抑制土著人口的政治诉求和社会进步。结果自然是拥有“语言资源”的人也“拥抱了贫困”。Ricento(2005)也对“语言资源”这一隐喻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在美国,语言资源观的倡导者实际上是一种为特定国家利益而发展的工具,其中作为地缘政治、国家外交(包括军事和安全问题)和国际贸易的“资源”是最重要的,其重要性远远超过语言社区本身的利益,拥有语言资源的社区自身并没有享受到语言“红利”。Grin(2006)则指出,“语言资源”的提法并不科学,反对将语言资源规划与自然资源管理进行比较,认为基于应用经济模型的“供给和需求”分析方法不适用于语言,原因之一就是语言与其他资源不同,越用反而越多,越被分享,其资源规模就越大。Grin同时指出,虽然语言常常被商品化为经济上可利用的东西,但是,在实际的语言规划过程中,基于国家利益的干预常常使“语言市场”扭曲,“在实现语言多样性目标时,几乎每种形式的市场失灵都会发生”(Grin 2006:83~84)。可以说,试图通过开发小族群语言资源来完全摆脱贫困和保持语言多样性,目前还只存在于理论探讨层面,全世界真实的案例还寥寥无几。
当我们将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处理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资源是需要全社会来维持的,“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独特的体现,都是我们应当珍惜的一份活的遗产”(UNESCO 2002)。既然我们声称濒危语言是全人类的精神財富,我们就应该共同维护,不能把这一重担仅仅交给濒危语言讲话人。选择学习什么样的语言是家庭和个人的自由,哪怕只是为了平等的机会。既然要鼓励少数民族或移民学习其母语,就应该给予其一定的经济补偿,因为对于大语言来说,只要有人以其为外语或二语来学习,大语言母语者就会受益,因为其交际价值得到了提升,语言Q值(即基于语言实力和交际潜力的市场价值)更高,比较优势更加明显(De Swaan 2001)。小群体可以守护其母语,但语言学习需要成本,包括时间成本、物质成本(文具、教材、师资等)和心理成本(如风险成本和转换成本),这也是“母语讲话人的生命的机会成本”(徐大明 2014:138)。语言资源保护的义务主体是政府,优势语言使用者需要主动分担责任。应该建立类似于政府主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通过补贴贫困群体来保护语言多样性,采用经济上给予优惠待遇和政府投资发展边远地区社会文化事业的办法加以调节。
(二)通用语教育也是一种人权,且更有利于消除贫困
在世界许多地区,将母语权利和母语教育理想化,已经遭到许多家庭的抛弃和国家层面的软抵制。语言人权仅仅是母语权吗?人们有没有学习国家和国际通用语的权利?仅仅关注尊严、正义、权利等远景理念和抽象概念,说话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却并没有真正提高。语言是平等的,但市场价值是不等的,片面强调母语教育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弱势群体对社会福利和权力结构的获取(Gupta 1997)。在南非,对于非洲教育中的母语原则,非洲人社团抵制尤烈,因为这些土著语言尽管与英语和阿非利堪斯语同为官方语言,受到法律保护,但都改变不了教育质量差和工作机会少的现状。统治精英信誓旦旦要推广多语制,宪法也给了土著语言很多的语言权利,但口惠而实不至,中看不中用(De Swaan 2001)。真正的语言权利是结果,不是条件。不能简单倡导贫困者具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权利,而要倡导让人们在摆脱贫困后享有自由选择和使用某种语言的权利。近些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开始重视语言与发展问题,强调基于母语的多语教育,其倡导的国际母语日、国际扫盲日也开始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
绝大多数父母关心的是孩子的教育是否成功,而不在乎是否是母语教育。况且,非母语教育不一定带来语言能力低下或教育失败。Ogbu(1987)在长期考察欧美移民家庭学生成绩后发现,虽然非洲裔英国学生和墨西哥裔美国学生在学校中一直表现不佳,但是亚裔学生在英国和美国的学业成绩都很好,这说明是不是使用母语进行教育并不重要,语言之外的群体文化因素更为重要。
在贫困地区,学生们掌握国家通用语不但有助于接受新鲜事物,掌握科技文化,学会一门职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而且有利于增强他们的公民意识,促进社会凝聚力,为全民脱贫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就像许多宣扬英语霸权或英语帝国主义的学者通常选择用英语发表论文一样,母语教育倡导者大多是已经摆脱贫困的社会精英,已没有通过掌握通用语而向上流动的紧迫需求,“站着说话不腰疼”。实际情况是,要真正认识到母语的价值,必须自身不因学习母语而受拖累,付出太多机会成本。比如,一些经济地位较低的拉丁裔美国人不支持其子女学习西班牙语,而希望孩子通过掌握英语,获得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当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产阶级后,对子女学习西班牙语就转变为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或许是因为西班牙语已不再是他们经济成功的障碍”(Lynch 2003)。也许可以这样说,“仓廪实而惜母语”。
(三)相对贫困是语言多样性减少的根本原因
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有比较才有所谓的贫困,正如有了发达国家,才有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表述。绝对贫困不一定会改变语言多样性,只有被感知到的贫困才会真正影响语言多样性。一些封闭的、地理位置偏远的“落后”社会,在生产生活方式上自给自足,没有太多的物质交换,市场规模很小,自然也没有什么收入和支出,地区生产总值很小。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一些地区年收入低于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似乎很贫穷。但其生活模式很和谐幸福,自我满足,没有现代城市人的精神贫困。例如,不丹是一个佛教国家,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但是国民幸福指数很高,生态良好,社会安定,人们的主观幸福指标排名很高。这样一个“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没有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冲击,语言多样性保存良好。
贫困之所以会导致语言多样性减少,是因为人们经过比较,发现自己身处(相对)贫困之中。穷则思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口流动性大、迁移程度高。虽然人口自由流动有助于各类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合理配置,使经济充满活力,让更多人摆脱贫困;但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破坏了原有的交际网络,带来母语人口流失。一些人远离母语社区,言语互动频率持续降低、单次互动时间不断缩短,母语言活力逐渐降低,在二代和三代内就出现语言转用,从而减少语言多样性。这里的决定因素并不是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引发的人口流出。
但我们也绝对不能为了保护语言而保留贫困,更不能像通过设定自然保护区一样来圈定“语言保护区”,那是有违社会正义和伦理道德的。Whiteley(2009:175~176)指出,想要“原汁原味”地延续美国霍皮人的语言和传统文化,群体成员们就需要继续生存在原来的经济模式和传统村寨和牧区中,就像北美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澳大利亚土著人居住地一样。但是这样他们就被隔绝于主流社会之外,不了解现代科学技术,无法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丧失追求现代生活质量的权利。
传统的语言规划观常常“惜语不惜人”,仅注重语言传承和语言保护,忽视了讲话人的利益,使得语言权利保护缺乏根基。语言调查者绝不能仅仅将社区作为利用的对象,把社区成员作为纯粹的数据来源,不为社区做点有意义的事作为回报,而仅仅带着研究材料离开,这是有违学术伦理的(Johnson 2013)。基于社区的语言规划重视社区利益,表现出对社区的真正关怀,通过研究语言问题来消除贫困在特定社区的传承,应该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学者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在贫困地区,更应该注重言语社区规划,倡导“以人为本”的语言规划理念,通过建设交通、医疗、教育、文化设施较为完备的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社会和谐、交际网络稳定、凝聚力强的言语社区,用以维持语言生活和语言生态(方小兵 2018),从而达到既消除贫困又传承语言的目的。
四、余 论
语言和贫困虽然相互关联,而且相互影响,但并不存在直接关联,更不存在因果关系。语言和贫困的相关性表现为一种概率关系,而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例如,虽然罗姆语是世界各地散居的吉卜赛人(大多位于社會中下层)的母语,而加泰罗尼亚语是西班牙经济富庶、文化发达区域的语言,但是,既有说罗姆语的百万富翁,也有说加泰罗尼亚语的流浪汉。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语言并非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仅凭语言因素也不能消除贫困。在美国,许多西裔移民的英语语言能力超过了白人,但仍然深陷贫困;在非洲,许多土著语言已获得国家语言或官方语言的地位,但土著民众依然贫困;在南亚和东南亚,许多低位语言使用者为了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放弃自己的母语权利,鼓励孩子学习优势语言;在拉丁美洲,一些旨在保护当地语言多样性的举措被当地民众视为分化和隔离的手段,保护和开发小族语言资源以消除贫困在实践中并未真正见效。应该承认的是,在致贫或脱贫的过程中,语言只是催化剂,不起决定性作用。
语言之所以与贫困相关,是因为有许多中介因素的存在,“源自语言与教育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信息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与互联网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密切关系”(李宇明 2018:5)。不过,这些中介因素发生的机制目前还不太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需要搜集大量真实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只有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语言差异是如何被那些贫困群体所体验和解释时,认识到在语言上被边缘化的贫困家庭子女如何被剥夺各种融入社会的机会时,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认清语言与贫困的复杂关系,从而制定出切实有效的语言政策。
参考文献
陈 平 2013 《政治、经济、社会与海外汉语教学——以澳大利亚为例》,《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方小兵 2018 《从家庭语言规划到社区语言规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吉尔斯·格雷尼尔 2018 《论语言及其多样性的经济价值》,刘国辉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井上史雄 2018 《语言景观与语言经济》,包联群译,《中国语言战略》第1期。
李宇明 2018 《修筑扶贫脱贫的语言大道》,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北京:商务印书馆。
史维国,杜广慧 2018 《语言扶贫是新时期普通话推广的重要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10月21日。
王春辉 2018 《论语言因素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江汉学术》第5期。
徐大明 2014 《语言贸易: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语言战略》,载李宇明 《中法语言政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Alsop, R. 2005. Power, Rights, and Poverty: Concepts and Connections. New York: The World Bank.
Ammon, U. 2012. Linguistic inequality and its effects on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on global knowledge accumulation—with a closer look at the problems of the second rank language communities. Applied Linguistic Review 3(2), 333–355.
Bernstein, B. 1971. Class, Code and Control: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 (Volume 1). London: Routledge Press.
Carrington, L. D. 1997. Social contexts conducive to the vernacularization of literacy. In A. Tabouret-Keller, et al. (eds.), Vernacular Literacy: A Re-evalu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barrubias, J., et al. 1983. Progress in Language Planning. New York: Mouton Publishers.
De Swaan, A. 2001. Words of the World: The Global Language Syst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Dobrin, L. M. 2010. Review of language and poverty.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Conservation (4), 159–168.
Duncan, G. J. and K. Magnuson. 2012.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gnitive Science 3(3), 377–386.
Fasold, R. 1992. Vernacular-language education reconsidered. In Kingsley Bolton & Helen Kwok (eds.), Sociolinguistics Toda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Ferguson, G. 2006. Language Planning and Educa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Fishman, J. A. 1966. Some contrasts between linguistically homogeneous and linguistically heterogeneous polities. Sociological Inquiry 36(2), 146–158.
Grin, F. 2003. Language Policy Evaluation and the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Grin, F. 2006.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policy. In Thomas Ricento (ed.),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olicy: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Blackwell, 77–94.
Gruen, G., D. Ottinger, and E. Zigler. 1970. Level of aspira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learning of middle- and lower-class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 133–142.
Gupta, A. F. 1997. When mother-tongue education is not preferred.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8 (6), 496–506.
Harbert, W., et al. 2009. Language and Povert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Johnson, D. 2013. Language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abov, W. 1970. The logic of nonstandard English. In Frederick Williams (ed.), Language and Poverty: Perspectives on a Them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Inc.
Lambert, W. E., et al. 1960. Evaluational reactions to spoken languag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1), 44–51.
Lipina, S. J. and M. Posner. 2012. The impact of pover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brain networks.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6(1), 238.
Lynch, A. 2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ond and heritage language acquisition: Notes on research and theory building. Heritage Language Journal 1(1), 26–43.
Marschak, Jacob. 1965. Economics of Language. Behavioral Science 10(2), 135–140.
Mohanty, A. K. 2009. Perpetuating inequality: Language disadvantage and capability deprivation of tribal mother tongue speakers in India. In W. Harbert, et al. (eds.), Language and Povert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Mufwene, S. S. 2010. The role of mother-tongue schooling in eradicating poverty: A response to language and poverty. Language 86(4), 910–932.
Nettle, D. 2000. Linguist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fishman-pool hypothesis reexam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48(2), 335–348.
Ogbu, J. U. 1987. Variability in minority school performance: A problem in search of an explanation.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18(4), 312–334.
Ottaviano, P. and G. Peri. 2005. Cities and cultur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 304–337.
Pennycook, A. 2002. Mother tongues, governmentality, and protectio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54, 11–28.
Pool, J. 1972.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diversity. In J. A. Fishman (ed.), Advance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Volume 2). The Hague: Mouton.
Ricento, T. 2005. Problems with the “language-as-resource” discourse in the promotion of heritage languages in the USA.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9(3), 348–368.
Romaine, S. 2009. Biodiversity,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poverty: Some global patterns and missing links. In W. Harbert, S. McConnell-Ginet, A. Miller, and J. Whitman (eds.), Language and Povert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Sharp, A. M., et al. 2012. Economics of Social Issues (20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Skutnabb-Kangas, T. 2000.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and teachers of English. In. J. K. Hall and W. G. Eggington (eds.), The Sociopolitics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Taylor, F. 2013. Multilingual Britain. London: Cumberland Lodge.
Tollefson, J. 1991.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UNESCO. 1953. The Use of Vernacular Languages in Education; Monographs on Fundamental Education, VIII. Paris: UNESCO.
UNESCO. 2000~2018. Message from Director-General of UNESCO on the Occasion of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Accessed at http://www.unesco.org/.
Vaillancourt, F. 2009. Language and poverty: Measurement, determinant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W. Harbert, et al. (eds.), Language and Povert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Whiteley, P. 2009. Losing the names: Native languages, identity and the state. In W. Harbert, et al. (eds.), Language and Povert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Williams, F. 1970. Some preliminaries and prospects. In Frederick Williams (ed.), Language and Poverty: Perspectives on a Them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orld Bank. 1980. Education Sector Policy Pape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