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眼中的优秀侦探小说
2019-05-29保罗·格里姆斯塔德
〔美国〕保罗·格里姆斯塔德

1944年,20世纪美国极为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们为什么看侦探小说?”的文章,充满了火药味。当时威尔逊正准备离开美国,去欧洲报道盟军轰炸德国的有关情况。威尔逊觉得自己早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成熟,不看侦探小说这种小儿科的东西了。他在十二岁之前就把早期侦探小说大师埃德加·爱伦·坡和阿瑟·柯南·道尔等人的作品都读了个遍。但是,在他的熟人圈里,好像所有人都迷上了侦探小说。他当时的妻子玛丽·麦卡锡有个习惯,经常把自己喜欢的侦探小说推荐给朋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玛丽还将自己买的侦探小说《喜欢蜂蜜》(A Taste for Honey)(作者是H.F.赫德)借给纳博科夫。彼时纳博科夫刚刚做过牙科手术,正在休养。《喜欢蜂蜜》这本侦探小说让他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纳博科夫看到威尔逊在《纽约客》上的那篇文章后,劝他在没有看过多萝西·赛耶斯的作品之前,不要将这种文学作品一棍子打死。威尔逊的身边全是些侦探小说的鉴赏行家,对此他真的十分困惑。他说,“那么,T.S.艾略特和保罗·埃尔默·摩尔都为之着迷的侦探小说到底有什么魅力,我为什么好像就体会不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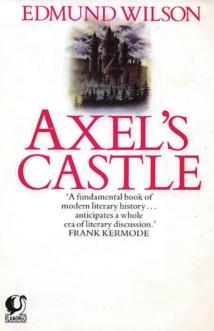
T.S.艾略特居然是侦探小说迷,这一定让威尔逊特别痛苦不安。艾略特创作了许多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著名长诗,他的每一句评论都会被学者教授们奉为圭臬,因此,在判断文学作品有无价值这件事上,艾略特应该有着无可辩驳的权威。艾略特文学地位的确立,威尔逊可谓功不可没。在他那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中,威尔逊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称赞艾略特这位诗人兼评论家“有着极其敏锐的审美能力”。在威尔逊看来,艾略特将这种能力用在侦探或推理小说这种幼稚且程式化的作品上,是一种浪费,太不值得了。
但是,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艾略特研究专家戴维·齐尼茨所指出的,和人们惯常的观点不同,艾略特对诸多流行艺术怀有一颗包容之心,其态度也常常摇摆不定。在他最为宏大的诗歌作品中,人们可以找到他小时候在圣路易斯耳濡目染的拉格泰姆(美国流行音乐形式之一,产生于19世纪末,发源于圣路易斯与新奥尔良,后在美国南方和中西部流行,是一种早期爵士乐,它影响了新奥尔良传统爵士乐的独奏与即兴演奏风格。—译注)中的节奏切分;他在晚年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在百老汇音乐剧方面取得成功。于是,侦探小说在威尔逊的朋友圈里成为阅读时尚之际,艾略特就已经是这一文类最为热心、最具洞察力的读者之一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S.艾略特散文全集》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宝藏,在该书的第三卷中有艾略特的侦探小说评论数篇。这些评论于1927年发表在他的文学杂志《标准》(The Criterion)上,但当时都没有署名。我们从这些评论中不仅可以看到艾略特对侦探小说的热爱,还可以看到他在相关文学研究上的努力—当侦探小说处于重大变革阶段的时候,他在试图整理出这种文学类型的创作规则。
艾略特的这些评论写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早期,当时多萝西·赛耶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翰·狄克森·卡尔这样的大家正不断推出具有古朴之风的侦探小说,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嫌疑人形形色色,犯罪手段也是千奇百怪。对艾略特来说,早期侦探小说的典范之作不是爱伦·坡或柯南·道尔的作品,而是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宝石》。这部小说1868年在狄更斯主编的杂志《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上连载,讲述了一颗印度宝石失而复得的离奇故事。艾略特在1928年为牛津世界经典丛书中《月亮宝石》所作的导读中,称这部作品是“第一部最长和最好的现代英国侦探小说”。这一赞美之词至今还出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月亮宝石》平装本上。《月亮宝石》的情节冗长复杂,通篇都是装腔作势的惊险故事,许多故事或情节和小说本身并无太大的关系。作者在讲述宝石失窃背景的同时,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女仆的阅读习惯(她喜欢看《鲁滨孙漂流记》)、英俊的富兰克林·布莱克和倔强的蕾切尔·范林达之间的坎坷爱情。艾略特认为,这些看似离题万里的描写恰恰赋予了这本侦探小说“一种无形的人文元素”。艾略特在1927年1月号的《标准》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所有好的侦探小说“常常朝着威尔基·柯林斯写作实践的方向靠拢,或者就是柯林斯写作的回归”。

黃金时代侦探小说的一个关键原则是“公平竞争”—从理论上来说,一位认真细致的读者在破案能力上必须和小说里的侦探处于同等水平。为了确定公平竞争的种种规范,艾略特说,“罪犯的人格和动机应该属于正常状态”,小说中应禁止出现“过于复杂、令人难以置信的伪装”。艾略特还认为,一篇优秀的侦探小说绝对不应该“依靠超自然现象或一些离群索居的科学家所做出的重大发现取胜”,“结构奇巧、功能古怪的机器设备在侦探小说中无足轻重”。后一条规则似乎将柯南·道尔的《花斑带奇案》(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排除出侦探小说杰作之列。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所写的谋杀是由一条经过训练的毒蛇来完成的—蛇从气窗爬进来,顺着拉铃绳爬到受害人的枕头旁。不过艾略特也承认,对于他说的这些规则,大部分侦探小说名作至少会打破其中一条。实际上,艾略特非常推崇柯南·道尔,常常在朋友的聚会上背诵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的段落,在自己所写的诗歌中也会借用一些观点或词句。在写给朋友约翰·海沃德的信中,艾略特说“《四首四重奏》中的‘在沼泽的边缘一句即是在致敬《巴斯克维尔的猎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里人迹罕至的沼泽”。
1927年6月,艾略特在《标准》上对十六部小说进行了评论,在细分了推理小说、犯罪纪实小说和侦探小说之后,继续阐述他的侦探小说标准。在那些小说中,他最喜欢的是S.S.范达因的《班森杀人事件》(The Benson Murder Case)。范达因是艾略特在分析并确立侦探小说创作标准时参考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作家之一。范达因原名威拉德·亨廷顿·莱特,艺术评论家、报刊的自由撰稿人,曾做过纽约的文学杂志《智者》(The Smart Set)的编辑。范达因曾经生过一场大病,为了消磨时间,同时也为了摆脱挫败感和沮丧的情绪,卧床休养的他花了两年时间,阅读了两千多部侦探小说,系统提炼出侦探小说的写作模式,然后开始自己创作。他笔下的侦探菲洛·凡斯是一个生活悠闲的艺术鉴赏家,常常喜欢对希腊塔纳格拉陶俑说上几句。艾略特用欣赏的口吻说,菲洛·凡斯侦探在破案时采用的方法“和伯纳德·贝伦森(1865—1959,美国艺术史学家,专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研究。—译注)在评论油画时的方法类似”。


1928年,范达因在《美国杂志》(The American Magazine)上发表了他自己的“侦探小说写作二十法则”,同年,罗纳德·A.诺克斯也推出了他的“侦探小说十戒”。诺克斯是一名天主教神父,也是伦敦侦探俱乐部的成员。该俱乐部由推理小说作家组成,成员有多萝西·赛耶斯、阿加莎·克里斯蒂、G.K.切斯特顿等。范达因和诺克斯是否知道艾略特此前发表的有关侦探小说的写作标准,现在已经难以确定,但是,他们二人提出的原则中有许多和艾略特“公平竞争”的原则遥相呼应:范达因提出“除凶手对侦探所玩弄的必要犯罪技巧之外,不应刻意欺骗或以不正当的诡计愚弄读者”,以诺克斯“侦探小说十戒”为基础的伦敦“侦探俱乐部宣言”要求,俱乐部成员保证在创作中避免使用“神的启示、女性本能、令人畏惧的东西、骗人的把戏、巧合或天灾”。阿加莎·克里斯蒂1926年出版的情节曲折的《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挑战了“公平竞争”原则的极限,在众多同好中掀起了波澜。1945年,埃德蒙·威尔逊在第一篇评论遭到读者潮水般的指责之后,又写了一篇题为“谁在乎谁杀死了罗杰·艾克罗伊德?”的评论。在这篇文章中,埃德蒙·威尔逊认为当下的推理小说令他更加失望。
但是,如果将艾略特的观点和这些侦探小说圈内人提出的规则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艾略特的判断非常怪异。范达因说“过长的描述性文字、在一些旁枝末节上玩弄文字、微妙的人物分析,都不应该出现在推理小说里”,而艾略特所推崇的《月亮宝石》恰恰具备上述特征。艾略特始终是一名文学史研究者,他认为侦探小说源于传奇剧。对他来说,传奇剧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从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悲剧到狄更斯发表于1852年至1853年间的《荒凉山庄》,都属于传奇剧。艾略特在一篇有关威尔基·柯林斯和狄更斯的论文中写道,“那些生活在‘高雅小说‘惊悚小说‘侦探小说之类的术语被发明出来之前的人,早就意识到传奇剧一直存在,而且人们对传奇剧的喜爱经久不衰。”好的侦探小说具有一种“数学难题才有的美感”。艾略特在上述论文中说,“如果一篇小说既没有给读者带来艾伦·坡式纯粹智力方面的愉悦,又没有表现出威尔基·柯林斯小说中的那种饱满生活”,那么它是不成功的。换言之,艾略特所欣赏的是侦探小说能够在齐整规范的形式框架里传达人类的丰富情感和体验,也许,我们在小说或诗歌上都可以找到这一特点。
艾略特在评论中丝毫没有谈及正在大西洋彼岸悄然成形的新侦探小说,难免令人失望。艾略特在《标准》杂志上发表他的侦探小说创作规则之时,达希爾·哈米特正在《黑面具》杂志上连载《马耳他之鹰》。达希尔曾在平克顿侦探社工作过,也是《荒原》的热心读者,他的《马耳他之鹰》标志着侦探小说摆脱了以往乡间小屋谜案那种厚重的写作传统,进入了色彩更加灰暗的都市犯罪小说的时代。在这些作案手段更加卑鄙、场景更加恐怖的侦探小说里,和人物活动所处的氛围相比,犯罪的方式方法常常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随着美国“硬汉侦探小说”的兴起,英国的侦探小说开始显得古雅奇特,或者说有些矫揉造作了。雷蒙·钱德勒在1950年《简单的谋杀艺术》一文中,将范达因笔下的菲洛·凡斯侦探视为“可能是侦探小说中最倔强的人物”。因此,人们不禁开始联想,以圣杯传说为基础写下不朽诗篇的艾略特,在看到《马耳他之鹰》中的各种怪人追随一个子虚乌有的线索时,会作何感想,因为这条线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圣殿骑士开始的中世纪。

但是,艾略特钟爱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这和它们本身具备的文学性可能只有部分关系。在写侦探小说评论的那年里,艾略特在政治上突然向右转,整日泡在厚厚的神学著作之中,为自己转信英国国教高教会派做准备。在1927年6月写给朋友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一封信里,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自己是“一个侦探小说和基督教历史专家”。他成为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之后,每天早晨去罗素广场的出版社上班之前都要做弥撒,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已经混乱得不堪忍受,而他那样做至少可以恢复一点秩序。
埃德蒙·威尔逊在1944年的那篇论文末尾处认为,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绝非偶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文明变得千疮百孔、分崩离析,侦探小说中的神探却能将所有的碎片联系起来,“惩治罪犯,匡扶正义”。在威尔逊看来,侦探小说中光明的结局正是它简单、肤浅的标志。但是,艾略特在《荒原》中将支离破碎的现代世界视为“一堆破碎的偶像”,于是,黄金时代侦探小说最重要的贡献是给人们提供了愉悦的秩序感,因为可以预见的程式化写作让读者知道混乱不堪的状态终将恢复秩序,令人欣慰。
(王海燕: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30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