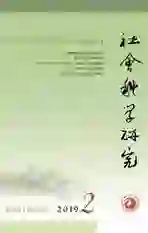历史的终结还是目标: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弗朗西斯?福山
2019-05-13王晴佳
〔摘要〕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之后,因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成为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战略思想家。自此之后,福山继续对世界局势的现状及其未来走向,做出种种分析和展望。福山的这些论著,展现了当代的一种思辨历史哲学。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鉴于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福山也补充、修正着自己的立场。不过从其2018年出版的《认同:追求尊重和仇恨政治》来看,福山的历史观基本未变,仍然从唯心主义的视角探究历史的演化。他始终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尽管多有曲折,但将沿着一个方向走向大同:人类历史不是走向终结,而是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关键词〕 思辨历史哲学;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黑格尔;后历史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2-0027-09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思辨的历史哲学逐渐走向了衰微,为分析的历史哲学取而代之。①但这一转向并不等于自此之后再无人分析和描述人类历史变化的踪迹和走向。如果将历史哲学定义为对历史演变进程、特点和走向的思考,那么这样的学者在当代仍大有人在。譬如中国学界熟知的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和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有趣的是,他们两位还有师生之谊;在福山求学哈佛大学的时候,亨廷顿是他的老师之一。显然,福山之后的写作,显现出了亨廷顿的影响。不过,他们两人的学术生涯和观点,却大相径庭。譬如,亨廷顿虽然被许多人视作影响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智者,但他一直在高校执教,真正为美国政府工作的时间,不足两年。与之相对照,福山从求学时代开始,就不同程度地涉足政界或智库机构,只是到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之后才进入教育界。从他们的世界观、历史观来看,两人的观点和立场也迥异。在一次访谈中,福山提到亨廷顿是对他的学术影响最大的三个人之一,不过他不同意亨廷顿的观点。②的确,与亨廷顿的谨慎冷静、矜持保守的学术态度相对,福山显得乐观自信、激情澎湃。当然,亨廷顿与福山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两人对1989年之后的世界历史走向,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预测。前者准确地预测了西方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的升级;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就是一个印证。而福山则认为苏联、东欧解体之后,世界将进入大同世界。③
毋庸赘言,我们说福山乐观、自信,主要依据他在1992年出版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换言之,福山与他的老师,在获取知名度方面,也显出了不小的差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他众多著作中最出名的一部,他写作该书的时候,已年近古稀。相反,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时候,刚及不惑之年;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出版之后,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又赢得了《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当时有些学者指出,福山暴得大名,但可能只有“十五分钟的知名度”,很快就会被人忘却。④與这些预言相反,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之后,著述不辍,成为当今世界一位活跃的思想家。他的“历史的终结”的论点,也让人将他视为一个“后历史”(posthistory)的现代历史哲学家。⑤
其实,如同笔者将在以下所述,福山指出历史的“终结”(end),让不少人大为吃惊,甚至群起而攻之,反而扩大了其著作的影响力,但许多福山的批评者,又没有完全理解福山使用这一词语的意思。本文试图对此做一澄清,并进而分析和梳理福山学术思想的演化。
一、历史如何终结?
从弗朗西斯·福山的名字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日裔美国人,1952年出生于芝加哥。他的祖父辈自20世纪初年来到美国,靠做一点小生意生存下来。像许多移民家庭一样,福山父亲这一辈开始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父亲虽然与所有日本人甚至日裔美国人一样,在二战中曾被关入集中营,但之后仍努力上进,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在宾州州立大学任教。他母亲则出生在日本,其父是京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大阪市立大学的校长。福山是独子,幼时主要在芝加哥、纽约的曼哈顿和宾州州立大学的校园长大。在这样的知识家庭成长,福山自小学业优秀,不过不会讲日语。他本科读的是康奈尔大学的古典系,其老师之一艾伦·布鲁姆 (Allan Bloom, 1937-1992)对他影响甚大。布鲁姆在1987年出版了《日益封闭的美国心智》(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提出尖锐的批评,成为当时的一本畅销书。⑥但布鲁姆对他的影响,那时主要还是在学业方面,比如福山专修了希腊语,可以阅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原著。⑦更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布鲁姆,他读到了其老师亚历山大·柯耶夫 (Alexrandre Kojève, 1902-1968)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解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时候,就多次提到了柯耶夫,将之与马克思相提并论,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黑格尔哲学的主要诠释者,而柯耶夫则是20世纪黑格尔思想最伟大的诠释者。⑧福山对世界历史的许多看法,包括他起的书名,都受到了柯耶夫的启发,我们将在下面再论。
大学毕业之后,福山到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硕士,并在巴黎待了半年,随法国两位后现代主义的先驱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1915-1980) 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学习。但他与两位接触之后,却对他们的思想及对现代性的批评失去了兴趣。福山从巴黎回到美国之后,转而到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的博士,从学于塞缪尔·亨廷顿等人。他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针对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所做出的批评。所以,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和休·雷蒙-皮卡德 (Hugh Rayment-Pickard)两人在编辑《历史哲学论集》的时候,将福山与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等人放在一起,视他们为“后历史”的思想家,显然误解了福山的历史哲学。
福山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进入了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任职。他在写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之前,给公司写过一篇分析苏联在伊拉克的报告。虽然这篇报告没有使用阿拉伯语,不过能娴熟地使用法语,显示出福山在耶鲁大学经受的比较文学训练。⑨这篇报告与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类似,显示出福山对苏联体制及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有着颇为深入的理解。他还与人合编过相关的著作。⑩福山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写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起因也与其在兰德公司的工作有关,虽然他在正式写作(包括写作发表于1989年的同名文章)的时候,已经离开了该公司。显然,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他在1989年写作同名文章时的说法(11),也是后来扩展成书的一个出发点。
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的内容,远远超过了作为一篇智库报告的规模和标准。福山虽然年轻,未及四十,却在几个方面具备了写作的条件。一是前述他对苏联体制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二是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深入体会,三是他对后现代主义思维的不满及对当代政治、历史和未来走向的关怀。他在写作《历史的终结?》一文的时候,虽然题目中有一个问号,但其实态度坚决、笔调坚定,显现出一种往往在年轻学者身上才有的高度自信。当然,与他年迈的老师亨廷顿相比,福山显然没有那么博学,对世界军事、政治、社会和文化都没那么有兴趣和专攻。福山的取径是借助他比较擅长的哲学功底,从意识形态方面对世界历史的现状和发展,做出分析和预测。
具体而言,福山认为20世纪的历史显现了两种意识形态的交战。他指出,冷战的结束,被有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福山并不同意。他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关联。福山举出东亚经济在战后的发展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改革为例,其成就世界瞩目。他强调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并不是采取資本主义的制度的结果。
福山的做法是,另辟蹊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分析世界历史的演化。由是他可以引入康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马克思、柯耶夫等人对之的解读和发展。他认为“历史的终结”的概念,由黑格尔提出,其含义是指人类在掌握了科学技术之后,不再受自然界的制约,而能充分运用理性,自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显然,黑格尔的界定,与福山想说的只是有些联系。所以福山借用黑格尔的提法,还得通过两个解读者,一个是马克思,另一个则是柯耶夫。福山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特别是将共产主义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前途的观点,实践了黑格尔“历史的终结”的概念。而柯耶夫虽然在美国并不知名,但在福山眼里,却是在当今世界复活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理由是,黑格尔曾将1806年的耶拿会战,视作世界历史的终结,因为拿破仑一世在该战役中,击败了普鲁士王朝的军队,将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付诸实践。这一看法在许多黑格尔的研究者中,并不特别受到重视。但柯耶夫不然。福山指出,柯耶夫在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时候,认为黑格尔的论点基本正确,因为耶拿会战至少在原则上代表一个新兴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正在走向胜利,即将取代以前的封建主义。而更重要的是,柯耶夫还认为,自此之后,世界历史虽有起伏,但基本会沿着这一走向演变。(12)
其实,福山所谓的自由主义,可以与现代性相比拟,指的是现代社会或现代化背后的思想渊源。而他认为,这一思想倾向,才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走向。福山的所谓“历史的终结”,即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的。我们在上面说他反对后现代主义,也正是体现在这个方面,尽管他指出“历史的终结”,常常被人们误以为是指现代社会的结束和“后现代”社会的来临。(13)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强调历史走向的多元性和相对性,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则指出人类历史将会殊途同归、百川归海。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都坚持了这样的历史观,即他所谓的“普遍史”的形成和演化。这一“普遍史”指的是一个历史观念的普遍性,已经为世界上的人所接受和遵循。
不过我们比较《历史的终结?》一文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可以明显看出福山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他在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之后,可谓一炮打响。但他在意识形态上宣告西方的凯旋,让学界不少人士感到他的论点过于极端、自信,因此提出了许多批评。这导致福山在写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的时候,其自信程度有所收敛。举例来说,他在《历史的终结?》一文的最后,略带矫情地写道,因为历史已经走向了终结,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达到了统一,让他产生了纠结和复杂的心情:
在后历史的阶段,将不再有艺术和哲学,只有保存人类历史博物馆的努力。我自己觉得,也看到我身边的人,都对过往的历史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感。事实上,这一怀旧感将继续支持着竞争和冲突,即使在后历史的阶段,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尽管我承认这一趋势的无可避免,但我对1945年以来欧洲创造的文明及其在北大西洋和亚洲的延伸,心里仍有浓浓的不舍之感。也许,在这个历史终结的时刻,看到未来的好几个世纪将会无所事事,这一期待将会重启历史向前的车轮。(14)
福山的这一写法,如同一个拳击赛中获胜了的选手,友善地伸手拉起倒在地上的对方那样,显示出一种得意的、胜利者的大度。不过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书末,没有出现他这种得意扬扬的笔调。相反,他的文笔虽然同样带有文学色彩,但口气则变得相当谨慎,甚至略带低沉:
柯耶夫相信,历史本身最终将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如果有足够多的马车入城这一情景会使任何有理性的人看到后,都必得承认只有一条路和一个终点。让人怀疑的是我们现在是否就处在这个节点上,因为无论近年来自由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如何蓬勃兴起,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关于马车的走向的证据仍然不足让我们得出明确的结论。在我们最后的分析中,我们也无法知道即使大多数马车最终都将到达同一个城镇,而车上的人会不会环顾一下新的环境之后,觉得这个环境并不如意而将目光投向一个新的、更遥远的征途。(15)
换言之,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结尾,不但自信感减弱了不少,甚至指出了他崇拜的柯耶夫的某些不足。
如果说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在立场上有所修正,也是因为他的论点的确有不足之处。比如他强调西方意识形态的凯旋,但即使在1980和1990年代,中东穆斯林世界也显然是个例外。至少从外部的立场来看,穆斯林对西方的文化“侵略”,恨之入骨。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文章和书,虽然提到宗教和民族主义会挑战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却对穆斯林对西方文明的抵制,尽量避而不谈。这与亨廷顿注重中东文明的做法,几有天壤之别。由此他误判了1990年代之后世界局势的发展,可以说是意料之中。(16)
二、人类的本性
尽管如此,福山之后还是坚持了以唯心主义的视角来总结、概括世界历史的进程和走向,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将是引导历史演进的主要动力。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已经强调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指出了人类追求被“认可”的欲求,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个持久的动力。(17)福山在其第二本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繁荣》中,继续将其发挥,从文化、思想和伦理的层面探讨历史发展的动因。在与中国学者的访谈中,福山自承《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繁荣》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一本著作。(18)这也许是因为此书有不少与东亚相关的内容,但从学理上而言,他或许的确需要补充一下对东亚文明的知识,不能将东亚的现代化,完全归结于西方文明的影响。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繁荣》一书的内容,看起来似乎不具世界性的规模,但实际上讨论的问题同样有全球的意义。福山写作此书,似乎是想回归自己文化的传统,也即从东亚的历史经验出发来讨论现代化的问题。显然,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复苏和起飞、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中国在近年的迅猛发展,是所有关心世界前途的人都无法回避和忽视的现象。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文章和著作中,几乎没有考虑东亚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文明的因素。如我們上面所引,他视其为欧洲文明在1949年之后的“延伸”。而他写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繁荣》则纠正和补充了上述看法。如书名所示,福山认为经济发展有文化和社会的因素,也即人与人之间信任度强弱的问题。他将欧美的大部分国家归为“高信任度”的社会,而中国、韩国、意大利乃至法国则是“低信任度”社会的代表。前者的特征是有较强的社团、社群意识,后者则从家族出发构建其社会关系。这两类社会的差别在于,前者会出现各种中间团体,充当国家与民众之间调停的角色。而在后者的社会中,这类组织即使存在,其作用也可有可无,因为那里的人对这些组织缺乏信任感,由此一来,政府的权力往往比较强大。福山对日本的看法是,日本虽然处在东亚,却更像“高信任度”的社会,所以日本的经济发展,与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大相径庭。(19)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繁荣》一书出版四年之后,福山又出版了《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其内容与前书有相似之处——两本书可以说是姊妹篇。不过福山处理的对象有所不同。他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繁荣》一书中虽然没有明言,但显然认为“高信任度的社会”优于“低信任度的社会”,而衡量的标准就是“繁荣”(prosperity)。大致而言,西欧、北美和日本的确比其他国家与地区更为繁荣,但韩国和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同样十分强劲,由此对福山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而在《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福山笔锋一转,针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他所谓的“大分裂”,指的是自195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经济走向了“后工业化时代”,但在社会层面,却出现了犯罪率提高、生育率下降、离婚率飙升、人口走向滑坡、人们对社会政府和未来的信任和信心大幅减弱的趋向。福山的意思是,西方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了转型期,而社会秩序和道德水准,却没有相应地跟上,以致引发了这一“大分裂”的现象。(20)
像《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繁荣》一样,福山写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是想为全世界的社会提供解决问题的出路和方向。他虽然从小不讲日语,对日本的了解也相对肤浅,但他在写作这两本书的时候,却对日本社会持有比较肯定的态度。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繁荣》中,他指出日本的社会属于“高信任度的社会”。而在《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他指出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大分裂”,也即社会秩序的崩坏,在日本和韩国尚未发生。(21)不过他也指出,在现代世界,这一趋向无可避免,重要的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福山的立场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和组成组织,这是人的本性,而这些组织构成了社会秩序,社会秩序需要“社会资本”来维持。福山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
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群体其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开始期望其他成员的举止行为将会是正当可靠的,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信任。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22)
由此可见,福山写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信任”的重要。他所指出的西方社会的“大分裂”,就是西方人在后工业化的社会,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因此他强调,克服“大分裂”的方法,就是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从而提高社会资本,重建社会秩序。在书的最后一部分,他指出这一重建是可能的,因为建立信任,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遵循一种公认的道德准则,是人类历史演化、进步的一个基础。(23)
福山写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的时候,已经渐渐进入学界,出任乔治·梅森大学的讲座教授,后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的外交学院,近年又转任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 (International Studies) 的教授。他因《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被视为能从理论的层面分析当代世界及其未来发展的思想家。而福山的理论分析,其取径是唯心主义的,注重的是思想、文化、道德、信仰等上层建筑因素,如何指引了人类历史的前行。而归根结底,福山认为上述思想、文化、道德行为的建设,来自人类的本性,因为人之为人,必然会与他人联系和交往,组成群体,而在群体交往和活动的时候,则需要寻求建立一种规则和秩序。
三、“后人类”历史的前景和挑战
从上述著作可以看出,福山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基本都还是正面和乐观的。换言之,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前,福山一直持有与塞缪尔·亨廷顿不同的看法,认为世界历史的路程虽有起伏,但最终会走向大同,建立良好的秩序,因为人类本性使然。不过他也有忧虑和怀疑的时候。1999年,也即在他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的十年之后,福山写了一篇旁人不太注意但十分重要的《再思:试管瓶中的最后之人》的文章,发表在《国家利益》杂志上。从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出,他对十年之前的自信满满有所反思和修正。而他的依据是,现代科技、特别是生物科技的长足发展,让科学家可以改变基因。对于福山而言,这一发展的结果是,科学可以改变人类的本性。如此一来,他论证人类必然走向大同的预测,就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24)
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的2002年,福山出版了《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结果》一书。他在书的序言中交代,此书的写作就是《再思:试管瓶中的最后之人》一文的延伸和扩展。或许是受到“9.11”事件发生之后笼罩美国的悲观情绪的影响,福山在书的第一章便表现出了悲天悯人的情绪。他举出两本20世纪著名的“反乌托邦”(dystopia) 著作为例,描绘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一本是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1984》,另一本则是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 Huxley, 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前者我们比较熟悉,而后者需要稍微介绍一下,与福山一书的关联性也更强。奥尔德斯·赫胥黎是阐释进化论的托马斯·赫胥黎 (Thomas Huxley, 1825-1895)、《天演论》一书的作者之孙,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美丽新世界》一书用讽刺的笔调,想象地描绘了一个崭新的、由人类科技创造的世界,其中人类的培植都依据了既定的模式,达到了完美的“社会控制”:有的生来就是领导、精英阶层,有的则处在社会的底层,一辈子劳作。因为他们的基因被改造了,这些不同阶层的人都会安居乐业、各守其职,其社会的箴言是“共有、统一、安定”,世界便因此而永享太平。值得一提的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一书的书名可以有不同的译法,因为“brave”一词具有不同的含义:除了“勇敢”“美丽”之外,还有“面对”的意思,所以有人将之译为《勇敢面对新世界》。而这个书名的原文出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描述了基本与世隔绝的米兰达用井底之蛙的腔调,赞美她生活的世界。赫胥黎用作书名,嘲讽的意味昭然若揭。
福山的《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结果》一书以《1984》和《美丽新世界》作为首章,体现了他写作上力求引人注目的手法,但也反映了他本人真实的忧虑。福山在书中注重的是当代神经药理学的发展,特别是“百忧解”(Prozac;其药理名称是Fluoxetine)和“利他林”(Ritalin;其药理名称是Methylphenidate)这两味药的生产和普及。前者治疗忧郁症,后者针对多动症。福山指出,这两味药的研制及成功,体现了科技的成果,但它们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后果,那就是让赫胥黎指出的“社会控制”得以最终实现。(25)而这一“社会控制”成功的代价就是,人类的本性被扭曲、改造,人类的历史由此走向了一个“后人类”的方向。对福山而言,这样的前景十分让人忧虑,因为如同《美丽新世界》一书所想象的那样:“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每个人都受到了软性的专制统治,虽然健康、快乐,却不再知道希望、恐惧和斗争意味着什么”。(26)对于人类科技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后果,福山的希望是从现在开始,政府就必须对科技的研究加以控制,以防不堪设想的后果。
在“9.11”事件发生之后至今,福山出版了许多新著,毫无封笔的迹象。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对此无法一一详论。不过就总体而言,这些新著基本反映了他历史观、世界观的一个明显变化,那就是对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没有从前那样乐观、自信。(27)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观察,他的学术立场已经渐渐向他的老师亨廷顿靠拢,认为历史不能自然而然地走向世界太平和大同,而是需要为了这一崇高目标,不断做出努力。这方面的例子有他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政体建设:21世紀的治国与世界秩序》及2006年主编的《民族国家的重建:阿富汗和伊拉克及其他》两本书为代表。(28)前者指出,西方文明与中东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主要原因在于在中东地区国家政治权力相对薄弱,而这些弱的政体造成这些国家无法有效地对待和处理社会矛盾,进而影响了国际间的秩序和世界和平。后者以阿富汗和伊拉克为例,探讨美国侵略这两国之后,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民族国家建设问题。2008年福山又主编了《落后:解释拉美与美国发展的差距》一书,亦从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探讨美国与拉美经济成败的原因。(29)福山写作、编辑这些书的主因是希望通过强化民族国家,促进世界和平。不过,他的历史观仍然以西方中心为基调。
不过饶有趣味的是,福山的政治立场在西方学界看来,显然是保守主义的——在他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之后,许多人视他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而新保守主义的特点就是强调西方文明的优越,并证明西方和美国向其他地区推进西方文明,不但有理,而且必需。但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福山对美国政坛的新保守主义,不仅保持了距离,而且多有批评。他在2006年出版的《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权力和新保守主义的遗产》一书,就是一个显例。此书依据他在耶鲁大学做的系列讲座写成,其宗旨是检讨乔治·W·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此书还有一个英国版,题目更为醒目:《声讨新保守派:右派错在哪里?》。(30)福山的主要论点是,布什政府及其幕僚所推行的新保守主义,对世界秩序的重建没有益处,反而带来了坏处。其原因在于新保守主义一方面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优于其他政体,但在其外交政策上又太务实,只要这些国家愿意支持美国,便对他们的政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这样的新保守主义,福山认为有损世界秩序与和平的建设。福山坚定地认为,美国已经当然地成为了世界的核心,其霸权的地位毋庸置疑,而美国应该做的是,更为积极坚定地主导整个世界的发展。从福山的这一观点来看,他的保守主义更胜于布什政府及其幕僚。
上面已经提到,福山近年开始向亨廷顿靠拢。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像亨廷顿一样,重视世界秩序并希望寻求重建这一秩序的办法——他强调全球范围民族国家的重建和他批评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和政策,都与此相关。二是他逐渐重视政治和政體,希望从这个视角来构建世界的和平和秩序。如果上述论著反映的是第一个方面,那么他最新出版的三本书,则表现了第二个方面。福山在2011和2014年分别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革命》和《政治秩序的兴衰:从工业革命到当代》两本书——前者更在扉页上写明纪念塞缪尔·亨廷顿。(31)这两本书就像姊妹篇,从全球的范围描述现代政治的缘起和兴衰。从概括的内容来看,福山试图比较各类政体,也恰当地承认这些政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有效性。但他最终的看法仍然是,民主政体虽然不是至高理想,但它仍然代表了世界历史的一个走向。
2018年福山又出版了《认同:追求尊重和仇恨政治》,其中阐述了他对当今世界和人类历史未来走向的最新看法。此书的出版,距他《历史的终结?》一文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出版,已经有近三十年之久。前面已经指出,面对这期间世界局势发生的许多变化,福山的立场和观点已经有所调整,其最大的不同是他之前的乐观、自信,似乎已经为冷静、谨慎甚至小心翼翼所取代。但福山的总体历史观,是否也有了根本的改变呢?他的《认同:追求尊重和仇恨政治》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福山对人类历史的走向,其基本立场没有什么改变。他在书中指出,自从他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出版之后,许多批评者都误解了他的意思,而这个误解就是对他使用的“终结”(end)一词,没有充分的体会。福山写道:“‘终结一词的意思不是‘终止,而是‘目的或‘目标”。(32)的确,“end”这个词有多重含义,不仅仅指“终止”或“终结”。相反,福山试图指出,由于冷战的结束,世界历史似乎朝着一个方向前进了。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人类历史自那时开始,循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前行、发展了。
〖JP2〗福山承认,他之写作《认同:追求尊重和仇恨政治》,目的是重申自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他显然没有改变他的基本历史观。但此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现实的目的,那就是解释近年世界发生的事件,如英国的脱离欧盟和美国唐纳德·特朗普之成功当选总统。福山希望从学术上,对这两件有点出人意料的事件做一分析。他的取径,还是从《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出发,从人之希望被认可来解释此类历史事件的发生。《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有一章题为“精神的起落”,其英文原文是“The Rise and Fall of Thymos”,其中“Thymos”一词是希腊语,原意指人的精神、情感状态,可以译成“精神”,但其意思与中文的“志气”“志向”相类。在这一章中,福山又用了两个希腊词:“Megalothymia”(译为“优越意识”)和“Isothymia”(译为“平等意识”)。前者指的是人希望成为人上人,后者指人希望得到平等的地位和待遇。这两个词都反映了人希望得到别人、社会认可的志向和愿望。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指出这一获得“认可”的欲望是人类历史的动力,而福山借用了这个观念,认为在民主政体下,这一获得“认可 ”的欲望最容易实现。(33)〖JP〗
福山写作《认同:追求尊重和仇恨政治》将这两个意识或精神状态从个人转到了国家政治。他指出希望得到别人或社会的尊重,是人之本性和常情。政府的存在和社会的规则,都需要建立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之上。福山认为其实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乃至世界秩序的维护,都需要遵循这一原则。不过他关注的主要方面,还是认同政治对民族国家秩序和政治的影响。他指出,获得认可、得到尊重的欲望,是个人或群体之认同的基础。但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潮流之下,这一认同受到了挑战,其主要表现为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产生的矛盾。前者虽然移居他国,但仍然希望保存自己原有的文化、宗教,也即获得认可和尊重。而后者对于外来移民的这一欲求,已经产生了诸多不满,认为这些新移民的要求,损害了他们原有的认同。于是,如他的书的副题所示,福山使用了“仇恨政治”来分析、描述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他的观点就是,正是这些认同之间的碰撞和冲突,而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才能全面解释英国的脱欧和特朗普之当选美国总统。虽然此类问题似乎无法用一种办法来解决(他在书的末尾指出当今世界的认同政治其实出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趋势),但他还是坚信,人类的历史走向最终还是百川归一。(34)
总而言之,福山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和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之后,著述不断。在他出版的众多论著中,有些反映了他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学术思路,譬如《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结果》一书。而其他著作,则有的显得新意欠缺、老调重弹,甚至给人江郎才尽的印象。福山在他最新的著作《认同:追求尊重和仇恨政治》一书的序言中也承认,他在书中的许多观点,与《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相比颇有类似之处,为此他对读者抱有些许歉意。作为一个理论家,福山对当代历史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重振了18、19世纪以来思辨历史哲学的传统,让人重新关心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走向(与其老师亨廷顿相比,福山的著作更受到哲学家的重视,就是一个明证);(35)二是他对人类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执拗的、持续的关注和思考。毋庸讳言,他的不少结论不免有臆测、简单和武断之处,但同时在不同程度上亦具有启发和思考的价值。
① 参见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第359-376页。另见王晴佳:《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② Li Yitian, Chen Jiagang, Xue Xiaoyuan & Lai Hairong, “Democracy,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History: A Chinese Interview with Francis Fukuyam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3∶〖KG-*3〗1 (April 2012),pp.95-107.提到亨廷顿的地方在第97页。
③ 有关亨廷顿与福山的不同,有不少论著,或可参见Stanley Kurtz, “The Future of ‘History: Francis Fukuyama vs. Samuel Huntington,”Policy Review, 113 (June & July 2002),pp.43-58。
④ 参见Ralf Dahrendorf,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urope: in a Letter Intended to Have Been Sent to a Gentleman in Warsaw,New York: Times Books, 1990。
⑤ 见Robert Burns &Hugh Rayment-Pickard, eds.,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From Enlightenment to Postmodernity,Malden MA: Blackwell, 2000,pp.318-321。杨生平也认为福山代表了“后历史”的史观,但视角不同,见《一种值得关注的新历史观:福山的后历史世界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6期。
⑥ 此书的中文译本是《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⑦ (18) Li Yitian, Chen Jiagang, Xue Xiaoyuan & Lai Hairong, “Democracy,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History: A Chinese Interview with Francis Fukuyam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pp.97,106.
⑧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4页。不过此段的译文不甚准确,读者可以参照此书的英文原版: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 Avon Books, 1992,p.65。
⑨ 见Francis Fukuyama, The Soviet Union and Iraq since〖KG*3〗〖QX(Y15〗1968〖QX)〗〖KG-*3〗,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980。这本小册子内部发行,读者对象是美国空军。
⑩ 见Andrzej Korbonski & Francis Fukuyama,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 The Last Three Decad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 (14)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pp.3-18,18.
(12) 有关柯耶夫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解读,见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ed. Allan Bloom, trans. James H. Nichols, J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另见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pp.4-5。刘小枫的《“历史的终结”与智慧的终结:福山 、科耶夫、尼采谈“历史终结”》,《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讨论了福山历史观的思想渊源。
(13) 参见Howard Williams, David Sullivan & E. Gwynn Matthews, Francis Fukuyama and the End of History,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7,特别是该书的结论部分,第160-178页。福山本人在回应别人的批评的时候,也指出他的立场与后现代主义颇为不同,见Francis Fukuyama, “R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History, Five Years Later,” 收入Timothy Burns, ed., After History? Francis Fukuyama and His Critics,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4,pp.259-262。
(15)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382页。但译文有误,此处做了必要的修改。参见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p.339。
(16) 福山:《歷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38-43和114-116页。不过译文有删节。参见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pp.23-38,101-108。
(17)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161-172页。
(19)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参见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20) 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8页。福山原书的书名是: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他用“Disruption”的意思是想表现社会秩序的破坏或瓦解,所以他指出了重建的必要和可能。因此书名译为“大瓦解”应该更为精确一点,当然“礼崩乐坏”更通俗易懂。
(21) (22) (23) 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第174-176、18、329-352页。
(24) Francis Fukuyama, “Second Thoughts: the Last Man in a Bottle,” National Interest, 56 (Summer 1999),pp.1-20.
(25) (26) F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2,pp.53,218.
(27) 刘仁营、肖娇的《福山放弃“历史终结论”了吗?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争论与思考》,《西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对此有所讨论。
(28) Francis Fukuyama,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KG*3〗〖QX(Y15〗21〖QX)〗〖KG-*3〗st Centur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和Francis Fukuyama, ed., Nation-Building: 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笔者在翻译这两本书的书名时,力图做一些区分,因为中文里的“state”和“nation”都可以译为“国家”,但福山的用法希图对两者有所区别,前者注重政体、机构的建设,而后者强调的是国家的民族共同性。
(29) Francis Fukuyama,ed.,Falling Behind: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0) Francis Fukuyama, After the Neo Cons: Where the Right Went Wrong,London: Profile Books, 2006.此书的书名用的是一个双关语:“after”一词在这里可以指“之后”,也可以指“声讨”。
(31)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1;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4.
(32)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8,p.xii.
(33)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161-238页和Fukuyama, 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pp.xii-xiii.
(34) Fukuyama, 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特别是第3-11、163-184页。
(35) 如同本文所述,福山不仅列名为当代的历史哲学家,而且让人重新拾起了对历史的终结和未來趋向的兴趣。参见上引Howard Williams, David Sullivan & E. Gwynn Matthews, Francis Fukuyama and the End of History;Timothy Burns, ed., After History? Francis Fukuyama and His Critics和Gregory Elliott, Ends in Sight: Marx/Fukuyama/Hobsbawm/Anderson,London: PlutoPress, 2008。至于研究福山历史思想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