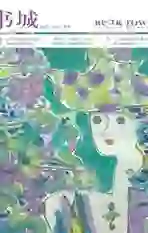理解杜拉斯的欲望
2019-05-10李伟长
李伟长
见过很多杜拉斯的照片,有两张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张是少女杜拉斯初长成,已有妩媚的样子,大眼睛,双眼皮很厚,头发卷曲,刘海斜过半个额头,鼻梁高挺,个子瘦小。那双眼睛顾盼幽深,令人过目难忘。盯住多看一会儿,摄人心魄。她小小年纪,身上就有一种莫名的媚态。
第二张是穿着睡衣的杜拉斯,梳起头发,身架瘦小,已有了女人的样子。两眼炯炯有神,引人注意,同样引人注意的还有黑眼圈。那应该是黑眼圈,据说可能是欲望留下的烙印。这时候的杜拉斯,经历了欲望的洗礼,相比小时候,更有风情,媚态绽放了。她手腕上有一只大镯子,是金镯子,还有中指上的戒指,这应该是中国情人送她的。杜拉斯没有拒绝他的钱,甚至是为了钱,她才没有拒绝那个中国情人。
不谈爱。杜拉斯这样说。只说欲望。
一
一九八四年,杜拉斯写出了《情人》,此时她已年过七十。

少女杜拉斯

穿着睡衣的杜拉斯
编辑一开始有些保守,只印了五千本,几天就卖光了,一个月内加印两万册。再卖断,再加印,最终卖过了几百万册,名副其实的畅销书,获得了当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一九八七年,有人问她,您对那个男人还留有什么其他的记忆?杜拉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喜欢他那中国人的身体,但我的身体让他有快感。彻彻底底的欲望,超越感情,不具人性的,盲目的,没法形容的欲望。我爱这个男人对我的爱,还有那情欲。(《杜拉斯谈杜拉斯:悬而未决的激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杜拉斯的话里有话,她强调的是欲望,似乎在有意地回避爱。
当年,中国情人大方地送杜拉斯礼物,用豪车接送她,请她全家上最贵的餐厅。她的家人讨厌他,席间都没有人愿意跟他说半句话,但依然坦然地接受他的金钱。那时候杜拉斯才十五岁,贫穷又乖戾的年纪,全家陷入了穷困潦倒的绝境。中国情人的钱缓解了她和家人的部分艰难。杜拉斯对这个中国情人有多少情感?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杜拉斯没有忘记他。在六十多年后,终于将这段故事写了出来,以欲望而不是以爱的名义。杜拉斯说,爱,渴望拥有另外一个人,渴望到想将其吞噬。这句话更像是从中国情人的角度说出来的,是他迷恋她的身体,迷恋到近乎吞噬的状态,讨好般地对待她和她那些不甚友好的家人。半个世纪之后,他打的那一通“著名”的电话,说一直爱着她,至死不渝云云,依然有着讨好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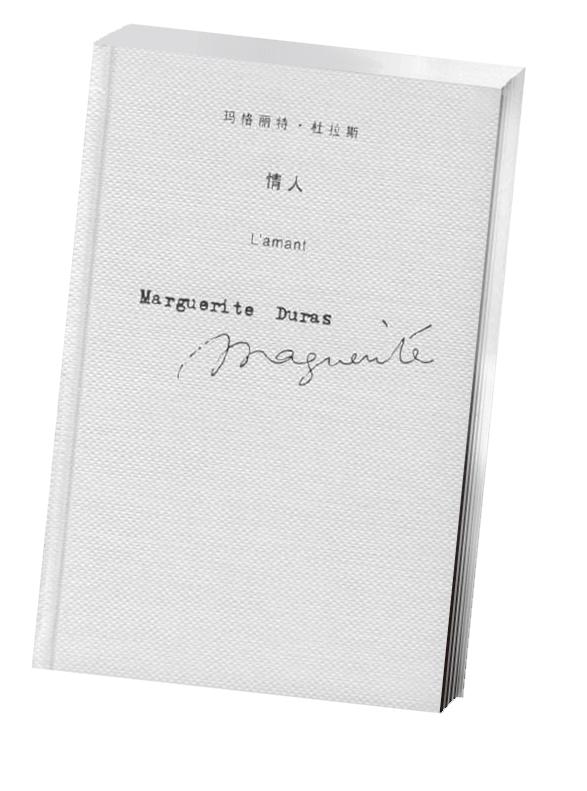
《情人》[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版
這段经历对杜拉斯当然重要。与这个多金的中国情人相恋的经历,将其他所有人的、所有告白过的、系统化的爱抛诸脑后,不置理会。欲望第一次击中了杜拉斯,贫富差异、种族差异、年龄差距,都必然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中国情人面前,杜拉斯一无所有,只有年轻的瘦小的身体。事实上,杜拉斯谈起爱时,显得有些玩世不恭。她说,爱只会存在片刻,随后便四散纷飞,消散于实际上不可能改变生命进程的不可能性中。只有欲望是永恒的,在与中国情人在一起的时候,杜拉斯说:“我体验到的是欲望的力量无所不在,无处不达,从那时候起,我的性经验总是十分丰富的,甚至是粗暴的。”
是欲望在主宰,而不是爱。爱只存在片刻。杜拉斯这样说服自己,也试图说服别人。在她看来,欲望是一种潜伏活动,跟书写类似:我们写出我们所欲想的。就像杜拉斯流传甚广的名句: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爱的多重奏》[ 法] 阿兰·巴迪欧著邓 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中国情人爱上她之后,一生未忘,很多年后,再次相见,就有了《情人》的开头:“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王道乾先生的译文真是雅致。如何理解这位中国情人半个世纪之后的这声告白?杜拉斯没有写出,她是怎么回应这句话的。在《情人》中,她迅速转向了回忆,十五岁在越南的那些年。假如我们天真一些,相信中国情人老去之后的情感和牵挂,那是否可以说,爱一直在他心里盘桓。念念不忘,确有回响。正是中国情人五十多年后的再次示爱,让杜拉斯终于下定决心,动手写这本书,为什么不是之前?我更愿意相信,杜拉斯确认了一点,中国情人对她的爱真的存在,并且历经漫长的岁月而未消失。当年这份爱留给杜拉斯的记忆更多的是激情和欲望,而不是情意绵绵。
二
爱的发生,要处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分离”(《爱的多重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二个是“偶然的相遇”。
“分离”的说法,颇有前置性。在爱发生之前,两个即将相爱的人,有着各自的生活轨迹。没错,是两个人,天生不同的两个人,来自不同社会位置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世间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相同的两个人。这种分离是未相见,是不同的生活气息,也是为相见相爱的准备。毫无疑问,这种分离也会是障碍。当两个原本分离的人相遇,自然是偶然的时间、地点,爱要做的就是将“偶然的相遇”变为“经常的相遇”。分离与相遇,彼此角力,相互拉扯,多少相遇最终败给了分离。
那个风度翩翩的男人从小汽车上走下来,吸着英国纸烟。他注意着这个戴着男式呢帽和穿镶金条带的鞋的少女。他慢慢地往她这边走过来。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胆怯的。开头他脸上没有笑容。一开始他就拿出一支烟请她吸。他的手直打颤。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打颤。(《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这是两人的初次相遇。风度翩翩,胆怯打颤,种族歧视,贫富差异,试图克服,尴尬而无效的努力。如此“分离”前提下的相遇,注定了日后的离散。
杜拉斯和中国情人对爱的理解有着明显的不同。杜拉斯说爱不会长久存在,欲望才是恒久的。中国情人在五十多年之后,将欲望、身体的交缠和情感混于一起,经由时间的熬制,变成的就是一份念想。这份念想穿越了时间,穿过了容颜的衰败,也穿过了消失殆尽的欲望。所谓更爱备受摧残的容颜,是因为他自己也容颜不在,欲望不在。当欲望被时间过滤之后,剩下的爱是否更为纯净一些?《情人》的开头之所以动人,不正是在于去除容颜和欲望之后的情感么!陷入激情中的男女,他们的情感是临时性的情感共同体,“当爱消散时,爱人共同体会留下某样东西的痕迹,这样的东西明明已经发生,却从未存在”。就像杜拉斯和她的中国情人之间的爱怨,的确已经发生,何处再去见它呢?爱不是可见的物质,它存在的方式,无非通过身体的接触(做爱)和言语的宣扬(说爱)。如果不再有性,不再相互说爱,那曾经发生的爱是否真的就不在了,还是有意埋藏在心底?
十五岁时的杜拉斯,真的太穷了,在中国情人面前,她毫无自信,加上破产的母亲、寻欢作乐的大哥、支离破碎的家庭、扭曲变形的生活,这些让敏感的杜拉斯多少感受到了屈辱。不平等的身份,不对等的关系,除了归于欲望,杜拉斯还能说什么?她的确是不喜欢“中国人的身体”,尽管他们彼此贪欢许久,深陷情欲之网。杜拉斯需要钱,给母亲治病,给大哥浪荡,支撑穷困潦倒的家。这导致杜拉斯和中国情人的感情之路,从一开始就与金钱沾上了边儿,难言纯粹。杜拉斯内心中应该是有屈辱感的。一个骄傲的女孩子,从情人处获得金钱供养家庭,情感的平衡必然发生倾斜。家人虽然接受了他的钱,但又瞧不起他的黄皮肤,此种分裂和诡异的家庭氛围,影响了杜拉斯的心绪。贫富的差距,阶层的迥异,肤色的不同,还有年龄的相差十二岁,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场情感的不平等。屈辱,幽冥,无望,成为杜拉斯数次提起的字眼。当杜拉斯六十年后,重新在书写中回忆这段往事,汹涌的情欲与颠沛流离的生活,神经兮兮的母亲,不务正业的大哥,英年早逝的小哥,还有中国情人的告别(娶了门当户对的富家小姐),各种情感杂糅在一起的滋味,早已洞穿了那情欲的自我保护。杜拉斯坚持说,没有在《情人》中写爱。姑且信之,如果在六十年之后,因为当年恋人的一通电话,决定将往事倾囊而出,这都不算爱的话,那只能说明欲望是爱的化身。
中国情人是胆怯的,懦弱的,缺乏抗争的勇气,也没有谋生的本事,他总是轻易地哭,他惶惶不安,始终害怕父亲,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十六岁的法国女孩面前,像一只柔弱的小兽。偏偏杜拉斯也是一个弱者,也是一个缺爱的人。如此的两个人的相遇,也只能是偶然,至多拉长一点的偶然。这样的爱人,来自中国大家族的少爷,留给杜拉斯的也只有绝望。搜索一下文学史,这样的少爷真像是那个时代的征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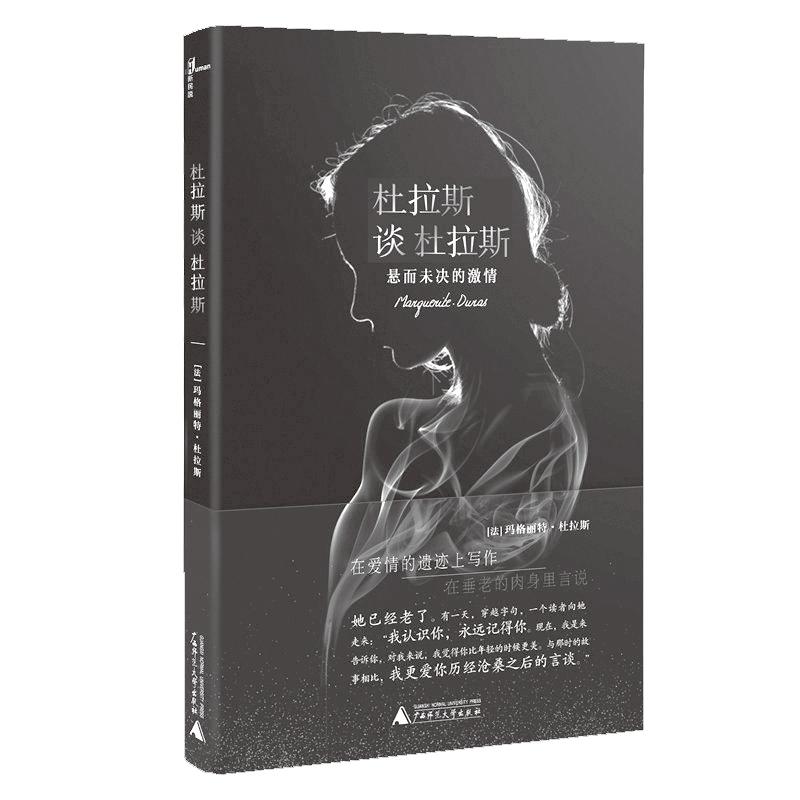
《杜拉斯談杜拉斯:悬而未决的激情》[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缪咏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我发现,要他违抗父命而爱我娶我、把我带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我,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的父亲的金钱。
于未来无望,才会放纵此刻。杜拉斯说:“十八岁的时候我就衰老了。”“一切都在迎合他的欲望,让他把我捕捉而去,让他要我。我变成了他的孩子。”最后在短暂中消耗中倾其所有,而后从欲望的深渊中绝尘而去,留下的就只有记忆,埋藏起来的长久的回忆。试图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努力不开口。然后,记忆可以被压抑,但不会消失,尤其是那些融入了他人痛苦的,并且经过欲望一遍遍确认和淘洗过的记忆。如桑塔格说的那样:“记忆是演出。记忆可以不请自来,而且难以驱除。”(《重点所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王小波对《情人》情有独钟,在不少文章中都提起这部作品,并视之为杰作:“从全书第一句‘我已经老了,给人带来无限的沧桑感开始,到结尾的一句‘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带来绝望的悲凉终,感情的变化都在准确的控制之下。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作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情人》没有按时间逻辑的顺序,自然是一种创造,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杜拉斯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就不完全在爱,而在年少时遭遇的种种生活。童年,青春期,令人绝望的家庭状况,战争,以及在此间遭遇的情感,没有了这些,杜拉斯也认为她的生活乏善可陈。这种将自我记忆随时调用,随时离题的写法,在杜拉斯自己看来,是遵从了记忆本身的特点,以及事件自身的影响方式。
我们常常觉得生命是依照各个事件所发生的先后顺序而随之高低起伏的,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事件的影响范围。让我重拾失去了的感觉的是记忆。然而,所有留存下来,依然可见、可叙述的,通常都很模糊、很表象,留在内心中的参与,晦暗、强烈到甚至无从追忆……书写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引发围绕在故事周遭的事物,作家时刻不间断地围绕着故事在创造。(《杜拉斯谈杜拉斯:悬而未决的激情》)
这种写法,杜拉斯称之为“流动的书写”。
没有具体的指向,游走于词语的波峰,转瞬即逝,又瞬间到来。它永远不会打断阅读,不会越俎代庖。没有给出说法,也不解释。可以写着大哥的落拓,转而又写到了湄公河的蓝。在写着与中国情人耳鬓厮磨时,又能进入母亲的悲剧命运。与其说这是一类写作技艺,不如说杜拉斯遵从了内心的记忆。可以被叙述出来的,依然是表象。《情人》的迷人之处,正在于那没有叙述出来的空白,以及当事人内心的幽暗。
三
杜拉斯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她的童年生活近乎灰暗,她是一个弱者。提到她的童年,必然提到她的母亲,作为真实的母亲,以及作为虚构角色的母亲。与此同时,还有她的大哥,一个在她看来专横地不知感情为何物的混蛋,还有英年早逝的二哥(小哥哥)。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张 容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
精力旺盛、疯疯癫癫,只有身为母亲的人才会像她那样。我们一生中所遇到的人里面,我相信母亲绝对是最怪异、最难以预料、最难以捉摸的那位……总是穿着破烂的衣服……绝望地尖叫,她很会讲故事,单调而又缓慢的声音……
她的疯狂,我永志不忘。她的悲观也是。她仿佛永远在等待战争、等待灾难,好把我们给毁了,所有的人。(《杜拉斯谈杜拉斯:悬而未决的激情》)
这个母亲形象,给予杜拉斯的精神影响,毋庸讳言。关于母亲的疯狂,在长篇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写得极为透彻。小说写了一个锲而不舍的母亲带着一双个性独特的儿女,用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土方法建造堤坝,以抵抗太平洋的潮水的故事,简直就是法国版的愚公移山。从满书的爱情事件里,我读出了一个愤怒的杜拉斯。关于杜拉斯,常被人谈起的是她笔下绝望、多情、孤独、神经质般的爱情叙事,以及她本人所经历的种种风流情事。这部长篇小说讲述的就是她母亲经历了怎样荒唐残酷的修建堤坝事件,关于她与“小哥哥”的微妙情意,关于她对真正男子汉的理解。

杜拉斯和她的母亲
有必要提到一段历史。一九二四年,杜拉斯的母亲玛丽在柬埔寨买了一块土地,饱受海潮之害。为了抵挡海潮,母亲贷款修筑堤坝,结果被海水冲走,为此身心交瘁而离开人世。说这件事情,是因为通常认为,杜拉斯小说的艺术魅力,很大一部分在于她自传自叙的叙述风格。从她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她自身生活的影子,她本人也乐于如此,这是杜拉斯的拿手好戏。现实的生活和文学的生活在杜拉斯这里没有决然明晰的界限。“我们邂逅、我们爱的、我们窥伺的人,其实都是别人,写故事的是作家,故事的导火线则握在别人手中。”
母亲修筑堤坝的真实故事,自然成了本小说的素材来源。因为发生在自家身上,有切肤之痛,对事情本身也有更多的了解。杜拉斯不仅以小说笔法,记述了这段家族经历,而且通过母亲的抱怨,直斥当时的殖民地土地管理者,如何贪赃枉法,如何设下陷阱引人上当,又是如何欺骗盘剥那些租借土地的穷人们。杜拉斯对殖民地政府不留任何情面,给予了愤怒的批判。感谢杜拉斯母亲的受苦,才有了她的愤怒和质疑。批判一词,看上去有一点严肃,似乎对读者够不上太多的吸引力,但对于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批判显然会增加深度和力度。
另有一段故事也值得我们注意,杜拉斯的二哥保尔,大她三岁,杜拉斯亲热地称他为“小哥哥”。他是杜拉斯年轻时的守护神,也是她的崇拜者和爱慕者。在杜拉斯眼里,“小哥哥”是男子汉的象征。他勇敢无畏,敢于独自到森林里去打黑豹。同二哥相比,大哥就一塌糊涂,抽鸦片,偷钱,又硬又冷,对妹妹丝毫没有照顾之心。母亲陷入了绝境,这个家庭也就陷入了绝境。在这种情况下,《情人》里的两个人要面对的困境何其艰难。
小说的叙事风格,一如既往,淡淡地展开,轻轻地收尾。关于这部小说,母亲的形象还能被理解为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被生活击倒,再一次次重来,疯狂地重来。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这本小说在杜拉斯的文学创作中具有代表性。我提起这部小说,是想从侧面印证一个事实,即杜拉斯的母亲如何影响了她,并从中获得杜拉斯的童年生活和少年生活的真实情况。杜拉斯楚楚可怜的样子,惹人心疼,《情人》中有一段对话:
他很可怜我,我对他说:不必,我没有什么好可怜的,除了我的母亲,谁也不值得可怜。他对我说:是因为我有钱,你才来的。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我说当初我看到他,他正坐在他那辆汽车上,本来就是有钱的,那时候我就想要他,我说,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可能知道我究竟该怎么办。他说:我真想把你带走,和你一起走。我说我母亲没有因痛苦而死去,我是不能离开她的。他说一定是他的运气太坏了,不能和我在一起,不过,钱他会给我的,叫我不要着急。他又躺下来。我们再一次沉默了。
他很清楚,杜拉斯是因为他有钱才来的。她不否认这一点,但也不全是钱,人和钱都想要。只是如果不是为了钱,杜拉斯也许不会那样勇敢,会更加不知所措。为家里找一个有钱人作庇护伞,这无形中给了她勇气和决然。这就像一个背负了任务的特工,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可以将真实的自我藏匿起来,变得无所顾忌,大胆自如。可以这样说,走向中国情人的杜拉斯,代表的是家庭和母亲,而不完全是她自己。在身体交融之后,另一个真实的杜拉斯才慢慢生成。由此,关于这场短暂厮守的书写,杜拉斯说没有想到爱也就不难理解。
很多年之后,杜拉斯的生活已经脱离了贫穷,成了著名作家、导演,名利双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钱人”。一个叫作杨·安德烈亚的青年男子,在杜拉斯六十六岁时进入了她的生活,那时杨才二十七岁。他给杜拉斯写了两年的信,终于在一个她心情不顺的日子等到了邀請。作为杜拉斯的书迷和灵魂的俘虏,这段跨越了时间的情感被人不断提起。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感时,不知道杜拉斯是否会想起,她十五岁遇见中国情人的时候,还会自问这是不是爱吗?当年她那么穷困潦倒,如今她有钱了,这个杨会像当年的她一样吗?就像杜拉斯说的,爱就是渴望拥有另外一个人,渴望到想将其吞噬,只是天总不遂人愿,年轻时无法做到真的拥有一个人,而今就行吗?
在《情人》的结尾,“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杜拉斯说自己没有爱,我是不信的,只是无奈吧。现实生活中,陪伴杜拉斯走向生命终点的是杨,一共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