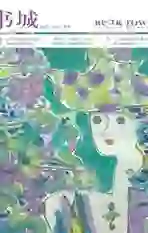海岸线
2019-05-10胡露
胡露
“我们每个人到底有多了解别人?对我来说,这一直让我饶有兴趣,也是促使我写作的理由之一。”《奥丽芙·基特里奇》的作者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如此解释自己的创作之源。这本书获得二○○九年的普利策小说奖,同时被HBO改编为迷你剧,该剧在二○一五年“黄金时间艾美奖”的评选中斩获六项殊荣。
与爱丽丝·门罗相比,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同样擅长描叙平淡生活。她触及更多的是人物在亲密关系中的隔离—夫妇之间、亲子关系,即使近在咫尺,也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作者借主人公奥丽芙的心理活动,写出她的理解:“亲密关系是你人生的支柱,但它们之中也都潜藏危险的暗流。正因为此,你也需要有点小插曲:比如布拉德利百货公司里有一名亲切友好的店员,或是多纳圈店里有一个知道你爱喝哪种咖啡的女服务生。那是一种微妙难言的感觉。”
伊丽莎白出生于美国缅因州的波特兰,《奥丽芙·基特里奇》中的十三个短篇故事,也都发生在缅因。在一个虚构的海滨小镇上,生活着一对平凡夫妇—奥丽芙·基特里奇和她的好好先生亨利。奥丽芙是一名数学老师,亨利则在邻镇做了几十年的药剂师。每当人物独处、凝神的时刻,借他们的感官,我们可以嗅到海滨小镇空气里飘散的咸味,感受到它的海湾、松树、阳光与晨雾。
对读者来说,奥丽芙是“熟悉的陌生人”,她会让我们联想起熟悉的某人,或是某位远亲,甚或是我们的外祖母。作者巧妙地让奥丽芙在这十三篇看似独立的故事里穿针引线,有些故事,奥丽芙是主人公,而另一些故事,她是旁观者,甚至只在别人的对话里惊鸿一瞥。她不怎么美,“个子很高,常给人笨拙的感觉……随着年纪增长,壮的体征突显出来;鼓鼓的脚踝,宽阔的后肩,手腕和手似乎也变得和男人的一样粗大”;她不解风情,亨利在日常生活里表达的脉脉温情总会被她不知趣地反讽回去;她喜怒无常,经常让家庭笼罩在不安之中。儿子成年后远离家乡,在纽约谋生,若干年后,他傲慢而平静地指责母亲是精神分裂者,给出的理由是—“不想活在对她的恐惧之中”。
奥丽芙粗犷外壳下的脆弱与温情,恐怕需要通过漫长的脑回路才能回味过来。就像《百年孤独》里的乌苏娜,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双目失明,不再用以往的感官来感受环境时,她才第一次理解了她的女儿—她向来斥之为傲慢无情的阿玛兰塔,其实是“最温柔的女人”。
而奥丽芙,这个逻辑强大、能够一眼洞穿事物虚伪的表象,却习惯依靠自己本能行事的女人,也拥有奇特的温柔。她喜欢创造东西,小到一日三餐,一件结婚礼服,大到一座为儿子建造的房屋,屋后的一片郁金香花丛,花朵从山坡一直延伸到海边。她对他人的体贴往往是以长捣直入的方式,有时令人难以招架,有时却是一剂奇效药。
谁爱自己,有多爱,人们知道得一清二楚—奥丽芙深信这一点。然而因这种自信,生活让她饱受挫败,因为她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她完全是两个人。亨利偶然吐露心声:“结婚这么久,这么多年,我相信你从来没有道过一次歉。不管为了什么事。”面对儿子克里斯,她的脆弱就更无处遁形。活到七十二岁,第一次被儿子邀请去他的小家庭。她与小家庭的氛围格格不入。家人一起出游,等待绿灯那几秒,她就站在儿子身后,对儿子的爱与思念,试图打破僵局的话语,长期行走的疲惫,都无人关心。儿子与儿媳的喁喁交谈屏蔽了她,“她回想起这些年间自己曾数度感到一种强烈的孤独,以致不久前她去补牙时,牙医用柔软的手指轻轻转动她的下巴,而她像是感受到了某种绵绵的温情,几乎痛彻心扉”。后来和孩子们一起吃奶油圣代,她的蓝色棉衬衫不小心染上一道奶油污迹。他们明明看见,却没有告诉她。这道奶油污迹对奥丽芙来说更是个悲伤的提醒。生活的挫败在细处积累,引发了第二天母子间的争吵。

《奥丽芙·基特里奇》 [ 美]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著张 芸译 南海出版公司2019 年版
横冲直撞的生命力冲击着充满稳定秩序的日常生活,它属于《奥丽芙·基特里奇》的内在张力。同样是平淡生活,爱丽丝·门罗笔下经常出现的停顿、空白或者断裂,回马枪一般直捣读者内心的恐惧与同情;而在《奥丽芙·基特里奇》里总有一匹冲向悬崖的烈马,性命攸关之际,却会被一条强有力的缰绳给稳稳勒住。
看一眼美国地图,缅因州远处东北角,它是新英格兰地区面积最大的州,因地理位置的优势而产生丰富的自然景观,像一片远离尘嚣的角落。凯文和克里斯,成年以后都去了纽约,凯文喜欢上纽约的地铁,因为那里充斥着各种晦暗的色彩和各式古怪的人,这让他感到轻松;而扎根在海滨小镇的亨利,只深信温和克制才是美利坚人的真正品格。第一个故事《药店》,讲述基特里奇夫妇各自的婚外情感。亨利与雇员丹妮丝在日常共事时产生默契,彼此惺惺相惜。丹妮丝的丈夫后来死于一场意外,于是在他们的默契之外,又增添了依赖与怜惜,而两人最亲密的接触,不过是亨利弯腰为她拾起一只掉落的红色连指手套,撑开腕口,注视着她把小手伸进去。亨利意識到他对丹妮丝的感情,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黑夜仿佛某种有生命的不祥之物,紧紧地贴在他的车窗上”。与之对应的,是奥丽芙爱上了她的同事—英语教师吉姆·奥凯西。夫妇俩知道彼此的情愫,却都没有点破。儿子成年以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将父亲中风及一切家庭不幸,都归咎于母亲,指责她与奥凯西的私情,奥丽芙回应:“你根本不懂得婚姻是什么,不懂与人白头偕老是怎么一回事。日子就是这么过的……结婚以后,我们都懂得了退缩。”
《海浪》里,凯文从自杀的边缘勒住,重新回归生活。《殊途》里,基特里奇夫妇从决裂边缘停下来,达成了新一轮的妥协与和解。《安检》里,母子俩不欢而散,奥丽芙随即搭乘回家的航班,过安检时执拗地不愿脱掉鞋子,害怕露出穿破的丝袜。但最终在安检人员的坚持下,不得不和其他乘客一样,乖奶牛一般过关,说:“好的,我很乐意。”日常秩序重归正轨,断裂终究没有出现。
如果说人类的情绪暗涌如海浪,那么日常、家庭、伦理、秩序就是海岸线,即使这样保守平静的海滨小镇,也无时无刻不在承受海浪的洗刷与冲击,保持它的壮丽与平静。欲望源于尘土,也归于尘土。整本书看完,不能不佩服奥丽芙的大鸣大放—有欲望、有性情、有脾气,不依赖药物,也不相信任何心理疗愈。她对生活那样充满信心,所以放任自己汹涌的破坏力及创造力冲击自我和他人,奇妙的是,最终她亦形成了如海岸线一般坚不可摧的秩序,那是独属于她的,同时也会成为他人的参照系。当这一切完成以后,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
她的丈夫亨利—奥丽芙终生的挚友与伴侣—难道不拥有自己的暗涌与秩序吗?若干年后他收到丹妮丝的明信片,卡片落款上第一次加上“爱你的”这三个字。于是—亨利向外凝视着海湾,注意到“细长挺拔的云杉沿岸耸立,美不胜收。上帝的宏伟力量,就蕴含在那平静威严的海岸线和微波荡漾的海水之中”。
任何时候翻开《奥丽芙·基特里奇》,一定会有某种力量吸引我们读下去。它的生活细节如此丰满鲜活,我们只能置身其中。伊丽莎白提及构筑场景的体验—“我向来喜欢从一个场景或一小部分场景开始写作。经过这些年,我已经学会了体会那种最紧迫的感受……再将这种情感转移到一个人物里。这会给故事场景带来生命力,从而不那么笨拙”。正因为《奥丽芙·基特里奇》中场景的真实与丰富,我第一次深深意识到小说所具有的强大治愈能力,它不是一碗煲热的鸡汤,也不是崇高正直的价值观输出,而是给你提供了各种幽微的存在感。一个海滨小镇,一个个失控与回归的故事,当我们阅读时,其实也在经历种种人性的测试,借一个幻象,尽可能地触碰真实。奥丽芙走完人生的全盛时期,又慢慢经历衰老与失去的晚年,在垂垂老矣的时候感叹,“生活让我感到挫败,但我还不想离开”。据说《奥丽芙·基特里奇》的续作也将出版了,说不定这也是作者在邀请她的同道中人—最终,我们能向命运要求的不是什么光明结局,而是逐渐看得更清楚此生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