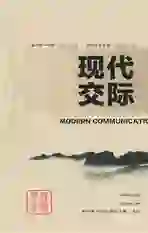责任伦理视角下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探究
2019-05-05顾桂清
顾桂清
摘要:本文以人口迁移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责任伦理视角下留守子女和留守老人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作用的三个假设,为后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子女留守 老人留守 居留意愿 责任伦理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5-0052-02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增至2017年的58.52%,年均增长1.03个百分点,截至2017年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7.4%,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仅占42.45%①,人口的非永久性迁移降低了我国的城镇化质量。2015年11月,国家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举家进城落户”的国家战略目标②,这个目标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新概念。截至2017年,为了响应国家进城落户的号召,各城镇降低了落户门槛,并取消了农业户口,然而城镇人口最终是否能吸引到流动人口进城落户,取决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不仅是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我国实现举家进城落户的现实问题。迅猛的城镇化给城市的经济发展增添无穷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乡村的衰落。2018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然而随着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迁移,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问题日益显著,“空心化”“老龄化”逐渐显现。
近年来,有关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已相当丰富,但主要是以流入地作为出发点,较少将研究视角集中在流出地,且研究多是从经济学视角,很少有学者从中国的家庭传统出发,研究家庭文化因素对流动者居留意愿的影响。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家庭观念的国家,有学者认为家庭关系应至少包含两个方面:婚姻关系和供养关系——即双亲对未成年子女的供养以及成年子女对年老体衰的双亲的供养,也只有这两种关系结合在同一社会之内,才组成家庭。[1]提到家庭,不仅有赡养责任,还有与之不可分割的抚养责任。在我国儒学伦理中,父慈子孝中的“父慈”体现的就是抚养责任,“子孝”就是赡养责任③。流动人口一方面作为子女,对照顾老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作为抚养子女的中心人物,在照料子女上起着不可替代的责任④。父辈对子代的代际支持,子代对父母的孝心赡养是责任伦理双向互动的题中应有之意。在此背景下,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不仅关系着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经济收益,而且关乎整个家庭未来的理想寄托,同时也维系了家庭和家族的繁衍与生产。基于此,笔者基于责任伦理的视角,研究留守老人与留守子女的存在对远在城市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提出了三个假设。我国流动人口又应如何去平衡家庭的赡养抚育功能和追求经济效益间的关系,在乡村衰落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本土化地理解我国流动人口的居留决策,也有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人口流动进程中的“衍生物”——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的这一存在。
二、理论基础
从理论视角来看,我国当前尚未形成解释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一个成熟分析框架[2],对居留意愿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迁移问题的延伸,我国对居留意愿的研究还是在西方成熟的人口迁移框架下,并结合本地基本国情进行的本土化研究。国外比较经典的迁移理论主要包括三种迁移理论:一是“推—拉”理论,它主要从宏观层面分析人口迁移的动因,认为迁移决策是由迁入地的拉力和迁出地的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3]但“推—拉”理论不能解释在迁移过程中个体之间存在的异质性,人力资本迁移理论基于微观视角,分析在同一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迁移动机选择的原因。[4]以上两种理论假设的决策主体都是个人,对家庭迁移动因的解释能力不足。近年来,流动人口迁移及在流入地的居留形态出现了新的趋势,即越来越倾向于“携家带口”迁移,家庭化迁移已经成为中国目前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形式之一。[5]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迁移理论弥补了上述缺陷,它把家庭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重要性,认为家庭迁移并不仅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预期收入,还为了使家庭风险减少到最低点。[6]Mincer从其他角度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较为类似的研究结论,即家庭是影响人们作出迁移决策的关键因素。[7]新家庭迁移理论虽已从个体迁移关注到家庭化迁移,但仍是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忽略家庭自身的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家庭功能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家庭的教育、组织经济生活以及实现人口再生产的社会功能依旧存在,而这些家庭功能是在代際之间的互动中实现的,家庭伦理也得以选择性地继承与发展。
“责任伦理”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他认为存在两种指导伦理取向行为的准则——“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8],韦伯从行为本身的价值和行为可预见后果之间差异,对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做了界定和区分:其中“信念伦理”属于主观的价值认定,行动者只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责任;“责任伦理”则要求行动者对自己行动可预见的后果负有责任,并以后果的善来抵偿为达成该后果所使用手段的不善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责任伦理”以有无责任感为道德善恶判定的标准,并以行动者所负的责任是否与应然的后果一致,作为判断行动主体是否尽责的标准。[9]但传统的伦理学更侧重于过去与现在的责任,而忽略了未来的责任。汉斯·约纳斯随后发展了韦伯的责任伦理,创立了责任伦理学,强调“责任伦理”的全程性和整体性,约纳斯以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伦理为例,认为父母责任在时间和本质上是所有责任的原型,指出父母抚育教养孩子的责任方方面面都要负到,且不以子女回报为目的。[10]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是家庭伦理提出的重要要求,它作为一种责任伦理,亦有道德的成分,是个人行为准则的原则,并被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接受且奉行。[11]而在中国的代际关系层面,责任伦理在强调子女对父母赡养责任的同时也不容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责任,这种责任伦理对家庭成员赋予责任、期望并对他们的行为产生规范和约束作用,[12]使他们履行对亲人陪伴、老人照顾、子女监护的价值感,从而缓解责任伦理约束作用带来的压力。
三、研究假设
父母家庭作为儿童成长的重要载体,对儿童初期的社会化起着重要作用,父母在流动到大城市,可能会由于户籍制度等二重结构因素无法携带自己的子女,在这种情况下,务工单位与家庭地理上的距离常使得他们外出务工、履行家庭经济义务与监护子女、照顾老人等其他责任、义务相冲突;当冲突难以调和时,出于家庭整体利益、责任的考虑,可能会选择返乡[13]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当老家有留守子女时,流动人口更不倾向于就地留城。
由于传统文化原因和社会保障网络体系的不完善,我国的家庭主要依靠家庭进行养老,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既包括对父母物质层面的生活照料与经济支持,也包括对父母精神层面的关心慰藉,一旦子女较长时间远离父母外出务工,他们对父母的养老支持就有可能弱化,进而影响留守父母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当老家有留守父母时,流动人口更不倾向于就地留城。
责任伦理在强调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责任时,同时也赋予了老人照顾孙辈的责任,老人普遍存在着对子孙的责任伦理。[14]在中国的农村社会,留守父母一方面作为需要赡养的“空巢老人”,是赡养责任的需求方牵制着子女的远行;另一方面,家庭化迁移虽已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体模式,子女随迁的现象也愈加普遍,但由于我国独特的二元户籍制度,“候鸟型”的劳动力流动仍使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难以把子女接到工作地同住,“隔代”照料、“单亲”照料依然是留守子女的主要照料方式。留守老人又成为抚养责任的替代方,替代子女去承担抚养责任,解决子女流动的部分后顾之忧,影响着子女的流动决策。由此,本来提出假设3:
假设3:当老家有留守子女时,留守老人或留守配偶的存在会削弱留守子女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四、结语
本文责任伦理视角,以人口迁移理论为基础,提出三个假设,认为在赡养责任和抚养责任的驱动下,子女留守和老人留守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且作为抚养责任的替代方,留守老人或者留守配偶的存在会削弱留守子女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而这种假设是否成立,仍需要数据的进一步验证。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OL].http://www.stats.gov.cn/.
②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③《礼记》中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④《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参考文献:
[1]蔡俊生.论群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李振刚.社会融合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14(3):100-117.
[3]Heberle R.The Cause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a Survey of German Theor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43(6):932-950.
[4]Becker G S.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3rd Edition)[J].Nber Books,1964,18(1):556.
[5]王子成,赵忠.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动态选择外出、回流还是再迁移[J].管理世界,2013(1):78-88.
[6]Stark O,Taylor J E.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J].Economic Journal,1989 ,101(408):1163-1178.
[7]Mincer J.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86(5):749-773
[8]田秀云,白臣.當代中国责任伦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伦理学研究,2010(3):130-135.
[9]陈拙.马克斯·韦伯论中国社会[J].华夏文化,2004(2):25-27.
[10]Hans Jonas.Wissenschaft als pers?nliches Erlebnis[M].G?ttingen,Vandenhoeck& Ruprecht Verlag,1987.
[11]杨善华,贺常梅.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Vol.41(1):71-84.
[12]潘允康.社会变迁中的家庭 : 家庭社会学[M].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社会学,2002.
[13]郭云涛.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回流行为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6-41.
[14]陈盛淦,吴宏洛.二孩政策背景下随迁老人城市居留意愿研究——基于责任伦理视角[J].东南学术,2016(3):62-67.
责任编辑:赵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