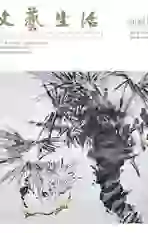诗意中撼动心灵
2019-04-23赵芮妤
赵芮妤
摘要:《麦田》,作为中国当代纪录片的翘楚,最坚决的恪守了纪录片客观公正的原则。影片大量的使用中性镜头,创作者试图不在影片中流露出任何情感倾向,时刻保持者自己的客观立场,将表达主体的各个方面展现给观者,让观者自行去判断。本文通过对《麦田》和《三十二》两部作品对比分析,在内容上、思想上的传达引申出对现世梦想的一种感召,从个性中寻求纪录片创作的共性。
关键词:《麦田》;存在;《三十二》;梦想;直接电影;真实电影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06-0101-02
纪录片《麦田》就像个巨大的情感出口,让我们可以借着这部片子,表达自己的内心,其实所有的片子都是这样。每个片子,到最后,感受到的都是自己。每一部影片,都是唤醒着人本身的情感。所有回顾的意义,都是当下。或者铭记,或者反思,或者感动。由郭柯导演的(仨十二》也是如此,克制而冷静的情感表达,诗意的镜头画面呈现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在说《三十二》,在说《麦田》,也在说我们自己。
汪峰的歌曲《存在》中有句歌词“我该如何存在”。看纪录片有时候是很神奇的感觉,在不长的观影时间,你仿佛被带入了另一种生命,一种与你目前际遇完全不同的生活。看完总会恍惚,这世间有那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生活着,你无法想象像他们一样生活,但可以感受他们的态度。看完之后,总会反观自我,会羞愧,自己的生活已是恩赐,却还在翻来覆去地苦恼。但过不多久,还是会被堆积的琐事和巨大的压力所困扰。于是懂得,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痛苦永远存在,是生命永恒的主题。换一种生活方式,只不过换了一种痛苦的接受形式,痛苦不会消失。我们能调整的,不过是自己的态度和心情罢了。
你无法肯定或指责任何一种生活,因为人生,也和这篇作业一样,没有标准答案。
相比(仨十二》,《麦田》似乎会大多数人更加欣赏。但欣赏不代表喜欢。其实对于《三十二》来说,影像给人们的冲击,文字也可以抵达。但是《麦田》,真真切切砸中了我们。它的方式,是只属于镜头语言的一种表达,文字和音乐无可替代。这个可能就是早期的一些纪录大师所探求的,只属于电影语言的诗性。
但是欣赏不代表喜欢。人们喜欢《三十二》里的那种温情,每一个镜头流淌过的那种温情。从韦绍兰老人眼睛里散发出的光芒,像是太阳。那种对生命的热爱,是从心底进发出的暖意。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自己过着这样的生活,是否能像老人一样热爱生命。我们不知道。没有经历过,也不敢妄说。相比老人,她的儿子的怨,凸显得鲜明。我们非常能理解儿子的怨,甚至是恨。对于他,从一出生就背负这样的烙印,这种痛苦,生命对他是苛刻的,是不公平的。但谁说生命就是公平的?儿子和母亲的不同看法,似乎在向人们昭示与其像儿子一样,一生与生命相怨相伴,不如去接受它,热爱它。因为无论怎样,生活是自己的,对生命抱怨,就是对自己抱怨。抱怨一辈子,又能改变什么呢。不如笑吧。这样的反差,让我们更加对韦绍兰老人充满了敬意。说,毕竟是容易的,真正做到,有多难,想象不出。
其实我们许多人,做的并不如韦绍兰老人。北京是一座有魔力的城,北京是一座永远也不缺少才华的城。许多人,意气风发地来到这里,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被迫思考着温饱的问题。你是没有办法在贫穷中谈论纯粹的理想的,面对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的主人公大刚一样做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磕磕绊绊中,我们总要融入社会,和我们抗争过的,握手言和。有些人,彻底地转变了自己,投向了世俗的怀抱,多年后回首青春,却将所有的责任都丢给命运。其实命运,就是自己。关于梦想的意义,总是相通的。
有多久没有背诵过食指的《相信未来》了,这些文字都是年轻时毫不动摇的信仰。许多人再次看到它们,竟然有一种陌生感,虽然很快就能再次熟悉并背诵,但还是有一种不可抑制的难过,就像面对曾经的自己,有些难堪,反问自己,你为什么变了?
天真的人,容易被天真打动,因为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天真。
对于片子,我们不谈手法,只谈感想。
或许人们并不知道《麦田》里的那些石像有没有什么象征意义,是作者刻意表达的。或许有,或许没有,都不重要。影片不是小说,作者把他的创作用镜头语言赤裸裸地告诉了我们,我们看到了它,就拥有了解读它的权利。我们从小在语文课上牵强附会得还不够吗?生要从作者的只言片语中引申出什么生活的意义,生存的道理。创作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如果在创作中还有空想什么我要用这个形象代表什么,来暗喻什么,那这个作品,一定是很难看的。人们可能在潜意识中有这样的想法,它融会在我的思想中,通过表达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我们称这是灵感。但表达是不可以预知的,也是不能设定的,这会破坏表达的流畅感。只有没灵感的人才会这么做。
《麦田》中拉琴的郭永章老人,是故事的旁白。他在热烈的阳光下,孤傲得像是尼采。他是中心,他是太阳。我们不得不相信并震撼,他生活的本质就是艺术。他与这个故事无关,又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他不像我们记忆里艺术家的模样,但他本来就是真正的艺术家。他和石像、太阳构成了一幅无比和谐的画面,让我禁不住恍惚,那曲子,是他在唱,还是石像在唱,又或是天地在唱?
作者没有说话,却一直在说,画面在说、曲子在说、收音机在说。影像中一直反复得不厌其烦地强调着时间。一遍又一遍,在时间漫长得几乎像静止的守护中,听到收音机讲神奇的遥控器可以跳过漫长的时间,真的忍不住被这讽刺逗笑,却又笑不出来,只有深深的无力感。守护的意义,就在于时间。如果跳过了漫长,何谈守护?
《麦田》里的石像,像个真正的万物之神,虽然村民是被雇来保护它们的,但石像更像守护者。它们在这片土地上,冷静旁观,看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沉默,再沉默。就像是个《等待戈多》一般的荒诞剧,究竟谁在守护谁?谁又需要被守护?我企图去想象,看多了生命的生长凋落,是不是真的会怀疑生存的意义。后来又想,可能会麻木了吧。人生的悲喜,正是因为时间的限定,才有了更多的意义。
人们杀了猪,将猪剁成了猪肉馅。少年最终用弹弓打死了鸟,尽管它曾在无聊时陪伴过他。生命的残忍与冷酷,在无聊之中相互折磨。时间是最好的药,也是最狠的毒。时间将感官钝感,将生命淹没。不知为何,看到《麦田》里这些镜头,使人们抑制不住地想起《铁皮鼓》里母亲吃鱼的镜头,一种生理上本能的反胃。许多人认为《铁皮鼓》是不会想再看第二遍的电影,用马头捕鳗鱼、被切掉的鱼头等等,那些直接直白的镜头语言让人从生理到心理都难以接受。冷静与冷酷,其实只有一字之差。这种看似旁观的表达,其实才是作者直接态度的无限放大。生活是冷酷的么?或许是吧。但生活之中还有温情。但是镜头语言的组合,像是种提炼,将其他的元素剥离,只留下了纯净的冷酷,沉默,让观看者毛骨悚然,反思,叹息。而这,也正是作者想让我们感受到的。
大学时代的我们会或许曾在课堂上天真地妄谈过对真实电影的喜爱和对直接电影的排斥,其实我们深知自己对他们的理解是那样浅薄。关于纪录片的真实性的问题的思考,真实对于纪录片,就是物质意识对于哲学。真实无疑是纪录片的生命,但是通往真实的道路有无数种,如果依照直接电影的真实观,那就永远无法拍到我们的梦了,梦是不能用墙上的苍蝇的方式拍到的。
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关于纪录片是直接电影还是真实电影的问题给了一个很好的诠释。一个作者,是不可以被这些观念束缚的,也不应该被束缚。是访问还是旁观,很重要吗?只要是我们认为的可以抵达真实的路,这些都是方式而己。我们表达的也只是我们自己以为的真实。就算真实在历史的角落笑我们,我们也用自己的眼睛,完成了对生命的纪录。每一段纪录片都是一个生命理解和表达另一个生命。上帝借用我们的眼睛,完成了另一种真实的回顾。就算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眼前,两个看到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没有必要纠结所谓的客不客观,人是不可以将自我完全剥离的,这是人类的局限,也是每个生命最可爱的地方。人的自我意识的参与,让纪录有了温度。我们不是机器人。在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中,连机器人都比我们更有温度,这才是最可悲的。
但你无法否认的是,在这部看似残酷窒息的影像背后,作者要进行的其实是一种暖意的表达。观看《麦田》,你仿佛觉得每一格画面都是静止的,但生活是在流动的,万物依然在变化。在让人窒息的静止中,什么也不能阻挡生长,凋落,再生长。在无力的时间面前,在庞大的琐碎的生活面前,真的让人禁不住怀疑,何为意义。但是在看到孩子上学了,孩子写作业时,人们还是被打动,渺小又怎样呢,琐碎又怎样呢。石像不知道,时间何其有限的人类用繁衍的方式,将生命延续,而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值得歌颂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万物在生长,生命也是。代代更替,生活本身就是意义。石像或许知道,但是它没有说。
结尾,郭永章老人虔誠地摸着石像。我们对于生命,又何曾不是瞎子摸象呢?最后一个石像的镜头,让人们仿佛看到了生命在俯瞰自己,人如同蝼蚁,充满敬畏。
3
老子说:“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了解生命而且热爱生命的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
前苏联的宇航员说:“我曾经认为自己是个太空人,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发现我只是一名星球之间的寂寞舞者。”
《三十二》里的韦绍兰老人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麦田》里拉琴的郭永章老人说:“一哭一笑这一辈子就算过去了。唱,唱的高兴。我一定要唱!”
我们或许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