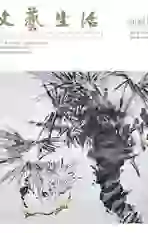论《塔杜施先生》中的对立性张力
2019-04-23汪汝文
汪汝文
摘要:《塔杜施先生》代表了波兰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创作的最高成就,这部长诗以波兰复兴和民族独立为历史背景,以霍雷什科及索普利查两大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为主要线索,通过时间叙事结构上的张力建构以及对立性人物性格的塑造,为读者展现了一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因此本文就将从长诗时间逻辑、空间叙事以及人物形象所包含的种种张力元素着手,分析《塔杜施先出》这部作品中的对立性张力。
关键词:《塔杜施先生》;密茨凯维奇;对立性张力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06-0053-03
一、记忆与预感
《塔杜施先生》创作于1832年,全诗共分为十二章,其中前十章一连串事件都集中发生在1811年夏日的短短几天之中。不同于欧洲其他浪漫主义流派的是,以密茨凯维奇为代表的波兰浪漫主义诗人总是带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气质。勃兰兑斯曾在《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中将密茨凯维奇与丹麦浪漫主义诗人亚当·艾伦许莱格以及瑞典诗人埃塞伊斯·泰格纳进行过对比,他认为密茨凯维奇在赞颂他的民族时,并非是到民族的传奇世界中去选择素材,或者从它的古代,甚至更是更遥远的过去取提炼创作主题,而是立足于自己有机会观察到的生活,在作品中再现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时间逻辑结构上的冲突和对立,在一种张力体系中将原本带有写实色彩的素材崇高化并加以升华。从全诗时间逻辑结构来看,《塔杜施先生》就是在这种记忆与预感的纠缠关系中展开的。长诗时间结构上的碰撞,不仅发生在人物的意识之中,也在密茨凯维奇的叙述中有所体现。
受父亲雅采克的指示,塔杜施从维尔诺回到索普利佐夫庄园。长诗从这里开始,就一直跟随塔杜施的脚步行走在索普利佐夫庄园,将镜头一下回溯到塔杜施的童年时代。塔杜施打量着这个古老的庄园,用一种近乎贪婪的眼神观察着四周古老的墙壁。庄园里的摆设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动,塔杜施甚至一眼认出了他曾用过的家具和帘帷。长诗转而写到了波兰民族英雄科希秋什科和波兰爱国志士雷坦等人,“这儿是科希秋什科,他穿着克拉科夫长衫抬头望天,手握一把双刃利剑;那时他站在祭坛的阶梯上立下誓言,说要用这宝剑把三强赶出波兰,否则就让自己殒命于此剑。”身穿波兰服装的雷坦则是坐着,“为失去自由而悲叹”。
塔杜施从维尔诺回到索普利佐夫庄园时是1811年,而根据后文,塔杜施当时只是“几乎满了二十岁”,可以推断塔杜施小时候生活在庄园的时期应该是在18世纪90年代,科希秋什科以及雷坦的主要活动则是发生在18世纪70、80年代,因此塔杜施的孩童年代与科希秋什科领导的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起义活动在时间上并非是重叠的。纵使塔杜施有关于科希秋什科以及雷坦的记忆,“他儿时的旧物”并无法促发他对民族起义的记忆。从“如今似乎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美的”“他儿时的旧物”到科希秋什科“用这宝剑把三强赶出波兰”两者之间的跳跃是密茨凯维奇有意为之。密茨凯维奇寄希望在长诗人物回忆过去的同时,也将长诗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历史维度之中。塔杜施“带着儿时的欢乐拉了一下钟绳”,“把东布罗夫斯基的军乐再听一遍”,这一情节则更是凸显了密茨凯维奇的意图。东布罗夫斯基这首乐曲是东布罗夫斯基在意大利为拿破仑作战时的军歌,创作于1797年,虽然后来传播到波兰,但真正意义上成为波兰最流行的歌曲则是在1830年十一月起义中,而十一月起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塔杜施先生》这部作品的诞生。1832年的密茨凯维奇在创作过程中,让塔杜施置身在1811年,回忆的却是能够引发诗人自身在1830年记忆的东布罗夫斯基的军乐,这种时间逻辑上的对立冲突在记忆中的碰撞构成一种极强的对立性张力。
晚餐后的法官以及他的宾客来到庄园的庭院准备享受夜晚的宁静,看到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之后,大管家沃依斯基开始讲述一些星座故事,比如老立陶宛都熟知的有关路锡福、利维坦的故事。但他们对此并没有兴趣,他们在意的是“最近在天上出现的一位新客人”——也就是出现在1811年的那颗彗星。大管家于是回忆起波兰国王扬三世在世的时候,出现在他们头顶的彗星,他们认为根据彗星的走向——“同穆罕默德的军队走同一条路,由东向西”,判断出这颗彗星是国王扬·索别斯基远征的预兆。老管家沃依斯基提到自己曾经读过雅·卡·鲁宾可夫斯基的作品《雅尼娜》,认为最近出现在天上的星星与索别斯基夺取穆罕默德旗帜前所出现的彗星是一样的。因而他们产生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预感一拿破仑进军波兰准备攻打沙皇俄国。立陶宛人很难不去相信这种神秘的预感,历史的记忆让他们保有对这种预示的敬畏,天空的奇迹“早在村村寨寨流行”,“仿佛是在那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有种朦胧的期盼,忧伤而又欣欢”。以至于除此以外,带着这种预感,他们也在其他许多别的迹象中找到蛛丝马迹,比如“不祥的鸟呜叫”以及看林人看见的从墓地走过的瘟疫女神。伯爵在回答泰莉梅娜的问题时说“这是命中注定,这是天意,神秘的预兆外加上神秘的动力催我到异乡干番事业”,预感一直在影响着立陶宛人,就像是赋予他们一种神圣而又神秘的使命感,吸引着他们走出家园干一番事业-跟随拿破仑大军反抗俄国统治。对于《塔杜施先生》中的人物来说,现实中预感的强大力量依托于对于历史的记忆;而对于读者来说,长诗中的预感也只不过是一种己成历史的记忆罢了。
二、缺席与在场
記忆与预感贯穿《塔杜施先生》长诗始终,而一种神秘的力量也至始至终地牵引着长诗的人物,索普利佐夫庄园以和霍雷什科家都被卷入了一个更大的对立结构的旋涡之中——即主人公的缺席与在场。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叫《塔杜施先生》,但长诗中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却并不是塔杜施,而是其父亲雅采克。雅采克是贯穿《塔杜施先生》的中心人物,是这部长诗的英雄人物,他影响着索普利佐夫庄园和霍雷什科家人物的一举一动。正如《塔杜施先生》译者易丽君所言,“诗人不仅花了最多的笔墨来塑造这个人物,而且在他身上投入了全部的爱、同情和钦佩,在刻画这个人物时不带丝毫的嘲弄,也不运用常用的旁敲侧击的诙谐手法。”《塔杜施先生》共分为十二章,然而对于读者以及长诗中的人物来说,英雄人物雅采克却直到第十章才真正意义上的“在场”,从第一章到第九章都处于现场意义上的“缺席”状态。
但这种现场的“缺席”并不代表着人物本身的消失,雅采克至始至终都没有脱离过长诗情节的发展。无论是塔杜施达到立陶宛的维尔诺去学习,还是再次回到索普利佐夫庄园继承索普利佐夫庄园的财产,都是受到其父亲雅采克的安排和控制。法官在与泰莉梅娜的一次谈话中说道:
“我倒愿意,可是新麻烦接踵而来!/雅采克不肯放弃对儿子的照顾,/这不又派了伯尔那修士来监护,/他是从维斯瓦河对岸来到此地,/是我哥哥的朋友,知道他的妙计;/因此他们安排了塔杜施的命运,/要他结婚,娶佐霞,你的被监护人。”并声称雅采克“有权支配一切”。
可以说,雅采克就是这样,处在“缺席”的状态之中,却又时时刻刻地“在场”。
密茨凯维奇通过让雅采克伪装成修士罗巴克实现了“缺席”与“在场”的对立性统一。在修士罗巴克出场时,密茨凯维奇这样介绍他,
“罗巴克也许是神秘的募化人:/……他常不戴头巾,身居修院也不久。/在他的右耳上方,略略高于额角,/有块手心宽的瘢痕皮早已被削落,/下巴上有处新伤是枪挑或弹穿;/读弥撒书决不会留下如此纪念。/不仅是这些伤痕和严峻的眼神,/连他的动作和声音也像个军人。”
第四章中霍雷什科家的管家盖尔瓦齐在分析到底是谁打死了熊的时候,提到:
“上帝便派了伯尔那神父前来相助。/他使我们感到羞耻;啊!伟大的信徒……/先生们,我老了,在我漫长的一生/只见过一个有此射击绝技的人。/那时候他以频繁的决斗而闻名,/能一枪打掉女人脚上的鞋后跟,/那恶棍中的恶棍,当年威慑全境,/他叫雅采克…..”
但读者读到这两处,并不会将神父与雅采克联系起来。对于除了法官以外其他所有人来说,罗巴克只是一个修士而己,真正的雅采克一直漂流在国外,霍雷什科家的管家甚至认为雅采克早就“连同胡子烂在了狱中”。长诗中的人物完全没有意识到雅采克就真真切切地站在他们身边,修士的身影消失后,众人的注意力便瞬间转移到了锅里的酸菜肉之上。
在第十章中,贵族们预感拿破仑大军的到来势必会引发波兰民族与俄国沙皇的又一次纷争,面对“不是打一账,就是到西伯利亚丧命”这种选择,波兰人选择了“去跟人抗争,同命运搏斗,无怨无悔”。就在塔杜施也准备动身前行之时,法官才向读者明确无误地指出了修士的真正身份就是雅采克,
“怎么,哥哥?还不直言相告?/就连现在?可怜的孩子就要走了,/你还是宁可什么都不叫他知道!”
而雅采克像霍雷什科家的总管真正挑明自己的身份也是在其之后,
“罗巴克那锐利的目光许久,许久/在总管眼睛上徘徊,越来越温柔,/末了,他似乎下定决心破釜沉舟,/用手捂住眼睛,鉴定有力地一吼:/‘我是雅采克·索普利查……”至此,雅采克才真正“出场”了。
“缺席”状态下的雅采克与“在场”的雅采克判若两人,当雅采克身份还未明了时,在盖尔瓦伊的描述里,读者会认为索普利查在那场混战中就的的确确是个“畜生”和“强盗”,這也成为索普利佐夫庄园与霍雷什科家之间血海深仇形成的原因,卖国贼的恶名像瘟疫一般缠绕着雅采克,他“同莫斯科鬼子合谋”,“血染霍雷什科”,他是“民族的罪人”。而事实上,雅采克却并非如此不堪。化身为伯尔那修士的雅采克“足迹踏遍临近所有的乡村,/在酒馆里常同乡下人促膝谈心”。雅采克表明自己的身份后,吐露了一切真相,他并不曾叛卖过他的祖国,为了不与俄国人同流合污逃离了立陶宛,因此受尽折磨,而之后他也感觉到“唯一有效的救药/是要从此改邪归正,摈弃那罪恶,/要竭尽所能将功补过”。他隐姓埋名,加入波兰军团,为波兰的解放和复兴而不断努力。密茨凯维奇将雅采克放置于“缺席”与“在场”的对立性叙事体系之中,塑造出了一个性格张力十足的人物形象。
三、“局内人”与“局外人”
13世纪中叶,在立陶宛形成了早期的封建国家,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格底敏统治时期,立陶宛发展成为东欧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立陶宛通过和平联姻的途径对罗斯进行不断地扩张,除其本部的8万平方公里外,立陶宛占领了西南罗斯(即此后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超过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曾有几个世纪,立陶宛的疆域往南一直延伸到黑海,往北则临近波罗的海,西边以布格河为界。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政治背景,再加上立陶宛臣民自身多神教的宗教信仰,使得在立陶宛的国土上,语言以及民族宗教关系异常复杂。立陶宛所占领的地区一直保持着他们的东正教以及原有的风俗习惯,虽然亚盖洛统治时期推行天主教,但受到抵制,使得立陶宛地区的宗教矛盾更加突出。在长诗《塔杜施先生》中,立陶宛边境的犹太人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矛盾冲突体系中。
当密茨凯维奇盛情赞扬“立陶宛的森林”,仿佛立陶宛的森林只属于贵族与他们的农奴时,身处立陶宛的犹太人却似乎成为了立陶宛森林的“局外人”,正如波兰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在谈及他的根时说道:“树有根,犹太人有腿。”。而事实并非如此,索普利佐夫庄园的少爷塔杜施曾说:“这儿,这儿,还有这儿,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犹太人。”扬介尔在劝说霍雷科夫家的管家盖尔瓦伊不要攻打索普利佐夫庄园时谈到了自己的犹太身份,他说:“他们犹太人都直接来自分界线上的小镇。”的确,从12世纪开始,很多犹太人就一直居住在立陶宛边境的乡村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乔安娜在其论文《波兰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犹太人和犹太教》中谈及了生活在“野蛮的荒野”里的犹太民族,称“他们的乡土气息一点不逊于科茨沃尔德的村民或者奥弗涅地区的农户”。立陶宛的犹太人并非是一般人观念中所谓的“城里人”,他们像“漆黑的密林深处住着的立陶宛农民”一样,“除了上天狂风怒号,地上野兽嘶鸣,/他们不懂得其他任何喧嚣的声音”,正如扬介尔所说:“我是一个犹太人,不懂得什么战争。”当“看到天上奇异的火光,听到轰的一声”时,犹太人也便同立陶宛的村民一起,像立陶宛的野牛一样,“生平第一次感到惊慌,/便立刻逃进更深的密林中去躲藏”了:没有根的犹太人不可思议地与立陶宛森林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立陶宛的“局内人”。
此外,密茨凯维奇自身也是一个集天主教、犹太人、改宗者以及弥赛亚主义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矛盾统一体,他“既非坚定的亲犹派,也并非始终如一的反犹派”。因此,他在《塔杜施先生》中体现了一个波兰爱国主义者对于犹太人的复杂情感,他塑造了扬介尔这一形象,一方面刻画出了波兰人对于犹太人的厌恶态度,另一方面也肯定了犹太人在波兰复兴时的積极作用以及他们的爱国热情。既是“局外人”又是“局内人”的犹太人,在密茨凯维奇笔下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对立性张力。在波兰人眼里,犹太人是“草木皆兵的怀疑论者”,如同密茨凯维奇在福音诗《波兰朝圣者》中称“他们高声畅谈,以此来蒙蔽自己的良心”。《塔杜施先生》中的扬介尔在霍雷科夫与索普利查家矛盾激化时,他选择退身而出,充当“局外人”,
“人群中乱哄哄,有的喝酒,有的祝伯爵/长命百岁,大家高呼:打索普利查去!/扬介尔跨上一匹无鞍马悄悄溜走。”
但另一方面,扬介尔却又对波兰充满着爱国热情。扬介尔:
“虽是犹太人,波兰语却发音纯真,/对于波兰的民间音乐他更钟情;/只要到涅曼河对岸作一次旅游,/他采集到的民歌民曲一定丰收,/有哈利奇的科沃梅卡和华沙的马祖卡……”
这些歌曲都曾在波兰的土地上流传,深邃而又热烈,雄浑、古老又充满着立陶宛森林的本能。
此外,扬介尔甚至到处传唱东布罗夫斯基的军歌《波兰还没有灭亡》。尤其是在长诗的结尾,扬介尔的这种爱国热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塔杜施的新娘佐霞要求扬介用赞巴罗在他们的婚礼上进行演奏,这个犹太人于是将这把古老的波兰扬琴把一场婚礼晚会变成了“一场爱国交流会”了。扬介尔:
“双颊上闪耀着奇异的红光,/炯炯有神的眼睛燃烧着青春之火”,“这老人抬头朝东布罗夫斯基一望,/忙遮住眼睛,泪水从指缝汨汨流淌:/‘将军,他说,‘我们立陶宛旱把你盼望,/像我们犹太人期待着弥赛亚一样……”
密茨凯维奇写道:
“这诚实的犹太老汉作为波兰人/忠贞不渝地热爱他的波兰祖国!/东布罗夫斯基伸手向他表示热忱,/扬介尔脱下帽子,在领袖手上亲吻。”
密茨凯维奇通过扬介尔的音乐寄寓他对于民族复兴的希望,同时,对于密茨凯维奇而言,被沙皇俄国放逐流浪的波兰人与遭受着背井离乡的犹太人一样,都经历着同样的苦痛,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和他们之间息息相关的命运在这场爱国音乐会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局外人”不再是“局外人”,在波兰复兴的道路上,犹太人便“成为古代传统的化身”,成为了不可分割的“局内人”。对立、冲突与矛盾在波兰传统音乐之中得到化解与融合,对立性张力从此统一于伟大的爱国热情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