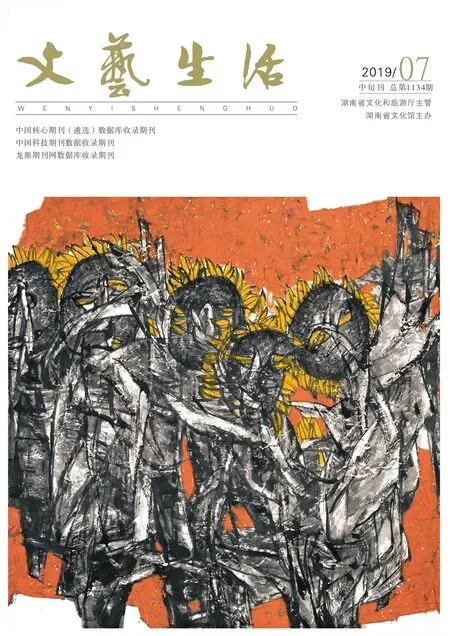李贺诗歌残落凄迷意象之探究
2019-04-08邵洪波
邵洪波
(台湾东海大学(Tunghai University),台湾 台中 40704)
一、日暮落花垂翅客:追问生命时间
《大堤曲》中李贺以横塘之春的降临作背景,暗陈女儿婉曲心事。从「桂香」到「莲风」,表示了江南之地经秋入春,而无严酷寒霜的冬天,后置的「北人」「襄阳」的意象,从符号意义上的「联想场」来看,就容易实现在词项集合中的迁移①,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远方飘零的场景。诗之前半部分的一切意象也都和满、清丽,洋溢着青春放达之气,颇有捉云弄月以修性爱洁的托谕。末句「今日菖蒲华,明朝枫树老」,彷佛青春和衰残的代换只在一夕之间,欢乐之景刚到来就忡忡于离别,是少年人对情郎不在身侧、理想不得实现的放大焦虑。
方瑜认为李贺所写乐府诗歌的恋情不能以自己的恋爱体验入诗,「眼光总是以『物』与『景』为主,如酒器、食物、服饰以及窗外的植物、天空、星辰等……表现出浓缩的实在感。」②事实上乐府诗的生命力并非就局限在爱情一环,应该注意到渗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意指,当然这些意指得以被攀跻摸索,也能部分归因于物景间的安排适切。诗人将现实生活中的零散经验片段组织起来,形成一种纯粹而完全经验的虚幻片段③。根据苏珊的观点,这段在诗歌中反映的「虚幻生活」可以是伟大的,也可以是淼小的。伟大如《奥德赛》,淼小则如一念之动、一景之察。但使其迥异于实际生活的突出标志则是事件的简化和觉察、评价的增加。李贺诗多以自我生平之气,发偃蹇浩歌,时而沾点悯默同情,同情之对象也是非类型化的,像这首诗中的大堤女儿,还有思乡心切的宫女(《宫娃歌》)、蓝田采玉的工人(《老夫采玉歌》)、被克削的越女(《感讽》)等,故其「文学的基本幻象」也是以个人生活为基底而出入伟大与淼小的。若要系统地考察李贺意象所具备的功能,还应与其生活背景相联结。],意象的铺排是个人生活体验的流动表现。因此李贺虽以第三者的立场叙述,透过他所用的「青云」「明月」等意象,诚可探知李贺秉挟少年锋芒和意气对时光的有意挽留和那份悠游亮丽自然、怜爱峻洁风神的境界,而「枫树」意象恰巧揭示了他唯恐蹑景不得、如堕汪茫的惶恐。
《感讽》组诗的第三首,李贺由世俗人境转向鬼魂灵域的越位思考,是其观览了人生的种种不公,长时间拷问生死谜题的产物。「鬼雨洒空草」,「南山」已被诗人定性为鬼魂游荡之所。时间流动在这首诗中是不明显的甚或是被消除的,「风吹令人老」,作为自然常态存在的空气就是衰老的加速器,「南山」成为李贺为追求生命时间所设想的一个时间停止流动的终点。他也曾设想过以人力克服流年,如《苦昼行》里「斩龙足、食龙肉」以求「朝不得回,夜不得伏」,又如《日出行》里「羿弯弓属矢」以求「中日足」而使晨昏再无流转的愿望。这些意象的使用都指向了其怀才不遇而投闲散置的命运遭遇,因而使其深受让时光虚耗有涯之生命的痛苦。④「低迷黄昏径,袅袅青栎道」和贾岛「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有出一辙,阴冷恐怖却唯以静默出之。日暮的意象被李贺反复使用,熟烂于心,并常常与残落的花瓣连词:「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春风不需媒」(《南园·其一》)。日暮带来的迫窒感在如此娇美、香艳,仍有劲迈长远的生长意志的花朵上表现得翰墨无馀,是时间的不允许造就了生命的脆薄不堪,前后的对比照映中包囿着无奈的哀感。「终南日色低平湾,神兮长在有无间。」(《神弦》)日暮更动摇了鬼神信仰,神鬼不过随女巫脸上表情的转变而嗔喜无常,从而在以人类情感为中心的叙述态势上揭发了生命只能随时间流逝奔向消亡的本质。
「月午树立影」,司职光明的已不再是太阳而是月亮,相较前首讨论的乐府诗纷丽烂漫的美好,这首诗已全然沉入凄迷幽暗的色调。李贺行笔至此已进入超现实化的叙写,在修辞与运用意象方面体现出「创造性的违反」的特异禀赋。阴冥世界竟然与人间是完全相反的,以月亮高挂中天为晓。意象选择的偶然保留着组合段上的句法形式的完备性,同时打破着「催化」(catalytic)作用⑤。语句组合轴上的自由性与偶然性有关,存在某种内容使句法形式趋于完备的或然性。如套服之内,由于衬衣、毛衣或背心的存在才是完备的。可诗歌创作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完备句式,而李贺运用意象善于把握这种偶然性从而提升语句在联想面(associational plan)上完备的或然率,增大语句在联想面上的宽度。],使词句的整体意境更加完满。如此看来,李贺将「月午」「白晓」和「影」这些看似反自然、无关联的意象盛入单个对句的容器中,借以对月午的氛围进行渲染,增强冥界时间和人界时间的对比差异,是颇有匠心的文本布置。
白发」「薄发」等标志着人体衰残的意象和以不断绝的「漏声」象征的时间永恒流动亦是值得研究的一组对比,「卫娘发薄不胜梳」然而「漏促水咽玉蟾蜍」(《浩歌》),「从君翠发芦花色」然而「漏声相将无断绝」(《官街鼓》)。李贺以意气扬发、青衫载酒的年纪,却不断延思至风烛暮景,甚至千年之后仙桃数度、神仙几葬,本不合常人情理。但通过对其笔下一些凋残、衰败、凄迷的意象,实实在在可以看出他追问时间的迫切。总结来说,李贺的衰老体验之形成大致有三个面向:
一是外物的代谢所引起其内心的感伤,如《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辞倂闰月》里随四季轮转多有「幽风寒绿」「坠红残萼」「衰蕙空园」等意象入调,末更结以「天官玉管灰剩飞」,年岁节候、朝代更替是任何外力都干预不了的,而李贺由人界想到天界,想到逍遥自得的神仙也抵不住时间,他对生命时间的追问所得到的是极致的无奈。
二是其理想的散灭,李贺在进仕途中饱受排挤,又因家世落没而对前途灰心丧志,更觉虚度光阴。
三是他虽年少,却看过了一番人世的起落变化,受尽了风霜冷眼,很难再返还到没有猜忌、鄙夷的童稚之心了。世俗对名讳的成见,官僚集团对其使才放纵性格的本能抗拒,使他遭遇过的都几乎是类似的困境,这样李贺便以为自己已窥尽命运安排的堂奥了,觉得人生不过如此,时间因「被安排」而失去了意义。
二、秋坟冷雨鲍家诗:出入俗世困境
李贺每在诗中不自觉地将个人的失意托诸他物,或者溯回百年取得人物典故,这是怨情的自然引申。钱锺书先生在其演讲文《诗可以怨》中罗列了一些西方作家学者关于诗是愁苦的溢泄的言论:「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最甜美的诗歌是诉说那些最忧伤的思想的」。⑥这些言论用于李贺身上往往合钿符节,因为他真实地觉察到身体上的衰弱不济、功名场上的无法回旋驭驾和国势上藩镇威吓、佞信窃权的动荡将倾,这种生命感受和体验真实而具体,他由个体生命、王朝兴衰以及一些身世同样不由自主、无聊如苇絮的普通人物等多个面向上感到了死亡的破坏力,这些都直观地投射到李贺诗歌的意象中。然则李贺并非堕落到炼狱底端的绝望,反而滋生出一股持剑学武、洒溅热血的豪情来,或者远离俗务以宽慰己心,都是其欲解脱俗世困境的体现。长吉「在冷落和寂静的世界中检敛生命,而另一方面又怀着中兴的信心」,「希望可以重返盛世的心态使中唐文人并不完全绝望」。⑦《高轩过》作于早年韩愈、皇甫湜二公来访时,李贺形容自身处境时用到了「秋蓬」「死草」等凋零的意象,形容自身则为「垂翅客」。但此时他是对未来抱有莫大期待的,二公的到来正如一阵「华风」,能使自己绝处逢生,声名鼎沸,而一举跃上台阁。这里凋零的意象不过用为其希望的陪衬,实现一种超拔昂扬的志意。
且看李贺进士之路受阻之初抒悲的《铜驼悲》和《开愁歌》。《铜驼悲》写道,落魄失意后,诗人欲寻花,我们实在不必考虑「寻花」这一动作的真实性,在这里,艺术作为「生活幻象」的特点明白无误。桃花、春意、马客和与之中心意指相左的铜驼、古人、北山、盘烛等词汇单元(Lexie)虽然属于同一语言结构(Architecture)之内,却均有更为深层的译解⑧。铜驼在洛阳街夹衢相望,「铜驼陌上集少年」,本应是繁盛喧闹的喜庆之景,因作者个人的失意却悲伤起来,而且那阵悲伤的力量简直撼动古今,「驼悲千万春」,由此可见,李贺的愁是延伸出去的,突破时间和物体限制的,铜驼原本最是无情之物,在诗人笔下却唯独能解春愁,能洞穿生命劳碌的真相。意象作为情感的荷载物,具有疏通脉络、敷润肌理的功用⑨:桥南虽多游客,北山处处古冢,这些生与死,热闹与荒冷的对立在后句「千年」的时间长度权限上,更加能说明繁盛事物的瞬时性,在风中鼓荡的「盘烛」正好拍板应响,解构了追求功名的意义。末句诗人赋予意象以表情,厌笑而哭,是因为预见了乐景之后的虚无。正是因为他在功名上受到的打击,他才得以看穿所谓的「一朝美酒」「一朝欢笑」「一朝春色」,终于要在时间的洪流中淘蚀膏脂而化为枯骨的。
与之相对的,《开愁歌》的描景和心境是直接贴合的,秋风、干草、晚寒、枯兰都是直接传输困滞潦倒的处境和愤懑不舒的心境。值得讨论的是云翳虬结、满布天空的白昼之景的意象,呈现出人世的白日,和南山上的鬼神之界的白日意象是不相同的。人界的无穷止的阴暗白日更表现为一种无所事事、耗费时光、功溃力怠的精神状态,还没有彻底切断对红尘俗名的那份眷恋。因此有诗尾的发谕,「主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灰」,撇下俗物骚扰,调养身心,虽然未必已经到达澄然无虑的境界,但这确实是作者在他人帮助下的一次自我解困,实现了诗意上的转折。
外界的险恶现实被李贺以奇伟的想象描绘为一种原始性生存迫害的威胁,如《公无出门》点化古诗「公无渡河」的母题,其中「佩兰客」的意象,作者虽未直接突出其残落凄迷的特质,但通过构建外界世界恐怖的「雪霜」「熊虺」「狻猊」「毒虬」「猰貐」等勐禽毒兽意象,将「佩兰客」作为单零受欺的对象,自然地表露出他凄凉、迷惘的处境。这首诗中的意象展现出丰富的「他性」(otherness)⑩。脱离现实的「他性」寓示着艺术的本质。实际之物在诗中以意象的方式起作用,带有纯想象的性质。意象作为象征,是抽象之物,即意义的荷载物。]和奇异性,非真实的色彩提供了纯粹的外观,反而引发读者切入深度思考,寻找拥有高洁人格的佩兰客阻塞道路的缘由。顺着诗意往下阅读,发现李贺认为这样的命运安排是上天的意志,是天在保护佩兰客免遭「衔啮」,所以收去他们的生命,从而提供了李贺对生命穷达走向的独特破译方式。
除此之外,《感春》里的「北郭骚」意象在日暖花香的诗境里,更加显得落魄穷苦,「江干幼客」(李贺之弟)在李贺想象感知、抽离现实秩序的「荒沟古水」、「蛴螬拱柳」等凄凉荒残的意象正衬下,更加表现得在经济困难的压迫下自己所亲爱的胞弟悲舟难返、歧路嶙峋的处境,都收到和佩兰客同样的效果。依照性质,通过意象群体和单个意象的划分对立,显示李贺对文士衄挫当代之原因的清醒认识和自我宽慰。
最能表现李贺结痕盈愁的生存状态的当属《秋来》一首。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
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
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
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此诗交融外物、宇宙时空,由意象钩串出一封流动细密的肌理(texture)。肌理一方面指局部语词的相互影响⑪,像「寒素」与「冷雨」,「桐风」与「衰灯」共同运造了一个凄冷衰飒的境界,而通过词义表层意义的深层联想,探寻符号背后的象征义,就可以把握到此境界非自然外物的物质境界,,更是诗稿难投、高官挤压,「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立言建功之路受阻的人文世界以及忧愤不平、与千古寒士发不平之鸣的心灵境界。一方面肌理也可以产生结构,像今夜的思牵肠直与千年的恨血埋土,营构了一个时间场域,正如《文心凋龙·神思》言:「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感发由个人而及诗鬼群体,情感力量一下子增强了;像由衰灯之前的眼前方寸之地到想象中的秋夜坟场的广袤之地,空间场域由狭及广,「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哀怨的质量一下子变得沉重了,千古失路之悲由这些意象交织组合的肌理铺张得寸微可感、兴悟淋漓。
前文述及,李贺并非全然绝望,由一些零星诗篇的意象中可以看出他对健全的生命仍有着热烈的向往。如〈野歌〉中「北风」「寒风」都极为萧条冷落,而诗人只身着「麻衣黑肥」,即肮脏简陋的粗麻衣裳,且诗中又一次出现了象征希望灭绝的「日晚」意象。可是观察诗人的情感态度,虽然对「枯荣不等」的天意安排嗔怒有加,但心志不穷,日暮时分纵酒放歌标志心情的豁朗,弯弓射落鸿雁标志能力的卓越。「春柳」的意象与「寒风」的意象对举,形成一个衬垫和转折,这里凄迷残落的意象充居次要,有助推光明鲜活的意象突出的作用,抑且表现出时间的推进。又《平城下》「日晚在城上,依稀望城下」,时间点也设置在日暮,而作者所见也尽是「枯蓬」「瘦马」等冷色调的景象,结末却发为豪迈之言:「唯愁裹尸归,不惜倒戈死」,申明宁为玉碎,报效国家的志向。艺术作品由诉诸感觉的因素(包括各种意象)组成,但其间必定有关联和组织,使其置于欣赏的智力范围内。⑫艺术作品虽由诉诸感觉的因素组成,但不是所有诉诸感觉的材料都能组成艺术作品。只有那些在完美的连续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材料,才是可组成艺术作品的材料。]李贺运用意象很好地把握了这点,或先将凄凉冷瑟的感觉烘染到极致,顺势发为悲慨,升华情感,由小我中解放,合沓紧密、顺接自然,或逆势倒转,以愿景来打破之前沉郁之气格,展现追求,由怨愤中走出,新巧别致、万象更新。诗歌的整体不会显得碎散零乱,意象之间相互绾合、吸引,牢固根基在脉络和肌理上,使诗气一贯。
李贺的时间观中有这样一不易发现的微妙认识:虽然时间永恒流动,人的寿命不能被延长,但同时生命时间就是这样轮替的,黑暗过后光明与温暖总会到来的。诡妙的是春柳生成后,「条条看即烟蒙蒙」,仍然趋向凄迷、溷沌。李贺的潜意识中洞穿了整个国情社会的本质,所以他抱有的希望仍是朦胧的,始终有一限象在阻碍他,终于不能旷达,这是李贺自身的性格的限制,也是整个焦灼、分裂的社会背景无形中对诗人的影响。
三、夜月愁烟几世欢:关照红尘他者
李贺笔下的他者大致有帝王、贵族、舞姬、宫女、守边戍卒几种类型。
上位者的荒侈无道、燕乐升平,耽溺长生之术,却抵不住朝代的兴废和人事的代谢,李贺看清了人为堕落的恶果,同时在这些事例的影响下加深了对生命凋零的恐惧和对国事的忧患。李贺以一篇〈昆仑使者〉鉴古知今,以汉武帝旧事暗刺宪宗服食求仙的虚妄。「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武帝曾向西王母求讨长生不老之药,可青鸟使者再也没有消息,武帝死后葬于茂陵,而陵冢旁的树木间弥漫着青烟彷佛至今仍带着愁色,而陵墓两旁的石麒麟和石虬龙在时间的侵蚀下也已开裂,只有高悬中天的明月孤独地照着茂陵。这些意象都有统一的风格,虽烟树、麒麟、虬龙一一如毕现目前,但李贺自不必亲至茂陵,当场写录,而是借助想象的法则构筑起「虚幻经验」,既已有宪宗荒诞不经之举,那些残破、荒凉特质的意象背后承载的意义自然完善了。
李贺诗中「墓地」意象特多,盖因其积郁已久,加之沉疴难起又眼见中唐气象不稳,褪去盛唐富丽之气,而心有耿耿焉,常触及残落、死亡之经验造成。其以「墓地」意象和历史及现世相联系,便有发人深省之功用。
如《王浚墓下作》全篇铺陈名门大将王浚墓地的衰败,取景时间设置在秋季,坟墓以马鬣般薄扁之形状封土,枯草附上霜气,藜藿荆杞绕地而生,菊花上沾满了露水,夜风不止。最具新鲜深细感觉的是「松柏愁香涩」,由视觉体验之外别开蹊径而刻之以嗅觉,嗅觉描写中又融入了通感手法,以味觉之涩感体验与之。意象运用通感手法,是一种「体验的深度」的展现,表明作者的感情充沛细密。五官虽有「异务」,仍能「借官」而感,如同为奇险派的诗人孟郊有「商气洗声瘦」句,就把体态上的瘦弱和声音的短促虚弱相结合。⑬
松柏在那种枯寂、苍凉的秋风里传送出树皮、枝叶、脂液的冲犯气味,而在观者体验却引发了一种愁苦哀思,只有在极为幽静的情境下观者才能闻到细腻的松香,也只有在周围景物协调地流露出伤感时,才能使这气味里增添愁苦。「南原几夜风」,秋风和松柏之味形成了因果照映之关系,在诗尾留下了回味咀嚼品读的空间。全诗那些荒凉的意象也都浑然一体,以王浚墓的衰败反映辉煌功业终成尘土,永垂不朽的只有时间本身而已,同时影射当朝良将埋没,削藩事业不振的尴尬局面。
「墓地」意象同时被借以书写女性,如著名的歌咏钱塘名妓苏小小的《苏小小墓》。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将女性肉身和装饰隐匿在自然风景下,草茵松盖、风裳水佩,很凝练地钩织出一个人迹杳淼的空间。烛光本应是散发光热的,李贺却刻意将其写成与鬼火类同的凄冷景观,喻示着苏小小的追求和思念是有巨大热情的,奈何早夭,只能寄托愁绪于幽兰的露水。苏小小的这种虚无处境和李贺的身世是极为相似的,墓地的冷落残破、寂静黯淡无不在象征着李贺的内心世界,他内心所燃起的烛火也已化为幽冷的鬼火,理想始终为长风夹雨、流言谤毁所打击着。周遭是全无回应的「幻见空间」,而这亦是苏小小(李贺本人)为保持欲望和追求的迂回再生,避免焦虑和空虚感的侵袭。⑭「当欲望消失,焦虑反被启动,唯有欲望以迂回循环的方式再去制造愿望,欲望才会被实现。」文中说明苏小小在空无一物、暧昧不明的「幻见空间」中降低焦虑感,延伸自己的欲望。]但作为作者的李贺对苏小小抱以无限同情,更揭发了幽冥世界本质上与人烟尘寰的断绝,无论是对苏小小来说执守的情,还是对作者本人来说的功名,都与这一空间相隔绝。在这篇名作中,意象联络了书写对象和作者本人的心理形态,怜悯他者的同时也对自己的身世产生无限唏嘘和悲慨。
贵族及其宾客的狎游歌舞为中唐的百姓带来了巨额的税务,直接导致了国库的空虚。李贺关注这一群体时仍旧采用流动的时间观念,今日车水马龙,明日也会变得杂草深苔,今日醉语欢歌、花好月圆,待到酒醒人散也会平添无限的寂寞。中唐一段时期内京城贵族兴起了赏玩牡丹花的风气,以致日日宴饮游乐,李贺有感于此,遂作了《牡丹种曲》。迎着拂晓的晨光绽放的花苞,到晚就披散萎缩了,曾经妍媸招宠的歌女经年而衰而亡,失去了贵公王孙的欢宠。「归霞帔拖罗帐昏」,再一次的日暮场景描写,李贺不直接点明时间,而用状似披肩的归霞和昏暗的花帐意象来暗示,紧接一句「嫣红落粉罢承恩」,表达得深衷婉约。「檀郎谢女眠何处,楼台月明燕夜语」。宴饮过后,年轻男女都不见了,只留下清冷的月光和燕子的啼鸣。
李贺诗歌还关照到深宫女子要求解放的心声。典型的如〈宫娃歌〉。李贺善用意象就在于他能抓住事物特征而表现张力,像诗篇起始的「蜡光」「吹香」「纱帐」都是生活温暖、物质条件优越的体现;进而照进宫女的内心世界,形成诗意的跌宕:「漏板」是时间的流动,象征宫女残耗的青春;「罘罳」是捕鸟之网,用在此地显然表示拘禁,而又作「寒」的宾语和进入空间,和昏沉的殿影对接,使诗境涨满了凄迷的情绪;「彩鸾帘额着霜痕」,李贺笔锋在句尾稍一扭转,即打破了之前花房香暖的焕丽虚像,表面上看来缤纷华丽的事物暴露出它凄寒的实质;「屈膝」「铜铺」的金属材质,决定了它们的沉重和冰冷,给人以锁禁关押的联想,「啼蛄吊月」则提供了深度的安静。之后,「天河落处长洲路」,将视角拉入非现实,充分发挥诗歌艺术「虚幻之现实经验」的特征,在这里,家乡的现实距离和心理距离同样遥远得无法碰触,写出了宫女渴盼踏上归途的焦躁心情,替她们发出了对自由的呼声。
此外,李贺的古风体诗还关注到心上人远游在外,遇合无期,孤闭深馆之女子。《有所思》中的妇人面对心上人的不断远行,抚琴不寐,穿丝织素,横亘在游人与思妇之间的是没有止境的迢递江山。此诗意象有许多来自直接的感触,「泪眼看灯乍明灭」,灯花被模煳的泪眼剪碎。「夜残高碧横长河,河上无梁空白波」,夜色将了未了的时分,妇人还未入睡或浅眠惊醒,眺望远处的江河,青碧色的天空悬浮在长河上,河面没有桥梁,只见白浪滚滚,正可以说是「相思无终极,相望不会面」。这种间阻的困境「反映出士人生存之困境,更体现出由此困境中而伸展出的精神世界之上升性」,是一种「理想生命苦闷之象征」⑮。这虽然是对作者作诗意图的揣摩和诠释,但我们应该进一步以活力和感官能力去直接经验体会诗中的意象,避免过度诠释造成的「知识肥大」弊端。⑯「诠释并不是一种绝对价值,亦非处于不受时间影响的能力领域中的一种心智姿态。」意即诠释会随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类意识变动而不断修订,因此直接以感官贴近意象能在不损失意象潜能的条件下,获致最纯粹显现的情感。]「鸦鸦向晓鸣森木,风过池塘响丛玉」,环绕四周的不过是些雅雀的叫声和风吹过檐下铁马的铃声,足可见居所的荒僻,这里也是直接的体会,没有曲笔。「西风未起悲龙梭」,妇人的情绪不是被外物调动起来的,而是内心涌出的幽居孤寂的哀伤,那全是因为「君书远游蜀」而自己「孤馆锁深窗」。李贺用代言的形式建构起男性伦理向度下的女性空间,或者是体现自我追求的意志,或者是怜悯古今天地间离别独居的他者在心灵层面上受到的摧残,但其中凄迷残落的意象却始终带有其自身的新鲜度和情感力量,带有反过度诠释而编织诗歌纯粹的肌底的机能。
四、结语
从李贺诗歌带有凄凉残落特征的意象所传达的符号象征或潜在感发中,我们固然可以发现李贺对于生命时间不可留驻而进身之途受阻的苦闷心理,却也可以看到他对于暗弱他者和衰颓国运的关照,他逐求个体在虚无欲望、权力压制下、时空限制下的解放,而执着于对永恒的追求,敏锐的生命感官使他碰触到历史更替的真相、求仙炼丹的虚妄和世态的炎凉冷暖,以至于少年老成。
然而李贺的生命观并不恒定,诗词意象间往往缺乏清晰的脉络和逻辑,但却妙绝蹊径地形成奇险特异、迷幻盘折的气象,或将意象相互对举以突出主体,或将意象先后安排照映,逆接倒衔以错综文意,他善于在深度体验的基础上调遣虚幻经验,设想架构神鬼所居的他国异域,以强化「应有」和实际「阙失」间的平衡。个体性的失意背后,李贺拓展寄意于群体性的沉溺和伤痕,他笔下关注的对象广博,从皇帝贵族到劳工歌女,以他者之憾恨愁怨呼应自身境遇,使用特殊意象搭建反映心灵诉求的桥梁,以意象串连支撑起诗歌的肌理,却并非预先制定的写作策略,而是在自然无意识的条件下生成。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凄迷残落的意象却反射出李贺的少年意气和热情仍然埋藏在心灵的深层,他存有对生命美好事物的热爱和对生命价值的看重。他「不惜倒戈死」,经历人世排挤和冷落的意志消磨后,一腔热血却并未冷却凝固,而渴望建功边关;他锺爱能薰洗尘虑的山川风光,「鲈鱼千头酒百斛,酒中倒卧南山绿」,这样欢畅的句子在其诗歌中虽属少见,但正可为其壮志未消的参证,在其他诗歌中,这样的情绪往往是在那些灰暗凄凉意象的反衬张力下体现出来的。
注释:
①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3.
②方瑜.李贺诗歌的造境,唐诗论文选集[M].台北:长安出版社,1985:419.
③苏珊·桑塔格.情感与形式[M].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242.
④杨文雄.李贺诗研究[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238.
⑤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2.
⑥钱锺书.七缀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29.
⑦陈燕妮.论李贺的生命意识和诗歌意象[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21.
⑧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2.
⑨苏珊·桑塔格.情感与形式[M].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267.
⑩苏珊·桑塔格.情感与形式[M].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56,.
⑪郑毓瑜.意象与肌理——由1930年汉语诗明白/晦涩的论争谈起[J].政大中文学报,2016:128.
⑫苏珊·桑塔格.情感与形式[M].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67.
⑬钱锺书.七缀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71-72.
⑭陈思嘉.李贺诗歌的幻见与穿越幻见研究[D].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11:202-204.
⑮陈燕妮.论李贺的生命意识和诗歌意象[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34.
⑯苏珊·桑塔格.反诠释[M].黄茗芬(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