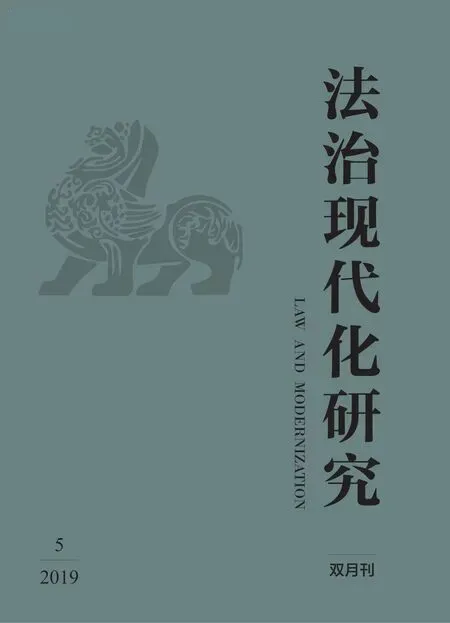论事后抢劫罪
2019-03-28桥爪隆王昭武
桥爪隆 著 王昭武 译
一、引 言
事后抢劫罪(日本《刑法》第238条)并非本来意义上的抢劫罪(日本《刑法》第236条),(1)日本《刑法》第236条【抢劫罪】:采取暴力或者胁迫手段,强取他人财物的,是抢劫罪,处5年以上有期惩役(第1款)。以前款方法,取得非法的财产性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与前款同(第2款)。——译者注但由于其与抢劫罪之间存在同质性、类似性,因而被视为应该作为抢劫罪来处理的犯罪类型,与昏醉抢劫罪(日本《刑法》第239条)一同被称为准抢劫罪。不过,事后抢劫罪是以出于一定目的而实施的暴力、胁迫行为作为处罚对象,因而不可否认,事后抢劫罪不具备“采取暴力、胁迫而夺取财物”这种抢劫罪的本质性要素。为此,通过重视何种视角而找出事后抢劫罪与抢劫罪之间具有同质性、类似性,这就属于理论上的重要问题。
本文想先就事后抢劫罪的结构进行探讨,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对解释论上的问题点也做些研究。
二、事后抢劫罪的结构
(一)讨论的前提
日本《刑法》第238条规定,“盗窃犯(2)日文原文使用的是“窃盗”。对此,西田典之教授认为,“本条中的‘窃盗’这一用语,就是指‘盗窃犯’(盗窃罪的罪犯)。”(参见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6版),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以下)。——译者注窃取财物之后为了防止财物被追回,或者为了逃避逮捕,或者为了隐灭罪迹,而实施暴力或者胁迫的,以抢劫论”。对于事后抢劫罪的解释,理所当然应该以对该条用语的解释作为出发点。事实上,在既往有关事后抢劫罪的讨论中,由于考虑到与抢劫罪之间的同质性、类似性而过于强调了某种视角,因而出现了与该条用语的关系上不太自然的解释,这种现象也并非罕见。但是,那种做法应该属于本末倒置吧?本文认为,我们终究还是要在意识到与第238条的用语解释之间的整合性的同时,尽力去揭示事后抢劫罪的结构。正是出于这种问题意识,作为讨论的前提,这里首先想就能够从第238条的用语中理所当然地推导出来的解释论上的结论,同时也对通说、判断的观点做些归纳。
1. 事后抢劫罪的主体
在现行法律中,正如从条文中逗号的位置也可看到的那样,“窃取财物”这一表述被包含在作为事后抢劫罪的目的要件之一的“窃取财物之后为了防止财物被追回”之中,因而“窃取财物”并非整个事后抢劫罪的成立要件。(3)关于这一点,参见山口厚:《問題探求刑法各論》,有斐閣1999年版,第137页。而且,如果是“为了逃避逮捕,或者为了隐灭罪迹”而实施的暴力、胁迫,盗窃的未遂犯也是完全有可能实施这种行为的。基于这种理解,通说认为,作为本罪主体的“盗窃犯”还包括盗窃的未遂犯。(4)不过,如后所述(既遂与未遂的区别),即便盗窃的未遂犯出于所规定的目的实施了暴力、胁迫,也不过是成立事后抢劫罪未遂。因此,即便说盗窃的未遂犯也是本罪的主体,但那不过是意味着,仅仅有可能相当于未遂犯的构成要件。相反,也有观点试图将事后抢劫罪限于已经窃取财物的盗窃犯为了防止财物被追回而实施暴力、胁迫的情形,从而主张应将本罪中的“盗窃犯”限于盗窃的既遂犯。(5)持这种观点者,参见松宫孝明:《刑法各論講義》(第4版),成文堂2016年版,第233页;金澤真理:《財物奪取後の暴行·脅迫》,载《阿部純二先生古稀祝賀·刑事法学の現代的課題》,第一法規2004年版,第307页。另外,西田典之教授亦承认也有这样解释的余地,参见西田典之:《刑法各論》(第6版),弘文堂2012年版,第182页。但是,作为对现行法律的解释,这种观点多少有些勉强。
2. 既遂与未遂的区别
由于事后抢劫罪也处罚未遂犯(参见日本《刑法》第243条),因而需要解决事后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别问题。首先,就暴力、胁迫而言,如果开始实施行为就立即达到既遂,因而几乎无法设想未遂阶段;其次,原本就没有处罚暴行罪、胁迫罪的未遂的规定。有鉴于此,就不应该以暴力、胁迫行为作为区别标准,而应该以盗窃行为的既遂或者未遂作为事后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别标准(最判昭和24·7·9刑集3卷8号1188页)。(6)相反,松宫孝明教授以应将盗窃的未遂犯排除在本罪主体之外这种理解为前提,对于(1)暴力、胁迫未能达到压制反抗程度的情形,以及(2)误以为盗窃归于未遂的情形,试图认定成立本罪的未遂(参见前引⑤,松宫孝明书,第238页)。但是,对此观点的疑问在于,按照论者的前提,原本来说,(既然盗窃罪的未遂犯被排除在事后抢劫罪的主体之外)第(2)种情形难道不应该是缺少事后抢劫罪的故意吗?(7)松宫孝明教授认为,“学界也有观点主张,达到了防止财物被追回或者逃避逮捕等本罪所规定的目的的,构成本罪既遂,未达到本罪目的的,则为未遂。但是,以‘实施(了)暴力或胁迫的’这一法条的用语为根据,这种解释未能得到支持。”“不过,从‘以抢劫论’这一法律效果来看,本罪所谓暴力、胁迫,需要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但无需实际压制了被害人反抗。因此,在已经开始实施的暴力、胁迫尚未达到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时,存在认定为本罪未遂之余地。在实施暴力、胁迫的行为人因为某种理由出现错误而使得盗窃归于未遂的,应认定为本罪的未遂”(松宫孝明:《刑法各论讲义》(第4版),王昭武、张小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页)。——译者注学界也有观点基于重视与抢劫罪的同质性的立场而主张,应该根据行为人最终是否确保了财物来区分既遂与未遂。(8)参见曽根威彦:《刑法各論》(第5版),弘文堂2012年版,第134页。作为相同旨趣的观点,参见稲垣悠一:《事後強盗罪の基本構造と共犯関係》,载《専修法研論集》第43号(2008年),第61页。另外,西田典之教授也认可这种解释的妥当性(参见前引⑤,西田典之书,第181页)。然而,日本《刑法》第238条针对的问题仅仅是,盗窃犯出于法定目的实施了暴力、胁迫,而不是针对是否得以防止财物被追回这一问题,因此,作为对现行法律的解释来说,难以采取这种观点。
3. 事后抢劫罪的“实行的着手”
这样,事后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是以盗窃行为的既遂或未遂为标准来判断的,不过,一般认为,要成立事后抢劫的未遂,以实施暴力、胁迫行为为必要。具体来说,仅限于盗窃罪的未遂犯人出于法定目的而实施了暴力、胁迫的场合,才成立事后抢劫罪未遂。即便在实施盗窃行为之时,已经存在出于事后抢劫的法定目的而进一步实施暴力、胁迫的意图,但由于不能认定存在发展至暴力、胁迫的具体危险性,因而在该阶段还难以认定成立事后抢劫罪的未遂。(9)有关事后抢劫罪的实行的着手时点的详细研究,参见原口伸夫:《事後強盗罪の実行行為と実行の着手時期》,载《JCCD》第100号(2007年),第150页以下。
(二)作为准抢劫罪的事后抢劫罪
1. 概述
基于上述前提,下面想进一步探讨事后抢劫罪的本质。正如法条所明文规定的那样,事后抢劫罪是“以抢劫论”,与抢劫罪做相同的处罚,因而还需要具备财产犯罪的性质。并且,要认定事后抢劫罪具有财产犯罪的性质,就绝对需要将盗窃行为一同作为该罪之处罚对象予以评价。(10)参见十河太朗:《事後強盗罪の本質》,载《同志社法学》第62卷第6号(2011年),第466页。不过,通过将盗窃行为一同作为该罪之处罚对象予以评价,即便能够确保本罪具有财产犯罪的性质,但仅凭这一点尚不足以说明本罪完全具有“以抢劫论”的实质。抢劫罪的结构是“暴力/胁迫→夺取财物”,事后抢劫罪的结构是“夺取财物→暴力/胁迫”,两者之间的不同似乎只是改变了“夺取财物”与“暴力/胁迫”之间的顺序,因而也许看上去,事后抢劫罪实质上与抢劫罪并无不同。但是,抢劫罪应该被理解为,是通过暴力或者胁迫而从反抗受到压制的被害人处强行夺取财物的犯罪,在限制被害人的行动自由或者意思决定自由的同时,又侵害了财产性利益这一点上,可以说,能够认定抢劫罪所具有的(超过了将其作为暴行罪、胁迫罪与盗窃罪的数罪并罚这种法律评价的)独立的法益侵害性。然而,事后抢劫罪改变了“夺取财物”与“暴力、胁迫”的顺序,就不能认定存在这种独立的法益侵害性。也就是说,仅凭将盗窃行为与(时间上、地点上接近的)暴力、胁迫行为一同作为处罚对象这一事实,还不足以提供能够被“以抢劫论”的实质性根据。(11)参见佐伯仁志:《事後強盗罪に関する覚書》,载《川端博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下)》,成文堂2014年版,第189页。
2. 与抢劫罪的同质性
正是出于这种问题意识,学界为了能将事后抢劫罪定位于抢劫罪的类型之一,提出了下述几种问题的解决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将事后抢劫罪理解为第2款抢劫罪的特别规定。事后抢劫罪的典型情形是,夺取了财物(窃得财物)的盗窃犯为了防止财物被追回,对被害人等实施了暴力、胁迫,这种行为具有侵犯被害人等针对财物的返还请求权的一面。这样,有力的观点倡导,在着眼于针对返还请求权的强行夺取这一视角,认定事后抢劫罪具有作为第2款抢劫罪的实质这一点上,来探寻事后抢劫罪的本质。(12)参见佐伯仁志:《事後強盗罪の共犯》,载《研修》第632号(2001年),第6页;島田聡一郎:《事後強盗罪の共犯》,载《現代刑事法》第44号(2002年),第18页;等等。的确,在典型的事后抢劫罪的案件中,是完全有可能采取“针对返还请求权的强行夺取”这种结构的,因而即便没有第238条有关事后抢劫罪的规定,也可将这种情形作为第2款抢劫罪的类型之一,按照抢劫罪予以处罚。但是,事后抢劫罪与第2款抢劫罪之间仍然存在以下几点巨大差异:(1)如果将事后抢劫罪定位于第2款抢劫的类似犯罪,那么,理应仅限于可以被称为已经逃避了被害人等的返还请求的场合,才能达到犯罪既遂,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盗窃犯(既遂犯)出于法定目的实施了暴力、胁迫的场合,即便财物被追回,也应成立事后抢劫罪既遂。(2)如后所述,要成立事后抢劫罪,以在盗窃的机会的持续过程中实施了暴力、胁迫为必要,如果将事后抢劫罪理解为第2款抢劫罪的类型之一,理应根本无法推导出这种时间上的限制。(13)参见山口厚:《事後強盗罪再考》,载《研修》第660号(2003年),第7页以下。(3)对于那些盗窃罪的未遂犯出于“为了逃避逮捕,或者为了隐灭罪迹”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的案件,还存在基本上无法认定具有第2款抢劫罪的实质这一问题。当然,该观点的论者也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对此作出了不同于为了防止财物被追回的类型的解释:对于第(3)点所谓事后抢劫,确实不能认定存在与抢劫罪相类似的性质,然而,毋宁说,鉴于盗窃犯在逃走之际往往会实施暴力、胁迫这种实际情况,这种情形属于从人身保护的角度而加重(通常的暴行罪、胁迫罪)责任的犯罪类型。(14)参见前引,佐伯仁志文,第7页以下。尽管这种解释的方向性是正确的,但将出于防止财物被追回的目的的情形与出于其他目的的情形作为完全不同的犯罪类型来把握,在这一点上,还存在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作为认定事后抢劫罪具有抢劫罪类似性的根据,第二种路径重视的是,与第1款抢劫罪之间的连续性。盗窃犯(既遂犯)在窃得财物之后逃走的场合,财物的占有已经被转移至盗窃犯,盗窃已经达到既遂,但是,盗窃犯的占有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况还不能被评价为,已经确保了财物。(15)这样就有可能进行下面这种解释:由于犯罪人的占有的归属尚不牢固,在这种场合下,针对财物的非法侵害也仍然在持续,被害人可以通过正当防卫来反抗(同样旨趣的判例,参见高松高判平成12·10·19判时1745号159页)。参见今井猛嘉等:《刑法総論》(第2版),有斐閣2012年版,第200页(橋爪隆执笔)。并且,在该阶段针对被害人等实施的暴力、胁迫行为,在通过暴力、胁迫确保对财物的占有这一意义上,存在认定其具有与第1款抢劫罪相类似的一面的余地。(16)参见林幹人:《判例刑法》,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363页。佐伯仁志教授也承认,对于盗窃犯为了防止财物被追回而实施的暴力、胁迫,作为指向确保对财物的占有的行为,与第1款抢劫罪之间存在类似性(参见前引,佐伯仁志文,第205页)。这样,在重视第1款抢劫罪与事后抢劫罪之间的连续性的场合,取得了财物的占有的犯罪人为了确保对财物的占有而对被害人实施的暴力、胁迫,究竟是构成第1款抢劫罪还是构成事后抢劫罪呢?这一点首先就成为问题。对于为了确保对所夺取的财物的占有而实施暴力、胁迫的场合,判例(最判昭和24·2·15刑集3卷2号164页)认定成立第1款抢劫罪。这种结论要得以正当化,就应该以在实施暴力、胁迫的阶段,被害人尚未完全丧失占有为前提。按照这种理解,对于逃跑过程中的暴力、胁迫,安廣文夫调查官就认为,第1款抢劫罪的法律构成与事后抢劫罪的法律构成存在相互重叠的部分(参见安廣文夫:《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61年度),法曹会1989年版,第299页)。按照这种理解(不同于第2款抢劫罪类似说),就很容易解释“盗窃机会的持续过程中”这一事后抢劫罪的要件。(尽管有点重复了)不过,就盗窃罪未遂犯实施的暴力、胁迫而言,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妥的。(17)有观点认为,对于盗窃罪的未遂犯的暴力、胁迫,也能由此观念到财物占有的危殆化。参见増田隆:《事後強盗罪の基本構造とその関与問題》,载《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法研論集》第114号(2005年),第175页。进一步而言,按照这种理解,如果未能成功确保财物,财物最后被追回,就不能认定成立事后抢劫罪既遂,但如前所述,我们也无法采取这种结论。
3. 探讨
无法否认,事后抢劫罪(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将不能被评价为通常的抢劫罪的行为类型包含在处罚对象之中,既然如此,要认定事后抢劫罪与第1款抢劫罪、第2款抢劫罪之间存在完全的同质性,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毋宁说,我们应该从下面这一点上来寻求将其作为准抢劫罪予以处罚的根据:与抢劫罪一样,同时具有作为财产犯罪的性质与作为人身犯罪的性质,两者的法益侵害性密切相关。
首先是盗窃犯出于防止财物被追回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的场合(以下简称为“第一种类型”)。在该场合下,存在先行的盗窃行为,而且,对于暴力、胁迫行为,也有将其评价为,为了强取返还请求权或者为了确保财物而实施的暴力、胁迫的余地。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就足以为本罪的财产犯性质提供根据。(18)通过一并考虑到先行的是盗窃既遂行为,即便是被被害人追回了财物的场合,也能够说明,作为财产犯罪已经达到了既遂。并且,盗窃犯为了确保财物而在盗窃现场等地实施暴力、胁迫等加害行为,这也是刑事法学上的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为了防止已经窃取的财物被追回,行为人进一步实施严重的暴力、胁迫行为的危险性也很大,因此,也能认定存在针对被害人的生命、身体的严重的危险性。(19)对于抢劫罪中的暴力、胁迫,嶋矢教授也要求具有针对生命、身体的严重危险性,可以说,嶋矢教授的这种理解是从针对生命、身体的危险性的角度,统一地把握抢劫罪与事后抢劫罪。参见嶋矢貴之:《強盗罪と恐喝罪の区別》,载《山口厚先生献呈論文集》,成文堂2014年版,第340页。这样,对于第一种类型,完全能认定存在财产犯罪的性质与人身犯罪的性质,因而也完全有可能被评价为准抢劫罪。
那么,第一种类型之外的其他情形又如何呢?典型的情形是,盗窃罪的未遂犯出于“为了逃避逮捕,或者隐灭罪迹”的目的,而实施暴力或者胁迫的场合(以下简称为“第二种类型”)。(20)盗窃罪的既遂犯出于“为了逃避逮捕,或者为了隐灭罪迹”的目的,而实施暴力或者胁迫的情形,当然也是有可能存在的,但由于一旦被逮捕,财物也会被追回,因此,基本上都可以作为同时存在出于防止财物被追回的目的的情形,而将其评价为第一种类型。在这种场合下,虽然在先行行为是盗窃未遂行为这一点上,也能够认定存在作为财产犯罪的一面,但就暴力、胁迫行为而言,则难以认定存在(与抢劫罪相类似的)财产犯罪的性质。对此,也许只能是强调人身犯罪的性质,也就是,在盗窃的机会之下(出于法定目的)实施的暴力、胁迫也有可能带来针对生命、身体的重大危险。例如,出于隐灭罪迹的目的而实施的暴力、胁迫类型,实际上,最终大多会发展至杀害目击证人的行为。(21)参见前引,佐伯仁志文,第207页以下。这种场合下,虽然无法否认其作为财产犯罪的性质已经多少有些弱化,(22)按照这种理解,学界有力观点提出了批判,主张对于第二种类型,作为立法论来说,应该将其从事后抢劫罪的类型中予以删除。参见佐伯仁志:《強盗罪(2)》,载《法学教室》第370号(2011年),第88页;前引⑤,松宫孝明书,第233页;等等。但在盗窃犯为了避免被发现或者遭受处罚而引起了针对被害人的生命、身体的重大危险这一点上,终于还是可以认定,存在足以作为抢劫罪未遂予以处罚的实质。
(三)与第2款抢劫罪之间的关系
对于事后抢劫罪的第一种类型,如前所述,从针对返还请求权的强取这一视角来看,可以说,具有与第2款抢劫罪相类似的一面。这里想就事后抢劫罪与第2款抢劫罪之间的关系,简单做些探讨。
首先,作为探讨的前提,我们需要确认:即便是通过盗窃罪、诈骗罪等财产犯罪而取得了财物的场合,也无法否认,被害人仍然具有财物的返还请求权,这种权利是作为财产上的利益而被当作独立的保护对象的。学界也有观点主张,在因先行的财产犯罪而取得了财物的场合,其后针对返还请求权的强取,就应该被评价为共罚的事后行为,不能另外将其作为第2款抢劫罪予以处罚。(23)参见町野朔:《犯罪各論の現在》,有斐閣1996年版,第142页以下;辰井聡子:《判批》,载山口厚等编:《刑法判例百選Ⅱ各論》(第7版),有斐閣2014年版,第81页;等等。林美月子教授也认为,不返还非法取得的财物的,由于不能被谓为新的法益侵害,因而这种场合下的返还请求权根本就不能作为财产犯罪予以保护(参见林美月子:《窃盗後の二項強盗》,载《立教法学》第79号(2010年),第19页以下)。的确,例如,在骗取了被害人的财物之后,通过暴力、胁迫而避免返还财物的,先行的第1款诈骗罪与后行的第2款抢劫罪实质上是指向同一法益的法益侵害,因此,认定同时成立两罪是不合适的,应该通过其中的任何一个犯罪予以处罚,来概括地评价两者的法益侵害。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根据法定刑的高低轻重以吸收关系来加以评价,这样一来,先行的第1款诈骗罪就被评价为共罚的事前行为,被后行的第2款抢劫罪所吸收。不考虑法定刑的轻重高低,返还请求权总是被财物侵害所吸收评价,应该说,鲜有这样理解之必然性。例如,被告人等是暴力团成员,先假装从被害人A处购买兴奋剂,打算在收到兴奋剂之后再杀死被害人,但最终归于杀人未遂。对此,最决昭和61·11·18刑集40卷7号523页认为,就取得兴奋剂的行为而言,是通过欺骗A而取得了兴奋剂,因而有成立诈骗罪的余地;不过,此后,被告人的同伙又违背A的意思拿着兴奋剂逃走了,也可以说,自这一阶段开始才取得了占有,因而也有成立盗窃罪的余地。在此前提之下,最高裁判所进一步指出,“被告人实施的手枪发射行为,显然是为了通过杀害A,以逃避向该人返还兴奋剂,或者逃避支付作为买主所应该支付的价款,进而取得这种非法的财产性利益……作为先行的取得本案兴奋剂的行为,无论该行为本身究竟是构成盗窃罪还是诈骗罪,鉴于前述事实,认为本案作为该罪与(第2款)抢劫杀人罪未遂的所谓包括的一罪,应以后面的重罪之刑予以处罚,这样理解是妥当的”,从而,明确地判定,通过暴力、胁迫而逃避返还财物的,应成立第2款抢劫罪。(2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案客体是兴奋剂,因而有这样理解的余地:兴奋剂的交付相当于不法原因给付,被害人原本就不能请求返还,而且,兴奋剂的买卖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原本就没有产生什么货款债权。按照这种理解,对于本案,也能以被害人的返还请求权与汇款请求权根本不值得保护为理由,否定成立第2款抢劫罪。不过,最高裁判所的判例显然没有采取这种理解。关于这一点,参见前引,安廣文夫文,第308页以下;前引,町野朔书,第144页。
最高裁判所昭和61年的判例在没有确定先行犯罪究竟是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的情况下,直接肯定成立第2款抢劫罪,因而,其前提显然在于,即便先行犯罪是盗窃罪,对于为了逃避返还财物而实施暴力、胁迫的,也应成立第2款抢劫罪。当然,盗窃犯为了逃避返还财物,(在盗窃机会仍然在持续的状况之下)实施了暴力、胁迫的,也应成立事后抢劫罪。不过,这只是针对同一法益侵害行为的不同法律评价而已,因而两罪处于法条竞合的关系。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事后抢劫罪一方面虽然被加上了“盗窃机会的持续过程中”这种时间上的限制,但并未要求达到实际逃避了返还请求的程度,也有与第2款抢劫罪相比扩张了成立范围的一面,因而两者并非简单地属于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之间的关系。因此,就两者的适用关系而言,(类似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那样的)相互之间并无哪一个优先适用的问题,因而在既成立第2款抢劫罪也成立事后抢劫罪的场合,检察官完全有可能以其中的任何一个罪名起诉,裁判所也只要就是否成立所起诉的罪名作出判断即可(虽说如此,但至少在刑法学的研修上,还是应该以首先探讨是否成立事后抢劫罪为原则)。相反,先行犯罪是诈骗罪、恐吓罪等其他财产犯罪的场合,则没有成立事后抢劫罪的余地,因而完全是是否成立第2款抢劫罪的问题。最高裁判所昭和61年判例的案件中,由于并未对先行犯罪究竟是盗窃罪还是诈骗罪作出确定性判断,因而讨论的完全是第2款抢劫罪成立与否的问题。
那么,例如,盗窃犯在时间上以及地点上均与盗窃现场相隔离的情况下,为了防止盗赃被追回而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胁迫的,应该如何处理呢?在这种场合下,由于不能说,盗窃的机会仍然在持续,因而不能认定成立事后抢劫罪,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被害人的返还请求权仍然是作为独立的利益而受到保护的,因此,仍然有成立第2款抢劫罪的余地。这是因为,即便认为,对于那些不能认定成立事后抢劫罪的情形也不成立第2款抢劫罪,(25)最高裁判所昭和61年判例中,谷口正孝裁判官的意见就是这种旨趣。持相同旨趣者,另见前引,林美月子文,第28页。但是,根据先行行为究竟是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第2款犯罪的成立范围也随之有所不同,这是不妥当的。(26)参见前引,佐伯仁志文,第87页。
三、暴力与胁迫的含义
(一)暴力、胁迫的程度
从确保与抢劫罪具有同质性这一角度,一般认为,事后抢劫罪中的暴力、胁迫,与抢劫罪一样,也应达到按照社会一般观念,一般情况下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具体而言,暴力、胁迫必须达到,从物理上或者心理上压制被害人追回财物或者实施逮捕行为的程度。例如,面对诸如警察、保安等不会轻易为一定程度的暴力、胁迫所压制的被害人,即便实施了徒手殴打面部等暴力,这种暴力很多时候也不能被评价为,达到了足以压制其追回财物、实施逮捕的程度。(27)参见長井秀典等:《強盗罪(中)》,载《判例タイムズ》第1352号(2011年),第100页以下;瀬川行太:《事後強盗罪における暴行の判断基準について》,载《北大法学論集》第66卷第5号(2016年),第197页以下;等等。
例如,为了免遭保安逮捕,用力推搡保安胸部,导致保安倒地,后脑勺受到撞击,一时半会无法动弹的,这种情形应如何处理呢?对于这种情形,也应该综合考虑暴力的程度与部位、被害人的体格、周边的具体状况等因素,如果能认定该暴力内含着会让被害人跌倒的高度危险性,该暴力就能够被评价为,足以压制逮捕行为的暴力;反之,如果不能认定存在足以为这种危险性奠定基础的具体情况,毋宁说,对于那些因被害人偶尔失去平衡而摔倒的情形,即便最终结果是达到了压制反抗的状态,但也不能认定存在事后抢劫罪中的暴力行为,只能被评价为盗窃罪与暴行罪(或者伤害罪)的并合罪(数罪并罚)。也就是说,在被害人被实际压制反抗的场合,通常情况下,作为手段行为的暴力就应该被评价为达到了足以压制反抗的程度,但对于那些因为某种偶发性因素发挥作用的案件,有时候也应该例外地认定,不属于事后抢劫罪的暴力。
(二)与目的要件之间的关联性
日本《刑法》第238条只是要求,在法定目的之下实施暴力、胁迫,并未要求通过暴力、胁迫达到了法定目的。例如,为了逃避逮捕,对保安实施了用刀子捅刺等暴力,但结果反而被保安控制遭到逮捕的,即便是这种情形,如果该暴力达到了足以压制逮捕行为的程度,也当然构成事后抢劫罪。
不过,行为人终究是意图达到一定目的而实施了暴力、胁迫,因此,该暴力、胁迫与目的达成之间必须存在(客观上的)关联性。例如,在盗窃犯逃离犯罪现场之际,误以为从背后接近自己的无关的第三人是追赶自己的被害人,出于防止财物被追回的目的,对该第三人实施了暴力,在这种场合下,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防止财物被追回的目的而对第三人实施了暴力。但是,针对本案第三人实施的暴力,对于防止财物被追回,客观上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连这种情形也要认定成立事后抢劫罪,本文认为并不妥当。
实际成为问题的情形是,例如,明明警察或者保安纯粹是出于其他动机而与行为人打了个招呼,但行为人误以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被发现了,于是,出于逃避逮捕的目的实施了暴力、胁迫的,如何处理呢?在该场合下,如果被害人已经意识到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则针对被害人的暴力、胁迫与逃避逮捕的目的之间,可以说存在客观上的关联性,因而完全有可能认定成立本罪。不过,在本案的具体状况下,我们也无法否认,这种针对被害人的暴力、胁迫,在与逃避逮捕的目的的关系上,实际上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行为,因此,按照这种理解,就有否定成立本罪的余地。(28)参见前引,佐伯仁志文,第89页。
(三)与转化抢劫之间的区别
例如,在着手实行盗窃之后,由于被害人回家了,产生了通过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胁迫以强取财物的意思,于是对被害人实施了(足以压制反抗的)暴力、胁迫,并夺取了财物的,在该场合下,行为人是以强取财物为目的而针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胁迫,因此,应成立第1款抢劫罪,先行的盗窃罪(未遂)被该罪第1款抢劫罪所吸收。(29)参见前引⑤,西田典之书,第181页(所谓“转化抢劫”,是指着手盗窃之后,或者在着手之前,因为被发现,转而出于强取财物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的情形,属于第236条的抢劫。——译者注)。这种案件一般被称为转化抢劫。
转化抢劫与事后抢劫的区别取决于行为人实施暴力、胁迫的目的。(30)参见吉田敏雄:《事後強盗罪をめぐる諸問題》,载《現代刑事法》第12号(2000年),第42页以下。就是在上述案件中,如果行为人没有想要夺取更多的财物,而完全是出于逃避逮捕的目的实施了暴力、胁迫的,当然应成立事后抢劫罪。因此,先行的盗窃行为究竟是既遂还是未遂这一事实,对于两者的区别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因为,即便是盗窃既遂的场合,也完全能想象到,行为人也可能会出于强取其他财物的意图而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胁迫。
这样,如果认为应该根据目的内容来区分两罪,例如,已经窃取财物的行为人在逃避逮捕的同时,又出于强取其他财物的意思将被害人捆绑起来夺取了其他财物的,首先,从先行的盗窃行为到此后的暴力行为,这可以被评价为事后抢劫罪,并且,对于通过暴力强取了新的财物这一点,也能认定成立第1款抢劫罪。不过,即便能认定成立两罪,由于两罪是在同一机会之下针对同一被害人的犯罪行为,因而应进行包括性评价,只要作为一个整体认定成立抢劫罪一罪即可。
四、盗窃机会的持续性
(一)概述
要成立事后抢劫罪,以暴力、胁迫是在“盗窃的机会”仍然在持续的过程中实施为必要。这要求的是,盗窃行为与暴力、胁迫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一般被认为是,之所以要求这一点,是为了能够认定与抢劫罪之间存在同质性。
最决平成14·2·14刑集56卷2号86页是有关盗窃机会的持续性的重要案例(决定)。大致案情为:本案被告人侵入被害人住宅窃取了戒指之后,由于一时间没什么地方可去,就想到要在被害人的阁楼上躲几天,饿了可以去偷吃被害人家的食物,于是,被告人便果真待在犯罪现场正上方的阁楼上。但是,在实施盗窃行为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被害人回到了家中,察觉到家中被盗以及盗贼就躲在自家阁楼上。在实施盗窃行为大约三小时之后,被告人被接到被害人报警而赶到现场的警察发现,为了逃避逮捕,拿出随身携带的(长把斜刃的)小刀刺向警察面部,造成伤害结果。对于该案,最高裁判所认为,“被告人在实施上述盗窃行为之后,停留在离犯罪现场很近的地方,这样,容易被被害人等发现,或者被追回财物,或者受到逮捕的状况仍然在持续,因此,应该说,上述暴力是在盗窃的机会的持续过程中实施的”,进而以此为理由,支持了判定成立(事后)抢劫致伤罪的原审判决。
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在判断盗窃机会的持续性之际重视的是,“容易被被害人等发现,或者被追回财物,或者受到逮捕的状况”的持续性。如果原封不动地适用该标准,只要持续潜伏在被害人住宅的阁楼,就可以说,总是容易被发现,受到逮捕的危险性也总是在持续,因此,在行为人滞留在犯罪现场的场合,不管经过了多长时间,均能认定盗窃机会的持续性。然而,如果在本案中,不是被害人偶然回家发现了被告人,而是被告人滞留在阁楼几天之后才被发现,被告人同样对接警而来的警察实施了相同暴力的,本文认为,要认定存在盗窃机会的持续性,就并不合适。(31)参见朝山芳史:《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14年度),法曹会2005年版,第69页。
原本来说,事后抢劫罪之所以要求存在盗窃机会的持续性,尤其是不管是前述第一种类型的事后抢劫罪还是第二种类型的事后抢劫罪均要求此要件,这是因为,与事后抢劫罪所具有的财产犯罪的一面相比,更多是基于事后抢劫罪所具有的人身犯罪的一面的要求。也就是,在盗窃行为之后的短时间内,通常会出现盗窃犯想方设法逃走,而被害人等(姑且不论实际会如何应对)则努力想要抓住盗窃犯,以追回被盗财物等情况。这样,正因为两者的利益尖锐对立的状况仍然在持续,基于法定目的而实施的暴力、胁迫,会因为这种相互对立的不断升级而给被害人的生命、身体带来重大危险。(32)参见嶋矢貴之:《事後強盗罪における「窃盗の機会」の意義》,载西田典之等编:《刑法の争点》,有斐閣2007年版,第177页。在此意义上,要认定盗窃机会的持续性,就应该要求,盗窃犯与被害人等之间紧迫的对立状态仍然在持续。(33)参见山口厚:《新判例から見た刑法》,有斐閣2015年版,第229页。西田典之教授也要求盗窃犯与被害人一方之间存在对立、对抗状态(参见前引⑤,西田典之书,第178页),想必也是同样旨趣。而且,林幹人教授以紧接着盗窃“之后的重大危险的实现”作为问题(参见前引,林幹人书,第352页),可以说也是同样的问题意识。判例所谓“容易被被害人等发现,或者被追回财物,或者受到逮捕的状况”这种表述,也应该被理解为,是从会持续受到被害人等的追究这种可能性的视角,将其当作判断“紧迫的对立状态”的标准之一。(34)参见安田拓人:《強盗》,载《法律時報》第85卷第1号(2013年),第40页。
按照这种理解,即便是持续滞留在被害人住宅的情形,一旦事态已经归于平静,丧失了情况的紧迫性,对此就应该否定盗窃机会的持续性。因此,如前一案件那样,对于行为人连续几天躲在阁楼的情形,即便地点上的接近性仍然在持续,也不能说,情况的紧迫性仍然在持续。相反,就最决平成14·2·14刑集56卷2号86页的案件事实而言,由于盗窃行为之后仅仅才经过了三个小时左右,时间上的间隔并不是很大,因而是有可能被评价为紧迫的状况仍然在持续的。尤其是就该案来说,并非三个小时之后才被被害人所发现,事实上一个小时之后就已经被发现,这一事实也是很重要的。(35)参见前引,朝山芳史文,第68页;前引,山口厚书,第228页。当然,就本案而言,三小时的间隔也并不是那么长,因而即便没有一小时之后被发现这一事实,也同样有可能认定盗窃机会的持续性。亦即,自盗窃行为实施一小时之后,任何时候被被害人发现都不奇怪这种状况在持续,能够被评价为,情况的紧迫性没有丧失,仍然在持续。与这种情况结合在一起,对于本案事实,就能够肯定盗窃机会的持续性。
(二)对具体案件的探讨
1. 回归现场型的案件
这样,要认定盗窃机会的持续性,就以盗窃犯与被害人等之间存在紧迫的对立状况为必要。那么,盗窃犯离开现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返回犯罪现场的,对此如何处理呢?最判平成16·12·10刑集58卷9号1047页就此类案件作出了具体的判断。大致案情为:本案被告人为了筹措8万日元的房租,临时起意打算入室盗窃,决意侵入偶尔路过的A家,于是在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左右,从一楼起居室没有上锁的垃圾口进入A家。在起居室窃取了装有现金的钱包与信封,几分钟之后便离开了A家,此时,没有被任何人发现,也没有被任何人追踪,骑着自行车前往距离现场一公里开外的公园。然而,在公园清点盗得的现金时,发现只有三万多一点,打算再次进入A家实施盗窃,于是便骑车折返回来,在下午一点二十分左右,打开A家大门口的便门时,察觉到家里有人,便关上便门,退到门外的停车场,被正好回家的B发现,为了逃避逮捕,从口袋中拿出小刀,刀尖指向B,趁B害怕后退之机逃离现场。
对于该案,原判决(东京高判平成15·11·27刑集58卷9号1057页)以被告人在将盗赃装在口袋的情况下,为了达到当初的盗窃目的,大约三十分钟之后又返回同一个被害人的家为理由,判定成立事后抢劫罪。然而,最高裁判所认为,“被告人窃取财物之后,没有被任何人发现,也没有被任何人追踪,一旦离开犯罪现场,且经过了一段时间。应该说,在此期间,容易被被害人等发现,或者被追回财物,或者受到逮捕的状况已经结束。这样的话,即便被告人此后出于再次实施盗窃的目的又返回犯罪现场,也不能说,此时实施的上述胁迫,是在盗窃机会的持续过程中所实施”,从而撤销原判决,并发回重审。
本文以为,如果在第二次实施入室盗窃行为的阶段,能认定存在新的盗窃的实行的着手,那么,就可以将该行为评价为“盗窃”(将行为人评价为“盗窃犯”——译者注),对于针对B的胁迫行为,认定成立事后抢劫罪(未遂)。但是,在本案中,在第二次实施入室盗窃行为的阶段,被告人仅仅是打开了大门口的便门,在这一阶段,其行为还不能被认定为盗窃的实行的着手,为此,本案才以是否成立基于当初的盗窃行为的事后抢劫罪这一点作为问题。正如本判决所指出的那样,被告人窃取财物之后,没有被任何人发现,也没有被任何人追踪,在离开犯罪现场一段距离的地方独自度过了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该阶段能够被评价为,紧迫的对立状况这种性质已经丧失。并且,即便被告返回犯罪现场又重新创造了对立状况,但也不能被评价为,那属于当初的对立状况的原样持续,因而就本案而言,一般被理解为,属于应否定盗窃机会的持续性的情形。(36)参见大野勝則:《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16年度),法曹会2007年版,第594页。相反,也有观点认为,也有这样评价的余地:一旦中断的盗窃机会的持续性,又通过自己的手加以修复了(参见安井哲章:《事後強盗罪の基本概念》,载《法学新報》第113卷1=2号(2006年),第396页)。按照这种理解,对于那些行为人重新返回犯罪现场的案件,仅限于诸如下述例外情况才能认定盗窃机会的持续性:(1)诸如被被害人等追赶那样,在对立状况仍然在持续的情形下,又返回到犯罪现场;(2)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没多久,就从犯罪现场附近的地方返回到犯罪现场;等等。
相反,学界有观点主张,对于那些能认定自始便有持续实施数次盗窃的意思的场合,由于返还现场的行为也属于“一系列的盗窃行为”的一部分,因而应认定盗窃机会的持续。(37)参见高橋則夫:《規範論と刑法解釈論》,成文堂2007年版,第219页。另有观点也以是否能将整体评价为一个盗窃行为作为问题(参见成瀬幸典:《判批》,载《ジュリスト》第1343号(2007年),第120页)。然而,数个盗窃行为在罪数论的层面能否被包括地评价为一罪,与能否说当事人之间的紧迫的对立状况仍然在持续,两者应该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38)参见岡上雅美:《判批》,载山口厚等编:《刑法判例百選Ⅱ各論(第7版)》,有斐閣2014年版,第87页。事实上,就是在本案中,被告人也是在意欲盗取八万日元这一共通的动机之下,实施了第二次侵入行为,(39)也有观点因为重视这一点,而暗示有肯定盗窃机会的持续性的余地。参见前引,成瀬幸典文,第120页。但本判决并未因为这一点而肯定盗窃机会的持续性。本文认为,即便是被告人起始便计划,直至盗取八万日元为止,无论几次侵入被告人住宅亦可,仅仅以这种动机的连续性为理由便认定机会的持续性,也是不妥当的。(40)参见前引,大野勝則文,第596页。
2. 隐灭罪迹目的的案件
作为盗窃机会的持续性的判断标准,最高裁判所平成14年判例与平成16年判例研究的都是“容易被被害人等发现,或者被追回财物,或者受到逮捕的状况”的持续性。在日本《刑法》第238条所规定的目的要件之中,这里存在与“防止财物被追回”的目的与“逃避逮捕”的目的相对应的要件,但没有与“隐灭罪迹”的目的相对应的要件。(41)参见前引,林幹人书,第350页。为此,学界就有观点认为,目的不同,机会的持续性的判断也可能不同,因而,对于出于“隐灭罪迹”的目的的暴力、胁迫,应适用与上述判例不同的标准。(42)参见林陽一:《判批》,载《法学教室》第265号(2002年),第143页。然而,盗窃机会的持续性,是为与抢劫罪的所谓同质性而奠定基础的情况,原本应该在行为人出于法定目的实施暴力、胁迫之前,就统一地判断是否存在这种持续性。按照这种理解,无论是出于日本《刑法》第238条所规定的何种目的实施了暴力、胁迫,对于盗窃机会的持续性的判断都不会不同。(43)参见嶋矢貴之:《判批》,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4号(2006年),第89页;長井秀典等:《強盗罪(下)》,载《判例タイムズ》第1354号(2011年),第27页;等等。
例如,行为人出于“隐灭罪迹”的目的,决意杀害目睹了其盗窃行为的被害人,于是,将被害人带离现场,即便在与共犯商量万全的杀害方法的几天内,一直监禁着被害人,在此期间,盗窃机会的持续性也未丧失。在该场合下,上述判例的判断标准确实未必适合。不过,如前所述,在盗窃机会的持续性的判断中,能否说紧迫的对立状况仍然在持续,这属于重要的视角。上述判例的标准,也不过是以与判例中实际成为问题的事实关系相对应的形式,而显示了其中的一个判断而已。并且,在出于杀害目的带走被害人的场合,由于行为人的杀害意思是连续的,可以说,在此期间,针对被害人的生命、身体的危险状况仍然在持续,因此,能够认定对立状况的持续性。
近年有这样一个判例:被告人出于窃取钱财的目的侵入与自己的住宅相邻的A宅,拿走A的提包之后,回到了自己家。但被告人突然想到自己的盗窃行为可能已经被A所察觉,在家中犹豫了十五分钟之后,又再次侵入A宅,出于“隐灭罪迹”的目的杀害了A。对于此案,东京高等裁判所认为,被告人窃取本案提包之后,没有受到任何人的追踪,顺利地回到了家,因此,“由于应该说,被告人已经完全脱离了被害人一方的支配领域,因而认定容易被被害人等发现,或者被追回财物,或者受到逮捕的状况已经不存在,这是相当的”,进而以此为理由,否定了盗窃机会的持续性(东京高判平成17·8·16高刑集58卷3号38页)。东京高等裁判所是依据与上述最高裁判所判例相同的标准来判断盗窃机会的持续性的,这是因为,在本案中,被告人没有被任何人发现,也没有被任何人追踪,回到了完全能被称为安全之地的自己的家,这一事实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尽管目的要件不同,但实质上仍然可以被评价为,本案是与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相类似的案件。相反,例如,被告人在实施盗窃行为的时点,就已经想到已经被A发觉,于是,出于“隐灭罪迹”的目的打算杀害A,并将A带至被告人自己的家中,此后,在自己家中杀害了A,如果案情是这样的话,那么,从杀害意思的连续性这一视角,也能认定盗窃机会的持续性。
五、事后抢劫罪的共犯
(一)问题之所在
在盗窃犯实施了盗窃行为之后参与进来,仅仅参与了盗窃犯的暴力、胁迫行为的,如何确定这种共犯的罪责,曾是学界热烈探讨的问题。最高裁判所对于该问题的态度尚不明确,但可以说,下述问题解决路径在下级裁判所已经基本确立:在事后抢劫罪是以盗窃犯为身份的身份犯这一理解之下,将此类案件作为非身份者加功于身份者的案件,通过适用第65条来解决。(44)日本《刑法》第65条【身份犯的共犯】规定,(1)加功于因犯罪人的身份才构成的犯罪行为时,即便是没有身份者,也是共犯(第1款);(2)因身份而特别存在刑的轻重时,对没有身份者科以通常之刑(第2款)。——译者注不过,对于盗窃犯这一身份究竟是第65条第1款的构成的身份犯还是第2款的加减的身份犯,判例的态度并不一致。(45)认定属于构成的身份的判例,参见大阪高判昭和62·7·17判时1253号141页;认定属于加减的身份的判例,参见新潟地判昭和42·12·5下刑集9卷12号1548页、东京地判昭和60·3·19判时1172号155页。
与下级裁判所的判例态度一样,学界也有学说认为事后抢劫罪是身份犯。这种学说的内部还存在将本罪理解为构成的身份犯的观点(46)参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515页以下;佐久間修:《刑法各論》(第2版),成文堂2012年版,第203页;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第6版),東京大学出版会2015年版,第200页;等等。与将本罪理解为加减的身份犯的观点(47)参见大冢仁:《刑法概説〔各論〕》(第3版増補版),有斐閣2005年版,第224页;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新版第4版補訂版),成文堂2015年版,第241页;前引⑤,松宫孝明书,第233页;内田文昭:《判批》,载《研修》第490号(1989年),第11页(认为也有可能作为承继的共犯来处理);岡野光雄:《判批》,载《研修》第494号(1989年),第9页;前引⑧,稲垣悠一文,第85页;等等。之间的对立。另有有力观点主张,本罪不是身份犯,而是以盗窃行为与暴力、胁迫作为实行行为的结合犯。(48)参见中森喜彦:《判批》,载《判例評論》第353号(《判例時報》第1273号)(1988年),第71页;西田典之:《新版·共犯と身分》,成文堂2003年版,第293页;古江瀬隆:《判批》,载《研修》第457号(1986年),第66页以下;川端博:《事後強盗と共犯》,载《研修》第558号(1994年),第11页;十河太朗:《事後強盗罪と共犯》,载《愛媛法学会雑誌》第27卷第1号(2000年),第176页以下(同时也认为,身份犯这种理解并非错误);伊東研祐:《事後強盗の共犯》,载西田典之等编:《刑法の争点》,有斐閣2007年版,第179页;前引,山口厚文,第4页以下;前引,島田聡一郎文,第19页;前引,高橋則夫文,第219页;山中敬一:《刑法各論(第3版)》,成文堂2015年版,第319页;松原芳博:《刑法各論》,日本評論社2016年版,第248页;等等。并且,按照将事后抢劫罪理解为结合犯的立场,这属于有关实行行为途中参与进来的共犯罪责的问题,也就是属于是否成立承继的共同正犯的问题。
(二)探讨
1. 基本的理解
首先,在结论上,本文认为,应该将事后抢劫罪理解为,以盗窃与暴力、胁迫为实行行为的结合犯。如前所述,要将事后抢劫罪作为类似于抢劫罪的财产犯来把握,就以将盗窃行为包含在该罪的处罚对象之内加以评价为必要。为此,真正合适的理解是,不是将盗窃行为定位于该罪的身份,而是将盗窃行为作为事后抢劫罪的处罚对象,也就是将盗窃行为定位于实行行为的一部分。所谓身份犯,并不是以具有身份本身作为处罚对象,而不过是只有身份犯的实行行为才能认定具有法益侵害性(公务员收受贿赂的行为才是违法行为,而非是成为公务员这一点被作为处罚对象)。本文认为,就是按照这种理解,将本身就属于事后抢劫罪的处罚对象的盗窃行为,作为该罪的身份犯来处理,也是不妥当的。(49)参见岡本勝:《事後強盗罪に関する一考察》,载《香川達夫博士古稀祝賀·刑事法学の課題と展望》,成文堂1996年版,第406页。
按照身份犯说,(虽未必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由于先行的盗窃行为本身没有被作为事后抢劫罪的处罚对象来评价,因而盗窃犯实施的暴力、胁迫与先行的盗窃行为就应构成不同的犯罪。(50)参见前引,山口厚文,第5页。当然,作为罪数评价来说,将先行的盗窃行为作为共犯的事前行为被事后抢劫罪所吸收,这样评价也不会出现什么特别的问题,然而,如果总是这样以事后抢劫罪吸收评价盗窃罪,这种处理方式本身无疑就是在说,盗窃行为属于事后抢劫罪的处罚内容的一部分。
这样,本文认为,应该将事后抢劫罪作为结合犯来理解。如前所述,下级裁判所一般是将本罪理解为身份犯。而且,日本《刑法》第238条规定的是,“盗窃犯窃取财物之后为了……而实施暴力或者胁迫的”,如果重视该规定的形式的一面,将事后抢劫罪理解为身份犯,也并非完全不可能。(51)不过,如果重视条文的形式的一面,抢劫致死伤罪(第240条)、抢劫强奸罪(第241条)也会被评价为,以抢劫犯作为身份的身份犯。如果认为这种结论不妥当,就应该认为,条文的形式的一面并非决定该罪是否是身份犯的决定性标准。并且,究竟是将本罪理解为结合犯还是身份犯,如果这种对立完全是限于如何处理那些仅仅加功于暴力、胁迫的共犯的问题,(52)既往的学说曾经一般认为,根据究竟是将本罪理解为身份犯还是结合犯,有关下面两个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1)事后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别标准;(2)事后抢劫罪的实行行为的着手时点。不过,近年来,有力观点认为,无论如何理解事后抢劫罪的结构,对于上述两点问题,都会得出共通的结论(例如,参见前引,島田聡一郎文,第17页以下;前引,佐伯仁志文,第87页;等等)。那么,即便将本罪理解为身份犯,如果能就该问题探讨出可以得出妥当结论的理论结构,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按照这种理解,针对如果将本罪理解为身份犯应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这里想一并做些简单探讨。
2. 作为承继的共同正犯的处理
就承继的共同正犯的问题学界尚存争议,本文的基本态度是,就共犯而言,即便没有对正犯的所有构成要件该当事实施加因果性,如果对该犯罪的法益侵害能认定存在因果性,就可以认定成立承继的共犯。(53)桥爪隆教授有关承继的共犯的基本观点,详见桥爪隆:《论承继的共犯》,王昭武译,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按照这种理解,如何把握相关犯罪类型的法益侵害的内容就成为重要的问题。就抢劫罪而言,一般认为,暴力、胁迫所引起的人身犯罪的一面,以及强取财物所引起的财产犯罪的一面一同构成了该罪的法益侵害性,因此,仅仅参与强取财物的后行行为人,不能成立抢劫罪的承继的共同正犯。(54)参见橋爪隆:《承継的共同正犯》,载《法学教室》第415号(2015年),第95页以下。那么,对于事后抢劫罪,要认定成立承继的共同正犯,对于那些仅仅参与暴力、胁迫的后行行为人,能否认定其行为与该罪的财产犯罪性质的法益侵害性之间存在因果性,也属于重要的判断标准。
以上述理解为前提,下面就【案例1】与【案例2】具体进行探讨。
【案例1】在Y窃取财物之后的逃跑过程中,因Y马上就要被被害人A抓住而被追回盗赃,X出于防止盗赃被追回的目的,与Y一同对A实施了暴力。
【案例2】Y着手实施盗窃,但未能盗得财物,在逃跑过程中,马上就要被被害人A抓住,此时,X出于使得Y逃避逮捕的意图,对A实施了暴力。
【案例1】中的X与由Y实施的盗窃既遂行为之间没有因果性。但是,X、Y实施的暴力,在妨害A行使返还请求权这一点上,是能够被评价为第2款抢劫罪的实行行为的。并且,在盗窃既遂犯为了防止财物被追回而实施暴力、胁迫的类型(第一种类型)中,在先行的盗窃行为的基础上再实施的暴力、胁迫行为,能够被评价为指向逃脱返还请求权或者确保财物的手段行为,能够为事后抢劫罪的(作为抢劫罪的)财产犯罪的性质奠定基础。这样考虑的话,【案例1】中的X通过共同实施暴力行为,而对事后抢劫罪作为财产犯罪的法益侵害性施加了因果性,因而X完全有可能成立事后抢劫罪的共同正犯。(55)参见前引⑥,西田典之书,第184页;前引,島田聡一郎文,第20页。
与这种理解相反,还有观点主张,X没有对作为事后抢劫罪的法益侵害性施加因果性,而只是对作为第2款抢劫罪的法益侵害性施加了因果性,因而应认定X成立第2款抢劫罪的共同正犯。(56)参见前引,松原芳博书,第255页。这样理解当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将X作为第2款抢劫罪的共同正犯,将Y作为事后抢劫罪的共同正犯来处理,共同正犯之间的既遂时点就会出现不同,因而这种处理方式总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毋宁说,(既然能认定成立第2款抢劫罪,那么,)产生了类似于第2款抢劫罪的法益侵害性这一点本身就可以构成事后抢劫罪的法益侵害性,因而以此为理由,直接认定X成立事后抢劫罪的共同正犯,这样理解可能在理论上更加清晰明快。
相反,对于【案例2】中的X而言,想必难以认定其成立事后抢劫罪的共同正犯。这是因为,X与Y实施的暴力完全是指向逃避逮捕的目的,这种暴力不会产生确保财物或者逃避返还财物的效果。因此,X(只要没有参与盗窃未遂行为)不可能对事后抢劫罪作为财产犯罪的法益侵害性施加因果性,只能是在能认定存在因果性的限度之内,作为暴行罪的共同正犯予以处罚。
3. 作为身份犯的处理
那么,如果认为事后抢劫罪是以盗窃犯为身份的身份犯,【案例1】与【案例2】又应该如何处理呢?这里,就需要解决事后抢劫罪究竟是65条第1款的构成的身份犯还是第2款的加减的身份犯的问题。
通说认为,只有存在身份才能认定具有可罚性的,这种犯罪是构成的身份犯;相反,加减的身份犯是指,没有身份也能成立,但根据是否具有身份,刑罚得以加重或者减轻的犯罪。(57)参见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新版第4版),成文堂2012年版,第450页。如果从形式上适用这种理解,就事后抢劫罪而言,即便没有盗窃犯这种身份,也完全有可能按照暴行罪或者胁迫罪予以处罚,因而似乎是加减的身份犯。不过,就是按照通说的立场,也并非要贯彻这种形式上的区别。例如,侵占委托物罪中的占有者的地位,一般被认为是第1款侵占罪的构成的身份(参见最判昭和27·9·19刑集6卷8号1083页),但即便没有占有者这一身份,取得财物的行为也是有可能作为侵占脱离占有物罪而受到处罚的。尽管如此,侵占委托物罪之所以没有被理解为加减的身份犯,是因为通过占有者这一身份的存在,被附加了对委托信任关系的侵犯这种新的法益侵害性,进而被评价为,是与侵占脱离占有物罪罪质不同的犯罪。这样,在判断究竟是第65条第1款的身份还是第65条第2款的身份之际,就是立足于通说立场,下面这种实质性判断也是不可或缺的:(1)是否因身份的存在而产生了新的法益侵害性?或者,(2)在同一犯罪类型的内部,是否因身份的存在而只是加重了刑罚?众所周知,作为第65条第1款与第2款的区别标准,有观点主张,在身份的存在是为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这一意义上的违法性奠定基础的场合(违法身份),适用第1款;在身份左右行为人的责任程度的场合(责任身份),适用第2款。(58)参见西田典之:《刑法総論》(第2版),弘文堂2010年版,第402页以下。事实上,即便是立足于通说的立场,这种实质性思考也是必要的。
基于这种前提,在探讨事后抢劫罪的身份犯性质之际,还是有必要像承继的共同正犯的情形那样,区分第一种类型与第二种类型。也就是,在第一种类型的场合,盗窃犯出于防止财物被追回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通过这一点便超越了单纯的暴力、胁迫这种人身犯罪的性质,具备了为了逃避返还财物而实施的暴力、胁迫这种类似于抢劫罪的法益侵害性。在此意义上,对于第一种类型,盗窃犯这一身份是为暴力、胁迫行为具备作为财产犯的法益侵害性奠定基础的身份,能够被理解为第65条第1款的身份(违法身份)。因此,对于【案例1】中的X,应适用第65条第1款,成立事后抢劫罪的共同正犯。
相反,在第二种类型的场合,即便具备了盗窃犯这种身份,也无法认定暴力、胁迫行为本身具有财产犯罪的性质。因此,盗窃犯这种身份对于出于逃避逮捕这一目的而实施的暴力、胁迫而言,由于与通常的暴力、胁迫相比具有更高的非难可能性,因而被理解为加重刑罚的身份,这样,对于第二种类型,盗窃犯这种身份就应该被理解为第65条第2款的身份(责任身份)。其结果是,【案例2】中的X成立暴行罪的共同正犯。
这样,即便将事后抢劫罪理解为身份犯,通过对第一种类型适用第65条第1款,对第二种类型适用第65条第2款,最终完全有可能得出与将其作为承继的共同正犯处理相同的结论。(59)持这种理解者(复合的身份犯说),参见佐伯仁志:《事後強盗罪の共犯》,载《研修》第632号(2001年),第6页以下。最后想特别确认一点,无论采取何种法律结构,第一种类型与第二种类型的区别都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