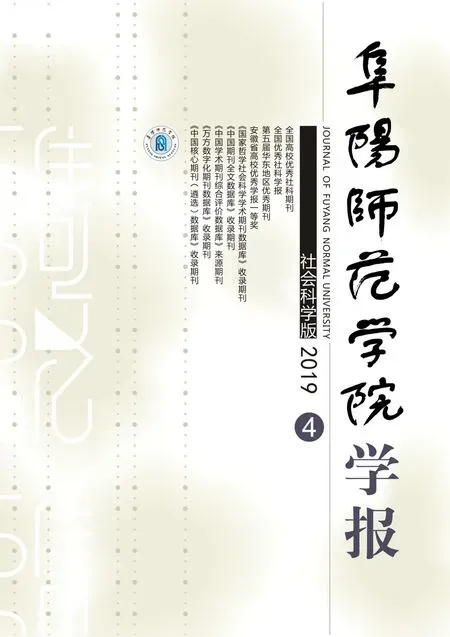庄子礼学思想研究
2019-03-28华云刚
华云刚
(常州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州,213022)
关于庄子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司马迁早有评论:“(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讠此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1]《庄子》的基本思想继承了《老子》,同时又“诋 讠此孔子”“剽剥儒、墨”,故其对于儒家与墨家的思想,尤其孔子的思想必然是非常熟悉的。“庄子之学与早期儒家学说有许多内在的思想联系,与同时期儒家人物的思想也是互相影响的。”[2]也正因此,《庄子》对于儒家核心思想的“礼”,必然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就是《庄子》的礼学思想。
当前学界关于《庄子》礼学思想已经有所探讨。梅珍生认为:“在礼的深层结构即‘礼质’层面上,庄子肯定了礼的秩序意识,认为礼中的尊卑秩序与宇宙秩序是一致的,具有客观性。”[3]即梅氏肯定了礼中尊卑秩序的含义。庞慧则认为《庄子》“抨击儒家拘守的‘世俗之礼’,主张安于‘性命之情’”,并逐渐以“理”代“礼”[4]。性命之情是庄子所提倡的,但“理”在《庄子》中能够替代“礼”却值得商榷。王新建则从“以道批礼”“由礼批儒”“以道解礼(礼仪)”“以礼解道”四个方面对《庄子》的礼学思想进行探究[5],融合儒道以解“礼”是其重点。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解读《庄子》对“礼”的态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对于“礼”的探究,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在庄子之前,儒家对于“礼”的解读已经深入人心,“礼”已经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哲学范畴之一。因此庄子必然不能越过这个前提,他只能在这一前提下展开讨论。同时,庄子并非全然继承儒家的礼学观念,他对于儒家先贤的礼学思想大抵是批判的。当然,这其中《庄子》也继承了这一哲学范畴,并重新界定分析,从而让原始儒家的核心思想概念具有“道”的哲学内涵。也就是说,《庄子》是在批判后继承了儒家之礼的哲学范畴,然后重新解读的。为了进一步阐释《庄子》的礼学思想,“礼”哲学范畴含义的演变过程就值得深入探究。
一、对儒家“礼”的评价
《庄子》对于儒家的礼,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因此把《庄子》中的礼分成两类:一是规范性的、习惯性的行为方式,二是被批判的礼。
(一)规范性、习惯性的行为方式
《庄子》中一些地方提到的“礼”,主要是指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没有是非对错之分,大都是一种规范性的行为习惯,如君臣之礼就是如此。《人间世》曰:“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也!”郭象注曰:“外形委曲,随人事之所当为也。”[6]君臣之礼,这在封建社会十分正常,庄子也不可能突破时代的局限,所以这里的礼就是面见君王的一种规范性的习惯性行为。大家都如此去做,自己也不能搞特殊化,这样才能隐藏自己的独特个性,和光同尘,“与人为徒”。
同时,以一种规范化的行为统治国家,也正是某些求道之士的人生目的。《刻意》曰:“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这个“礼”正是“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致功并兼者”所崇尚的,他们重视功名,讲究上下尊卑、社会秩序。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这个“礼”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一部分中,庄子对于这种规范性、习惯性的礼并没有直接地批判或提倡,只是一种基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描述。
(二)被批判的礼
虽然《庄子》有对规范性、习惯性的礼的接受,但它绝不是儒家“礼学”思想的拥护者,更多的时候,《庄子》对于礼是持批判态度的。
第一,庄子批判礼的仪式与外形。《田子方》曰:“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矣。”在这里,《庄子》将礼义作为一种外在表现,与人的内心对立起来,从而批判执着于外在的礼仪。于是《庄子》提倡忘,忘掉礼乐。《大宗师》曰“回忘礼乐矣”,礼的仪式是最形象直观的,是礼中最容易认识的部分。郭象注曰:“礼者,形体之用。乐者,乐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对于这种重视外在行为规范、仪容仪表的礼仪,《庄子》加以反对,因为不在意各种礼仪形式,更看中礼背后的意义。这种形式化的内容《庄子》是不认同的,需要忘记或者打破。在《庄子》中,很多的“礼”都是处在被批判的地位的,但其被批判的内容却又有所不同。
“礼别异”,故儒家的礼主要用来区别尊卑贵贱,其所区分的方式不过颜色、大小、多少的不同,因此,各种礼法当中具体的数字等级也是庄子批判的地方。《天道》曰:“礼法数度,刑名比详,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正因为可以通过人们熟悉的颜色、大小、多少来区分,所以上下相因,由此形成一种工具的特征,变成一种统治手段和工具。形式化的统治形式早已消失了礼的原始意义。《天道》曰:“礼法数度,刑名比详,治之末也。”即便是一种统治方法,也是最末等的,最不入流的。在《庄子》看来,以立法数度来治理天下,是治国的末术,完全不值得提倡。
第二,庄子批判儒家的礼不符合自然的法则。《大宗师》曰:“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郭象注曰:“其所以观示于众人者,皆其尘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在这里,庄子认为人生天地之间,死与生都只是一种存在方式,不必斤斤计较。“来,夫子时也;去,夫子顺也。”因此可以看出,道家不以人的生死为意,追求一种自然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与礼无关。若以世俗之礼来左右人们的耳目,礼就不符合自然的法则。
《庄子》不仅认为儒家的礼有不合自然的地方,同时还认为这种礼并不是常规,甚至是可以变化的。《秋水》曰:“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也就是说,在《庄子》看来,礼是因时而定的,并不是长行不变的真理。既然礼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那么为什么还学习呢?为什么还要拘泥呢?在《庄子》看来,永恒不变的真理只有一个:“道”。
第三,《庄子》不仅批判儒家礼的学说,还进一步批判儒家思想中的仁、义、圣、知等其他思想。《在宥》曰:“而且说明邪,是淫于色也;说聪邪,是淫于声也;说仁邪,是乱于徳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说知邪,是相于疪也。”在儒家思想中,礼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仁、义、圣、智等组成的一个系统。《庄子》为了批判儒家的礼,甚至对整个儒家的思想体系展开批判。尤其当礼乐文化包裹着仁义的思想时,《庄子》的批判就更加严苛。因为在《胠箧》有:“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此时的仁义已经与圣人无关,它的评价标准在大盗手里,就能变成杀人的武器。圣人无法左右。如《骈拇》曰:“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在《庄子》看来,礼乐、仁义、道德都已“异化”,变成一种统治工具,不再是人的本性之自然状态。故而不值得提倡,甚至应当尽量忘掉、破坏掉。这样的批判在《庄子》中数见不鲜。《马蹄》曰:“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 在这里,《庄子》把儒家的礼乐文化与其仁义、人伦等内容对天下的残害、对性情的损坏都放在一起,对儒家的批判之深可见一斑。当然,《庄子》批判的立足点都在于人的自然本性。它认为,所有的礼乐、仁义不过是一种樊网、一种羁绊,一种破坏,所以才被置于批判的地位。
第四,《庄子》更多的时候是把儒家的礼与乐放在一起批判的,这是对孔子礼乐文化的最直接的批判。如果说前文所谓的礼、义、仁等是儒家的哲学范畴,此时《庄子》批判的着眼点则集中于儒家的礼乐文化的政治理想。《天道》曰:“通乎道,合乎德,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郭象注曰:“以情性为主也。”成玄英疏曰:“退仁义之浇薄,进道德之淳和,摈礼乐之浮华,主无为之虚淡。”在这里,“宾礼乐”就是“摈礼乐之浮华”,把儒家的礼乐文化置于被批判的地位,驳斥其浇薄、浮华的一面,从而提倡道德的淳和、虚淡。《渔父》曰:“礼乐不节,财用穷匮,人伦不饬,百姓淫乱,天子有司之忧也。”下文又曰:“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不泰多事乎?”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礼乐文化中的浮华、奢靡是庄子批判的重点,也是庄子重建新秩序必须打破的障碍。
第五,《庄子》不仅批判儒家的礼学形式与思想,还批判汇聚儒家思想的经书典籍。《外物》曰:“儒以《诗》《礼》发冢。”郭象注曰:“《诗》《礼》者,先王之陈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为奸,则迹不足恃也。”大儒带着小儒去盗墓,做的事情完全与儒家尊祖敬宗的理想相违背,但嘴里却念叨着圣人之教化——《诗经》与《尚书》。这一段嘻嘻怒骂,全都通过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寓言故事表现出来,读来令人喷饭。《南华雪心编》段后评曰:“撰出一篇发冢奇文,写尽伪儒变态,笔有化工,正不必求其人以实之也。”[7]其实被批判的何止是儒者?连同儒家的典籍也成为盗墓的帮凶,所以庄子也不禁揶揄一把,甚至加以嘲讽。
综上所述,在论述儒家之礼时,《庄子》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对于一般规范性、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庄子》并不在意。而对于儒家礼学的仪式、思想与儒家典籍,则采取强烈的批判态度。鲁迅所谓:“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凌轹诸子。”[8]从自然的角度来看,礼确有与道相违背的地方,而儒家以礼治国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礼对自然本性的影响,更没有考虑到个体生命的差异性。因此在《庄子》看来,这些礼都是奢靡的、损生伤性的,并不利于人类的健康发展。
二、庄子的礼学观点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庄子》对于礼的价值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说《庄子》对于礼学有自己的认识和观点。在继承了儒家的哲学范畴后,《庄子》又对其进行了全新的“改造”。经过改造后的“礼”与儒家的“礼”属于相同的哲学范畴,但具有决然不同的哲学意义,其具有如下特征:
(一)“礼法自然”
《庄子》赋予“礼”以新的内涵与精神,与其称呼这是“礼”,不如说这是旧瓶装新酒,庄子用“礼”的名字而“借尸还魂”,最终宣传的是道与自然。在《庄子》中,“礼”已经不再是儒家所说的“礼”了,却显现出道家的哲学精神。因为《庄子》认为“礼法自然”。《缮性》曰:“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郭象注曰:“信行容体而顺乎自然之节文者,其迹则礼也。” 也就是说顺乎自然的行为便是礼。《在宥》曰:“应于礼而不讳。”郭象注曰:“自然应礼,非由忌讳。”儒家认为,礼要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尤其是名字的避讳,在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上,名讳已经成为一种专门文化。但在《庄子》看来,自然相处即可,不必强为忌讳,设置更多的障碍。它甚至认为,真正的礼就是不忌讳。庄子鼓盆而歌,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临尸而歌,在儒家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以《庄子》的视角来看,生死之间又有什么差别?生亦何乐,死亦何苦?都只是自然现象而已,不必以各种礼来包装本无二至的情感与言行。
《庄子》用道家自然无为的原则来解释礼,解放了人们的日常行动,同时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庄子》认为随性所至,便都是礼。《山木》曰:“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郭象注曰:“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则万方得矣,不亦大乎!”因此,不用管礼义的具体内容与要求是什么,只要顺着自己的心意,哪怕猖狂恣意的言行也都是符合礼的。这与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9]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孔子的“从心所欲”是从十五岁有志于学以来逐步锻炼出来的一种习惯性行为;而庄子则更为洒脱,他认为不必在乎外在礼义的约束,只要随着自己的心性去做,就是符合礼法的。
在礼之外,《庄子》还借用“真”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其实这也是一种对礼的规范,而这种“礼”却是崇尚自然的,也就是“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父》曰:“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这里《庄子》举“真”以继承“天”的特性、自然的特征,并认为“天”“真”是人们效法学习的对象,而遵守世俗之礼只是愚者的行为而已。其实,《庄子》中“真”字多次出现,如“真”“真人”“真知”“真性”“真理”等等。并且,庄子对于“真”赋予了更高的境界与追求。“‘真’可以说是庄子哲学追求的一种境域,庄子之‘道’就是通往‘真’的道路。”[10]正因为庄子是真人,所以其所言,虽略显猖狂,但仍是符合礼的。只是《庄子》“礼”的主要内涵是“天”与“真”,而不再是儒家所提倡的礼了。
(二)“礼无定式”
除了“礼法自然”之外,《庄子》还认为礼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有了固定的模式,反而容易被有心之人所利用,然后伪造出许多“伪礼”的行为。《在宥》曰:“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郭象注曰:“夫礼节者,患于系一,故物物体之,则积而周矣。”意思是说,礼最大的忧患在于统一、在于批量生产。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就会丧失自然之性。从礼推而广之,乐也是如此。如果天下有一套礼乐的成规,可以一一按照它们的模式去做,消解了个体差异性,那么天下一定大乱了。《缮性》曰:“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郭象注曰:“以一体之所履,一志之所乐,行之天下,则一方得而万方失也。”这其实就是由个体的自由,“一志之所乐”,推广到天下人,如果人人都遵守这种礼乐,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批量生产的工具了。只为了一个定规的“礼”而完全丧失自己的个性,在《庄子》看来,这是不足取法的。
《庄子》不仅从正面论述礼没有一定的规矩与程式,而且还从反面论证有了程式之后出现的种种弊端,尤其是虚伪的事情。《知北游》曰:“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郭象注曰:“礼有常则,故矫诈之所由生也。”因为仁、义,包括礼,都是可以伪装的,所以礼一定不能是“常则”,如果给了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是礼的规定,那么不能做到的人都会想尽办法伪装自己,伪礼也就随之产生了,当伪礼的行为越来越多,礼也就失去了原来的约束力和道德价值,反而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了。比如汉魏时期的“孝廉”就是如此,因此才有“举孝廉,父别居”童谣唱出来的政治笑话。
(三)礼重情性
礼不仅崇尚自然,《庄子》认为礼还要深入人类的情性,并从情感与人性的角度建立礼学思想。《大宗师》曰:“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这里面主要涉及的“临尸而歌”的外在行为与“礼意”之间的关系。在儒家看来,“临尸而歌”从形式上确实是违反礼法的。郭象注曰:“夫知礼意者,必游外以经内,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声,牵乎形制,则孝不以诚,慈不任实。父子兄弟,怀情相欺,岂礼之大意哉?”在《庄子》看来,形式上的礼都不足以真正解读“礼意”。“庄子根据对生死本质的理解,否定了世俗的价值,也否定了世俗的礼仪。”[11]《庄子》批判儒家只重形式的礼仪,其所持的武器便是“情性”,只有“称情而直往”才能在深层次与礼相契合。因此,《庄子》认为礼重情性。也就是说,礼是一种规范,但并不是牢笼,它要考虑到人的情感以及人类的本性。如果放弃所有,追求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来约束人,那一定是不合理的。
从前面的“礼无定式”也可以知道,“伪礼”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过于关注礼的仪式与外在表现。也正因为儒家很多的礼都侧重于仪式或者形式,所以容易被模仿和伪装。那该如何解决“伪礼”的问题呢?《庄子》以内在的情性与外在仪式之间的矛盾为切入点,借助内在的情性来充实礼的具体内涵,并以内在情性规范外在行为,故从内外两个方面界定礼的范畴,对于礼的思想有重要贡献。同时,对于批判虚伪、“伪礼”等现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至礼不人”
儒家提出许多思想观念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对于后世的诸子百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比如,儒家讲仁,道家反对,就用“至仁”来重新定义“仁”。这与《老子》论证“不仁”相似。《老子·5 章》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2]93河上公注曰:“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王弼也认为:“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子相理,故不仁也。”[13]陈鼓应认为此处的意思是天地无所偏爱,万物在天地间遵循着自然法则而运行,并没有人类仁与不仁的种种情感色彩[12]93。在“仁”的基础上,提出“至仁”的概念以补救提倡“仁”的思想带来的种种弊端,正是哲学不断演进的趋势。
对于“礼”,《庄子》所用的方式也是如此。《庚桑楚》曰:“至礼有不人。”郭象注曰:“不人者,视人若已。视人若已则不相辞谢,斯乃礼之至也。”对于此处讨论的“至礼”,《庄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并不是根据人的性别、样貌、地位等等来定的,礼遵循的并不是人间的规则,它更崇尚自然无为的根本。“至礼不人”还有一层解释,即“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在《庄子》看来,礼是很肤浅的,尤其在“道”的面前,礼只是知识和真理的皮毛,却是产生动乱的罪魁祸首。因此,如果用“道”的眼光看待礼,只有摒弃人为,才能基本接近“真礼”。“不人”即可入道,然后就能成为真正的礼。
总之,在儒家的礼学之外,《庄子》化用了儒家的这一哲学范畴,总结了一套自己的礼学观点。《庄子》从人的自然本性、自然情感等方面对礼进行重新的定义和阐发,又从社会的角度发现“礼无定一”,而通过“道”的眼光来观照礼,可以看到礼不是人为的。这些观点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庄子的礼学追求
既然《庄子》一方面反对现有的儒家世俗之礼,一方面对礼又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庄子》的礼学追求是什么呢?什么才是《庄子》理想的“礼”呢?
(一)“礼综百家”
《庄子》批评儒家的礼是为了建立新的礼学体系,而这个体系也借鉴了儒家、墨家、法家等其他诸子思想的精华。《大宗师》曰:“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徳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郭注曰:“礼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郭象的《庄子注·自序》曰:“至仁极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已能,忠信发乎天光。”通过郭象的注,可以发现,刑、礼、知、德四者都是构成人们做事行为的规范,四者各司其职。于是,《庄子》借助于诸子百家的思想与哲学范畴建立自己的礼学体系。成玄英疏曰:“礼虽忠信之薄,而为御世之首,故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动,非礼勿言。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礼之于治,要哉!羽翼人伦,所以大行于世者也。”成玄英则重新把世俗化的礼拉回《庄子》书中,这是不太符合庄子思想的。综合郭象的观点,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在后世学者的心目中,《庄子》的礼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儒家的礼的概念,它变得更加庞大,大有融合诸子百家的趋势。
虽然庄子的礼综合其他各家的思想,但并不是把它们杂糅到一起,而是有具体分工的。如《天下》曰:“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薫然慈仁,谓之君子。”由此可以看出,庄子主要借鉴礼在行为方面的意义,来构建自己的礼学思想体系。同时借助其他哲学思想概念一并建立君子的形象,并从内到外对君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人物,如圣人、神人、真人、至人等等都是在此基础之上境界的不断提升。在这里,明显能看到《庄子》的一种综合性,强化的是礼的实践性意义。这在构成一个完整人格的君子时,是十分必要的。
(二)“礼变于治”
不管礼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点,但礼最终还是指向人类社会的。这一点即便是与社会有一定距离的道家,也不外如是。因此,《庄子》最终把不同时空的礼联合起来做比较,其礼义规范或时有不同,但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天下。《天运》曰:“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郭象注曰:“期于合时宜、应治体而已。”可见,虽时移世易,但是礼的功能性却是恒久不变的,自古及今,设置各种礼都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而已。所以经过诸多的社会形态,礼义总是为了实现天下大治的手段和功能,而不是为了“同”,保持与古代相同的简单复古主义。
礼是因时而变的。《天运》曰:“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棃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也就是说,礼仪法度,不管每个朝代是什么样子,都会因时而变,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治理天下。让天下处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之中,这就是《庄子》礼的理想与追求。
综上所述,《庄子》对于儒家的世俗之礼采取不同的态度,对于其中一些习惯性、规范性的行为方式,《庄子》不置可否,大抵默认。但对于另外一些礼则加以批判。《庄子》认为儒家的礼注重外在仪式,与人的自然本性相违背,礼与仁、义、乐成为约束人们的枷锁,残生伤性。在此基础上,《庄子》对于儒家的礼乐文化及其文化载体的《诗》《书》等儒家典籍也大加批驳。正是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出《庄子》对于“礼”有自己的认识。当然,《庄子》并没有完全否定儒家的礼,在一定程度上,庄子也承认礼有一定的仪式,并且标志着上下尊卑等级。如《天下》曰:“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庄子》创造性地化用了儒家“礼”的意义,并注入道家的哲学精神,使儒家的哲学范畴中蕴含着道家的哲学思想。《庄子》的“礼”认为“礼法自然”“礼无定一”礼重情性和“至礼不人”。经过如此转换,其实《庄子》是在借助儒家的哲学范畴来宣传自己的思想而已。因此,它的礼学思想也留下了深深的道家烙印。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庄子》有了自己的礼学追求:“礼综百家”且“礼变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