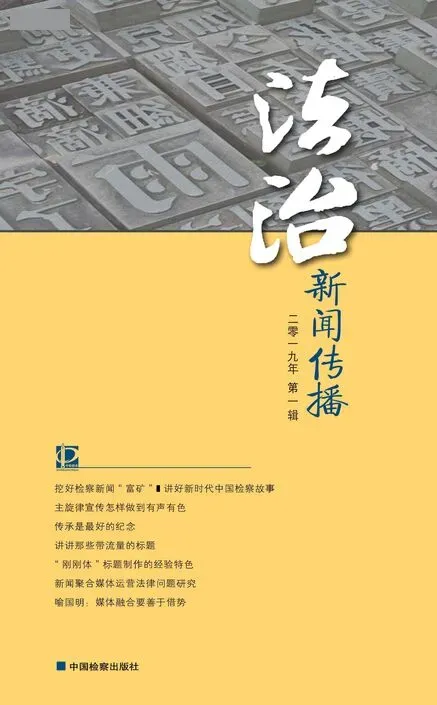啥是爷爷
2019-03-28邱春艳
■邱春艳
最近,《啥是佩奇》火了。它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爷爷对于孙子的那份朴素而深沉的爱。为了弄清孙子最喜欢的佩奇到底是什么东东,爷爷可谓费尽心思。可是有多少人反过来想过,啥是爷爷?对于孙子来说,爷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看完以下几个小故事,也许你心中就会有答案。
(一)
年底前,父亲因为杀猪的事情和母亲争吵起来。因为二老时常不在老家,所以没有养猪。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自己家里怎么着也得有一头猪。过年时,叫杀过年猪。
妹妹妹夫家离我们家不远。于是,父亲就在自己女儿女婿家买了一头猪,让女儿家帮忙养一段时间,等过年时再杀。恰好前段时间有猪瘟,妹妹家担心被传染,就想早点帮父亲把猪杀了,以降低被传染的风险。这样双赢的考虑,可是当妹妹给父亲说了这之后,父亲竟然不同意。坚持要到腊月二十九才杀。
妹妹拿老爸没办法,只好给在广东带孙子的妈打电话。母亲接了电话,又给父亲打电话,让他早点把猪杀了算了。
可是好说歹说,父亲硬是不同意。母亲和妹妹只好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干这得罪人的差事——说服老爸早点杀猪。
我接了电话也觉得奇怪:父亲虽然脾气倔,有时候还挺古怪,但也并非不讲道理的人。这事的道理很简单:猪多留一日就多一日被传染猪瘟的风险,而早杀似乎没有什么损失。
我怀着十分不解的心情给父亲打电话询问他坚持的理由。在我一再“逼问”下,父亲才道出真实想法:那啥,小毛不是喜欢看猪嘛,我就想等你们回来之后再杀猪。可你们放假放得那么晚,我就想等到腊月二十九再杀过年猪,一是让小毛多看看猪,二是也让他感受一下咱们老家过年的习惯和氛围。
原来如此。我告诉父亲,小毛这几年见过好多次猪了,他已经不觉得稀奇了。你还是听劝,早点把过年猪杀了,以免猪瘟传染过来。父亲这才释然,“好好好,那早点杀,”一边喃喃道,“小毛前两年还喜欢看猪呢,怎么就不稀奇了呢……”
夏天的时候,我们一家回老家休假。到家之后,父亲主动提出可以把鱼塘的水放干了抓鱼。这让我有些意外。
父亲不喜欢吃鱼,却喜欢养鱼。他在老家鼓捣了好几个鱼塘,可因为他只养不吃,我们也跟着吃不到他的鱼。而且,他最不喜欢别人把他的鱼塘的水放了(塘里的水放了之后要灌满很不容易)抓鱼。这次怎么心甘情愿地请我们去抓他的鱼了呢?
等水快见底时,鱼在混水里扑腾。连小孩也能抓住鱼了。哥哥家的子恒和我家的小毛下塘捉鱼,捉到最后,直接在鱼塘里打滚抓鱼,虽然满脸是泥,但却乐不可支。看着两个孙子在鱼塘里玩得很开心,一旁的父亲也开心地笑了。
我终于知道他这次为什么这么大方了。
啥是爷爷?爷爷就是那个听说孙子喜欢啥就去弄啥,千方百计无条件去“讨”孙子欢心的人。
(二)
某一年,父亲来北京帮我们看娃。一次,父亲和我带着孩子出去散步。
回来的时候经过一家小卖部,孩子盯着小卖部的一排排“养乐多”挪不开脚了。哼着要我买给他喝。在我们看来,这些都属于“垃圾食品”行列,各种添加剂,因而不愿买给孩子喝。
我坚决喝止了儿子的“非法”请求,把他从怀里放到地上,假装生气地说,你不走,我们都走了。于是,我就独自往前走。
原以为父亲很配合。可走了一段,却发现爷孙俩没有跟上来。
一回头,却发现儿子手上拿着一排“养乐多”乐呵呵地笑,尽管刚才的眼泪还挂在腮帮子上。
不用说,肯定是父亲受不了孙子眼泪巴巴地请求,就给他买了。不仅买了,还买了一长排!
我心里有点气,想埋怨父亲几句。回头时,正好和父亲四目相碰,他的眼神本能地闪躲——怕我埋怨他乱给孩子东西吃。
父亲年轻时身体好得很,可进入老年后常年咳嗽,这抱着孙子走上一段,更是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看着父亲抱着儿子蹒跚慢行的样子,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再想到父亲刚才那个躲闪的眼神,想到他看到孙子开怀大笑时的欣慰,我哪还有心思埋怨他——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
一次,母亲带着我和儿子去她的娘家拜访她的伯娘。我管老人家叫嘎嘎(意为外婆),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儿子应该叫她太嘎。老人家见我们去看她,非常开心。特别是看到曾孙辈的小屁孩,更是开心。从一个黑乎乎的柜子里颤巍巍地拿出了一包东西给孩子。
我们以为是啥好东西,到光线好的地方一看,是包方便面!再看一下日期,是过期很久的方便面。为了不让老人失望,我们表现出很惊喜的样子,说要把这好东西带回家吃——在常年不出门的老人的心里,她以为这就是现世最好的东西,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了孩子。
老人们对孙辈的爱,就是把自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他。爷爷对孙子更是如此。
(三)
孩子其实多半是势利的。
在自己蹒跚学步或者不会走路的时候,都喜欢爷爷奶奶,特别是喜欢爷爷奶奶抱他出去“浪”。而一旦自己走路利索了,对爷爷奶奶依赖程度降低后,就对他们不怎么“感冒”了。特别是进入七八岁,有了自己的想法和主见后,孩子对爷爷奶奶就更不感冒了——在他们看来,爷爷奶奶的那些陪他玩的“把戏”都太老套过时了。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兴趣。
有一次,在老家过完年后,我们回到北京。在出租车上,我给老爸打电话报平安,也让儿子与爷爷说几句。这家伙倒是应景,大声地告诉爷爷,我们到北京了,我们都想你了。父亲大约就只听明白了这两句。儿子在北京生长,字正腔圆,父亲虽是教师出身,但普通话毕竟用得少,说起来就有些蹩脚,再加上老家的信号不好。爷孙二人的对话也就有些困难。
孙子问:爷爷,你在做什么?
爷爷问:小毛,你说什么?
爷爷问:小毛,你在做什么?
孙子问:爷爷,你说什么?
这一番对话把出租车司机都给逗乐了。我却有些伤感——爷爷似乎听不懂孙子的想念,尽管孙子的这些想念还是被儿子“逼”出来的。
在儿女还未成家立业的时候,父辈们往往很挂念我们的事业。而一旦我们的家庭和事业逐渐定型,他们就不怎么关注我们如何了,而是更关注孙子们如何。
很多时候,孩子有了自己的世界,视频和电话都不愿和爷爷奶奶多说了,多半是被父母逼着和爷爷奶奶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但即便是这样,爷爷奶奶也很高兴。
有时候,他们主动发来视频,第一句话就是:我孙子呢。让我看看孙子。可是孙子偏偏对见爷爷奶奶兴趣索然。在父母的一顿威逼利诱之下才肯出镜。可即便是孙子心不在焉的问候,爷爷奶奶看着听着也很是高兴。
有时候,我甚至有个不恰当的比方,祖孙三代有点像三角恋:爷爷爱孙子,孙子不爱爷爷爱爸爸,爸爸爱爷爷。
啥是爷爷。爷爷就是那个想着孙子念着孙子“暗恋着”孙子不图回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