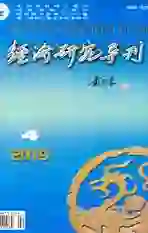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发展协调机制研究
2019-03-26刘云忠
刘云忠
摘 要:我国西部地区在大力发展民生的同时,面临着生态环境的严峻考验。以我国西部地区民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为研究对象,探讨民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机制。
关键词:民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4-0154-03
近年来,西部地区大力发展经济,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好转,但却对自然环境、生态资源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影响了人民正常的工作、生活,而且阻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
一、国内外研究述评
19世纪50年代国外开始对经济、生态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是由于“二战”给参战国带来了诸多的环境问题,以及战后这些国家为了恢复国力,大力发展经济而不顾环境问题造成的。
第一阶段,1960年以前,协调只是经济系统自身的协调;第二阶段,1960—1970年,保护环境就意味着放弃发展经济;第三阶段,1970年至今,生态与经济应该协调发展。Young-Seok Moon(1996)为了了解能源和经济之间的相关关系运用内生增长模型对二者进行了研究。因为有的地区相对落后而且地理位置偏僻,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数据不完整或者根本收集不到数据,因而对这些地区的研究不能进行。Konstantion Bithas等(1996)提出,在这种情况下,运用专家知识系统对这些地区进行建模分析。70年代初,中国才意识到环境问题。随着对环境问题的深入了解,中国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对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从含义方面看,姜子青等(1992)提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共同、持续的意思,并不是说两者的发展地位是平等的,而是指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张坤等(1999)则提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只是比较浅层次的发展,人类应该追求更深层次的发展(即社会、生态、经济等多个方面共同作用下的协调发展)。
从研究方法方面看,中国学者总结前人经验提出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环境状况,要运用不同的发展战略。张坤等(1999)通过构建模型,对经济发展相对较落后地区进行研究。杨世琦等(2005)以协同发展为基础,构建了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函数,并结合协调等级理论,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进行研究。许振宇等(2007)运用生态足迹理论与协调度结合的方法,对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进行评价。于文良等(2009)则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研究了可持续发展变化趋势并且分析了影响因素。
二、西部地区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能力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能力,所以将数据收集方向分为两个大的方面:生态环境和经济。进而选取与生态环境和经济联系密切的指标,生态环境指标体系选择了12个指标,经济指标体系选择了12个指标。结合西部地区独特的区域背景,查询相关资料,最终确定生态环境系统指标由资源供给、环境污染、环境治理3个方面12个指标构成;经济系统指标由经济运行总情、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消费、社会发展4个方面12个指标构成。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原始数据处理,可以得到影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各指标的累计贡献表。影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24个指标,得到3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59.833%、18.197%、8.749%,累计贡献率为86.779%,而86.779%>85%,则说明这3个主成分基本包含了原始数据中的大部分信息,所以可以用这3个主成分来反映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现状。从成分矩阵中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民人均纯收入、社会从业人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人均GDP、土地面积、森林覆盖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的变量绝对值系数比较大,因此可以发现第一主成分是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第二主成分中第二产业从业人数、降水量、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人均耕地面積、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变量绝对值系数比较大,因此可以发现第二主成分是反映环境状况的。第三主成分中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变量绝对值系数相对比较大,因此可以发现第三主成分是大体上是反映产业结构的。计算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根据熵值法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值。此方法是以原始信息为基础,通过分析指标间的联系程度及提供的信息量来得到指标权重的,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主观影响因素带来的偏差。用熵值法计算权重:n和p分别为样本个数和指标个数。
从图中可以看出,2005—2015年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大体上都呈明显的上升状态。但单就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这条折线而言,2005—2011年以及2012—2015年这两段时间综合发展水平折线都是上升趋势,只有其间的2011—2012这一年综合发展水平是下降的,说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势头很不错,2005—2015年大幅度上升;单就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这条折线而言,2005—2008年综合发展水平折线呈上升趋势,其后的2008—2015年折线波动次数较多。这说明,人们在保护环境这个问题上持续度是不够的,还需大力提升环境保护的力度、强度和持续度。
三、结语
从本文图表可以看出,2005—2015年西部地区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5年为濒临失调;第二阶段是2006—2007年为勉强失调;第三阶段是2008—2009年为初级协调;第四阶段是2010—2014年为中级协调;第五阶段是2015年为良好协调。可以看出,这十一年里西部地区经济—环境系统一直朝着越来越好的协调程度前行。由图表同样也可以看出,中级协调阶段在朝着良好协调阶段发展时经历了五年时间,而勉强失调阶段向着初级协调阶段以及初级协调阶段向着中级协调阶段发展时都只经历了两年时间,相比较来说五年算是比较长的时间。这说明,经济—环境系统在渐渐朝着更好地协调程度发展过程中,当协调程度越来越高时,发展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发展速度就会越来越慢,所需时间也会越来越长;反之,当协调程度处在较低阶段时,要朝着较高阶段发展就相对比较容易,发展速度就会越快,所需时间就会越短。
参考文献:
[1] 杨世琦,王国升,高旺盛.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评价研究——以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4):299-301.
[2] 许振宇,贺健林,刘望保.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能力测评——基于生态足迹理论和生态协调度的实证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6):736-738.
[3] 于文良,王伯铎,吴良兴.陕西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9,(6):14-18.
[4] 姜子青,等.协调发展的理论探索[J].环境保护,1992,(1):9-12.
[5] 张坤,任勇.欠发达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
[6] Young-Seok Moon.Productiv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rowth:endogenous growth model an its empirical application[J].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es,1996,(18):189-200.
[7] Konstantions Bithas,Peter Nijkamp.Environmental-economic modeling with semantic insufficiency and factual uncertainty[J].Environmental System,1996,(2):167-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