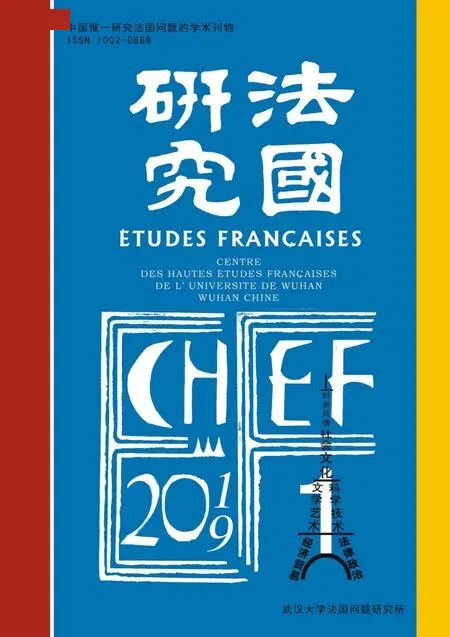肉身的神话:加缪半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中的神话隐喻
2019-03-26顾晓燕
顾晓燕
肉身的神话:加缪半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中的神话隐喻
顾晓燕
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一个人》是加缪的最后一部小说,在这部作家未竟的半自传体小说中,加缪描写了一个法国青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寻根历程,其内容囊括了“黑脚”法国人从第一代殖民者到二战之间的全部经历,是研究加缪人生和思想历程的重要作品。本文认为在除去传统意义上对小说作者生平研究及其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态度的研究视角外,还可以从加缪的“神话”创作角度分析这部遗作。希腊和希伯来的神话以其各自的张力为这部小说增添了历史的厚重,铺开了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加缪如同神话中失乐园的亚当、寒夜诞生的耶稣和执着返乡的奥德赛一般,在“寻根”之旅中踯躅前行,寻求自身身份的构建。
加缪 第一个人 神话 隐喻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其代表作《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等享誉世界,他的思想在二战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影响了一代西方人的成长。1957年,加缪因“全身心地投入人生的重大基本问题的思考”,“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①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60年1月4日星期一,加缪在车祸中身亡。在车祸的残骸中,人们找到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第一个人》的手稿。这部小说是加缪所有作品中最具个人自传性质的一部,他在其中糅合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期。而事实上,这也是一部未竟之作,小说只完成了第一部分《寻父》,第二部分《儿子或第一个人》只完成了一半,第三部《母亲》则只留下了一些大纲和散记。因此《第一个人》也是“最后一人”,是加缪的遗嘱,却也因此为读者留下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加缪在这部半自传体的小说中,描写一个法国青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寻根历程,囊括了黑脚法国人(pieds-noirs)从第一代殖民者到二战之间的全部经历。虽然小说用第三人称为叙事角度,但从手稿中偶然笔误出现的“Vve Camus”和“Germain”先生②,不难发现小说作者的代入感和自传的份量。与《局外人》中那个虽以“我”叙事、但其实为“他”的主人公相反,《第一个人》中言说的“他”其实就是“我”,这一方面体现了加缪不同寻常的叙事方式,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加缪试图超脱个人化叙事,而从更广义的层面诠释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的身份困惑和无根之痛。
一、加缪和神话
在加缪的计划中,《第一个人》将是他自己的《战争与和平》③。在传统的叙事方式下,加缪利用神话的隐喻为作品注入了史诗般的悲情和壮美,展开了他自己的宏大叙事。在民俗学意义上,神话是指关于人类和世界变迁的神圣故事。在广义上,“神话”可以指任何古老传说,是用故事形式表达出来的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加缪对神话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文学应复活神话。在小说《堕落》中,加缪就通过小说人物克莱芒丝说:“希腊在我身上某处、在记忆的边缘衍生。”上世纪50年代时,加缪就想过写这样一部小说,1959年他把计划告诉格尔尼埃老师:“我尝试写一部直接的小说,我的意思是不管怎样,要像我以前的作品一样,是一种经过组织的神话。这将是一种情感教育之类的东西,42岁时,我可以试试。”④可见,他将自己此前的作品视为“神话”,认为自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家,更确切说是一个艺术家,在激情和焦虑中创造神话”,尤其他对第一部小说《局外人》如此评论:“《局外人》既不是现实也不是魔幻,我在它身上看到更多的是化身在岁月里有热度的肉身的神话”⑤。
加缪说:“世上于我最惬意之所便是希腊神话”。但他的神话并非只有一个故乡,希腊固然是其心神向往之所,但基督教的伦理和审美也构成作家情感写作的一个重要渠道。一方面,加缪对希腊神话的引用和再度阐释清晰地展现在他的众多散文之中,如《西西弗的神话》、《米诺托或奥兰的逗留》、《地狱中的普罗米修斯》、《流放海伦》等,希腊神话以其内在闪烁之理性成为加缪思考荒诞与反抗的历史源泉;而另一方面,加缪以一个非信徒(non croyant)⑥的身份对基督教的伦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其研究生毕业论文《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中可见一斑,在加缪的中短篇小说《堕落》、《流放与王国》、《约拿》、《不贞的妻子》等中作者更多地展现了对伦理的思考。因此,我们可以说希腊和希伯来神话贯穿了加缪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而在最后的小说《第一个人》中,加缪虽然没有像《局外人》、《鼠疫》、《卡利古拉》和《西西弗的神话》那样明显地汲取希腊神话的力量,但他依然通过古希腊和希伯来的神话隐喻为作品增加了不一般的厚度和张力。
二、亚当与失乐园
关于《第一个人》,加缪在1954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道:“我设想了第一人,他从零开始,他没有文化,没有道德观,没有宗教信仰”⑦。小说的书名具有极强的隐喻意义,“第一个人”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语境下首先让人想到的便是上帝伊甸园里的亚当,“第一”一词更多隐射的是伊甸园神话的内核而非一般的时间概念,他之所以是第一,是因为“他是整个人类后代的鼻祖。他的源初性是道德和天性意义上的,是本体论的。”⑧。将第一个人和亚当结合在一起的联想并非毫无根据,加缪当初确实一度曾想把这本书称作《亚当》,他在1959年记者采访时:“希望可以给这个书名以神话或神秘的感觉[……]事实上,我们中的每个人,包括我自己,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第一个人,我们是自己历史的亚当”⑨。
小说里的“第一个人”既可以指雅克本人,也可以指他寻访的父亲。雅克的父亲代表了第一代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早期移居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有可能否认他们的祖籍,“犹如一入伍就放弃国籍的外籍军团的士兵,犹如被社会所排挤的、在离故土遥远的地方开始新生活的犯人。”⑩遗忘就是他这样的人最终的天国,也是无根生活的结局。当然这第一个人更可能是雅克甚至加缪自己,因为无论是小说主人公还是现实中的作家,他们的父亲都早已去世,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变得坚硬,最后风化碎解、开裂倒坍,因而只有当世之人暂时留下来,继续无根的生活,没有自己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移民的历史上“人人都是第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亚当。加缪曾经说过:“我于是构想‘第一个人’,从零开始,不会念书,也不会写字,不知道什么是道德和宗教,也就是说,那是一种没有老师的教育,小说放在现代历史的革命和战争之间展开”⑪。和所有生长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样,雅克是没有过去的,关于祖先,甚至祖国的概念在他的脑海中都是一片空白。“他们感到自己属于另一类人,没有过去,没有祖居地……只在理论上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国家的公民”,“没人能给他们出主意……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是孤立无援的”⑫。
纯真的构想与上帝的失乐园何其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加缪的伊甸园不是富庶恬静和无忧无虑的代名词。加缪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港口城市阿尔及尔读过的,地中海的阳光、沙滩和海水承载着加缪深深的眷恋和乡愁,但同时那样的故乡又处于贫穷的窘境,每次离开巴黎去非洲时,心里就像打开了新的天地,然而一瞧见郊区的房子,心就揪得紧紧的。正如Jacques Chabrol指出的,雅克的背叛,其实就是第二个从伊甸园里被驱逐出去的亚当⑬。
三、耶稣的诞生
《第一个人》的开篇是一辆风雨兼程赶往索尔弗里诺的马车。车上坐的是满怀希望又忐忑不安的高麦利夫妇,到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一到达目的地,他们的第二个儿子,雅克˙高麦利就降生了。
开篇第一句话“一辆简陋的马车,行驶在布满碎石的路上。黄昏中,大片的乌云朝着东方疾飞。”以阴沉而雄壮的基调预示雅克的出生,这是他记忆所无法到达的地方,他只能通过想象复原场景,因此所谓如实的叙述其实也只是是一种虚构,加缪对过往的还原而做出的努力夹杂着想象和记忆。这样的场景既非记忆,也非历史,因为他是以神话的形式书写的,而神话正是人类史前的记忆。小雅克的出生不能仅仅视为个人意义上的获得生命,加缪在这样出生的场景中赋予了神话的意义。雅克的父母没有具体的名字称谓,只用“男人”、“妇女”来称呼,具有超越个人化的张力。雨夜、如注的暴雨、被淹没的村庄,“这样的出生融入了圣经中关于创世纪、大洪水和耶稣诞生的主题。”⑭对耶稣诞生的隐喻既不是记忆也不是历史,而是神话的形式。加缪向我们讲述了圣经福音中“第一个人”的圣诞,因为耶稣是神袛创造之外的第一个人。《加缪传》的作者同样认为小说的开场“几乎就是《圣经》的出生场面,他的父母坐着马车来到他的出生地,新生儿就是阿尔贝·加缪,阿拉伯人围在四周,其中一人点亮了油灯,就像三博士朝拜初生耶稣一样”。⑮
耶稣的诞生依然紧扣亚当的神话,因为基督教传统中常常把耶稣视为第二个亚当。雅克的出生蕴含了耶稣降生的隐喻,他是一个“全知”,甚至是“超知”的叙述者。对出生的描写超越自知范围,这样的“猜叙”,并非要美化事实,而是给自己寻了一个根。生命诞生的艰难,以及他出生之时就嗅到的一贫如洗的味道,似乎预示了他并不平坦的未来。加缪用希伯来人的神话隐喻为小说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张力和一种史诗般的宏大叙事,这也对应于加缪意在将《第一个人》写成一部非洲大地上《战争与和平》般的鸿篇巨制的雄心。在阿尔及利亚生活的法国移民,生于斯,长于斯,北非是他们的第一故乡,法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欧洲移民者的历史和移民者的后代之间复杂的血缘关系是加缪生活和创作中的一笔痛苦而沉痛的精神遗产,他深刻地感觉到一种无根的状态,没有过往历史,没有伦理道德,没有前车之鉴、没有宗教信,未曾留下一丝痕迹,与世隔绝,永远地被人遗忘。加缪和他笔下的人物像诞生的耶稣一样注定肩负沉重的使命,在历史的困境中踯躅前行。
四、奥德赛式的精神返乡
《第一个人》作为加缪的半自传体小说,显示出一种强大的回归情结,一种西方文学创作中的奥德赛式的返乡神话,这主要体现在对加缪一生创作的回顾式关照和百转千回般的寻根精神之旅中。
1. 创作的回归
学界对《第一个人》的分析和批评视角常常将目光聚焦在加缪的殖民问题的态度上,但事实上小说在叙事的细节上完成了对加缪以往小说的一次回顾和发展,因而这也是一次对作品的回归。加缪说:“每一个艺术家在他的内心深处保留这一眼唯一的泉水,在其一生中滋润着他之所是和他之所说”,“对于我,我知道我的泉水在《反与正》之中,在这个交织这贫穷和光明的世界之中,我曾经长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加缪始终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追寻一种创作的回归,“尽管做出了如此多的努力,要建立一种语言,赋予一些神话以生命,如果我还不能重写《正与反》,我将一事无成,这是我隐隐约约的信念”⑯。《第一个人》无疑是对《反与正》创作源泉的一次回应,是加缪循环式叙事的一次综括。
加缪作品里常有一个默不作声的母亲,早在1937年发表的《反与正》中,加缪就描写了一个严厉的外祖母和一个温柔安静的母亲,《局外人》里默尔索的母亲“一天到晚总是看着我,不说话”;《鼠疫》中的里厄大夫的母亲“一个人坐在窗前,目光凝视着前方”,“最后把她静坐不动的轮廓淹没在黑暗里”。《第一个人》中的母亲依旧是隐忍懦弱的形象。《局外人》和《第一个人》中最后都有对母亲的忏悔。又如,父与子在加缪作品中是合而为一的,其形象可以相互印证。《反与正》里儿子问母亲:“我真的像我的父亲吗?”母亲回答说:“啊,跟你的父亲一模一样!”而在《第一个人》中,母亲也跟他说过,“他们长得很像”⑰。“阿尔及利亚的贫穷和光明”构成了加缪一生创作的源泉,存在于此前的诸多作品之中,而《第一个人》以自传的叙事方式将这些作品中的记忆的印记重新搬到了人生的前台,用回顾式地笔法进行新一轮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人》开始了(但并没有完成)对以往作品的一次关照与回归。
2. 精神返乡
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缪通过《第一个人》主人公雅克的寻根之旅复活了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者的历史记忆,在这些唤醒的记忆中,加缪再次发现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并赋予其所经历过的贫穷和孤寂的生活以一种新的意义,雅克的寻根之旅指向的是一个已死亡多年的父亲和一片如他乡的故土。
一方面,雅克的寻根之旅是以寻找父亲的踪迹开始的。《第一个人》的中心人物是父亲,而非母亲、祖母或叔叔,这是区别于此前加缪作品的一个特点,几乎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追父》,第二部分才是“儿子或第一个人”,第三部分应该是写母亲的。因而以我们能看到的小说现状,它处于父和子的张力之下,即父亲——第一个人和儿子——第一个人之间的冲突和联系。整部小说的出发点正如他在所写的:“二十九岁。一种想法猛地触动了他,身心都受到震撼。他今年四十岁,这块墓板下的曾为人父的人比儿子还要年轻⑱。在第一部分的“寻父”中,叙述者40岁,力图重构自己的童年和父亲的历史,经历了四次寻父之旅:寻墓、重返阿尔及利亚、与母亲和贝尔纳先生重聚,赴蒙多纬寻根,每一个场景都是以旅行开场,在父亲和母亲的马车上追寻生命,乘坐火车前往位于圣布里约的父亲之墓,坐船重返阿尔及利亚,坐飞机去往蒙多纬,雅克的精神返乡物化于每一次的交通工具,每一段的旅程虽然奔赴不同的地方,但都似乎是奥德赛式的返乡之旅——重返精神的故土,寻生命之根,回到“贫穷和光明”的世界之中。然而在墓地里的父亲比墓外的儿子更加年轻,雅克寻找到的父亲只是没有历史和消失于历史的符号。在整个第一部分中,“回忆”这个动词多次出现,而“想象”这个动词也同样常见,因此正如前文所说,“寻父”的过程实际上是被建构起来的,雅克(或者加缪)所追寻到的父亲只能是一个被重新创造和构建的父亲,而非真实意义上的父亲。加缪的精神返乡无法抵达终点。和《局外人》一样,《第一个人》的结局回归到了母亲,展现了对母亲的忏悔和对自己的重新认识,主人公似乎为自己找到了情感的归宿,但本质上两者都发生在父亲缺席的状态下,这样的漂泊返乡实际上不彻底的。
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作为雅克的故乡却是一个他魂牵梦绕却又意欲逃离的地方。离开阿尔及利亚无论对加缪的人生还是创作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离开阿尔及利亚也使加缪在精神上成为背井离乡的流浪者和漂泊者。阿尔及利亚的生活使加缪的作品植根于阿尔及利亚,也让他与阿尔及利亚结合在一起。也正是这个原因,加缪内心是不能接受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对他来说,阿尔及利亚是他难以割舍的情怀,是他艺术生命的母体。加缪一生都在维护他心中和谐的阿尔及利亚的形象,只不过他的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图”是虚无飘渺的,仅平添了他对青少年时代的一些美好生活的回忆而已:旧时的朋友只剩下“一张张已经几乎认不出来的苍老的面孔”,盛大的晚会“就像一座使我迷失方向的城市”“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和他形影不离,他决意尽可能少回阿尔及利亚”⑲。因而魂牵梦绕的故园也只是作者想象中建构起来的乐土,回忆纵然美好,童年的故园也只存在于想象中,乡愁依旧,故园不再,加缪奥德赛式的返乡终究无法抵达终点。
结论
《第一个人》是一部寻根小说,加缪用他那双热情而冷漠,敏锐而真挚,幸福而痛苦的眼睛在文中探寻他的家庭史,也探寻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史。借助于希伯来和希腊神话的力量,加缪为作品注入了史诗的雄壮和悲凉,小说的主人公“雅克”作为北非法国移民的代表,如“第一个人”亚当一般没有祖先、没有历史、没有根基,如踯躅前行的耶稣一般在20世纪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在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殖民帝国里发出自己的回响,为寻找灵魂的父辈和精神的家园如奥德赛一般执着返乡。
①1957年12月17日,瑞典文学院为加缪授予加缪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评语。
② “Vve Camus”出现在小说的开头:“说情者:寡妇加缪,致永远无法读此书的你”;热尔曼(Germain)先生是加缪的小学老师,对后者有知遇之恩,加缪在诺贝尔奖致谢词中提到了这位老师。
③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肖云上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第2页。
④ Josephe Jurt, “Le Mythe d’Adam, le Premier Homme d’Albert Camus”, In PEYTEL Gérard (eds).. Bordeaux: Université Bordeaux III, 2002, p.309.
⑤ Ibid., p.309.
⑥加缪在众多场合宣布自己并非一个基督教徒,但在许多作品中恰恰清晰地表现出他对基督教精神的理解和领悟,因此学界将加缪视为一个非信徒(non-croyant),而非一个无神论者(athée)。
⑦ 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肖云上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第3页。
⑧ Josephe Jurt, “Le Mythe d’Adam, le Premier Homme d’Albert Camus”, In PEYTEL Gérard (eds).. Bordeaux: Université Bordeaux III, 2002, p.311.
⑨ Ibid. p.310.
⑩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肖云上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第4页。
⑪ 同上,第585页。
⑫加缪:《加缪文集》,郭宏安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第130页。
⑬ Josephe Jurt, “Le Mythe d’Adam, le Premier Homme d’Albert Camus”, In PEYTEL Gérard (eds).. Bordeaux: Université Bordeaux III, 2002, p.314.
⑭ Ibid., p.312.
⑮ 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肖云上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第4页。
⑯ 加缪:《加缪文集3》,郭宏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第4-13页。
⑰ 加缪.:《加缪文集》,郭宏安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⑱ 同上,第20页。.
⑲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肖云上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503-504页。
(责任编辑: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