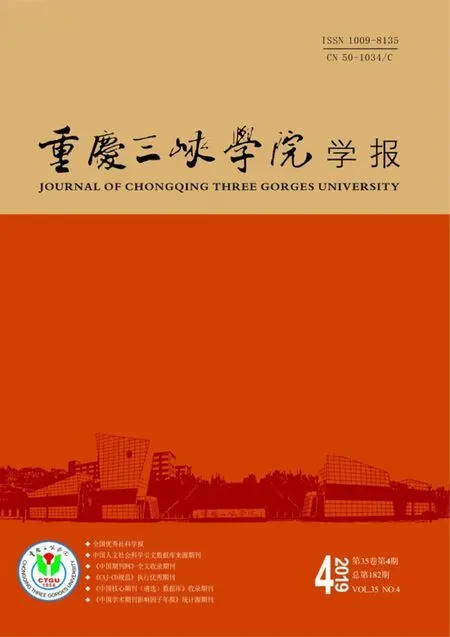论古代三峡地区农业垦殖状况与本土文学家分布之关系
2019-03-23周长慧
李 俊 周长慧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404120)
由于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必然受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较之经济繁荣、文化昌明之地,古代三峡地区本土文学家相对较少,且文学成就相对不高,与该地区长期以来较低的农业垦殖水平密切相关。
一、古代三峡地区农业垦殖与本土文学家分布关系概述
三峡地区的人类活动可以上溯至204万年前的巫山人时期,成熟的经济活动也可以上溯至公元前4400—前3300年时期的大溪文化。也就是说,距今6 000多年前,三峡先民们已经开始在这一地区进行稻作、渔猎、圈养家畜等经济活动了。虽然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开展较早,但一直因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方式粗放、民族构成复杂、战争动乱频仍等原因,较之中国其他地区,三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许多,直到现在,渝东、鄂西之地仍是中国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中国古代,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是农业经济,蓝勇教授《长江三峡历史地理》一书对三峡地区农业发展状况——尤其是农业垦殖水平作了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三峡地区农业发展的基本面貌。
相对于全国的总体发展水平,从汉至清,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以下特征:人口偏少;人均耕地不多;垦殖指数也不高。蓝勇教授计算,“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有耕地8 275 360顷,人59 594 978口,人均耕地13.88亩”;“汉代三峡地区已开垦的耕地约为4 797 563亩(合3 290 547公亩),垦殖指数为2.35%”;“唐开元天宝间全国有耕地775万公顷”,包括渝州、涪州、忠州、万州、开州、夔州、归州、峡州在内的三峡地区有耕地4 145 151亩,垦殖指数为3.1%;宋元丰间长江三峡各州(夔州、恭州、南平军、涪州、忠州、万州、开州、云安军、梁山军、大宁监、归州、峡州)耕地总数6 465 628亩,平均垦殖指数为5.4%;明代三峡地区除夷陵州本州垦殖指数为10.8%、长寿为48%、开县为27.9%之外,归州、巴东、兴山、奉节、巫山、云阳、万县、大宁、南川等州县的垦殖指数在1.2%~5.7%之间;清代嘉庆时期三峡地区的平均垦殖指数在7.4%,其中巴县、长寿、涪州、江北厅、忠州的垦殖指数分别为31%、22%、22%、26%、10.3%,奉节、巫山、云阳、万县、开县、丰都、石砫、东湖、归州、兴山、巴东均在4.0%以下①本文所引垦殖数据均参见蓝勇《长江三峡历史地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这些数据表明,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较之同时期的经济活跃地区,长江三峡地区农业生产处于相对滞后、农业垦殖指数相对较低的状态。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中国古代,将上述数据作为本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指标,足以说明长江三峡地区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版图中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因此,从社会生产与文学发展之间制约与被制约关系的角度进行审视,与本地区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几近一致的是,文学的发展也处于一种长时期的衰败与凋敝状态。三峡地区本土文学家相对较少,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济对文学的上述制约作用,出自宽泛意义上的文学发展观念,如果从微观上进行审视,三峡地区农业生产状况对文学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相当明显的。
从中国古代社会的耕读文化来审视农业,则农业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生产方式,或者一种单纯的谋生策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安放生命的方式,一种价值择取方式,一种精神存在方式——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必然广泛而深远地影响该地区的文学发展。因为该地区的农业生产采用何种方式,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直接关联于本地区是否形成浓厚的耕读文化氛围;而这种氛围的形成,与本地区人们的精神存在与表达方式密切相关。在文学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主要精神表达方式的前提下,农业生产水平及其与之相连的耕读文化是否蔚然成风,则注定关联着文学的繁荣与凋敝。
耕读文化是深入古代中国文化血脉中的文化形态。尽管先秦时代,有人将耕作之事排除在君子修为之外,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1]1282卷三十二《卫灵公下》并将请求“学稼及为圃”的学生樊迟指斥为小人:“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1032-1033卷二十六《子路上》孟子将劳心劳力截然分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2]241《孟子章句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不过,孔孟时代亦有荷蓧丈人、许行之属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主张践行耕作与人物的精神修为相与为一,并行不悖。荷蓧丈人斥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1]1457卷三十七《微子下》许行则理直气壮地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2]240《孟子章句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儒鄙视稼穑的观念开始丕变,崇尚耕作并将其与修身、道义、德行、学问等联系起来,成为一种颇常见的观念。如扬雄《法言》:“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3]卷二范晔《后汉书》:“(袁闳)服阕,累征聘举召,皆不应。居处仄陋,以耕学为业。”[4]卷四十五《袁闳传》葛洪《抱朴子》:“躬稼基克配之业,耦耕有不改之乐……造远者莫能兼通于歧路,有为者莫能并举于耕学。”[5]卷三十五《安塉》《晋书》记朱冲“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6]卷九十四《隐逸传》。颜之推《颜氏家训》认为“生民之本”,在于“当穑而食,桑麻而衣”[7]卷一《治家》。可以说,自汉以后,及至中国古代社会终结,耕读文化总是一种与传统农耕经济形影相随的文化形态。
耕读文化的存在,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的。一是形成耕读传家、诗书传家的文化传承模式,进而催生了地域之中稳定的书香门第、世家大族,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家族以及相应的家族文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二是耕读文化形态下世家大族在相关地域中的定居性,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该地区包括文学风气在内的文化风气,为地域文学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三是耕读文化不仅为文学家提供了相应的写作题材,也提供了文学家感受、体验生活的独特方式,所以关于归耕、羡农、哀农、悯农等社会生活内容,常出现在历代诗人笔下,经久不衰。
成熟的耕读文化形态在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在长江三峡地区,因为这样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所以也制约了本地区较为成熟的耕读文化形成,进而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从地形地势来看,如常璩《华阳国志》所说“江州以东,滨江山险”[8]卷一《巴志》,高峡深谷密布,平地绝少,农业规模小,生产方式粗放。峡中民族成分复杂,多獽、蜑、獠之属,他们偏好渔猎。所以峡江地区就是一幅典型的垂直农业景观。艰难穿行过峡江的范成大,对三峡地区农业生产状况有生动描述:峡谷底部,渔户打鱼;江滨平地之处,是小块的稻田,“山骨鳞皴火种难,山下流泉却宜稻”[9]222诗集卷十六《峡石铺》,稻田甚小,所产并不藉以自给,“东屯平田粳米软,不到贫人饭甑中”[9]220诗集卷十六《夔州竹枝词九首》其七;山腰及至山顶,便是刀耕火种的畲田农作方式,“峡农生甚艰,斫畲大山巅”[9]217诗集卷十六《牢畲耕》。峡江地区兼有畜牧业,但谈不上规模,因地形原因,显得相当矮小,如范成大所云“峡马类黄狗,不能长鸣嘶”[9]205诗集卷十五《初入峡山效孟东野》。这样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导致了前述社会经济落后、垦殖指数较低、人口长时期低水平徘徊等后果。外人来此,所见所闻的最初印象,便是落后、贫穷。如王十朋赴任夔州知府,感慨“郡城深僻处,车马罕经过”[10]诗集卷二十二《十八坊诗·和风》。陆游来万州,认为此地乃“峡中天下最穷处”[11]《剑南诗稿校注》卷三《偶忆万州戏作短歌》;忠州也好不到哪里去,“忠州在陕(峡)路,与万州最号穷陋,岂复有为郡之乐”[12]110卷五?峡江地区农垦经济水平的直接后果,是形成不了平原地区那样发达的庄园式封建经济,因此也不能形成平原地区常见的宗族文化恒定承传的封建大家族。由于较低的农业产出,居民们不得不为果腹蔽体而疲于奔命,耕作更多的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不是安身立命或者价值择取、精神存在的方式,更不会成为他们自由审美精神的表达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边耕作、边读书、边写作的耕读模式,对生存于其中的人们来说,必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此,历史上相当长时期内,三峡地区并没有出现像中原、关中、江南、成都平原那样的耕读文化,也绝少这种耕读文化背景下兴起的封建大家族;文学世家、家族文学以及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本土文学等耕读文化的伴生物也踪迹寥寥。本土文学家相对较少,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二、明、清两代三峡垦殖水平与本土文学家分布状况关系详解
上述峡江地区农业生产水平较低,耕读文化不发达,是从总体评价上的相对说法——一方面是相对于中原、关中、江南、成都周边地区而言的,另一方面是就三峡地区总体情况而言的。该地域内耕作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比如巴县、长寿、宜昌等地,经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后,涌入了来自文化更为发达地区的移民,不仅带来了迥异的文化观念,也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先进的生产方式。因此,这些地区在明、清两代的农业生产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前文所引数据说明了这一点:明代,夷陵州、长寿、开县垦殖指数均超过10%,长寿县超过了40%;清嘉庆时期三峡地区的平均垦殖指数达到7.4%,其中巴县、长寿、涪州、江北厅、忠州的垦殖指数分别为31%、22%、22%、26%、10.3%。
移民们带来的先进耕作技术,以及包括耕读传家在内的更为先进的文化观念,不仅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也使当地产生了一些藉诗书文化恒久传家的大家族。比如明代巴县便出现了刘氏、蹇氏、牟氏、曹氏这些书香门第。
民国二十六年(1937)修撰的《巴县志》记载:“《明史》称县刘氏世以科第显,刘氏自撰《科第志》,县人王应熊为叙,谓‘巴之世家,明初称蹇氏……又牟氏、曹氏,科第亦号蝉联,惟刘氏子孙则累世弥衍’。”[13]356卷十《人物列传中之上·诸刘传》
上述家族渊源,今已不能逐一准确考证,但如果对巴县刘氏进行考察,就会说明耕读文化的引进对一个地区文学家兴起的重要性。关于刘氏在巴地的兴起,《巴县志》说:“(刘氏之先)本家于湖广兴国州之乌崖,《兴国州志》云:乌崖刘氏为宋太师刘韐之苗裔,元至正间有珉一者始来迁。”[13]356卷十《人物列传中之上·诸刘传》说明刘氏家族来源于耕读文化更为成熟的江南之地。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之兴起,家族文化的世代承传,在科举选拔的古代,不仅带给家族因子弟频频及第、出仕入宦的荣耀,如巴县刘氏一门便有刘刚、刘规、刘春、刘台、刘彭年、刘鹤年、刘起宗、刘世会、刘世赏、刘綡、刘道开、刘如汉等先后登科;而且在事实上促成了地区内文学家族的产生,如刘氏一门便不乏喜欢吟诗作赋的文学家:“刘刚,字弘毅,性英敏,能吟咏,尤工楷法。”[13]356卷十《人物列传中之上·诸刘传》“(刘)台字衡季,号是闲……与兄春并有文名,兄弟皆解元,一时艳称职。台工诗文,尤长小令。”[13]359卷十《人物列传中之上·诸刘传》“(刘)道开……顺治甲午,子如汉举于乡,己亥成进士,入翰林院。道开就养入都,逾年卒。道开为人质朴好古……又有诗文集《拟寒山诗》《巴合王子美死节传》数种。”[13]365卷十《人物列传中之下》“刘慈,字康成,号鹭溪,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举人……好古力学,著有《鹭溪集》。”[13]367卷十《人物列传中之下》“(刘)如汉,字倬章,有《山居诗》,论者方之北宋名家云。”[13]366卷十《人物列传中之下》等等。
明、清两代如巴县刘氏这样偏好文学的家族,对当地有风气渐染的效果,假以时日,则文化风气渐浓,世风为之一变,耕读时尚蔚然而兴,不仅如刘氏子弟一样,登科及第者甚众,而且喜好吟诗作赋的人更多,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遍检三峡地区各州县方志及相关文献,其实会发现一个问题:各州县中,明、清两代擅长文学的人——即本土文学家①本文主要依据三峡地区相关州县方志文献采集文学家名录,除方志《艺文志》部分著有诗文的本土人物之外,方志“人物”部分所载“以文显”“工诗赋”的各类人物也一并认定为相关州县的本土文学家。,从数量上来说并不均衡,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多者如重庆府巴县、宜昌府宜昌县(清称东湖县)分别有39人、28人之多,少者如巴东县,则阙如焉。撇开巴县、宜昌县分别是府治政治、文化中心是因素外,这种不均衡现象与农业生产条件有无联系呢?不妨将明清时期长江三峡各地文学家数量与农业垦殖指数做一比较。
巴县:无明代数据,清代垦殖指数为31%。据嘉庆《四川通志》、民国《巴县志》,计有江朝宗、明辅、蹇英、蹇达、刘台、刘綡、月文宪、邓之屏、倪斯慧、吴嘉宾、王应熊、邓璜、李之华、刘如汉、刘纲、刘道开、刘慈、李以宁、周开基、周开丰、覃为谷、高继光、罗醇仁、冉广燏、吴伯裔、周国彦、朱沣、孙珏、龚有融、文现瑞、黄中瑜、范坦、邹峄、潘清荫、梅树南、汪世芳、王金成、杜成章、吴淞39位文学家。
长寿县:明代垦殖指数为48%,清代下降为22%。据嘉庆《四川通志》、民国《长寿县志》数据,计有杨应春、黄之久、戴锦、郑明郁、李先植、李开先、李瑞鹤、余光、韩芳、韩鼎晋、杨世瀛、宋继璟、杨树棻13位文学家。
涪州:明代垦殖指数为48%,清代降为22%。据嘉庆《四川通志》、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数据,计有何轼、何铠、何行先、夏国云、夏子云5位文学家。
丰都县:无明代数据,清代垦殖指数为4%。据嘉庆《四川通志》、民国《丰都县志》数据,计有林明俊、熊兰征、王怡3位文学家。
石砫直隶厅:无明代数据,清代垦殖指数低至0.38%。据嘉庆《四川通志》、道光《补辑石砫厅志》数据,计有秦良玉、马宗大、马斗慧、冉天拱等5位文学家。
忠州:无明代数据,清代垦殖指数为10.3%。据嘉庆《四川通志》、道光《忠州直隶州志》数据,计有田登年、周琳、成文运、杜鹤翔、许杰、李国凤、朱帜、杜炳、郭凭山9位文学家。
万县:明代垦殖指数为1.8%,清代上升为3.32%。据嘉庆《四川通志》、同治《万县志》数据,计有王淑、陈士杰、何志高、沈巨儒4位文学家。
开县:明代垦殖指数为27.9%,清代降为3.78%。据嘉庆《四川通志》、咸丰《开县志》数据,计有汪安宅、傅复2位文学家。
云阳县:明代垦殖指数为1.8%,清代为1.67%。据嘉庆《四川通志》、民国《云阳县志》数据,计有鄢绶、王瓒、王彦奇、魏翰、曾在衡、刘海鳌、庐志修、郭文珍8位文学家。
奉节县:明代垦殖指数为1.5%,清代为2.14%。据嘉庆《四川通志》、光绪《奉节县志》数据,计有傅作楫、马天麟、刘諹3位文学家。
巫山县:明代垦殖指数为2.3%,清代为1.97%。据嘉庆《四川通志》、民国《巫山县志》数据,计有杨士禄、王朝桓、余价、向智、柳林5位文学家。
巴东:明代垦殖指数为5.7%,清代为0.69%。同治《巴东县志》无本土文学家记载。
秭归(归州):明代垦殖指数为4.6%,清代1.82%。据同治《宜昌府志》数据,计有向阳昶、胡吉臣2位文学家。
夷陵州(清东湖县):明代垦殖指数为10.8%,清代为3.26%。据同治《宜昌府志》数据,计有郭思温、陶性、王篆、陈禹谟、陶若曾、雷思霈、杨文燃、刘戡之、冯三溪、龙万化、王庶民、王永禩、龙为纪、郭键、罗宏备、陈士望、刘廷僖、戈保泰、陈嵩极、张天然、郭光禄、王言惠、何毓秀、毛一骢、刘家麟、刘家凤、吴秉纶、罗佳珩28位文学家。
上述省志、府志、县志的写作者选择材料时难免存在兴趣上的偏差——比如有的重视人物的武功,有的重视人物的治绩,有的重视人物的德行,有的重视人物的文学成就,记录人物生平事迹时,并不能做绝对全面的描述,所收录的各地文学家并非没有遗漏。不过,因为中国古代重视诗教、重视立言的文化传统,一般说来,志书的写作者并不漠视人物吟诗作赋的才能、著书立说的成就。本文所引志书都有“艺文志”卷,除《巴东县志》外,其他府、县志所载,都不乏这方面才能与成绩的人。这足以说明,古代修纂方志的人还是非常重视考察人物的文学才能的。因此,本文依据省府县志等文献来把握三峡地区各县文学家的分布情况,还是有说服力的。
上述文学家的排列,采用了沿江而下的顺序。人数的多寡呈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重庆府所在地巴县39人居首,宜昌府所在地(明代为夷陵、清代为东湖县)29人次之,然后依次是长寿13人,忠州9人,云阳8人,涪州、石砫、巫山各5人,万县4人,丰都3人,奉节3人,开县、秭归各2人,巴东无。各地文学家的数量,总体上与当地垦殖指数成正比,垦殖指数越高,文学家数量就越多,巴县、长寿、忠州三地表现得尤为明显。宜昌府所在地的垦殖指数,放到整个三峡地区看,其实并不高,不过考虑到这一地区居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地形地势特点,其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比高峡深谷的三峡腹地要高出若干倍,所以,即使垦殖指数不高,开垦的土地面积总量不大,但其农业生产比三峡腹地更发达,应该不是一个悬疑的问题。加之宜昌更靠近中国文明的发达区域,故其文学家数量比峡中诸县更多,也有理可循。当然,农业生产及其相应的耕读文化形成、成熟情况,只是决定该地区文学发展、本土文学家分布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除此之外,诸如所在地的文化传统、政治地位、社会秩序等,也是决定该地文学家分布的重要原因。巴县、宜昌本身就分别是重庆府、宜昌府府治所在地,作为地区政治中心,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事业相对其他地区较为发达,也是自然的事情。另外如石砫,由于秦良玉等人在明末清初积极应对各种变乱,外来势力始终不能踏入石砫一步,号称四川唯一太平的地方,所以在相对安定和谐的社会背景下,其文学家数量也达到了5个。
三、结 语
上述分析表明,包含三峡地区农业垦殖状况在内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本地区文学相对凋敝、本土文学家稀缺的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考察三峡地区本土文学以及本土文学家的历史发展状况,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还需关注很多因素,诸如民族构成状况、居民精神特性、地处蛮荒、战争频仍、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等。历代兵燹、灾害造成文学文献的焚毁状况,也必须高度重视。如同治《宜昌府志》载:“归州生员向昞吉尝考其(繁知一)生平,为之立传。”但遗憾的是,“惜教匪焚归州,遂失其稿”[14]484卷十三《士女传上》。乾隆《巴县志》亦云,巴县地接“坤舆灵淑之气,磅礴郁积,必有瑰奇卓荦之人挺生其间。巴自炎汉来,人才接踵代生”,但“自志乘毁于兵火,前贤懿范邈矣,难追簿书”[15]卷九《人物志》。
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6]作为一种历史结果,三峡地区本土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三峡本土作家数量的多寡,并不单单取决于社会结构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众多要素共同参与、相互作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