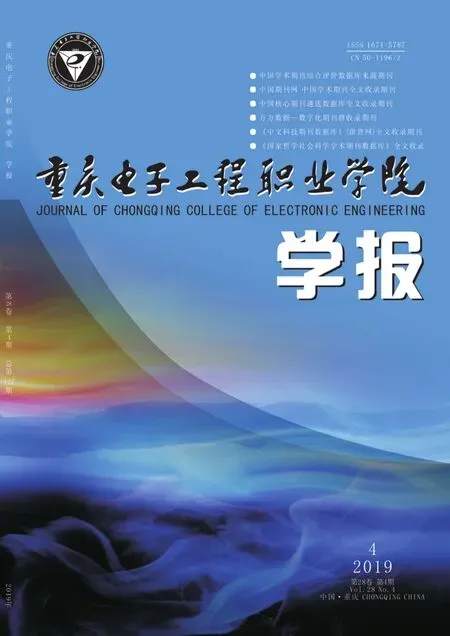日本文学中的“物哀”美学的嬗变
2019-03-22马亚琴
马亚琴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东语系,湖南 长沙 410000)
日本俳句有言“一明一灭一尺间,寂寞何以堪”,世事变迁,皆能引起内心的触动,在深入肺腑的五感间发现必然的寂寞,再由寂寞衍生出各种情致,拥抱周遭的自然人事。有感于眼,有怀于情,有动于心,在对微渺意识的耽溺中感悟世界的宏大,这就是日本美学框架下的“物哀”。关于“物哀”美学的内涵,本居宣长、大西克礼等学者皆有论述,本文将根据新的维度进行分析,在准确把握“物哀”意涵的基础上探究“物哀”美学在日本文学中的表述嬗变。
1 “物哀”美学的内涵
某种思想美学的产生与物质世界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1]。日本远离大陆、四面环海的区位特征和频发的自然灾害给日本国民带来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压抑感。不知何时会发生的灾难如同达摩克里斯之剑悬于日本国民的头顶,造就日本民族对生命的矛盾情绪。日本自古以来崇尚精细柔和的美,魏晋玄学和晚唐蕴含着悲怆意味的文学审美观念对日本思想界产生深远的影响,禅宗“五蕴皆空”的宗教旨趣在日本得到推崇。无法改变的自然因素和长期浸润的思想文化使得 “物哀”意识影响日本的民族心理基因,日本国民认为残月、花蕾、花落中潜藏着一种令人惋惜的哀愁情绪,会增加美感[2],留恋无常,看淡生死,在永恒的痛苦和无奈中寻求短暂愉悦的审美意趣由此出现在日本的文艺创作中。“物哀”是主体对外在事物的情感共振,本居宣长在《紫文要领》中解释为“把万事万物都放到心中来品味,内心里把这些事物的情致一一辨清,就是懂得事物的情致,就是懂得物之哀”。“物”并非某类具体的事物,而包含世间万事万物,“哀”不止哀伤愁绪,而蕴含着更加玄微复杂的情愫。触物而感物,在体验、思辨的过程中达到个体情感与外部世界的融合,即是“物哀”美学的基本内涵。久松潜一在《日本文学思潮史》中将“物哀”美学分为感动、调和、优美、情趣和哀感五类,最突出的是哀感,在五维境界下阐释“物哀”美学,方能全面精准地把握其深层内涵。
1.1 感动
感动是个体接触外界事物后最基础的情绪感应,直观的视听反映至大脑,经内部心灵发酵而产生同情、震惊、支持等意识。此层面的“物哀”尚未具有民族性,仍符合普世审美,不管任何民族、任何性别、任何年纪、任何教育背景的个体,在面对周遭世界时都会不自觉地触发心理活动,外部景色事件走进内心时,已经带有喜怒哀乐的情绪标签。在初春欣赏漫山遍野的樱花,在山涧峡谷观赏洁净的雪,在幽深庭园中垂帘听雨,这些寻常的活动都能引起感动。应当说感动是“物”与“哀”互鉴的初级结果,“物”还不是引起“哀”的物,“哀”还没有因“物”而风起云涌,所有的情绪都游离在相对平和的范围内,可以被主体自主控制。记贯之在一首和歌中说:“虽说呜呼哀哉的叹息并没有什么实用,可是碰到触动人心的事,总会情不自禁地叹息啊。”情不知所起是感动的根源,在客观事物中体会到美,但这种美还没有升华为审美意蕴,既不指向“物”,也不指向“哀”,是主体心灵相对独立的结晶。
1.2 调和
关于“物哀”美学,最普遍的片面解读就是限制“哀”的范畴,将其视作针对特定事物的哀伤情感。实际上,由于日语的暧昧性,“哀”有着与字面不同的释义。本居宣长、叶渭渠、王向远都从词源学角度对“哀”进行考据,《古语拾遗》《万叶集》《日本书纪》《古今和歌集》《后撰和歌集》等日本文艺作品皆有“哀”的用例,基本用作感叹词以修饰被感叹的事物。“哀”包含悲哀的情思,同时含有惊叹、怜悯、同情、幽哀、悲壮、壮美等因素,“物哀”是动态运动的思想结构,其审美表述随主体心境的变化而改变。当“物”与“哀”间产生连续的联系,此时的主体心理已经超越感动的范围,在“物”启发下激起激烈的波动。所谓调和,指消解对立和矛盾,以和谐的姿态包罗万象。主观情感与客观世界的碰撞使得各种情绪此起彼伏、此消彼长,此时的心与物已经拥有深刻的指向性,“一叶知秋”“睹花洒泪”,个中包含的情思难以统论概括,在繁杂的思绪中感悟稍纵即逝的美,任由心灵在喧嚣的尘世中细细揣摩。
1.3 优美
指向“物”的“哀”回归本源,主体调和诸思绪而达到和顺的审美状态,即来到“物哀”的第三层境界。王国维提出“美之为物有两种,一曰优美,二曰壮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向来侧重消极审美,在对自然神性的高度崇拜中隐含着时光易逝、难以追怀的无可奈何,他们注重物呈现出来的简洁平和的风雅,习惯在纤细雅致的情调中体悟艺术的崇高。“物”勾起“哀”的无限拓展,以悲观的眼光看待万事万物,在悲剧性中发现潜流在灵魂中对真善美的渴求,由此消弥悲与美的隔阂,在宏大的世界观中实现主客体的对话与和解。“物哀”有不同的程度,正如听到陌生人的事情和听到朝夕相处的朋友的事情,感受不同,同是感知物哀,熟悉与不熟悉有很大差别[3]。辨别粗拙和高雅,摆脱表面的知物哀,真正透解“物”的肌理,通世故而晓真理,以真情体会细小琐碎的美感,突破物的平庸而获得超脱的生命情志。
1.4 情趣
“物哀”美学是私情的美学,不同主体对同“物”的感触截然不同,初层次的感动经过调和以获得美的真谛,达到优美的情状,这种情绪再被审美主体提炼加工而成为独特的志趣。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主人公邂逅舞女,两人互相钟情却从未表露自己的倾慕,若有若无的情愫在两人的对视和动作间积聚。两者似乎能察觉对方对自己的感情,又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含混暗昧的感情中,似是而非的爱情在男女主人公间弥漫,制造出缠绵悱恻的情趣。“物哀”中的情趣是纯粹的文化精神,有强烈的个人化特质,主体的感情投射到所接触的事物上,再由物来表达万千细碎的情绪,在这些连绵起伏的欢喜忧愁中深化主观体验,到达情景交融的忘我状态。“物哀”不是机械化的格物,没有标准、限制和要求,凭借感性直觉的“哀”往往因用情至深而发生扭曲,可能会违背社会主流伦理道德观。但“物哀”并非要设立评价善恶的道德框架,而强调情起时难以自禁的兴叹,置于艺术思维下的“物哀”因而是对美的真实诠释,是放下所有思绪后平地起波澜的精神,是个性的表达,是无法言喻的审美情调。
1.5 哀感
久松潜一将哀感视为“物哀”美学的主体,这与叶渭渠所说的“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有共通性[4]。哀感触发“物哀”,同时是“物哀”的皈依和消化,由哀愁衍生的悲叹、憧憬、爱怜、惋惜等情绪经主体心灵的调和,取得特别的情趣,再在主观意绪的循环往复中重新体验到淡淡的、徘徊的哀。赏樱即体现典型的日本“物哀”美学,在春天绽放的樱花有粉嫩俏丽的颜色和热烈绚丽的品性,然而花期短暂,当日开放的樱花可能翌日就已随风散落。看到洋洋洒洒的落樱,能深切地体会到转瞬即逝的美,在惊讶、喜悦过后,睹物思人而涌现复杂的情绪,当一切思绪回归平静,看着满地萧瑟而感到透入骨髓的,难以用言语表述却充斥着全身细胞的哀感,倏忽能感知变迁世事中的宝贵年华和生死法则。哀感是对“物哀”超越后的沉淀,缱绻的余绪挥之不去,使得主体和客体都沉浸在朦胧的氛围中,在时隐时现的情绪波动中达到性情的平衡,完成清雅闲寂的审美体验。
2 日本文学中“物哀”美学的嬗变
在悲凄荒凉的心境中产生出的悲剧美、忧郁美,就是“物哀”之美,作为日本传统文化核心和文学创作特色,日本文学中的“物哀”美学在基本稳定的精神内核中有所嬗变。总体来说,“物哀”美学在文学中的表现由含蓄抒情到展现极端化的色彩,再到在哀中揉进希望和救赎,呈现积极干脆的精神渴望。源自生命本真需求的“物哀”审美,在与儒家义理的抗衡中,逐渐取得优势的地位,并在作家个性化的写作创新中得到不断深化[5]。
紫式部在平安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是“物哀”审美的源流,她在写作中系统地贯彻哀情,据统计,仅“哀伤”一词在四千余个词汇中的出现率就超过一千余次[6]。小说描绘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被降为臣籍的皇子源氏的爱情和命运,源氏12岁与葵姬结婚,但不改寻欢作乐的本性,与藤壶、花散里、末摘花、紫姬等众多女性保持着情爱关系。他有着无法排解的浓烈感情,因幼年失母而格外钟情长相酷似母亲的女性,同时不甘寂寞,屡次做出乱伦出格之事。源氏不矫揉造作、不遮掩情欲,他敢于直接表达情感诉求,真切认真地对待每段感情,但无法避免自己和周边女性的悲剧命运。葵姬被杀、紫姬病逝、三公主落发为尼、源氏在饱经伦理谴责和情感煎熬后选择出家,书中的人物即使有片刻的欢愉,仍无法摆脱不幸的命运,由此贯穿着浓厚的宿命思想和低迷婉转的哀感。“物哀”在《源氏物语》中的美学表达是隐晦内敛的,通篇弥漫着哀绪但不点破,作者从“物哀”出发勾勒出有悖于寻常道德的善恶标准,书中的主人公皆通情而知物哀,在人世百态中表现着最真实的感情。哀婉幽怨的风格使得《源氏物语》中的“物哀”具有浪漫疏离的色调,人物充沛的感情和纤细的体验有古典美,表现出他们在苦情中的痛苦、自责和彷徨。
在“物哀”美学的发端下,日本的文学家普遍怀有哀意识,擅长塑造无常的命运故事。江户时期的小说家井原西鹤共创作小说二十余部,从前期描写男欢女爱的艳情小说到后期关注社会现实,反映市井生活的町人小说,他的作品中含有追求物欲和情欲时盛衰难料的宿命论思想。以短篇《道场夜话平太郎》为例,从伊势远道而来的男子因为不擅经商,在大年三十晚回家却被妻子赶出家门,只能落魄地到寺庙中迎接新年。《若死同浪枕》讲述神崎式部在同僚的托付下安排两人的儿子一同出行,因遇到风暴导致同僚的儿子死亡,神崎式部深感愧疚而命令自己的儿子陪同赴死,随后自己和同僚出家为僧。这些故事题材各异,但都蕴含着鲜明的哀感。幕府君主臣从的统治体系和市民阶级不断兴起的对人性的号召间出现激烈的矛盾,对信义、忠诚、孝悌等义理的无条件服从背后是人情的抑制和忍耐。井原西鹤书中的主人公常常出家,或者出现与寺院有关的意象,以此渲染宗教化的“物哀”审美。他们的愁绪和悲情,在耽于色欲的市井冗杂中有着缠绵绮丽的平民特质。
生于江户中后期的为永春水是人情本的创立者,他在《春色历梅》中描绘美男子丹次郎和诸女性的恋爱故事,用词大胆直接,文风热烈绚烂。在世俗男女情爱中,主人公通常面临着情感折磨和爱欲纠缠,囿于日常生活的他们不再被严苛的义理束缚,表达欲望绝不拖泥带水,悲痛、嫉妒、失落等负面情绪都淋漓地表达出来,町人小说中清淡的哀感在这里变得极其浓烈。人情本中的物哀继承日本文学的“物哀”审美传统,同时与市民阶级的审美趣味相结合,被赋予痴情、哀恸、执着的调性[7],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性中的本能欲望。虽天宝改革时人情本被施罪遭禁,但其正视至深至真的人情,重新审视日本民族对凋落之物天然而生的审美需求,将原本隐约凄美的“物哀”意识用壮烈明艳的形式呈现出来,推动“物哀”美学在日本文学中的持续演变。
日本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以更凄凉极端的状态表现“物哀”美学,川端康成天性忧郁,在佛教思想和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将“决绝”作为作品的底色。《夕阳下的少女》《少女的港湾》《少女开眼》等少女主题小说中的主人公有强烈的感情冲动,她们追求爱的感觉,遵从内心的选择,却因现实的残酷而无法获得圆满的结局。美只存在于瞬间,即使努力把握也会如水般流走,在用情至深而不得后,等待她们的只有挣扎和死亡。川端康成改变日本传统审美观中女性柔弱、逆来顺受的形象,使她们有自己的欲望和选择,并给予她们充分的怜惜和同情。这些女性纯真的感情期待因各种原因落空,映射出生活的悲观和虚无,曲折的情节在欲说还休的伤感氛围中强化哀感,使得“物哀”的美学表达变得极致。《雪国》是川端康成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之一,讲述一位男性与两位女性的三角恋故事。艺伎驹子爱上艺术研究员岛村,岛村却爱慕少女叶子,他清楚驹子对自己的感情,却苦涩于驹子的生存困境,倾心叶子却可望而不可即。三角恋中的任何人,都在情欲的苦海中漂流,有着空虚而沉寂的生命状态。川端康成习惯用清幽寂静的景色描写和细腻唯美的心理描写来奠定悲伤的基调,再用人物的死亡来增强悲剧性,虚空幻灭、超脱净逸的“物哀”美学由此成为作品的主旋律。
发展至20世纪,村上春树因轻盈雅丽而饱含深意的风格被视为日本文学旗手。他精准地掌握日本文化精神特质并将其融进作品中,他的小说秉承并创新“物哀”美学,在空、寂、凄、虚的审美视野中增添些许明快的色调,使得物哀之美在表现消极情态的同时更加符合普世价值观。村上春树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挪威的森林》中人生屡经打击而后坚强走出困境的渡边,《且听风吟》中被不辞而别的女友所困扰的少年,《眠》中在失眠中探究人生的家庭主妇。这些人物敏感但不脆弱,颓废但不自暴自弃,他们借由个体命运窠臼思考自己的生存价值,挖掘出其中既定的孤独、酸涩、无奈。人生的本质向来悲大于喜,坦然面对该失去的,经受该痛苦的,记住该留恋的,在萌生感情的时候任情而动,即使过去过于悲伤不愿缅怀,未来不甚美好无所期待,尚可以通过顺其自然向世界妥协。除《源氏物语》以来一脉相通的凄静淡然的哀感,村上春树的“物哀”美学还兼有一抹亮色,有对悲苦人生的通达和向生的期许。既然死亡总会到来,为何不先好好活着,没有脱离传统物哀之美的人物不再将死亡作为践行“物哀”的必然选择,而可以选择活下去,这并非是对哀情的忤逆,而是个体精神达到绝对自由后的意志和信仰。
3 结语
“物哀”以朦胧微茫但直抵内心的感性感情开创独特的审美风潮,独特的东亚风土孕育出“物哀”意识,其以纯净的美学向度制造出清冷纤细的哀感,成为日本文学独树一帜的美学概念。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日本民族深深崇尚且引以为傲的“物哀”美学艺术,将在全球文化的互通互鉴中迎来更加开放的审美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