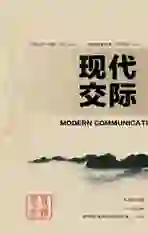教师惩戒权立法研究
2019-03-21蒋凯
蒋凯
摘要:教育是育人的活动,也是不断纠正学生失范行为的过程。教师惩戒权作为教师的职权,以学生改掉缺点、成长成才为目的。针对当前社会对惩戒权的误读、滥用、缺失等现象,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明确,以便教师在教学管理中规范行使。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教师的教书育人作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
关键词:教师惩戒权 性质 立法 必要性 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2-0043-04
一、教师惩戒权的概念及法律性质
(一)教师惩戒权的概念
对于教师惩戒权,新闻媒体多有提及,对于其准确概念,尚未有统一标准,甚至将惩戒与惩罚、体罚等词语混同。这种概念的模糊造成了社会大众对教师惩戒权的立法提议存在抵触情绪,故必须对教师惩戒权及其相关概念予以界定区分。
首先,“惩戒”不同于“惩罚”,具体表现在两者的目的不同。“惩戒”一词的落脚点在“戒”上,意指通过相应措施,警示失范者,以达到使其认识并戒除失范行为的目的。而“惩罚”一词的落脚点在“罚”上,意指对学生施以强制性措施,使其为自己的失范行为承担否定性的评价并付出相应的代价。
其次,“惩戒”不同于“体罚”,具体表现在两者方式和程度不同。“惩戒”一般以口头或肢体的方式作用于学生的心理或身体,其烈度较低,一般以警醒为限。而“体罚”则是直接给予身体、心靈以外力,使被体罚者感到严重不适,具有烈度大,损害身心的特征。
据此,教师惩戒权可以定义为:通过给学生身心施加某种影响,使其感到痛苦和羞耻,激发其悔改之意,以达到矫正的目的的行为。①
(二)教师惩戒权的法律性质
在明确教师惩戒权中“惩戒”行为之后,需要将落脚点归于“权”字的理解之上。“权”在法律话语中一般含有两层意义,一为“权利”,二为“权力”。对于惩戒权到底属于权利或是权力,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持“权力说”的代表学者有陈胜祥老师,他认为:“教师惩戒权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依法拥有的对学生的失范行为进行处罚以避免失范行为的再次发生,促合范行为的产生与巩固的一种权力,是教师的职权之一。”②持“权利说”的学者认为:教师有权在其职责范围内作出有关专业性的惩戒行为,这是教师职业性权利的应有之义。也有学者认为,教师惩戒权既是权利又是权力,如劳凯声认为:“教师惩戒权是教师基于其职业地位而拥有的一种强制性权力,它来源于教师的教育权力,是维持教育活动正常秩序、保证教育教学顺利进行的权力,也是教师的职业权利之一。”③
笔者认为,教师惩戒权是教师基于其职业特性所享有的职权,将其归于“权力”更为妥当,理由如下:
第一,惩戒权有公法来源。《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了我国的教育制度,使得教育权有了宪法基础。学校办学进行教学管理具有公权性质。《教师法》第三条将教师定义为履行教育职责的专业人员,意味着教师是教育权的具体实施者。同时,该法第八条规定,教师有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现象的义务。由此可见,教师惩戒权是教育权的延伸,是教师享有的职权,是一种“权力”。
第二,惩戒权的行使无法使教师从中直接获益。若是权利,则其行使的结果为权利人可从中获益,但是教师惩戒权的行使从结果看是使受惩戒者和学校受益,相反,对于教师来说,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是心里的痛苦和自责这种不利益表现。故明知不可得而为之的行为,就只能解释为教师惩戒权是教师的职权,是一种公权性质的行为。
第三,将惩戒权归于“权力”范畴,可督促部分教师的教育不作为。权利可放弃,但职权必须为。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失范的行为时,不采取惩戒不足以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的秩序时,如果不实施惩戒行为就是一种渎职行为。教师这一职业具有神圣性,作为三大古老职业之一,意味着这一群体对人类文明的推动具有重要影响,需要教师积极地行使教育职权。但现实中,部分教师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无视失范行为的发生及泛滥,这其实是一种教育不作为,教育失职行为。
第四,教师惩戒权类似于“家长权”。“在所有的动物中,人类的孩子是最难管教的,因为在她身体中存在着还没有加以规范的理性源泉;她是最隐秘、有最优智力和最不顺从的动物。几乎所有的孩子或迟或早都要与她的父母发生分歧,但既然她现在年幼无知,不能自理,那么她会爱她的父母,他们也爱她。她以后总会回到她的家,那时她才发现只有她的家人才是她的同盟者。”这是柏拉图关于父母和子女彼此的法权关系的最早言论。④对子孙的“教令权”是家长权中极重要的权力,中西家长都不否认这一点。洛克在《政府论》中关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权问题的论述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认为:“人们生来就是隶属于他们的父母的,因此,不能够自由。他把这种父母的威权叫做‘王权‘父权或‘父亲身份的权利”。⑤所谓“父权”或“父亲身份”,应该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中华传统中,所谓教令,就是又教又令。教的内容,主要是为人之礼。具体地说,就是《礼记·月令》篇所说的“六礼”。子女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以明人义。家长对子女的行为负有法律上教导、监管的义务。而师生关系与师徒关系,就类似于如今的家长子女关系。师生之间的纽带不是金钱、不是利益而是一种情感,一种来自长者的慈爱关怀,所以古人才会发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感慨。所以,教师的惩戒权与家长对孩子的管教权一样,应当是基于特殊身份享有的一种“权威”,而这种“权威”对学生的施加,并不是为了加害学生,相反是为了促进其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教师惩戒权是教师的一种权力,是教师基于其职业特殊身份而获得的职权,而不宜表述为是教师的一种“权利”。
二、教师惩戒权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教师惩戒权立法的必要性
(1)规制惩戒权滥用现象。如前所述,对惩戒权概念的不明确,导致了实践中惩戒权滥用现象频发。教师在教学管理过程中,通过过度惩罚,甚至体罚的手段来管教失范学生,造成学生受教育权、身心健康权遭到严重侵犯。一方面,虽然惩戒权是教师享有的权力,但受教育权同样是学生享有的合法权利,故惩戒权的行使不能损害到学生的受教育权。我国民间有谚语“严师出高徒”的说法,但是“严格”不等于“极端”,现实中因缺少法律法规约束而造成的例如教师辱骂学生、让学生下跪等粗暴行为,对学生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而且极大地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特别是很多地区依据存在着例如棍棒殴打、脚踢、手捏等恶性的体罚事件,这是对学生身体健康权的严重侵犯。这些行为都是对惩戒权的滥用,而且非但不能对学生起到教育作用,还有可能适得其反,让学生在心理阴影中长大,走上歧途,这些是与教育目的、教师职业道德背道而驰的。因此,亟须通过立法来明确规定惩戒权的范围和界限。
(2)防止惩戒权缺失现象。与前条相反,现实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教师处于种种原因怠于行使惩戒权,造成教育不作为现象。一方面,教师由于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怕麻烦心理,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失范行为选择视而不见,没有切实履行教育过程中的批评纠正的职能,而结果往往是学生变本加厉,无视纪律。另一方面,有的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体系有缺陷,“唯成绩论”的标准似乎很普遍,对于成绩好的学生,其失范行为就可能被容忍或“赦免”,忽略了对学生的言行教育。此外,近年来,一种“赏识教育”模式在教育界大行其道,对必要的惩戒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教育应当和风细雨,对学生只能用鼓励的方式来激发他们的潜能。这种教育模式有其道理,但是“赏识教育”并不能以丢弃惩戒权为代价,对于学生的违纪违法行为,必须及时纠正,将它扼杀在摇篮里。因为学生的心智毕竟不成熟,对于是非的判断存在滞后性,不能等到他们的恶习已成习惯再予以纠正,这样难度将大大增加。
(3)改变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偏见。曾经,教师职业在人们心中是一个无比崇高而神圣的职业,如有人将其比作“蜡烛”“春泥”“春蚕”“园丁”等,这些无私、优美的词汇无不体现着社会对教师的尊敬。而今,一起起教师体罚事件将教师职业逼上了风口浪尖。部分社会传媒对教育中恶性惩罚事件的误导性报道,污化了教师群体的整体形象,激化了教师的信任危机。家长和学生往往对教育中正常的惩戒行为动辄得咎,造成维权过度。这严重打击教师实施惩戒的积极性,限制了教师实施惩戒的自由。因此,只有通过立法,让教师正确合规行使惩戒权,而且是从心里“放心”地去行使。将惩戒权规范化能消除社会对教师惩戒行为的顾虑,以期慢慢改变社会对教师的偏见,修复渐渐逝去的“师生关系”“家校关系”。
(二)教师惩戒权立法的可行性
(1)教师惩戒权立法符合教育的目的。笔者认为,将教师比作“辛勤的园丁”是有道理的。教育行为与植树行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教育是一种塑造人的活动,也是一个不断“修剪”岔枝,矫正失范行为的过程。其根本目的是把人培养成能经得住风雨,符合社会需要的“栋梁”。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同样,在中国也将“传道”与“授业”“教书”与“育人”联系在一起,可见,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育之为人。在学生成人过程中,难免会走歪路,需要有人指引。这个“引路人”的角色在家里是家长,在学校便是老师。家长对孩子享有管教权,使其步入正轨,相应地也应当赋予教师以惩戒权,让教师尽职尽责地充当好人生“引路人”的角色。
(2)理性呼声助力惩戒权回归。虽然前段时间社会对教师的行为存在偏见,但那毕竟是对体罚行为的讨伐,是对教师惩戒权的误解。所以,近期有理性声音站出来,为教师群体发声,提议惩戒权的回归。比如,《南方周末》 在2018年5月撰文《教师惩戒权丧失,最终伤了谁?》,《人民日报》在2018年6月11日撰文《老师放弃对学生的管教 后果将是灾难性的》,6月12日报道“四川乐至班主任因管教学生被学生家长暴打”以及之前一位女中学老师的一封催泪辞职信,这些新闻报道在近期集中出现,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理性人士逐渐意识到教师惩戒权的重要性,期盼教师惩戒权立法的回归。因此,现阶段惩戒权立法具有舆论基础。
(3)国外立法为我国惩戒权立法提供经验。在惩戒权立法方面,很多国家都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明确制订了有关教师对违纪学生的惩戒制度,值得我们借鉴。如日本《学校教育法》规定,学校可以对学生进行惩戒,但是严令禁止体罚,并且明列了6项体罚。英国视教师惩戒权立法是现实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是解除家长与学校之间矛盾冲突的關键。比如:允许教师对违纪学生采取罚写作文;周末不让回家,陪值班老师值班;见校长,让校长惩罚和停学等不同程度的措施。⑥在韩国,关于教师惩戒权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于2002年6月26日公布的《学校生活规定预示案》,其中规定教师可以对违反纪律和学校规章制度的学生实施体罚,并且对实施体罚的方式和程序做了严格规定。⑦美国关于教师惩罚权的规定相对比较细致,比如允许扣留学生在学校,但“不得超过半小时”;“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到底有多严重,师生心里都很清楚,谁都不得越界。西方各国的立法探索与实践,为我国教师惩戒权立法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
三、教师惩戒权的行使
(一)教师惩戒权行使的原则
教师在行使惩戒权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平等与差别对待相结合原则。教师对学生的惩戒应当有体现公平,不偏私,不徇情,对学生的失范行为公平公正对待,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当然,平等不是一刀切,面对不同的情况,地域差异等因素,我们也应当采取个别差异对待,如由于先天遗传、后天环境的影响,学生之间的身心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这就需要教师在尊重公正原则的基础上实行特殊学生特殊对待。
第二,合法原则。惩戒权必须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行使的方式、程序、时间等都需要有法律的明确性规定。如果惩戒权行使超出了法律的规定,则可能构成对学生教育权、身体健康权的侵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合目的性原则。行使惩罚权必须出于善意,是为了让其改掉自身的陋习,健康正向地成长。只有出于关爱、善意的惩戒才能让学生真正接受。任何公报私仇、宣泄情绪的惩戒行为都是恶意的,应当予以禁止。
第四,比例原则。因为惩戒权属于“权力”范畴,故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也可以在此借鉴。即惩戒权的行使要有必要限度,要以损害最小的方式达到目的。如果手段超过了必要限度,则可能构成体罚,而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二)惩戒权行使的救济机制
任何权力的行使都需要被监督,惩戒权同样如此。因此,需要建立并完善惩戒权的监督机构,负责监督教师惩戒权的行使。一方面可以敦促教师积极行使惩戒权,另一方面,对于滥用惩戒权的行为可以提供举报渠道。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首先,可以在校内成立监督委员会,赋予其监督权,统一受理学生的投诉、申诉,力求在校内解决纠纷。其次,成立社会调解组织,对纠纷进行调解,以求缓和师生冲突。最后可以允许学生通过诉讼途径,起诉学校,以学校的教育权滥用为由起诉,维护其合法权益。
(三)高校教师惩戒权的行使
(1)高校师生关系的特殊性。在讨论高校教师的惩戒权时,有一个客观现象必须承认,即受惩戒一方通常情况下为成年学生。这与中小学还是未成年人是存在区别的,一方面,对未成年人的惩戒权一部分来源于国家公权力,另一部分来源于家长权的渡让。而对于成年人则在法律层面上说双方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成年人的交往模式中,互相尊重是我国历来的一个传统,虽然存在年龄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更多反映在资历上,此时学生对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已经初步具备,所以在此情况下,教师往往采取提醒的方式,温和地指出学生的失范行为。而学生对教师的善意提点,也往往进行着自我选择,有的选择谨记教诲,有的选择一笑而过。但是,是否意味着在高校中,教师惩戒权就没有存在必要呢?笔者认为恰恰相反,高校时光是学生从懵懂稚嫩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正如何兆武老先生说的,24、25岁的时候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定型阶段,是相当重要的。学生在这时候往往处于半社会化状态,对于外界的复杂好奇又无知,需要教师予以正确引导,矫正学生的不当言行。如果可能,更需要对学生的价值观、道德感进行栽培,引领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人。这个过程中,教师惩戒权就有存在必要,只是以缓和的方式行使,往往“点到为止”。
(2)辅导员代行惩戒权。在高校中,存在这样一个特殊群体,“辅导员”或者“班导”。一般由与学生年龄相近的毕业研究生担任。高校辅导员处于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第一线,对大学生的学业、心理、就业、交友等方面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与学生接触最多的可能就是辅导员,可以说辅导员是类似于家族中“成年兄姐”的存在。很多高校的辅导员会通过巡视宿舍、与学生谈心等方式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业,同时对于学生的违规违纪行为,也会行使相应的惩戒措施,如扣分、写检讨等方式,这是惩戒权的另一种行使主体。
(3)高校教师惩戒权的行使方式。正如前文提到,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是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其惩戒权的行使更多地会顾及到双方的“面子”问题,所以方式就会稍显温和、含蓄。比如当场口头惩诫教育,主要是通过言语批评等方式直接对学生的轻微越轨行为及时进行劝导改正、口头纠错。对学生进行综合考评,通过扣分制度,予以警示等。
(4)事中惩戒,事后安抚相结合。笔者认为这是整个惩戒权行使过程中最为关键且重要的一环。因为惩戒只是手段,其真正的目的是让学生意识并改正缺点,如果对学生进行单纯的处罚之后就将其晾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非但起不到教育作用,反而会让学生对老师存在抵触情绪,拉开师生的距离。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惩戒之后,与学生进行一次深入交流,向其详细解释惩戒的原因、目的,让学生感受到“冰冷”的惩戒背后还有爱的“温度”,这样学生就会从心里去接受它,同时也不会让师生关系在一次次的惩戒中渐行渐远。
总之,教师惩戒权是教师的重要职权,对其进行立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同时教师惩戒权的行使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法律范围内来达到其惩戒、教育的功能。
注释:
①劳凯声,郑新蓉.规矩与方圆:教育管理与法律[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268.
②公丕祥.法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99.
③劳凯声.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375.
④(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M].張智(下转第42页)(上接第45页)仁,何勤华译,孙增霖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65.
⑤(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6-48.
⑥易招娣.教师惩戒权法律问题研究[D].温州大学,2011.
⑦曹辉,赵明星.关于我国“教师惩戒权”立法问题的思考[J].教育科学研究,2012.
参考文献:
[1]徐艳伟.教师惩戒权的现实考查与理性回归[J].教育评论,2016.
[2]张忠涛.教师惩戒权:让“滥用”与“不用”回归“正常用”[J].中国教育学刊,2015.
[3]曹辉,赵明星.关于我国“教师惩戒权”立法问题的思考[J].教育科学研究,2012.
[4]贾成宽.论我国公立高校和教师惩戒权法制的缺失及完善——以公立高职院校为视角[J].今日中国论坛,2012.
[5]钟勇为.教师惩戒权立法是否可行[J].当代教育科学,2012.
[6]吴安新,余乐.高校教师惩戒权的法理基础与合理行使[J].现代教育管理,2011.
[7]吴安新,余乐.高校教师惩戒权的法理基础与合理行使[J].现代教育管理,2011.
[8]卢秀平.绿色惩戒:高校教师惩戒权的运用[J].科教导刊(上旬刊),2011.
[9]苏平.大学生受教育权与大学惩戒权的冲突与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
[10]陈胜祥.“教师惩戒权”的概念辨析[J].教师教育研究,2005.
[11]王辉.论教师的惩戒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
[12]张玲玲.教师惩戒权立法的理念与结构研究[D].江苏大学,2016.
[13]李丹.教师惩戒权立法的必要性及其相关建议[D].华中师范大学,2012.
[14]宇培峰.“家长权”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11.
[15]易招娣.教师惩戒权法律问题研究[D].温州大学,2011.
[16]尹甲民.中小学教师惩戒权立法研究[D].山东大学,2010.
[17]李永林.高等教育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7.
责任编辑:杨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