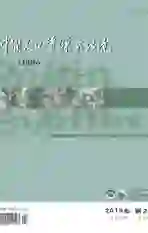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及其动态风险研究
2019-03-21孙晗霖刘新智张鹏瑶
孙晗霖 刘新智 张鹏瑶
摘要精准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已成为后扶贫时期我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选择生计资本和代际可持续性两个关键属性构建了生计可持续性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資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五类,将后代教育作为代际可持续性评估要素。在此基础上,采用全国社科基金规划重点项目课题组于2016—2017年分三次进行的大规模微观农户入户调查数据,构建BP神经网筛选计算出可持续生计24项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对各贫困地区可持续生计指数的预测结果表明:甘肃、山西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较强,可持续生计指数分别为4.288和4.161;云南、江西、重庆精准脱贫户生计较稳定,可持续生计指数差别较小且均超过3.6;四川、湖南精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指数为3.377和3.135,生计水平较低;贵州地区可持续生计指数为2.953,精准脱贫户生计脆弱。基于生计动态转换视角,采用生存分析法探讨了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风险率的关键因素:因能力、教育、环境致贫的精准脱贫户在脱贫后生计稳定性较好,分别为3.423、2.750、2.642 a,心理因素致贫的可持续生计的生存时间较短,生理因素致贫的生计稳定的生存时间最短,仅为1.876 a。女性户主生计稳定持续时间(1.841 a)明显低于男性户主(2.792 a)。对生计稳定的精准脱贫户生计动荡的比例风险模型估计结果,与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的直观分析结果基本一致: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对于精准脱贫可持续生计的重要程度最强,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稳定有较大影响。综合分析认为: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2年应成为脱贫保障的重点“观察期”,在这个期间应重点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积累视角对生计尚欠稳定的精准脱贫户实施后帮扶和追踪支持,帮助精准脱贫户稳步实现可持续生计,让脱贫成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关键词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动态风险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9)02-0145-11DOI:10.12062/cpre.20180904
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2013年至2016年间累积减贫6 600多万人,年均减少1 300万人以上。随着贫困人口的骤减,达到退出标准而退出帮扶项目的“精准脱贫户”陡增。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贫困户一旦脱贫,帮扶重心必然转移,社会对其支持力度也会大幅缩减,有限的资源必将流向其他贫困群体。这部分“已脱贫”群众既处于扶贫项目的退出边缘,又兼具风险脆弱性和返贫可能性等特点,更容易陷入“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的恶性循环,甚至脱贫后富裕起来的农户也会因家庭经济条件恶化而再度返贫[1]。全面小康,不是追求一时的脱贫和摘帽,而是实现可持续脱贫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小康,还需要剔除已脱贫农户的潜在致贫因素,规避或降解生计风险,确保在政策逐渐脱钩后精准脱贫户能够依靠自身能力和现有条件实现生计可持续。而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精准脱贫户返贫呈现出高发态势,各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年返贫率均超过20%,且当前生计风险极高的潜在返贫群体约5 825万人[2],精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已成为后扶贫时期的重要关注点。
1文献回顾
精准脱贫战略对于我国贫困人口的减少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暂时性的帮扶项目无法解决其他持续存在的外部社会风险,因此单靠货币转移还不足以可持续地减少贫困[3]。帮扶项目退出意味着从整个项目领域撤出外部提供的资源,受助主体所享受的一切福利待遇就此终止[4],对于退出帮扶计划的家庭而言,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关注:一是退出后是否继续有能力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5]。若这些家庭生计的改善是暂时性的,则在遭遇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冲击时极有可能再度陷入贫困;二是是否积累了足够的生计资本,以防范家庭收入的暂时性波动[6],尤其是对于抚养负担较重的家庭而言,是否能在失去现金补贴激励的情况下维持子女的健康状况、承担其教育支出,直接关系到家庭生计的代际传递[7]。因此,对这部分退出帮扶项目群体的可持续生计评估是十分重要的[8]。退出不等于单纯地催促贫困人口脱离项目,项目退出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提高受益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6]。通过评估他们的生计前景来瞄准弱势家庭,并采用贴合受助者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的教育、就业培训等干预措施消除潜在动态风险[9],稳定弱势家庭财务状况,保障其良性发展轨迹,这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关键[10]。
“可持续生计”是家庭为长远改善生产生活状况而所获得的谋生能力、所积累的资本、可借助的外部支撑以及以增加收入为核心的行动,其基本思想来源于Sen[11]、Chambers &Conway[12]等对贫困问题的深化理解。可持续生计是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主题,是扶贫终极目标之一,对可持续生计分析(SLA)方法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3],如今可持续生计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世界减贫与发展事业中。它基于二维平面图,通过分析潜在生计风险因素寻求最佳的生计资本组合和生计决策模式,从而促进可持续的生计增长和限制脆弱性,其优势在于基于因果分析对个体或家庭可持续生计形成过程的全面把控[14]。可持续生计框架强调生计结构和过程的转变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重要途径,反映了生计资本结构、生计策略和生计目标之间的交互作用[15]。Chambers [12]认为家庭是理性的决策者,可以获得有形与无形的资本组合,他们结合自己的生计目标,根据自己可支配和可获得的资本作出相对应生计决策,以更好地维持家庭生计。但家庭的生计决策不仅取决于户主的自身能力,还取决于在脆弱性背景下可用的资本组合[16],人们要获得积极生计成果,必须具备不同类型的资本存量(包括自然、物质、金融、社会、人力资本),这五类资本被认为是可持续性生计框架的核心内容,它形象地表现出人们的资产状况[17],反映出个体或家庭在外部影响下改善其资本的能力[18],在各种外部趋势和影响因素的控制下,家庭利用现有的生计资本,选择相应的生计策略,会产生不同的生计效果[19]。
通过以上研究可发现,可持续生计评估作为以干预为目标的帮扶政策精准实施的先决条件和关键指标,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现有研究主要着眼于贫困人口生计情况,而对于“精准脱贫户”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仍处于空白。其二,发展中国家农村家庭的生计通常由于其资本存量、生计风险、生计策略等差异而呈现出异质性特点[20],因而许多关注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文献由于采用了综合分析而忽视了家庭构成的巨大变化最终会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21]。其三,现有的可持续生计评价大多基于既定的SLA构建指标体系,但可持续生计框架所强调的是基于生计资本而进行生计策略选择最终实现可持续生计输出的过程,无法反映出代际可持续的能力大小,对于精准脱贫户而言,预防贫困反扑和斩断贫困代际传递是精准脱贫战略成功实施的直接体现。其四,现有精准脱贫对于后续保障的相关研究甚少且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各地在实际帮扶过程中对于后续保障措施的实施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基于此,本文以已退出帮扶项目的脱贫户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这部分特殊群体的可持续生计,本研究优化了传统的可持续生计指标体系对精准脱贫户生计进行多维评价,在此基础上从生计风险动态转换视角出发,采用生存分析法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的关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对于“后扶贫时期”保障措施研究较少且多为理论研究和定性描述的短板,从而揭示了以往研究并未论及的精准脱贫户生计问题“黑箱”。
2可持续生计评估
2.1可持续生计框架优化与指标选取
在构建可持续生计指数之前,需确定与可持续生计有关的关键属性和变量。为了准确评估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态,学者在指标选择方面进行了大量探讨。Fang[22]将可持续生计指标简化为五种资本(即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以反映生计的可持续性。Yan[21]提出生计脆弱性指数(LVI),从暴露程度、敏感程度、响应能力三个维度分析气候变化、土地丧失、地理环境对于农户的生计影响[23-24],其他指标也被用于计算可持续生计,如可持续生计安全指数(SLSI)和家庭生计安全(HLS)。上述指标被用于评估贫困人口的生理需求,其关注重点是缓解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然而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于生存困境得到解决的低收入群体而言,高质量的后代教育已取代温饱成为代际可持续性的核心需求[25-26],也是實现永续脱贫的根本途径[27]。因而本文选择生计资本和代际可持续性分别代表两个关键属性。在子组件层面,本文将生计资本进一步分化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五类。
(1)自然资本指标选取。在我国,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自然资本,是农户最传统的生计来源,也是最根本的生计保障[28]。由于自然资本其本身具有折旧性、变化性、节律性、区域性等特点,其收益受到自然资本规模和质量的直接影响而呈现出不确定性。因此,结合我国贫困地区实际情况,本文将自然资产细化为家庭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两个二级指标。
(2)物质资本指标选取。个体和家庭用于生产生活的各项物质设备和基础设施统称为物质资本。实地调研中发现,当前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在退出帮扶项目后其基本的民生需求已得到满足,其资本存量之间差距较小,因而本文选择价值量较高或差异较大的物质资本作为相应指标 ,包括饮用水是否经过处理、是否有独立冲水式卫生间、拥有生活耐用品和农机价值、房屋价值。
(3)人力资本指标选取。从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双重维度测量人力资本,包括“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比重”“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是否所有家庭成员均处于健康状态”“家庭抚养负担”“家庭规模”等代理指标。
(4)社会资本指标选取。由于贫困地区农户社会资本网络的非规则性,体现为:一方面,除了行政组织外,贫困地区农村社区组织缺失,农民参与某种协会或组织的自我组织程度不高;另一方面,农户社会网络主要表现为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亲戚网络、基于地缘关系的乡邻网络和基于行政隶属关系的行政组织网络等[29]。因此,本文对农户社会资本结合实际状况用两类指标来衡量:一是街坊邻里关系,这一指标可反映农户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获取帮助的情况和社会融入程度;二是农户城市亲朋数量和干部亲朋好友数量,这两个指标可以大体反映农户在面临风险时获得支持的强弱和稀缺资源的获取能力。
(5)金融资本指标选取。从积累存量角度衡量精准脱贫户的金融资本,涵盖农业收入、非农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储蓄几部分。其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是该家庭整体生计策略的反馈和体现,而由于风险冲击和脆弱性的不确定性,难以加以量化,因此考虑从通过家庭储蓄额角度评估对未来不确定风险的应急响应能力和抗风险冲击能力。
(6)在既有的文献中,“后代教育”通常被用于反映家庭代际可持续性。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能实现收益的代际转移,其收益主要表现为子女生计资本存量优化,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增加、信息渠道增多,社会地位提升,健康状况改善,劳动力素质提高,既体现为社会的水平流动,也体现为社会的垂直流动,最终实现子女及整个家庭可持续生计。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其自身生计资本的快速积累,最终获得较高的生计水平,并且有能力为其子女提供更好的营养条件、学习机会和生活环境,从而提高子女学习能力和竞争力,使其获得更高等的教育机会,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从源头遏制贫困代际传递[30]。Aizer等进一步指出由于父母生计水平的差异导致对子女的初等教育投资力度差别较大,而初等教育处于生命周期当中认知可塑性阶段,可为有针对性地干预提供潜在的“机会之窗”[31],所积累的人力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复杂的动力和互补性,直接影响子女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和程度,因此,相比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对代际可持续性的作用更为显著[32]。因此,本文将后代教育引入作为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代际可持续性评估指标,选择“家庭教育投资费用”“是否家庭劳动力都完成小学义务教育”“是否所有学龄儿童都在上学”作为代理指标。
2.4精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评价
表2即为神经网络预测得出的精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指数,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精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指数差异较大。Barrett[36]将生计脆弱性与动态资产门槛之间的差异相结合,将生计得分标记为“易受伤害”()和“绝望”低水平的均衡(7/10),本文根据其研究思路以及调查区精准脱贫户家庭实际反馈,将低于阈值2.8的生计综合指数定义为生计缓冲能力较弱,即不可持续生计,将高于阈值2.8而低于阈值3.6看作是“易受伤害”生计。具体来看,甘肃、山西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状况较好,生计可持续性较强,其可持续生计指数分别为4.288和4.161。云南、江西、重庆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指数差别较小且均超过3.6,反映出该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较稳定。四川、湖南两地精准脱贫户家庭可持续生计指数为3.377和3.135,生计水平较低,而贵州地区可持续生计指数为2.953,反映出该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较为脆弱,在不利的外部风险冲击下容易再度返贫。
按照调研区的实际情况,本文将精准脱贫户退出贫困项目前的致贫原因归结为生理致贫、心理致贫、能力致贫、环境致贫和教育致贫。其中,生理致贫包括由于家庭成员身体原因而造成的贫困,例如疾病,残疾等;心理致贫涵盖了由于个体心理因素而导致的贫困,如惰性思维,缺乏自信等;能力致贫则反映了由于个体人力资本存量偏低,教育机会缺失,就业技能不足而导致的收入增长乏力;环境致贫主要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地区自我造血能力不足,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恶劣等因素;教育致贫即未成年子女较多,家庭抚养负担过重而造成的贫困。由表2可知,八个贫困地区中由于心理、能力、环境、教育原因致贫的精准脱贫户生计指数得分相对较高,这与我国现行的通过提升地区和个体自我发展能力的“造血式”精准帮扶战略高度相符,反映出上述地区践行脱贫战略精准落地。纵向比较可发现,由于生理原因导致贫困的家庭在脱贫后可持续生计指数均相对较低,反映出该类精准脱贫户潜在的生计脆弱性较强,后期脱贫保障政策应给予重点关注。
生计策略是个体为实现其生计目标而进行生计的活动和选择范围和组合,可被理解为应对外部干扰和维持生计能力的手段,直接决定了家庭可持续生计的实现[37]。本文按照相关研究和实际情况将精准脱贫户生计策略分为农业主导型、非农业主导型、农工均衡型和其他类型,进一步探讨不同生计策略的精准脱贫户家庭可持续生计指数。相比于其他类型生计策略,非农生计策略的可持续生计得分在各地区水平均处于较高水平,反映出结合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现状,非農生计策略可能更有利于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的持续。
表5显示了精准脱贫户生计动荡的比例风险模型估计结果。对于精准脱贫户的家庭异质性特征而言,家庭抚养比和家庭规模越大,其陷入生计动荡的可能性越大。其中抚养比每提高1个单位会使得生计动荡概率提高1.567倍,家庭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会使得生计发生动荡概率增加1.083。户主是否为党员、户主年龄与帮扶年限与生计动荡的关系不显著。年龄的不显著可以被尝试理解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人力资本加速折旧,生计风险率提升,但与此同时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随着时间增长而不断积淀,有助于生计能力的提高,因而从整体上看年龄对生计动荡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方面,精准脱贫户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接受培训、家庭成员健康状态、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水平与生计动荡的概率均呈现负相关关系,体现出了人力资本对于可持续生计的重要作用。其中,家庭劳动能力每提升1个单位,会使得生计动荡概率降低77.1%,参与就业培训的精准脱贫户的生计动荡概率比不参加就业培训的精准脱贫户低79.1%,家庭成员健康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家庭生计动荡概率会随之降低81.9%,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每提升1个单位,生计稳定的概率将增加84.3%。物质资本方面,精准脱贫户家庭所拥有的生活耐用品和房屋是其生活质量和生计水平的部分体现,二者皆有助于降低精准脱贫户的生计动荡概率,生活耐用品和房屋价值每提高一个单位,会使得生计动荡概率分别降低68.4%和79.7%。金融资本方面,家庭人均收入、储蓄和可以获得的信贷金额均有助于提高家庭生计持续能力,延长家庭生计稳定时间。其中,家庭人均收入、储蓄和可以获得的信贷金额每提高1个单位,其生计动荡的概率会分别随之减少90.4%、80.6%、77.3%,反映出金融资本对维持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稳定的基础性作用。社会资本方面,邻里关系、官员亲友数量以及城镇地区亲友数量与生计动荡的概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其每提高1个单位,有助于分别降低37.2%、56.6%和39.7%的生计风险概率。自然资本方面,土地作为农户最根本的生计保障,对于防止生计动荡具有十分积极的正向作用,耕地面积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得精准脱贫户陷入生计动荡的概率降低74.7%,而耕地质量的改善所带来的产出比的增加也显著减少精准脱贫户生计动荡概率,延长生计稳定时间。
本文按照协变量均值进一步估算了脱贫户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从整体上看,在脱贫退出后的两年内精准脱贫户更易发生生计动荡情况,因此,考虑到贫困地区致贫原因复杂,返贫率畸高的现实情况,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两年应成为脱贫保障的重点“观察期”,相关部门应在脱贫退出后的2年内重点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积累视角对生计尚欠稳定的精准脱贫户实施扶持政策不减、工作力度不减的后帮扶工作和追踪支持,帮助精准脱贫户稳步实现可持续生计,避免返贫扶贫和阶段性扶贫,让脱贫成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4结论与政策蕴含
本文基于改良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BP神经网络和生计分析法对精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及动态风险进行了多维度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其一,不同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的生计差异较大,同一区域不同致贫因素的精准脱贫家庭,其生计状况未达到同等水平。其中,由于心理、能力、环境、教育因素致贫的农户脱贫退出后生计改善明显,说明该部分困难群体对于当地精准脱贫战略实施的反馈更为积极,而由于生理原因(疾病或残疾等)致贫的家庭在脱贫后可持续生计能力仍较弱,风险脆弱性较高,后期脱贫保障政策应给予重点关注。其二,结合当前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将非农就业作为生计策略更有利于生计的稳定和脱贫效果的持续。其三,在脱贫后的两年内精准脱贫户生计动荡风险较高,其中生理致贫家庭和女性户主的生计动荡风险分别高于其他致贫类型家庭和男性户主。家庭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扩大,其陷入生计动荡的可能性越大,而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均有助于降低生计动荡风险,延长生计稳定时间。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 加强村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发挥人力资本对于可持续生计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应根据精准脱贫户家庭特征、个体差异和个人意愿等实际情况,建立完善多层级教育体系,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开展适应当地产业特色的技能培训,扩大农户对于教育内容的选择面以及教育机会的可获得性,不断增加精准脱贫户个体知识储备量,提高技能水平,以提升自身就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从而获取稳定的生计来源。另一方面,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有机组成,是实现可持续生计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区级医院的指导下,以乡镇卫生院为主体,村卫生室为基础,建立健全涵盖卫生监管、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康复保健、基本医疗为一体的三级医疗保健网,突破由于地理位置而造成的医疗服务壁垒,防范生计风险冲击,降低生计脆弱性。
着力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专业水平,定期与市级医疗卫生机构合作展开保健诊疗绿色服务,积极发展以健康保险和疾病救助为核心的脱贫保障机制,培育精准脱贫户健康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帮助脱贫户从日常生活中摆脱贫困“亚文化”影响。
第二, 重视非农生计策略的增收作用。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非农生计策略对于提升当地精准脱贫户的生计稳定性的积极作用,在帮扶过程中应重点加强当地运输、通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产业为平台,通过土地租赁、股权投资等方式,将自然资源、农户自有资源以及各类扶贫资金资产化,引导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群体参与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强调产业发展过程中资源利用与低收入群体获利与发展间的关系,为其带来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并提供多样化、实用性的非农技能培训以提高精准脱贫户的参与度,切实保障培训方式的规范性、长期性和培训结果的有效性、收益性,将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与通过就业和参与生产的其它产业扶贫模式相结合,创新探索低收入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之间利益联结机制,为当地群众提供多元化的非农就业渠道,让精准脱贫户在自我能力提高和内生动力增强的基础上,稳定增加资产性收入,以实现稳定脱贫、可持续脱贫。
第三, 给予“生理致贫”家庭更多的生计保护。相比其他致贫因素,生理性致贫的个体其劳动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普遍偏弱,先天性和后天性人力资本存量均不足,家庭负担更重,贫困修复期更长,生计改善能力较差,脱贫后生计动荡可能性较大。针对上述群体应建立和优化精准识别的长效机制,整合扶贫资金,加大生计保护力度,确保贫困地区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健康维护四合一的保险制度落地。同时,要通过实用技术培训等帮助他们逐步恢复劳动能力,拓宽实名制绿色就业渠道,强化就业形式的灵活性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包容性,在脱贫中坚定意志,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巩固生计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第四,创新后续保障机制,提高生计稳定性。一方面,考虑到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的波动性和脆弱性特征,应在脱贫后给予脱贫户为期两年的“脱贫缓冲期”,在此期间继续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的连续性,做到干劲不松、力度不减,加大产业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人力资本培育,并积极引导精准脱贫户树立致富信心,提升社会参与度和积极性,不断增强群众自我发展的能力,不断加大生计资本积累,巩固可持续生计能力。另一方面,搭建脱贫群众生计动态监测平台,准确掌握贫困户脱贫退出后两年内的家庭情况和生计状况,做好跟踪支持和保障服务工作,及时捕捉潜在短期或长期生计动荡因素并予以纠正,将生计动荡及贫困边缘脱贫户及时纳入帮扶范围,让精准脱贫群体能够稳步脱贫、避免返贫,使精准扶贫和脱贫效果有效和可持续。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
[1]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 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2]李君如.人权蓝皮书: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3]MOURELO E L, ESCUDERO V. Effectiveness of active labor market tools in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programs:evidence for Argentina[J].World development, 2017, 94(6): 422-447.
[4]BANE M J, EllWOOD D T. Welfare realities: from rhetoric to reform[M].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5]李裕瑞,曹智,鄭小玉, 等.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的区域模式与可持续途径[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279-287.
[6]SIMONEC.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mes:the recent experienc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M]. New York:United Nations,2011: 89-132.
[7]房连泉.国际扶贫中的退出机制——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J].国际经济评论,2016(11):86-104.
[8]MICHELLE M D S S. Poverty reduction, education, and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184.
[9]RITA A, EMANUELA G. Jumpstarting selfemployment? evidence for welfare participants in Argent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5): 742-755.
[10]ELLWOODD T, ADAMS E K. Medicaid mysteries: transitional benefits, medicaid coverage, and welfare exits[J]. Health care financing review, 1990(11): 119-131.
[11]SENA.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30-53.
[12]CHAMBERSR, CONWAY G R.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R].UK: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1:296.
[13]Department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livelihood guidance sheets[R]. London:DFID, 1999.
[14]FARRINGTONJ.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rights and the new architecture of aid[R].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1: 123-145.
[15]PANTHI J, ARYAL S, DAHAL P, et al.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approach to assessing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mixed agrolivestock smallholders around the Gandaki River Basin in Nepal[J].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6, 16(4):1121-1132.
[16]STEPHENM, NORA M N.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a critique of theory and practice[M]. Dordrecht: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3:34-56.
[17]何仁偉.山区聚落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分析: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J].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2014,31(2):221-230.
[18]HUANG T, XI J C, GE Q S. Livelihoo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wo villages in Yesanpo tourism district in China[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17, 14(11): 2359-2372.
[19]GENTLEP, MARASENI T N. Climate change, poverty and livelihoods: adaptation practices by rural mountain communities in Nepal[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2, 21(12): 24-34.
[20]WANGC, YANG Y, ZHANG Y. Economic development, rural livelihoods,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AMBIO, 2011, 40(1): 78-87.
[21]YAN J, ZHANG Y.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farmers and nomads in eastern ecotone of Tibetan Plateau[J].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2011(7):858-867.
[22]FANGY P, FAN J, SHEN M Y, et al. Sensitivity of livelihood strategy to livelihood capital in mountain area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ifferent settlement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Minjiang River, China[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4,38:225-235.
[23]HUANG X J,HUANG X,HE Y B, et al. Assessment of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landlost farmers in urban fringes: a case study of Xian,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2017,59:1-9.
[24]LIU Y G,HUANG C M. WANQ, et al. Assessment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d geographic detection of settlement sites in ethnically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the Aba Prefecture,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2018,7(1):1-18.
[25]BRAUWA D,ROZELLE S. Reconciling the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offFarm wage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8(12):57-71.
[26]ASADULLAH M N, RAHMAN S. Farm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in rural Bangladesh: the role of education revisited[J]. Applied economic, 2009, 41(1):17-33.
[27]REIMERSM, KLASEN S. Revisit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3, 95 (1):131-152.
[28]王彥星,潘石玉,卢涛, 等.生计资本对青藏高原东缘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及区域差异[J].资源科学,2014,36(10):2157-2165.
[29]杨云彦,赵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9(3):58-65.
[30]DENG Z, TREIMAN D J.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103(2):391-428.
[31]AIZERA, CUNHA F. The Production of child human capital: endowments, investments, and fertility[D]. Cambridge: Brown University, 2012.
[32]CUNHA F,HECKMAN J J. Formulating,identifying and estimating the technology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2008,43(4):738-782.
[33]VINCENT K. Uncertainty in adaptive capac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scale[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7,17(1):12-24.
[34]WANGC C, ZHANG Y Q, YANG Y S, et al. Assessment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different farmers in hilly red soil erosion areas of Southern China[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6,64:123-131.
[35]刘恩来,徐定德,谢芳婷, 等.基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生计资本度量:以四川省402户农户为例[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12):59-65.
[36]BARRETTC B, MARENYA P P, MCPEAK J, et al. Welfare dynamics in rural Kenya and Madagascar[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6, 42(2):248-277.
[37]PANDEYR, JHA S K, ALATALO J M, et 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based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for Himalayan communities[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7,79:338-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