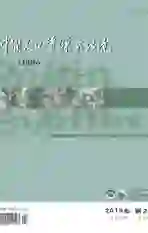中国省域耕地生态补偿研究
2019-03-21刘利花杨彬如
刘利花 杨彬如
摘要耕地是重要的生态资源,以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耕地生态补偿的依据,具有科学客观性。以中国各省为例,采用当量因子法和功能价值法相结合的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负面价值,补充完善了以往只研究耕地生态系统服务正面价值或仅研究部分负面价值的不足,并引入地方政府支付能力指数和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等补偿系数,以保证制定出来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全国31个省份中,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面价值均超过其负面价值,是负面价值的1.05倍(西藏)至7.59倍(重庆)。②在耕地生態系统服务的负面价值中,化肥施用和农业耗水产生的负面价值所占比重最大,两者之和占负面总价值的比例范围为71.11%(江西)至98.75%(西藏),是耕地生态系统服务负面价值的主要来源。可以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补贴政策,根据技术规程,对合理减少化肥等化学品使用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业环境保护补贴;通过大力推广高效节水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以降低因化肥的施用和农业耗水产生的负面价值。③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占其GDP的比例范围为0.04%(北京)至5.94%(云南),其中,有23个省份的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占其GDP的比重超过了1%。④依据省域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制定出省域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范围为142.04元/hm2(西藏)至28 69481元/hm2(上海),补偿额度占各省财政收入的比例范围为0.23%(北京)至29.36%(黑龙江)。丰富和完善生态补偿理论,有助于建立科学合理的耕地生态补偿体系,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提供技术支撑和依据。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耕地;生态补偿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9)02-0052-11DOI:10.12062/cpre.20180906
耕地不仅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还是重要的生态资源。耕地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吃饭”“建设”和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6]31号)提出要加强森林、草地、湿地、耕地等领域的补偿。国内外学者认为生态补偿的标准和依据直接决定了生态补偿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生态补偿的核心,也是生态补偿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施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往往仅根据耕地产出的经济价值,对耕地生态补偿的投入远滞后于耕地对社会和生态的贡献,如2014年10月苏州市出台的《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规定:“稻田的生态补偿标准为420元/亩/年。”根据《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中府[2014]72号)规定:“基本农田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100、150、200元/亩/年,其他耕地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50、75、100元/亩/年,执行期限为2015至2017年。”从这些补偿的实践可以看出,现行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并没有有效解决耕地质量持续恶化、耕地撂荒及数量减少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缺乏科学依据,没有真正体现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导致政策的实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耕地生态补偿研究,将有助于明确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完善我国的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助推农业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促进乡村振兴和“美丽中国”的实现。
1文献综述
生态补偿理论来源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ecosystem services)。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所有惠益,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以及支持服务等。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是生态补偿、生态环境保护等的基础和重要依据。而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难点和热点,国内外的众多研究陆续提出了各自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但由于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没有统一和标准化,导致结果差异较大,如Costanza等[1]估算世界多样性的年度经济价值是Pimentel[1]估算结果的10多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不统一也限制了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的客观认知。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生态补偿的研究,如针对森林、草地和水体等领域的生态补偿,促进了生态补偿理论的发展。但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体系,且由于评估出来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地方实际补偿能力相差较大,使得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生态补偿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仅能作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理论参考值。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是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关键。综合已有研究,现行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有两种:当量因子法[2-5]和功能价值法[6-8]。当量因子法是我国学者谢高地 [3-5]基于Costanza等[2]对生态系统服务分类的基础上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该方法构建了准确客观的当量因子表,已经广泛应用于不同区域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4,9-10],其优点是直观易用,不需要过多繁杂的数据,非常适用于区域和全国全球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9,11]。功能价值法是根据生态系统服务量的多少和单位价格求得其价值,通过建立单一服务与局部生态环境变量之间的生产方程以模拟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12-13],计算过程复杂,参数较多,对每种服务的价值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难以统一[14-17]。
目前,耕地生态系统除了生产食物和原材料外,还提供气体调节、水文调节、废物处理、保持土壤、维护生物多样性、提供美学景观等多种服务,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18-19]。国内的部分研究虽然评估了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但多集中于局部地区耕地生态系统服务正面价值的评估,如魏宁宁等[20]、刘利花等[21]、任平等[22]采用当量因子法分别测算了南京市、湖南省、四川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正面价值,依次为55.08×108元、19.8×104元/hm2、369 692.69元/hm2。除了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面价值,少部分学者还研究了因农药、化肥、地膜等的使用及温室气体排放等带来的耕地生态系统服务负面价值,如元媛等[23]采用功能价值法评估了栾城县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负面价值分别为46.20×108元、4.05×108元,其中,耕地生态系统服务负面价值包括地下水资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地膜污染、农药污染、化肥流失。叶延琼等[24]计算了佛山市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负面价值分别为82.86×108元、73.09×108元。张微微等[25]计算了关中-天水经济区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负面价值分别为26 378.413×108元、29.425×108元。
虽然国内外相关研究评估了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负面价值,但鲜有同时从耕地生态系统服务正、负面价值的角度进行耕地生态补偿研究的。少数文献虽然从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方面研究了生态补偿,但也仅仅研究了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面价值,而忽略了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负面价值,并简单的将计算结果作为补偿标准,使确立的补偿标准往往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不具有实践可操作性。本研究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研究耕地生态补偿,首次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负面价值,采用当量因子法和功能价值法相结合的方法计算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负面价值,并引入地方政府支付能力指数、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等补偿系数修正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生态补偿理论,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提供技术支撑和依据。
2研究思路
在耕地生态系统服务正面价值分类的基础上,采用当量因子法测算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面价值。在测算耕地生态系统每项服务的当量因子时,学者谢高地等[4-5]研究的范围是全国,使用的是全国粮食平均单产。为增加对各省研究的准确性,本文在计算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面价值时,引入各省复种指数与全国复种指数的比值对谢高地等提出的当量因子进行修正。采用功能价值法、替代法等测算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负面价值。基于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负面价值,计算出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净价值,引入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地方财政支付能力指数,确立各省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
4.2耕地生态系统服务负面价值的测算结果
中国省域耕地生态系统因使用化肥、农药而造成的环境污染负面价值由公式(4)计算得出(见表2)。其中,化肥、农药的单价是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7》里各省各种农作物化肥、农药单价的加权平均所得。使用化肥导致环境污染负面价值排在前5位的省份分别
为广东、福建、河南、海南、湖北,排在后5位的省份为内蒙古、甘肃、黑龙江、青海、西藏,最大值的广东是最小值西藏的8.98倍。使用农药导致环境污染负面价值排在前5位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浙江、江西、湖南、江苏,排在后5位的省份为内蒙古、贵州、甘肃、青海、西藏,最大值的广东是最小值西藏的9.74倍。
中国省域耕地生态系统残留农用地膜造成的环境污染负面价值由公式(5)计算得出(见表2)。其中,粮食的市场价格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7》里各省四大主粮(稻谷、玉米、小麦、马铃薯)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所得。该部分负面价值排在前5位的省份分别为新
疆、山东、湖南、甘肃、河北,排在后5位的省份为广东、江西、吉林、黑龙江、西藏,最大值的新疆是最小值西藏的67.18倍。
中国省域耕地生态系统农业水资源消耗产生的负面价值由公式(6)计算得出(见表2)。该部分负面价值排在前5位的省份分别为新疆、西藏、广东、宁夏、海南,排在后5位的省份为河南、山西、贵州、北京、重庆,最大值的新疆是最小值重庆的27.38倍。
中国省域耕地温室气体排放负面价值(见表3):①计算耕地生态系统年CH4排放量。由于我国不同省份温度、湿度等自然禀赋的不同,各省水稻生产期内CH4排放率也存在差异。王明星等[33]根据各省的气候、施肥和土壤等条件计算出各省的稻田CH4排放系数,由于该系数已经包含施肥对稻田CH4排放量的影响,因此,在计算时不考虑施用化肥产生的CH4排放量。早稻、晚稻和中季稻由于生长期的不同,CH4排放系数也不同[33]。除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重庆(同四川)、贵州、云南种植早稻、晚稻和中季稻外,其余省份仅种植中季稻,青海不种植水稻。早稻、晚稻和中季稻均种植的省份根据其早稻、晚稻和中季稻生产的CH4排放系数,按照加权平均法求出总的水稻生产的CH4排放系数。根据公式(8)求出各省耕地生态系统年CH4排放量。由于在各个统计年鉴上,青海省均没有稻谷播种面积,因此,青海省耕地的CH4排放量为零,相应的,因水稻CH4排放产生的负面价值也为零。根据公式(7)得出中国各省耕地生态系统CH4排放负面价值。②计算耕地生态系统年N2O排放量。国内学者根据众多实验得出了我国主要农产品的N2O排放系数[34-38]。冬小麦和春小麦均种植的省份按照加权平均法得出其小麦生产的N2O排放系数。本研究将马铃薯、花生、油菜籽、棉花、烤烟、甘蔗和甜菜归为其他旱地作物。归纳已有研究,可以得出我国农产品N2O排放系数主要分为三类:本底(未施肥时)N2O排放通量——水稻为0.24 kg/hm2、小麦为1.075 kg/hm2、玉米为2.532 kg/hm2、大豆为2.29 kg/hm2、其他旱地作物为0.95 kg/hm2;氮肥N2O排放系数——水稻为0.30%、小麦为0.80%、玉米为0.83%、大豆为6.605%、其他旱地作物为0.30%;复合肥N2O排放系数——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其他旱地作物均为011%。根据公式(9)得出中国各省耕地生态系统N2O排放量,根据公式(7)得出中国各省耕地生态系统N2O排放负面价值。
耕地温室气体排放负面价值排在前5位的省份分别为江西、湖南、广东、福建、江苏,排在后5位的省份为宁夏、甘肃、北京、青海、西藏,最大值的江西是最小值西藏的105.15倍。其中,耕地CH4排放负面价值排在前5位的省份分别为江西、湖南、广东、福建、江苏,排在后5位的省份分别为西藏、北京、甘肃、山西、青海,最大值的江西是最小值青海的1 582.06倍。耕地N2O排放负面价值排在前5位的省份分別为河南、山东、河北、天津、江苏,排在后5位的省份分别为福建、浙江、上海、海南、西藏,最大值的河南是最小值西藏的10.91倍。
根据公式(3)得出中国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负面价值(见表4),该值排在前5位的省份分别为新疆、广东、福建、海南、江西,排在后5位的省份为北京、甘肃、内蒙古、山西、贵州,最大值的新疆是最小值贵州的6.42倍。对比
中国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五部分负面价值,可以看出使用化肥和农业耗水产生的负面价值所占比重最大,两者之和占负面总价值的比例范围为71.11%(江西)至98.75%(西藏),两者之和所占比例排在前5位的省份分别为:西藏、青海、新疆、宁夏、陕西。农业耗水负面价值占负面总价值的比例范围为15.64%(重庆)至91.59%(西藏),其中,超过60%的省份为西藏、新疆、青海、宁夏、黑龙江、甘肃。使用化肥产生的负面价值占负面总价值的比例范围为7.16%(西藏)至68.51%(河南),其中,超过
50%的省份有河南、北京、重庆、陕西、山东。使用农药产生的负面价值占负面总价值的比例范围为0.94%(西藏)至12.9%(北京),其中,超过10%的省份仅有3个:北京、浙江、山东。残留农用地膜负面价值占负面总价值的比例范围为0.08%(西藏)至3.42%(山东)。温室气体排放负面价值占负面总价值的比例范围为0.24%(西藏)至21.55%(江西),其中,超过10%的省份仅有8个:江西、湖南、上海、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广东。由此可以得出,耕地生态系统服务负面价值的主要来源为化肥的使用和农业耗水。
由表5可知,在全国31个省份中,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面价值均大大超过其负面价值,是负面价值的1.05倍(西藏)至7.59倍(重庆)。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排在前5位的省份分别为上海、福建、湖南、广西、广东,排在后5位的省份为北京、宁夏、青海、甘肃、西藏,最大值的上海是最小值西藏的66.54倍。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占GDP比重的范围为0.04%(北京)至5.94%(云南),比值最高的5个省份依次是:云南、黑龙江、广西、贵州、新疆。相对而言,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占GDP比重最少的5个省份依次为浙江、天津、上海、西藏、北京。
4.3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结果
根据公式(12)、公式(13)、公式(14)得出各省的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地方政府支付能力指数。根据公式(11)得出省域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范围为142.04元/hm2(西藏)至28 694.81元/hm2(上海)(见表5)。耕地生态补
偿标准最高的5个省份分别为上海、福建、江苏、广东、浙
江,相对最低的5个省份为山西、宁夏、青海、甘肃、西藏,最高值的上海是最低值西藏的202.02倍。结合各省的耕地面积,可得出各省的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有24个省份的补偿额度占省财政收入的比重小于15%,其中,有15个省份的补偿额度占省财政收入的比重小于10%,剩余7个省份的补偿额度占省财政收入的比重大于15%。黑龙江、广西、吉林、河南、湖南、内蒙古、云南是7个补偿额度占省财政收入的比重大于15%的省份,原因在于这些省份的耕地面积大,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尤其是黑龙江,其耕地面积在全国位列第一,耕地生态补偿额度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最高,接近30%。
5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1)耕地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全国31个省份中,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面价值均大大超过其负面价值,是负面价值的1.05倍(西藏)至7.59倍(重庆)。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占其GDP的比例范围为0.04%(北京)至5.94%(云南),其中,有23个省份的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占其GDP的比重超过了1%。耕地生态系统服务负面价值的主要来源为化肥的施用和农业耗水,两者的负面价值之和占负面总价值的比例范围为71.11%(江西)至98.75%(西藏),这两部分负面价值降低了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净价值。
(2)制定出省域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范围为142.04元/hm2(西藏)至28 694.81元/hm2(上海),最大补偿值是最小补偿值的202.02倍。结合各省的耕地面积,有24个省份的补偿额度占省财政收入的比重小于15%,剩余7个省份的补偿额度占省财政收入的比重大于15%,原因在于这些省份的耕地面积大,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尤其是黑龙江,耕地面积位居全国第一,其生态补偿额度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最高,接近30%,中央政府应加大对这些省份的财政补贴力度,扶持农业大省,减少这些省份的财政负担。
(3)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耕地生态补偿的资金扶持力度,提高现行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以达到生态补偿政策的预期效果。以江苏省、广东省为例,本研究得出江苏省耕地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7 194.46元/hm2,约为1 146.30元/667 m2,远高于江苏省苏州市现行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420元/667 m2;本研究得出广东省耕地生态补偿标准为14 323.34元/hm2,约为954.89元/667 m2,远高于广东省中山市2018年2月修订后的耕地生态补偿最高标准268元/667 m2。
5.2讨论
(1)本研究以省域为单位,首次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面、负面价值,补充完善了以往只研究耕地生态系统服务正面价值或仅研究部分负面价值的不足。采用目前比较成熟且应用较广的当量因子法和功能价值法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准确地测算了中国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各省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具有科学客观性。通过补偿系数的修订,使制定出来的生态补偿标准具有实践可操作性,既能反映出耕地资源的真正价值,也使制定出来的补偿标准在地方政府的可承受范围之内。研究结果为政府出台耕地生态补偿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但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需要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可行性及严密性。
(2)要构建科学合理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成立各级耕地生态补偿基金委,负责确立耕地生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资金的收缴、管理和监管。补偿方式可以采用资金、实物、技术、政策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手段。补偿资金可以通过以下方面获得:①发展生态农业,盘活农业生态资本。②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通过生态彩票、绿色保险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可以考虑在生态敏感区征收资源环境保护税,推进土地税收体系的“生态改造”,加强整合资源类税收。③根据一定比例,从每年收取的土地出讓金、耕地占用税等费税中收取耕地生态补偿资金。④中央财政可以通过设立耕地生态补偿项目,进行专项拨款。⑤各级政府可以向下一级政府征收GDP增长提成,以此作为补偿资金。建立包括中央政府调控及第三方机构监督的调控监督机制。同时,要建立实现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有效持久运行的保障体系,一是建立全国性的耕地生态环境监测网络,随时监测耕地质量和数量上的变化;二是逐步建立耕地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体系。
(3)要采取多种措施,降低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负面价值,特别是要降低因化肥的施用和农业耗水产生的负面价值。一是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补贴政策。按照技术规程,对合理减少农药、化肥等化学品使用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补贴,推广使用农业绿色生产方式,推动生态友好型农业的发展。二是要大力推广高效节水农业生产技术,如渠道防渗技术、滴灌技术、喷灌技术等,推广农田保墒技术如秸秆覆盖、地膜覆盖、耕作保墒、水肥耦合技术等,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从资金、政策等方面加大对农业节水项目的投资力度,加强农业节水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农业节水灌溉面积。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
[1]王长胜.生态补偿: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49-74.
[2]COSTANZAR,DARGE R,GROOT R D,et 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Nature,1999,387(1):3-15.
[3]谢高地,鲁春霞,冷允法,等.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价值评估[J].自然资源学报,2003,18(2):189-196.
[4]谢高地,甄霖,鲁春霞,等.一个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J].自然资源学报,2008,23(5):911-919.
[5]谢高地,张彩霞,张雷明,等.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改进[J].自然资源学报,2015,30(8):1243-1254.
[6]赵同谦,欧阳志云,王效科,等.中國陆地地表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生态经济价值评价[J].自然资源学报,2003,18(4):443-452.
[7]王景升,李文华,任青山,等.西藏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J].自然资源学报,2007,22(5):831-841.
[8]王兵,鲁绍伟.中国经济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J].应用生态学报,2009,20(2):417-425.
[9]COSTANZA R,GROOT R D,SUTTON P,et al.Changes in the global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14,26(1):152-158.
[10]赵永华,张玲玲,王晓峰.陕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及时空差异[J].应用生态学报,2011,22(10):2662-2672.
[11]WANGW J,GUO H C,CHUAI X W,et al.The impa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the temporospatial variations of ecosystems services value in China and an optimized land use solution[J].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4, 44:62-72.
[12]KAREIVAP,MARVIER M.Conserving biodiversity coldspots:recent calls to direct conservation funding to the worlds biodiversity hotspots may be bad investment advice[J].American scientist,2003,91(4):220.
[13]ROBERTSONG P, SWINTON S M. Reconcil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a grand challenge for agriculture[J].Frontiers in ecology & the environment,2005,3(1):38-46.
[14]ZHANGB,LI W H,XIE G D.Ecosystem services research in China: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J].Ecological economics,2010,69(7):1389-1395.
[15]YU Z Y, BI H. The key problems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research[J].Energy procedia,2011(5):64-68.
[16]YU Z Y,BI H. Status quo of research on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in China and suggestions to future research[J].Energy procedia,2011(5):1044-1048.
[17]SUN J. Research advances and trends i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evaluation in China[J].Procedia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11,10(10):1791-1796.
[18]乔旭宁,顾羊羊,唐宏,等.渭干河流域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15,33(2):237-245.
[19]张宏锋,欧阳志云,郑华,等.玛纳斯河流域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9,17(6):1259-1264.
[20]魏宁宁,李丽,高连辉.耕地资源利用的生态外部性价值核算及其补偿研究[J].科技导报,2018,36(2):61-66.
[21]刘利花,杨永福,李全新.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补偿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30-38.
[22]任平,吴涛,周介铭.耕地资源非农化价值损失评价模型与补偿机制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2014,47(4):786-795.
[23]元媛,刘金铜,靳占忠.栾城县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正负效应综合评价[J].生态学杂志,2011,30(12):2809-2814.
[24]叶延琼,章家恩,秦钟,等.佛山市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损益[J].生态学报,2012,32(14):4593-4604.
[25]张微微,李晶,刘焱序.关中-天水经濟区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12,30(2):201-205.
[26]谢高地,肖玉,甄霖,等.我国粮食生产的生态服务价值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5,13(3):10-13.
[27]肖玉,谢高地,安凯,等.华北平原小麦-玉米农田生态系统服务评价[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1,19(2):429-435.
[28]祁兴芬.区域农田生态系统正、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34(5):622-626.
[29]孙新章,周海林,谢高地.中国农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及其经济价值[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7(4):55-60.
[30]刘光栋.区域农业生产环境影响的价值评估方法及应用[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04:87-93.
[31]闵继胜,胡浩.中国农业生产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7):21-27.
[32]李晓赛,朱永明,赵丽,等.基于价值系数动态调整的青龙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5,23(3):373-381.
[33]王明星,李晶,郑循华.稻田甲烷排放及产生、转化、输送机理[J].大气科学,1998,22(4):600-612.
[34]王智平.中国农田N2O排放量的估算[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1997,13(2):51-55.
[35]王少彬,苏维瀚.中国地区氧化亚氮排放量及其变化的估算[J].环境科学,1993,14(3):42-46.
[36]黄国宏,陈冠雄,吴杰,等.东北典型旱作农田N2O和CH4排放通量研究[J].应用生态学报,1995,6(4):383-396.
[37]于可伟,陈冠雄,杨思河,等.几种旱地农作物在农田N2O释放中的作用及环境因素的影响[J].应用生态学报,1995,6(4):387-391.
[38]苏维瀚,宋文质,张桦,等.华北典型冬麦区农田氧化亚氮通量[J].环境化学,1992,11(2):2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