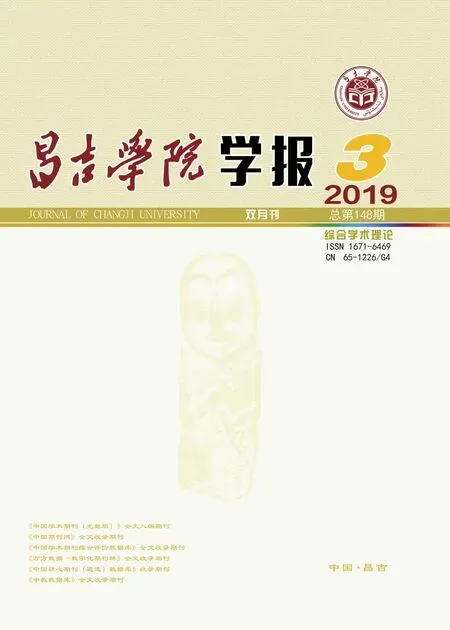婉而多讽,众生喧哗
——论老向长篇小说《寻心》的创作艺术
2019-03-21李静
李 静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重庆 400715)
在抗战时期,与老舍同样声名远播的还有一个作家是老向,他的原名叫王向辰,与老舍、何容(即老谈)并称“三老”。他是兼具京派文学、幽默派文学、通俗文学又自成一家的一位特殊的人物,他是论语派的代表性期刊《论语》《宇宙风》等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主编过抗战期刊《抗到底》,在抗战时期的诸多期刊杂志上都有小说与散文发表。但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已鲜有人认识老向,更遑论读过老向的作品。老舍与鲁迅等人位列现代经典作家的席位,作品被选入教材,从黄口小儿到专家学者,几乎无人不读老舍。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老向却是个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的作家,学术界也很少有人研究他的作品,对于文学珍宝的遗忘与忽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本文将试着去探讨老向的长篇小说《寻心》,廓清其艺术特点及价值,重新界定老向在文学史的地位。
一、反英雄形象全大杵
长篇小说《寻心》于1936年始,陆续发表在谈风社周黎庵等人创办于上海的论语派刊物《谈风》上,是老向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之一。故事的主人公是抗日英雄全大杵,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左臂膀和右手上的四个指头,战后被送入残废院养老,却不愿意过寡淡无味的生活。
可是据他自己陈述战功的时候说,连一颗赤淋淋的心也被敌人剜出来,抛去了。政府为了奖励人民执戈卫国,对这位抗战老将,设尽了法子去酬劳他,允许他到残废院去养老终身;人民也异口同声的称他为英雄,为民族英雄,认为他应该受国家的优待,然而他自己却以为领些干薪原无不可,拘在残废院当废物看待,是有损他的英雄身份。他愿意努力创造自己的前途,打算走遍天涯也要把失掉的心寻回来;有了心,当然可以再替国家出力。他的口号是“寻心救国”。[1]
全大英雄不愿意拘在残废院当废物,声称自己的心被剜去了,得到了国家颁发的可以通行全国的护照以后,他便以扫墓为名,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全家富,从此引出了与全家富乡民之间的故事。
全大杵是航空队的队长,负责驾驶飞机作战,身体有残疾,又耐不住残废院里死水一样的生活,要踏上寻心之旅。他声称要回乡扫墓,在临行之前,耗资准备了一套西服,又去很奢华的店里挑选了一条假胳膊和一只假手,他不坐火车,不骑马,专门挑了一头很壮实的水牛,骑着它滑稽地回乡去了。小说关于全大杵的人物面貌和心理相关的直接描写较少,多从他的动作和行为着手。他虽是战斗英雄,并没有普通战士抖擞的精神,没有为国效劳的壮志凌云情怀。他常常贪睡,又不按时间落地,不守纪律,其实做为一个战士也并没有得到太多尊重。儿童见了他虽然对他行军礼,却只是为了让他还一个军礼,以便能看到他残废的手指,猎奇和取笑的意图分明。关于他寻心的说法,政府和人民其实都不认同,认为他作战之前也未必有心,即便有心也许是在贪睡的时候丢掉了。政府答应他的请求,实属因他身体残疾和失魂落魄而同情他。全大英雄处处想维护自己战斗英雄的面子和尊严,在城市中实则是失落的,于是他的回乡应有荣归故里,想要获得村民拥簇与尊重的用意。他穿着洋服骑着水牛,把牵水牛的绳索系在领带上,其实十分滑稽可笑,他却认为英雄做事就要与众不同,一个自欺欺人的反英雄角色便跃然纸上。
全大杵在回乡的时候,凑巧遇到蝗灾,满山遍野的村民正在鸣锣击鼓,斗志昂扬地驱赶蝗虫。他误以为这些鼓声和欢呼声是乡民为迎接他而特意安排,心中感动万分,并差点落泪,于是反复练习怎么做手势,怎么说话,盘算怎么像首长省亲一样同村民打招呼。他被乡民簇拥进祠堂,首先凭吊的却是一座狗碑,牵涉出来一段关于狗的往事。全大杵初得势之时回乡重修了祠堂,他养了一条美国犬,起名贵妃,每天必须投喂三磅牛肉和一磅牛奶,十分娇贵,族长因唆使土狗与它打架,贵妃受伤医治无效死去。全大杵拿法律吓唬不懂法的族长,甚至要用飞机轰炸族长家里,最后以族长为狗立碑并按时祭祀了事。此时的全大杵在狗碑面前想起了往事,伤感地念出了狗碑的碑文:“彼亦狗也,尔何畏彼哉?尔为狗雄,我为英雄,两雄不并立乎?”幽默之中,讽刺意味立现。全大英雄本是穷苦出身,自小没了娘,舅舅携带娘家人在他母亲下葬时抢夺他的家产,并阻拦他正常安葬母亲,村民们替他出气,并时常给予他帮助。他回乡以后并没有去扫墓,也对时三宝的死与儿时伙伴小燕子的死不闻不问,只是享受着村民的恭维与孝敬,并让村民叫来了戏班子搭台唱戏。一个所谓的战斗英雄在战争中贪睡,表现不积极,在得势之时回乡大修祠堂,因为一条狗的死而欺侮百姓,战争结束以后得了英雄之名,作威作福,贪图享受,并不关心儿时曾帮助过他的乡民,即便有冤案,也漠不关心,一个以英雄自居的人,实则是官僚做派,虚伪冷漠,仗势欺人的反英雄人物。
二、乡间小人物群像
除了反英雄人物全大杵之外,小说中有许多性格多样化的乡间小人物群像。哈喽全是一名修铁路的工头,开过许多山洞,技术过硬,外国人也很喜欢他,常常叫他“哈喽,全”,于是村民依样画葫芦给他起了个外国名“哈喽全”。他没有结婚,没有儿女,喜欢逗孩子玩,别人不想理的人他都不忘帮衬,全飞做牢的时候,只有他去送饭探监,全寡妇的颠颠妮儿生了私生子,他跑去帮忙掩埋,他是一个“多事精”,永远闲不住,谁家有事他都会去帮忙,有一年麦收时,晚上天气突变,狂风骤雨,村民们怂恿哈喽全去地里用草毡把麦垛盖起来,他开足马力奔跑,却因失控与全飞相撞,把全飞的鼻子撞塌了,从此又得了“火车头”的绰号,这个绰号也的确形象地概括了他风风火火像个火车头似的赶往每一个事发地点的姿态。他是村子里最热心的人,村民们并不怎么领情,却常常使坏捉弄他,“不过哈喽全是见过世面的了,而又天生性子好,对于任何人的叽讽嘲弄,都能够不走心。”[2]他为人善良又幽默风趣,不做坏事,活的知足踏实,他说:“我不害人,不坑人,不给别人绾圈套。我的心善还不是一个顶好的避雷针?你几时看见过一个善人会教天雷打?”[3]他活的坦坦荡荡,无畏无惧,他是唯一一个不顾自己利益,时刻想着村民,为村民办实事的人。他日夜守护全大杵的水牛,哪里打架了,他跑去劝架,谁家地里麦收时忙不过来,他下地帮忙收割麦子。时三宝受冤时,他不忘安慰时虎子,替他想办法,唱戏时帮村民给邻村的亲戚捎信来看戏,顺带着帮忙办些采购之类的杂事,当他为村民请回戏班子并安顿好戏子的住处时,本想去茶馆洗把脸,意外得知时三宝居然在冤情未了的状态下愤然已离世,“他大跺一脚,仿佛是自己作了孤哀子,立刻便跑到时虎子家去,不叩头也不举哀,开口就问:‘怎么?就这么胡里胡涂的完了?'”[4]墙倒众人推的时候,村民只是在得知噩耗时赶到时虎子家,公式化的寒暄几句,然后都去听戏了,族长全方舟因为同媳妇吵架心情憋闷,端着架子回家睡觉去了,只有哈喽全一腔悲愤,又想帮助时虎子料理后事,只是时虎子却冷冷淡淡,不搭理人,哈喽全有心无处用,只好无奈离开。他悲伤地来到牛棚,对着水牛自说自话:“你来到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好人不!你看我们这里有谁是快乐的?回你们南方去吧,这里太干燥了。”[5]哈喽全虽有一副热心肠,却没有什么权利,并不能惩恶扬善,为时三宝鸣冤。他虽是个先人后己的活雷锋,永远有用不完的精神,却并不被村民尊重和爱戴,是个可怜又可敬的底层小人物。
全寡妇是个亦正亦邪的人物。她出生在城里,父亲是文捕快,她后来嫁给了全族长的堂兄,生了五个女儿,做姑娘的时候就常常出入赌场、茶馆,人称盖西门。“所以她从小就把人这个动物琢磨透了,越怕什么,越有什么来敲门;大家认为走不通的,只要你有苦瞻走,硬闯出来一条路也并不艰难。乡下人,尤其是女的,是最容易教人拿一把的,是他们怯官,而她对于进趟衙门,闹场官司,比着吃块豆腐还不搁牙……”[6]寡妇在封建残余仍然较深厚的乡村,做什么都容易被指责,全寡妇却被村民称作活祖宗,谁都不敢招惹她。她活得很张扬,在赌场上叱咤风云,全飞的圈套也套不住她。她聪明通透,不畏任何权贵,在各种紧急事务中游刃有余。全族长因为她没有生出来儿子,要给她过继儿子,她不同意,又夹杂一些陈年旧账,惹恼了族长。全方舟一直想尽各种方法想要活埋她,把她告上法庭,不肯让步。全寡妇用那张能言善辩的嘴,恩威并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拿衙门里做事的兄弟和全方舟女儿的名声要挟他,斗的全方舟再也不敢在全寡妇面前作威作福。全寡妇和几个女儿虽然生活作风都不检点,做人却很仗义,村里人常常热热闹闹地围在她家里谈天说地。村子里的各种人事她都看的通透,她也帮助过小时候失去娘亲的全大杵,也常替哈喽全洗衣服,牌桌上有人串通起来对她使阴招,她也会用非正常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四个女儿嫁了人,死了一个,其余的都离婚了。她们家十分迷信,常常给村里人算命,并在家里祭瘟神,四女儿甚至被称为“天眼通”“四仙姑”,在蒙昧未开化的乡村里甚得人心。全寡妇知道女儿跟了卖私盐的全飞,也从不过问。她也了解时三宝的死和全飞有关,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她并不是个黑白分明的人,难以用好和坏给她定性,却是个在全家富活得春风得意、如鱼得水的人。
全方舟家是村里最体面最富裕的门户,房子是最奢华的大宅院,他是一族之长,最会摆谱,不干实事,却总是被全寡妇和哈喽全盖过风头,在村庄里是个日渐失势的封建族长的代表。他的祖父全举人是个狠角色,家里的螺狗踢了母马,他就气急败坏,把螺狗砸成了肉酱,长毛造反的时候,有异乡口音的人路过村子,他都把他们活埋在乱葬岗。全方舟虽然是个世袭的绅士,却一直想以一人之力统摄全村,全寡妇损害他的利益时,他就想编各种名目活埋她。全大杵来到村子里,他拿着官架子发号施令,对哈喽全骂骂咧咧,本想在全大英雄面前耍耍威风,却总是不能得逞。他虽是大宅院的人,身边环绕着莺莺燕燕,总是调戏尼姑和颠颠妮儿,她的媳妇在颠颠妮儿的挑唆下甚至不顾大宅院爱面子主张忍耐稳重的传统,同他大吵大闹,让村里人分外吃惊,争相赶来看他家的笑话。村子里出了事故他不会第一个出头去维护村民利益,“他虽是个首事,但一遇上谁家遭丧,他的架子立刻端起来。孝子不亲去给他叩三遍头,他不会自动的给办事。若像时虎子这样败落的门户,就是叩四遍头,头磕破了,他也不会照管。”[7]全方舟为人狠毒,欺软怕硬,攀附权贵,践踏穷苦之人,虽然他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远去,却仍旧是全家富当权派的代表。
除此之外,全飞也是一个弄权派,他是私盐贩子,什么违法的事情都敢做,设计陷害时三宝,最后伤重的时三宝被气身亡,到死不知道是被谁摆布了命运,时三宝出事时,他假意帮时虎子出主意,等到时三宝气绝而身亡时,他又冠冕堂皇地前去吊孝,可见是个没有良知,心狠手辣,虚伪狡诈之人。颠颠妮儿是个搬弄是非的人,谁家的事她都知道,但凡她得到消息一定会挨家挨户地去传播,多少家庭的矛盾都因她而起。她同时性格豪爽,敢作敢为,同哈喽全交好,是个性情中人。时虎子是个蠢笨的人,看不透各种厉害关系,遇到事情没有对策,一旦灾祸降临,不调查原因,只会消极忍受,冷漠对人。这些乡村的人物被老向刻画地活灵活现,都是不完美的人物,却都来自于底层民间,读者能从偌大的中国土地上找到千千万万个像哈喽全和盖西门等等同类的人。
三、朴实幽默的小说语言
首先,老向是一个为农民创作的作家,所以语言很朴实。老向出生于河北一个农村,儿时成绩优异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小学当了校长,因为出了一些安全事故被免职,后又考入了北京大学,在大学里常听林语堂的课,受林语堂的幽默文学影响巨大,与林语堂交好,在重庆时,两家住在一起,林语堂的孩子都很喜欢老向。他曾与何容一起参加过北伐,在军队里做政治指导员,写过许多与抗战相关的报告文学,也曾在河北定县平教会工作,提倡通俗文学的创作。在冯玉祥的支持下,主编了抗战期刊《抗到底》,抗战时期与老舍都是抗敌文协的发起人。他创作的《抗日三字经》发行量惊人,在抗战时期影响巨大。解放后在重庆整理戏剧史料,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打成右派后病逝。老向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也常常自认为一身黄土泥,是个农民作家,在大学里受过高等教育,在抗日救亡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一直主张“文章下乡”,提倡通俗文学创作,致力于创作让农民和士兵都能看得懂的文学作品,为抗日积极做宣传。
其次,生活中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所以小说语言十分幽默。“他,矮胖小棵子,圆胖脸,紫红血色,一对小眼睛,在眼镜后面眯缝着。很健谈,意趣横生,引得你心花怒放。虽然是个小胖个子,话音却特别洪亮,并且越谈越起劲,越谈越引人入港,不禁使人想到夏蛙”[8]他性格极好,十分健谈,为人乐观开朗,讲课时颇受学生喜爱,朋友们很喜欢与他了解,他是一个充满智慧对生活有见地的人,积极向上地生活和创作,常常为身边的人带来欢乐。
再次,老向的小说语言极为通俗,文笔流畅,意味悠长。老向与老舍都是京味作家,用笔幽默,但是老向却不同于老舍,他的文章语言更为通俗。他自小浸染北方农村的乡风乡俗,民间谚语信手拈来:例如“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宁开盐店,不做知县”,“打折了胳膊往袖子里装”,“河里无鱼市上看,出处不如聚处多”等等。多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句,比如形容全方舟知道放炮仗的是全寡妇后,本来发怒的族长“立刻像是脚踏车蹦了内袋,瘪了。”[9]老向笔下的农村黄昏是诗意盎然的:
一到黄昏,全家富这个农村原本是最有生趣的一幅图画。鸡儿都棲上树。鸟儿都赶回窠。在田间工作的人们,扶犁荷锄都缓步的归来;前面走的是牛犊马狗,不时有一阵天真烂漫的狂奔,引起大家无限的欢乐。他们满怀着‘饥能得食,疲能得息'的快慰,遥望着屋顶上的缕缕炊烟。低声歌唱着。街上许多孩子们跳着,嚷着,作着各种民间游戏。长日关在家里的老太太们,抱子携孙也都走出了大门来谈天。卖杂货的,卖凉粉的,还有其他的小贩们也都赶来凑热闹。情形虽然复杂,但是总不失为一种太平景象。[10]
乡间的黄昏时刻,操劳了一天的人们和牲畜们都悠哉地游走在夕阳下,大街小巷里,嬉戏的孩童,叫卖的小贩,坐在门前谈天的老人,动静相宜,那些童真的、欢乐的、安逸的话语仿佛能从字里行间传入读者的耳中,不免使人感慨陶渊明笔下的“带月荷锄归”不过如此罢了,历朝历代人们追逐的、热望的平和安宁的生活也不过如此罢了。老舍热爱北京这座城,文学语言中的京味儿地道至极,又吸收了西方的语言艺术,形成了雅词雅句。老向与老舍不同,他在北方这片广阔的泥土地上成长,他的小说语言如散文一样优美,透着泥土的清香,还有对黄土地深入骨髓的热爱。老向对乡间的一切人物,一切语言,一切景象都过熟稔,务农的乡民农忙时节在田间的劳作,天气突变时,乡亲们奔跑着去收拾农作物和衣物,农闲时,聚在十字街说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请来草台班子组织庙会,人们聚在台下热热闹闹看戏时的议论,丧葬之礼上人们组织事务时干脆利落的语言,都非常符合农村生活的环境,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小说的人物对话十分顺畅并且符合人物性格,读者代入感很强,如同身临其境。小说中口语化的对白能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在简单明了的语言背后是老向积累的生活智慧,语言活泼诙谐,让人忍俊不禁,可见老向驾驭语言的功底十分深厚。老向本人又非常喜欢戏剧、民谣、相声,他的小说语言故事性强,很快能将读者引入一个幽默风趣的故事情景中,老向的小说语言历久弥香,每一句话都能让人咂摸出一种属于北方乡村的乡土味道,意味隽永。
四、婉而多讽,众声喧哗
自晚清出现谴责小说以来,讽刺小说在中国层出不绝。林语堂虽然主张闲适文学,行文讲究幽默风趣,其实这些京派作家或论语派作家创作的文学主旨大多都是讽刺的,国民性的批判都藏在温柔的语言背后。老向的文章是婉而多讽的,他的批判充满温情。《寻心》主人公全大杵就是作者用漫画手笔刻画出来的人物,他本身并不是让人民景仰的英雄,是个自称英雄没有做过英雄事的人,并被作者称作全大英雄,人物出场的戏谑之味就分外浓重。在描写全大杵挑选假肢的时候,作者用笔极为夸张,有一条假腿甚至有“孟尝君三千门客腿,朝秦暮楚,最善走门路”之称,语言诙谐有趣,意在讽刺最会钻营的社会不良风气。全大英雄一本正经地欺辱乡民,为狗立碑,荒唐至极,却无人敢怒敢言,乡民们都争当说客,促成了立碑之事。村民们不懂法律,全大杵危言耸听,传播杀狗与杀人同罪,甚至是刑事案件的荒谬法律。全大英雄严肃地为狗立碑文,在狗碑面前哀悼,与他面对村中冤屈事件视若无睹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批判了村民的愚昧与奴性,讽刺了全大杵玩弄权术无所不用其极。村民们胆小怕事,能躲就躲,时三宝家出了事,颠颠妮儿只顾传播流言,并不关心邻居的死活。墙倒众人推,不幸之门,鲜少有人会踏足,村民们到时虎子家吊孝,只是唏嘘长叹,心里想着“哪家庙里没有屈死鬼”,对不幸的人们并不会有多少悲哀痛苦的共情性。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认为,全民性的狂欢虽代表着民俗文化,庆典的高潮一般也会呈现悲剧,这种欢乐的庆典就具有讽刺性和象征性。小说的狂欢化叙事一般通过大型的仪式,用隐喻与象征表达悲剧性的思想主题。“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11]文学中的狂欢化结构有时是作者的刻意安排,这种文字背后的人类狂欢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故事是在全大杵回乡之时,村民们捉蝗虫的喧闹中开篇的,村子里的锣鼓、铁锅、铜面盆、洋铁簸箕,学校的上课铃等等所有能发出声响的东西都被村民征用了,锣鼓喧天的氛围下,全大英雄走进了自己的故乡,落下的泪水也多么悲哀又讽刺。而在全家富请来了草台班子,搭好戏台,好戏开锣时,时三宝悲愤地去世,此时故事达到了高潮。全村人都把自己的亲戚喊来听戏,一些年轻的小伙子挤在全寡妇家看戏子,不希被泼热水,也不忘热情高涨地调戏着戏子,全然无视村里这件冤案,时三宝家除了哈喽全没有一个真正关心的人去出谋划策料理丧事。时虎子心灰意冷,宁可犯了重丧,也不搭丧棚,只打算用一个薄皮匣子草草掩埋父亲,做好了一家人去讨饭吃的心理准备。小说的结尾,大戏还在唱着,牛棚着了火,小颠子也被人抢走了,村民人开始慌乱地救火,故事又在众声喧哗中结束,与开头形成对照。贾宝玉迎娶薛宝钗,锣鼓唢呐声响彻云霄时,林黛玉孤独惨死,时三宝死在众人欢天喜地听大戏的一片喧哗中,悲剧的意味在这悲与喜的极致对比下,更加强烈。夏志清曾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都有感时忧国的传统,老向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热爱故土,将身边的人事用乡土化的视角倾注于笔端,他对国民性的思索也是深刻的,他不曾放弃期待人性的善良与互助,在那个战火纷飞、人人自危的时代,老向无疑也有悲伤的忧愁,所以《寻心》的结尾并不是大团圆结尾。小说的最后,有一段作者对全大杵的评论这样写道:
全大英雄自从回到故乡,除了接受村民的抬举,就只等着明天去看戏。其余的如天热,蝗灾,打架,骂街,以及舅舅的被人赶跑,小燕子的被人枪毙,一切等等,他都不放在心上,无怪他自以为是“失了心”的人。他这次回家的借口是扫墓,是的,扫墓不过是借口,事实上他连父母的坟边都没看见。然而大人物们往往以为只须自己登高一呼,天下的风气就会突然的变好。[12]
可见全大杵的寻心之旅也是讽刺的,作者已然按捺不住对他的批判,认为众人给他的心是草的,假的,木的,他却只适合一颗铁心,因为他就是没血没肉极度冷血的人。
结语
老向做为一个通俗作家,创作过诸多小说、散文、民谣、戏剧,例如《庶务日记》和《黄土泥》都是他的代表作,他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的特点,鲜少运用心理描写,人物的行为用漫画式夸张手法进行书写,小说有结构松散、人物脸谱化、性格不够立体等缺点。老向是民国时期为了抗日救亡大部分时期都在宣传抗日精神的启蒙者。他一生都关注底层人物的命运,并不用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小人物,而是用温和的幽默讽刺手法带着读者去感知他笔下的那片黄土地上生活的像尘埃一样的人物。他是一个幽默可爱的作家,也是一个充满底层责任感的作家。他的作品像涓涓的溪流淌在人们的心底,温暖的文字背后,同样不缺乏国民性的批评,不缺乏对人性的探讨。老向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也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值得读者拂去历史的尘埃,去重新界定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