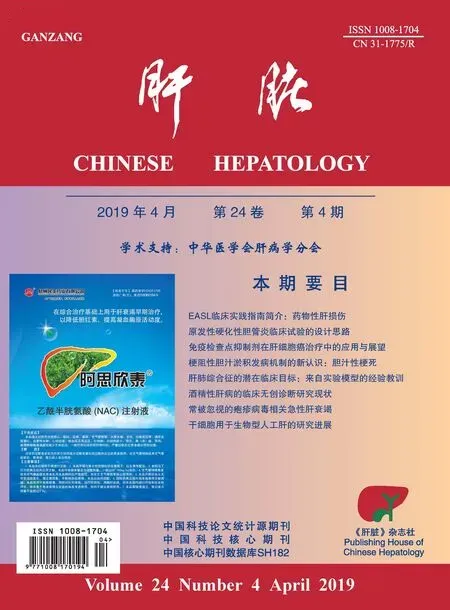整合素与肝脏疾病
2019-03-19张迎超陈晶
张迎超 陈晶
整合素是最早于1986年研究发现的异二聚体黏附分子,存在于多种细胞表面,主要介导细胞与细胞、细胞与细胞外基质(ECM),并且双向传导传递信号,例如生长、发育、止血、白细胞运输、免疫反应以及伤口修复。迄今已发现有24种不同的整合素,并有大量实验研究证明这些整合素参与调节多种基因和人类疾病,不仅存在于正常肝组织中,在疾病发展及治疗过程中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本文分别从肝炎、肝硬化、肝癌方面重点阐述整合素与肝脏疾病关系。
整合素是一种细胞表面受体,由α及β组成,Hynes发现有18个α和8个β亚基,通过非共价键形成24个异二聚体,目前已发现至少18个α亚基,包括α1-α11、αD、αE、αI、αM、αV、αX和αIIb。9个不同的α亚基(α1,α2,α10,α11,αD,αL,αE,αM,αX)含有I-结构域结构,这是配体结合位点的关键,其他几个α亚基(α3、α4、α5、α6、α7、α8、α9、αν、αIIb)不含I-结构域,但由β-Propeller构成配体结合位点。整合素β的家族可分为β1-β8,它们与α结构相结合分布在各种细胞及组织中,如β1的广泛分布,β2分布在白细胞中,β3分布在血小板及巨噬细胞,β4及β6分布在上皮细胞,β5分布在神经细胞及肿瘤细胞,β7分布在NK细胞及B细胞及β8分布在转化细胞等。整合素相关黏连蛋白如辅助肌动蛋白、桩蛋白等的作用经研究包括增强基质黏附位点的信号转导来刺激整合素介导的细胞与基质的黏附等[1]。整合素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有相似结构,因为它们在各种生理细胞功能中起着核心作用,包括许多疾病的病理生物学[2],已逐渐成为细胞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和病理学的研究热点。大量的研究人员将整合素独特的结构和生物学功能应用于人或动物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如胃癌、肝癌,受损的组织等。研究表明,正常肝脏组织中及病理肝组织中存在多种整合素,并具有各种生物学功能,参与生物学过程。
一、整合素与肝炎
我国是肝炎大国,以具有传染性的病毒性肝炎为常见,最新一项对于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研究表明,细胞中分泌的骨桥蛋白(OPN)与整合素ανβ3和CD44的相互作用是HCV复制和组装的关键。OPN是一种含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RGD)的趋化因子样的细胞内磷酸糖蛋白,在炎症、肝损伤、肿瘤发生和血管生成过程中都有重要作用,能促进细胞趋化、黏附和迁移。以往研究表明,OPN通过与整合素ανβ3结合,促进IL-12的产生,并通过与CD44相互作用抑制IL-10的产生,从而促进Th1型免疫应答[1],丙型肝炎病毒基因组是一个长度约为9.6kb的单链RNA,编码由病毒蛋白酶和宿主细胞信号肽酶切割为成熟结构的前体多蛋白:核心蛋白、E1、E2和非结构蛋白(P7、NS2、NS3、NS4A、NS4B、NS5A和NS5B),为探讨CD44和整合素ανβ3在OPN介导的丙型肝炎病毒蛋白表达中的作用,采用Westernblotting方法进行了抗HCVNS3、抗HCVNS5A、抗HCVNS5B细胞裂解物的分析。结果表明,NS3、NS5A、NS5B和用siCD 44和siβ3转染的HCV感染细胞核心低于对照组,提示CD 44和ανβ3在HCV复制中起重要作用[3]。这种HCV-宿主依赖性的发现是抗病毒的新策略,并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病毒的发病机制和潜在的治疗靶点。
二、整合素与肝纤维化
肝纤维化是对慢性肝损伤的过度愈合反应,随后发展为肝硬化,导致门静脉高压、肝细胞癌或肝功能衰竭[4]。ECM过度沉积是慢性肝病发展到肝纤维化的必经阶段,纤维黏连蛋白(FN)是ECM的主要成分,而FN是整合素的相关配体。肝星状细胞(HSC)活化是肝纤维化发展的关键环节,肝纤维化形成涉及多种细胞因子。整合素在肝纤维化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HSC及肝窦内皮细胞(HSEC)表面均存在整合素α5β1、ανβ3、ανβ5[5],研究表明,整合素ανβ3、ανβ5在肝脏纤维化中,与促进胶原沉积、促进细胞增殖有关。曾报道过整合素ανβ3和α5β1分别是大鼠HSC或大鼠胰腺星状细胞上的CCN2(结缔组织生长因子)受体。而这些受体的主要结合位点位于CCN2的c端103残基中[6],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CN 2,又称CTGF)是一种在HSC介导的纤维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细胞蛋白。ccn2分子由四个结构模块(ccn2 1-4)组成,研究中发现大鼠活化的HSC通过模块4与整合素ανβ3结合,诱导肝纤维化[7]。先天性肝纤维化是一种遗传性胆管病变,是由PKHD1基因突变引起的,Locatelli等[8]实验表明了PKHD1胆管细胞通过上调整合素ανβ6对巨噬细胞释放的促炎细胞因子作出反应,从而诱导纤维化发生。Sugiyama A等对整合素配体骨膜蛋白(periostin)的研究表明,periostin发挥由整合素αν介导的强效促纤维化活性,表明periostin-整合素αν轴可作为肝纤维化的新型治疗靶点[9]。在晚期纤维化中,HSC和肌成纤维细胞(MF)被ECM激活,并通过整合素β1来收缩和增加ECM合成。整合素的激活可促进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的激活,从而发生MMPs的下调发生纤维化,除此之外,不受调控的MMPs的产生和活动也会促进组织损伤,并驱动继发性成纤维反应,目前,人们也对整合素方面做很多研究,总结整合素拮抗剂αν的前临床和临床性研究[10-12],在靶点和纤维化特异性方面,着重强调整合素ανβ1和ανβ6。尤其是整合素ανβ6,它仅在活化的胆管细胞上表达,具有成纤维祖细胞的特征。ανβ6将增殖的胆管细胞的牵引力传递到潜伏期相关蛋白(LAP),从而使活化的转化生长因子(TGF β1)释放,这种最有效的纤维原性细胞因子,来自其不活跃的前体LAP,引发相邻HSC/MF的纤维激活[13]。以上机制同样适用于在免疫细胞上更广泛表达的整合素ανβ8。因此口服活性小分子抑制剂和抗整合素ανβ6的阻断抗体可有效抑制胆道和非胆道纤维化的发生。
三、整合素与肝癌
肝癌是各种肝病最终发展阶段,肝癌组织中整合素通过各种通路与配体发生作用,有研究采用PCR和原位杂交技术检测肝癌、癌旁组织和正常肝组织中整合素α5β1mRNA的表达水平。肝癌组织中整合素α5β1的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和正常肝组织,整合素α5β1表达水平与肝癌分化程度及恶性转化密切相关[14]。肿瘤细胞和宿主细胞表达的整合素可直接参与癌症转移的控制和进展。在肿瘤发生过程中,整合素表达的变化、细胞内整合素功能的调控和整合素配体结合所感受到的信号变化,影响着肿瘤细胞与周围环境[15]。有研究表明敲低整合素β1的表达显著降低了肝癌细胞(HCC)的增殖,整合素β1可以激活多种细胞内通路,包括FAK通路,调节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存活。小鼠肝脏中过度表达的胶原I增加了整合素β1和下游磷酸-FAK表达,胶原蛋白I通过调节途径整合素β1/FAK途径促进HCC细胞增殖,胶原蛋白可作为治疗的新靶点[16]。HCC分泌大量层黏连蛋白(Ln-332),刺激肝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Ln-332是整合素α3β1和α6β4主要的配体蛋白,通过整合素连接激酶、焦黏连激酶和磷酸肌醇3-激酶等信号介质,触发不同的胞内信号通路。整合素α3β1和α6β4在肝癌细胞表面有不同表达,调节细胞的黏附、迁移和侵袭等不同功能。有研究探讨索拉菲尼(Sorafenib)与Ln-332的作用,在Ln-332和HSC条件培养液(CM)存在下,索拉菲尼能抑制肝癌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17]。既往研究表明,OPN通过与整合素ανβ3受体的相互作用参与肝癌的进展和转移[18]。相关实验表明,当ανβ3被刺激因子激活时,它可以与增强子或启动子序列结合,来控制靶基因刺激炎症和细胞增殖的激活和转录,用免疫组化方法对OPN及整合素ανβ3受体的关系进行临床分析,从305例肝癌患者的存档石蜡包埋组织切片中获取临床资料,305例正常肝组织标本从癌灶周围获取作为对照,使用增殖标记ki-67对肝癌肿瘤细胞进行OPN和ανβ3的检测。Ki-67指数在肝癌中较高,而在正常肝组织中较低,OPN主要表达于细胞质,ανβ3主要表达于细胞膜或细胞质,肝癌组织中ανβ3的表达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19]。血管生成样蛋白质(ANGPTL1)与肿瘤细胞血管侵袭、肿瘤细胞转移及肝癌预后不良有关,在肝癌细胞中异位表达的ANGPTL1有效降低了它们在体外和体内的致瘤性、细胞运动性和血管生成,ANGPTL1通过减弱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和蛋白激酶(AKT)信号传导抑制血管生成,并与整合素α1β1受体相互作用以抑制下游的FAK/SCR-JAK-STAT3信号传导途径,因此发现了ANGPTL1是HCC的新型治疗剂[20]。
既往做过大量实验表明整合素与肝脏疾病无论是肝炎、肝纤维化还是肝癌都存在着密切联系,并通过对整合素在肝病中的作用,研究出相关治疗肝病的药物,目前一些已开发的拮抗剂正等待临床前和临床评估。除此之外,仍有许多问题有待阐明,如确切的调控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确定整合素介导的细胞在不同细胞或组织中的增殖、迁移。因此,更好地了解整合素的特性及其对人或动物功能蛋白的影响,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