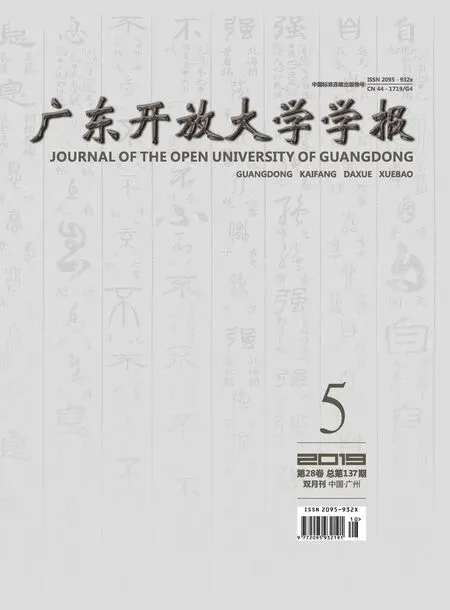《诗家直说》研究综述
2019-03-17崔洪爱山秀坤
崔洪爱 山秀坤
(1.济南大学,山东济南,250022;2.济南科技中等职业学校,山东济南,250022)
谢榛,字茂秦,号“四溟山人”,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市)人。其生卒年在学界还未形成统一的定论。李庆立先生在《谢榛生卒考》中指出,谢榛应生于1499年,卒于1579年[1]。谢榛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并称“后七子”,高举复古的大旗,将明代文学的复古潮流推向高潮。后七子成立之初,谢榛复古派提供了理论的指导,钱谦益在《列朝诗集》曾言:“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茫无适从,茂秦曰:‘选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摈茂秦,其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2]钱氏认为谢榛实际上是后七子的理论先行者,为尚处在迷茫期的李攀龙等人提供了复古的方法,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在谢榛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谢榛诗学思想的正是《诗家直说》(又名《四溟诗话》)。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诗家直说》的著作不断增加,其中包括大量的校注整理本和选录本,以其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有李庆立先生的《谢榛研究》和赵旭的《谢榛的诗学及其时代》;较早涉及《诗家直说》研究的是范建明先生的《谢榛及其诗论》。
一、版本研究
关于《诗家直说》版本的考证较为完善的是李庆立先生的《谢榛<诗家直说>考述》以及《<诗家直说>版本源流及“重修赵府本”讹误匡正》。后者是由前者再次整理编辑而成,内容总体相差不大,前者收录在《谢榛研究》一书中,后者于1995年发表在古籍研究整理学刊上。前者考证更为详细,对于书名、成书年代、书之真伪都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考证了《海山仙馆丛书》中《王渔洋序》的真伪,指出此序并非王士祯所作,而是照搬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谢榛》条的内容,只是略微改动了其中的几字而已。但是后世的许多版本依旧多用其为《王渔洋序》。李庆立先生在《谢榛<诗家直说>考述》中考证了《诗家直说》现存的五种明代版本,“万历二十四年赵府冰玉堂刻《四溟山人全集》后四卷《诗家直说》、万历三十六年剞劂《四溟山人全集》重修后四卷《诗家直说》、万历三十九年邢琦等校刊《诗家直说》四卷单行本、万历四十年盛以进编刻《四溟集》附于卷首之《诗家直说》二卷、陶珽辑《续说郛》34著录之《诗家直说》,其书名均为《诗家直说》”[3]。李庆立先生共考证了《诗家直说》的17个版本,除了以上5个明代版本,李先生还提到了清顺治年间陈允衡编刻《诗慰》初集,将诗与诗话合为一卷;清乾隆甲戌年间胡曾耘雅堂刻本,清道光乙巳年潘仕成辑的《海山仙馆丛书》录本,清光绪十一年间王启原《谈艺丛珠》著录本等版本。在此文中,李庆立先生详细说明了由《诗家直说》到《四溟诗话》名称的演变的过程,胡曾耘雅堂刻的《四溟诗话》四卷单行本是最早使用《四溟诗话》一名的,也就是说,《四溟诗话》本就是《诗家直说》的别名,不应将其视为两种书。此外,对于成书年代在历代著作中,都不曾提及,而李庆立先生则在此文中考证了《诗家直说》的成书年代。李庆立先生认为《诗家直说》一书大概是谢榛1563年游历山西时开始写作,大约到1568年回安阳的第二年才完成。此外,李庆立先生还匡正了《诗家直说》“重修赵府本”的96处讹误,在这两篇文章中均有记载。李庆立先生对于《诗家直说》源流的考证是十分完整和详细的,基本勾勒出了《诗家直说》的版本演变历史,这为系统研究《诗家直说》提供了便利。
另外关于《诗家直说》版本问题进行过考证的是赵伯陶先生的《<四溟诗话>考补》,他的考证要早于李庆立先生,对于《诗家直说》版本源流的考证与李庆立先生基本一致,其中对于万历四十年盛以进编刻两卷都因是残本,两位先生对此版本与原作是否有出入存疑,有待考证。
两位先生的版本考证为《诗家直说》的研究提供了源头作用,为后代研究者选用《诗家直说》本子提供了指导。
二、诗学思想研究
关于谢榛在《诗家直说》中所体现的诗学思想的研究是历代研究者的重点,从前后七子整体研究,再到后七子研究,再到谢榛思想个案研究,对于谢榛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完备,无论从论文还是专著,其论甚多,因为篇幅原因,在此只选录部分文章或专著作为代表。
1987年朱恩彬先生的《谢榛及其<四溟诗话>》指出谢榛的文学思想与何景明是一脉相承的[4],分析了《诗家直说》中“自成一家”的具体要求、对严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文学批评观等方面,反对仅仅将谢榛的文学思想视为形式主义,这对谢榛《诗家直说》思想的研究无疑是具有推动作用的。但当时结合西方文论评析中国文论尚处于起步阶段,此文论述尚有青涩之感。张晶的《论谢榛的诗学思想》除了论及谢榛对严羽的开拓外,还将目光转向了谢榛的“情景论”,从整体论述过渡到关注谢榛诗说的要点。而李庆立先生的《谢榛的情景交融说》则对“情景交融”说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他(谢榛)把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相触’,看做诗歌产生的基础,并强调这是诗人必须遵循的常轨,无疑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的”[5],并且论述了兴、虚实关系、“含糊说”等,进一步论述了《诗家直说》的论点,从而扩大了《诗家直说》理论研究的范围。杜宗兰的《谢榛的生平及其诗学理论》对《诗家直说》中提到的诗法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并对自然、情景、悟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将诗法与诗论相结合,进而完善了《诗家直说》研究的范围和系统性。孙青玥《谢榛诗学理论批评研究》从《诗家直说》的诗歌创作论、作品论、批评论出发,主要论述了《诗家直说》中的感兴、立意、情景、真实、养悟、句法、修改、繁简、虚实、复古、诗格、诗韵等问题,认为“他(谢榛)推崇先秦汉魏古诗,但却反对刻意为古;推崇盛唐而贬斥宋、明诗歌,但同时也看到了宋明诗歌的可贵之处”[6]。此文看到了谢榛对宋代诗歌的关注,这对打破复古派一味追求诗学盛唐的偏见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孙青钥还发表了十几篇相关的论文,但是也都只是停留在对《诗家直说》内容的分类和整理上。张丽锋《谢榛诗学范畴论》从哲学范畴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述了《诗家直说》的诗法论、“浑”和“悟”的渊源以及表现,认为“(谢榛)后虽然被排挤出社,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诗坛的影响,主要是在于他所提出的诗歌理论有着众多合理的因素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7]。客观评价了谢榛的文坛地位,并将其诗歌理论的研究回归历史现场,这是十分可贵的。但是整篇文章虽用哲学范畴一词,角度新颖,但是观点与前人无异。王志军《<四溟诗话>:倾注“诗心”的诗学论著》提出“以‘诗心’为中心论题,就是认为谢榛作为诗人,他的丰富深刻的生活体验,他的饱满热烈充满诗性的情感,他的兴感颖悟的思维,他的正直坦荡的胸襟,都昭示了他是出色的诗歌批评家”[8],此文论述了《四溟诗话》中的以情为本质内容的诗歌所体现的“诗心”范畴,以“兴”和“悟”为中心的“诗心”表现。赵旭的《谢榛的时代及其诗学》论述了《诗家直说》中的本体论、方法论以及批评鉴赏论,认为“他(谢榛)积极教人作诗,结合具体的例证,深入浅出地对相关理论问题进行阐释,对诗歌的评鉴和创作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意见。在中国诗学史上,谢榛的诗学有着承前启后的地位”[9]。肯定了《诗家直说》重要的理论意义,并对里面包含的诗学理论进行系统的阐释,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借鉴。此外周宇婧《谢榛其人与其诗论》一文将谢榛的生平与诗论结合研究,其中重点论述了《诗家直说》中的“歌诗”问题。以上硕博论文大多从总体把握《诗家直说》的诗学理论,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从“点”出发,论及《诗家直说》的思想内容。
(一)诗法研究
谢榛的诗法绕不开的就是他的“以盛唐为法”。李庆立先生的《论谢榛“以盛唐为法”》认为“谢榛‘以盛唐为法’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曰全、曰合、曰中、曰活”[10],并且将“以盛唐为法”的重要途径定为“悟”;《再论谢榛“以盛唐为法”》提到“其所标举之‘盛唐’,乃是直接继承了高棅之说”[11],从而表明明代的复古实际上是早早就已经开始了的。此外,此文还论及了谢榛的声律论、兴和点化,分析了谢榛的点化之法:缩银法、偷狐白裘法、取形法、翻案法。美中不足的是,这两篇文章只是停留在了理论的分析层面上,而未能结合创作实践加以分析。孙学堂先生的《论谢榛诗学》则结合谢榛的创作对谢榛的诗学思想进行了评价,其评价较为公允,既看到谢榛学古保守,拘于外在格调的一面,又肯定了“《四溟诗话》是明代诗论中转变风气的过渡者,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12]。而《谢榛的改唐诗综论》则将谢榛的改作与唐代诗人的原作进行比较,分析谢榛的“点化之法”,“调”、“格”之方法论。孙学堂先生认为谢榛的改唐诗反映了后七子“格调说”的弊病,只是学习了唐代诗歌的外在形式[13]。对孙学堂先生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的是他的弟子瞿勇。瞿勇在《谢榛的唐诗学》中结合谢榛的诗作较为详细的论述了谢榛诗法中“以盛唐为法”和改唐诗,观点与其师无异,但论述更为详尽,进一步完善了对谢榛诗法的研究。李琳的《谢榛诗法简论》,在前人的基础上作者将谢榛的诗法总结为“提魂摄魄之法、临字之法、先江南而后河东、三剥其皮、缩银法、妙在含糊、取鱼弃筌、戴帽法、酿蜜法、远而近、直取心肝法”[14]等十一种,但只是简单介绍了这些作诗法的含义,并没有深入挖掘其内在要求。而对谢榛的诗法论论述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是李伟的《谢榛诗法论研究》,此文分析了谢榛的命意、句法、篇法等具体方法,并将其和谢榛的批评论和创作实践相结合,“在以诗法感悟诗歌,以诗歌证明诗法,以及对他人诗作的修改中,谢榛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见解,为我国古代诗法论的不断拓展与深入作出了杰出贡献”[15]。但是在分析批评论时只是选取了李、杜二人,忽视了谢榛对同时代人的批评,有所欠缺。
(二)审美鉴赏思想研究
1986年陈朝慧发表《论谢榛的美学思想》,从“那种‘妙在含糊,方见作手’的审美意境朦胧性、‘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的主题宽泛性、‘以兴为主,漫然成篇’的情感自由性以及‘作诗贵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的艺术辩证思想”[16]论述了谢榛的美学思想,对谢榛的美学思想做了初步探讨;1987年李庆立先生发表《谢榛的美学思想二题》,论述了谢榛美学思想中的中正思想和自然之美,但是并没有展开讨论。1992年李庆立先生又发表《谢榛美学思想探索》,指出“崇尚‘中正’,是谢榛的重要美学思想”[17],而这种“中正”的内容主要便体现在集盛唐诸家之长而自成一家、适度和谐调等主张中。此文后被收入先生的《谢榛研究》一书中。另外一篇《“天然与浑然,无适而不可”——谢榛美学思想探索之二》,探讨了谢榛的自然与浑然,也就是自然之美和精工之妙之间的关系,语言、声韵、法式、风格、情感、感兴等方面是对天然之美的追求,诗的风格、寓意、命题、语言、结构等方面是浑然之美的追求,指出谢榛美学思想中对矛盾对立双方和谐统一的追求[18]。1999年发表的《天然与浑然沆瀣融会是诗歌追求的极境──谢榛美学思想再探》与上文观点相同,在此便不再赘述。王顺贵先生的《谢榛诗歌审美体验方式论》,分析了谢榛以“悟”为中心的审美体验论;《谢榛诗歌审美体验生成论刍议》,从“兴”的角度分析了谢榛审美体验论;《谢榛诗歌审美艺术风格论》从谢榛对诗歌审美艺术风格的形成、结构及表现三方面论述了谢榛诗歌审美风格;《谢榛诗歌审美主体建构论》,从谢榛德才兼备的审美胸襟、自成一家的审美胆识与审美能力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谢榛的审美主体的建构。《从<四溟诗话>看谢榛的诗歌审美意象论》,探讨了《四溟诗话》中对于诗歌审美意象的生成、结构和特性,主要从情与景的关系层面进行论述。王顺贵先生的这一系列论文,较为系统的论述了《诗家直说》的美学思想,虽然某些地方的论述略显生硬,但是也开拓了《诗家直说》研究的新方向。冯仲平的《论<诗家直说>的审美理想》认为“自然全美、性情之真与境界之妙组成了《诗家直说》的审美理想结构”[19],作者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对《诗家直说》的单个文本研究,而是多加追溯,颇为可贵。张晶《谢榛诗论的美学诠释》认为“谢榛诗论颇有美学探究的价值和空间,对我们今天思考美学问题的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可以提供更为深入的思考向度”[20],此文从审美发生角度论谢榛的“感兴”,并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层面分析了谢榛有关情与景之间的关系,作为审美主体,此文还论述了“悟”对诗人的重要性和要求。较之于王顺贵先生的论述,此文更加深入。瞿勇的《“听之金声玉振”——谢榛对诗歌音乐美的追求》强调了谢榛对于诗歌音乐美的追求,同时也指出了谢榛追求音乐美而忽视内容的弊病[21]。这是对于研究《诗家直说》声律较新的视野。
(三)比较研究
《诗家直说》与其他诗学的比较研究中,较多的是与严羽的比较研究,基本认为谢榛的《诗家直说》是继承发展了严羽的“格调”、“妙悟”之说。张晶、刘洁的《谢榛诗学对严羽的超越及其时代意义》认为谢榛继承了严羽的“格调”、“妙悟”,但又加以改造,使格调说开始向性灵说、神韵说转变[22]。作者以独特的眼光看到了《诗家直说》思想的承上启下作用,但是对于严羽与谢榛思想本源的探究作者却有所疏忽。同样提及《诗家直说》思想的承前启后性的还有李义天的《谢榛:复古在承前启后之间》。曾君之的《论<四溟诗话>对<沧浪诗话>的继承与发展》还论述了两者在诗法上的异同,角度新颖,但是论述缺乏深度。文章最后还比较了谢榛与严羽身份的不同,谢榛不仅仅是诗论家,同时还是一位诗人,但是这种比较缺乏意义。而吕君丽的硕士论文《试论谢榛对严羽诗论的继承和开拓》,较为全面的阐述了谢榛对于严羽的继承和发展,认为“谢榛的诗法相对于严羽,趋于具体、精微化,更多结合了古人作品来谈”[23]。除了论述“感兴”、“禅悟”外,作者还论述了谢榛在诗法和审美鉴赏方面对严羽诗学思想的开拓,颇有新意。
除了与严羽的比较研究,还有一些研究将目光聚集在了谢榛与后七子其他成员的比较中。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将后七子理论总体进行了论述,将其理论视为一体研究,拓展了人们对于复古派的认识,但是忽视了其诗论的差异性。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中,将谢榛诗学思想作为单独一节来论述,比较了其与李攀龙“视古修辞,宁失诸理”[24]的差别,“谢榛的《诗家直说》不仅一扫李攀龙‘视古修辞,宁失诸理’的机械论和盲目性给诗文批评投下的暗影,而且在理论上平添了不少辩证思维的亮色”[25]。陈书录在此重点论述了谢榛的“超悟”和辩证思维,分析了《诗家直说》中强调气格与“妙悟”、变俗为雅等之间的矛盾,颇有深度。林启柱的《谢榛、王世贞诗论比较》将谢榛与王世贞的“格调”进行比较研究,两者强调的方面各有不同,但是两者都表现出复古阵营的新变,都体现了在复古运动后期,复古派思想向性灵、神韵方向靠拢的趋势[26],是一篇较为新颖的文章。
此外还有马宁的《浅论黄庭坚、谢榛的诗歌创作观》,既看到了黄庭坚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法与谢榛的酿蜜法实质上就是改诗论的本质特征,又看到了两者因为时代、自身经历等原因所造成的具体要求的不同[28],拓展了《诗家直说》比较研究的视野。
三、近现代校注整理研究
(一)《四溟诗话别裁》
此本载于张世尧(字振宇)所编《诗话别裁三种》,根据《海山仙馆丛书》本《四溟诗话》,从中择取八十五条。文稿不曾刊行,现仅存稿本,藏于北京图书馆。
(二)《历代诗话续编》
《历代诗话续编》由丁福保编录,其中收录《四溟诗话》四卷,共401条,主要依据《海山仙馆丛书》。但是没有收录“海山本”卷二中的六条诗论。1983年再版时李庆立先生、王季欣先生等曾进行过校订、增补,保留了胡曾的《序》和《王渔洋序》,在校订过程中选择了“胡曾本”作为底本。但对于赵府冰玉堂刊刻的版本、陈珽辑本、陈允恒本不曾顾及。作为重要的诗话总集,《历代诗话续编》的版本依旧不能忽视。
(三)《四溟诗话》
目前以《四溟诗话》为名的点校本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为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溟诗话》,此书收在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处编》中,共四卷,407条。此本依据《海山仙馆丛书》著录《四溟诗话》为底版,加以点校,内容与《历代诗话续编》基本一致。
第二种是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溟诗话》,与《姜斋诗话》合订为一本。宛平在《校点后记》中提到,此版是以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为底本,并且依据潘仕成《海山仙馆丛书》进行增补、改正。但是由于版本选择不甚严谨,而且点校者较为疏忽,此本错误较多,漏收了许多条目。据李庆立先生统计,此本讹误有四十多处。在前代版本基本现存的情况下,出现如此之多的错误,实有不该。此本错误之处王季欣先生曾发表《<四溟诗话>校补》,增补了其中六条,指出其中八处文字错误。后赵伯陶先生在《四溟诗话考补》中再一次对此本进行了辑补,补充了十九条。
(四)《诗家直说笺注》
《诗家直说笺注》于1987年5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共四卷,416条。本书主要以万历三十六年剞劂重修赵府冰玉堂本为底本,并参考其他历代版本进行校勘,资料详实,对先前十几个版本进行了对照,全书按语100多处,校语108处,引用书目400多种,近680条笺语,1100多条注释,广征博引而又不失己见,既有纵览古今的大气,在细微处又见严谨。贾炳棣先生曾言:“《诗家直说笺注》的出版,对于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谢榛乃至把握前后七子的诗论和明代诗坛风气,有着积极意义。”[30]对于明代诗文历来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尤其是对前后七子摹拟之风更是诟病甚多,但李先生此书为研究明后七子的文学理论提供了便利,对重新审视复古派的文学主张与文学成就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纵观《诗家直说》的研究,建国以来对于其理论价值挖掘不断深入,这对重新认识《诗家直说》的理论意义以及复古派的文学理论都有重要意义。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首先。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于其美学思想和诗法论的分析上,对于其诗论与作品的关系论者甚少。目前对谢榛的诗歌进行研究的有邵传永的《谢榛论》、瞿勇的《略论谢榛诗歌》、王莹的《诗歌研究》等少量学位或期刊论文。李庆立先生的《谢榛全集校笺》对谢榛的文学作品做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后来的研究者应当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一些。谢榛是一个理论家,但是同时也是诗人,在研究其理论时不应该完全脱离其作品,而要坚持“两条腿走路”。
另外,还应该以小见大,通过此类的个案研究而把握时代的脉搏,知人论世是文学研究不能抛弃的重要原则。对于时代背景对其思想的影响还有待探讨。
最后,对于谢榛的一些比较研究还有所欠缺,其与后七子以及其他诗论家的理论比较研究有待进一步挖掘,在这种比较研究中应当看到谢榛对宋代文学的关注,这对于重新审视明代复古派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李庆立先生所言:“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应是有利于当前创作和理论的发展,不能仅仅为研究而研究。”[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