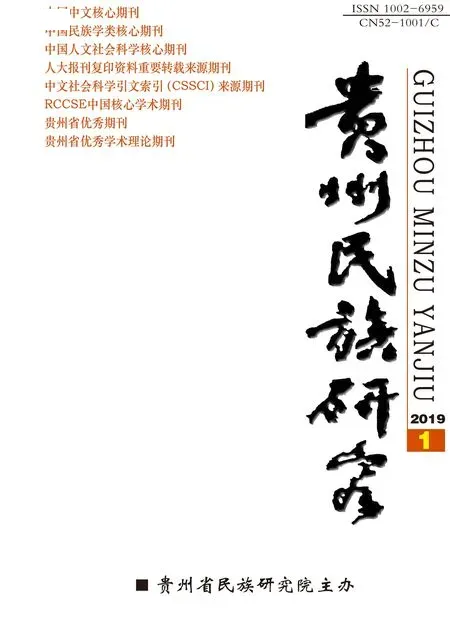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生活与家庭伦理特征探析
2019-03-17冯盛国
冯盛国
(宝鸡文理学院 政法学院,陕西·宝鸡 721013)
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中国北方地区由于复杂的历史地理气候原因,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与中原农耕文明生产方式差异较大的游牧社会,专业化游牧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该社会以游牧作为主要特点,流动性和分散性为其主要特征。游牧社会的社会生活和家庭伦理价值也与中原农耕社会形成巨大的差异,本文选取对待老人的态度与婚姻行为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力求厘清游牧民族家庭伦理的独特性,在此基础上对游牧民族家庭伦理的价值特点和生成模式进行分析。
一、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环境
北方游牧民族是指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以游牧为主要生业方式的人群。一般说来,按照中国地理气候分布,中国北方游牧区由西向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的游牧社会,分别为高山草甸、草原和临海地区的游牧生活。最为典型的游牧民族应当是鄂尔多斯形态的草原游牧民族类型,以早期的匈奴民族为代表。
在历史早期,中国地理分界线农牧分界的西北部族群混杂。这些游牧民族在历史上一般都处于游牧分界线上,也就是400毫米年等水量线的西北方向。在公元前1500年开始的气候干冷化到公元前4世纪完成了农业和牧业的分离,农牧交错就已确立[1]。农牧交错带逐渐形成了差异明显的人文景观,即游牧区和农耕区。
我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处于亚欧大陆的内陆地区,受到大陆和海洋的影响,气候环境呈现出经度地带性与纬度地带性共同作用的情况。在西部高原地带,还受到垂直地带性的影响。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年降水量低于400毫米,就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上文论述的农牧交错带的核心区域基本上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诸多研究成果表明,在温带半干旱地区,绝大多数的光热资源都已经满足了旱作农业的要求,能使得旱作农业存在和维持的另一个基本气候条件是年降水量大于400毫米。[2]
我国受到东亚季风的影响,降水年际变化较大,农牧的分界线也有所摆动,总体说来,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农牧分界线以今天天水地区为圆心,向北延伸到今天大兴安岭北部地区,向南延伸到云南腾冲地区,这条线将中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东南部适合农耕,包括旱作和水作农业,西北部主要以畜牧为主。农牧分界区域是族群冲突的重要舞台。[3]在这条分界线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也有一定的变化,大致说来,西周后期整个中国气候已经转向寒冷,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大象向中国南部迁徙。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波动期,形成两个波谷一个波峰,气温总体趋势是升高的。[4]西周到春秋之际正是北方游牧社会逐步形成的时期。
中国的地形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态势,黄土高原的北缘,山西和陕西北部就是农牧分界区,更北部的蒙古高原则是以畜牧为主的地区。在青藏高原的东缘,河湟谷底一带也有游牧活动。我们可以根据自然地差异将畜牧业分为西部高原型、中部鄂尔多斯型和东北型。典型的蒙古高原型可以作为分析的样本。从气候地理的角度讲,畜牧和农耕是两种自然形态决定的结果,直接影响了社会生产的方式。
二、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
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生活的特征是对游牧社会自然地理的因应,游牧民族生存的社会环境主要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居民主要从事游牧活动,其社会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暴力和掠夺的性质,社会组织呈现出移动和分散的特点。
游牧生产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几乎完全依赖动物的生产方式,通过不间断地改变位置放牧间接获取动物性食物的一种组织生产的形式。王明珂先生结合中国北方地理气候条件,按照实际的情况,把中国北方专业游牧化的起源分三种情形进行了分析,针对中国最为典型的游牧民族生产方式即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和辽西地区的专业化游牧的起源作了细致的研究。[5]研究认为,专业化游牧社会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社会的分裂性与移动性。
游牧经济的特点是移动性,就是传统典籍记载的“逐水草而居住”,畜群要有青草才能生存,牧民放牧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自然利用的过程,不是一个干预控制的过程。《国语》记载“戎狄贵物而易土”,当一个草场的青草被吃完了之后,为了保护草根,就必须转场,依据气候的变化和温度的差异,有“冬营地”和“夏营地”区分,古书将这种国家称为“行国”。这种迁徙并非漫无目的的流浪,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和线路进行的。大体是季节性的迁徙,可以分为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按照季节规律进行周期性的迁移。
第二个特点是经济生产的分散性。根据牲畜的种类和食性进行分散放牧,马、牛、羊所吃的草各有差异,各自的放牧方式也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放牧不能过分集中。草原的承载量是有限的,所以就会出现相当的分散性。经济生产的分散性也就决定了人群的分散性特征[6]。
在移动性和分散性的基础之上,人们的生活特征就呈现出第三个特征,就是生产的不稳定性。游牧经济是一种脆弱的经济形式,干旱、狂风、大雨、暴雪这些灾害性天气往往都威胁着游牧民族的生存安全。一旦出现灾害性天气,其生产就会受到较大影响。
在极端的恶劣环境下,人们的文化传承难以顺利进行,周期性的灾害会降低人们对于经验积累的依赖,生产技术不容易被总结和传承,会出现同一地区的游牧民族,后者反倒比前者落后的情况。鲜卑在匈奴之后占领其故地,其生产力水平比匈奴更为低下。[7]概括来说,与中原农耕社会相比较,北方的游牧部落呈现出分散性的特点,社会生产也具有不稳定性。可以概括为分裂和平等自主的特征,为“分裂型的社会结构”,管理层级也简单得多。[8]
社会生产方式主要指人们用何种方式获得物质资料,在生产过程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组成方式,是人们用何种方式获得能量得到物质的生产过程。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人们都是间接获得太阳能。定居农业生产是通过严格管理,控制农作物的生产过程,直接获得食物和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畜牧业则是通过饲养动物,间接获得食物和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实际上,西周到春秋时期,许多边缘族群是二元的生产方式,即农业和畜牧业兼营。随着气候的变迁,在北方逐渐出现了专业游牧化的趋势。这些特征都加剧了生存的困难,使得一个老人在社会中的贡献会降到很低,尤其是在战争和类似战争的劫掠生存状态下,老人确实会成为社会的负担,所以往往老人就会被遗弃让其自生自灭。
三、游牧民族在尊老和婚姻形式方面伦理的独特性
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其形成与人们所在社会的背景环境密切相关。尊老这种价值观念深入中国文化的脊髓,即后世的百善孝为先的思想观念。可是在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中对待老人的态度却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体现出贱老的价值取向。《史记·匈奴列传》云:“其畜之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9]前面一句话是说以游牧为主,具有移动性的特点,后面主要表述对老人的态度,肥美的食物由健壮者享用,老者只能吃剩余的食物,饮食的高下差别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体现,在北方游牧社会中,确实存在着贱老,歧视老人的道德取向。可以看到,在对待老人的态度上,北方游牧部落与中原华夏部族差别甚大,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
对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家庭伦理价值的比较中,除了对待老人的态度的差别之外,在婚姻形式上也呈现出与农耕民族不同的道德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对待后母和寡嫂的婚姻问题上。在周代礼乐文化系统中,婚姻制度和宗法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嫡长子继承制落到实处,保证王位继承权的稳定。春秋时期的文献提到贵族婚姻中有陪嫁媵婚制,即在嫁女之时以新娘的妹妹或者侄女为媵,是为了确保后代继承人的问题。即使到了春秋时期礼仪文化面临崩坏的危险,贵族社会仍然遵守一定的规则,坚决反对烝报婚姻。所谓烝,就是嫡子与庶母或者庶子与嫡母之间的婚姻,也就是父亲去世之后儿子娶父亲的妻妾。报就是指“淫亲属之妻”,指贵族男女旁系亲属不同辈分的婚姻,可以是侄子辈与叔母或婶母,也可以是叔收继嫂子的行为。这种婚姻制度在春秋时期是被礼仪文化所唾弃的,也不是婚姻的主要形式。这种价值与周代礼乐文化所遵从的价值观是相违背的[10],相关资料证明,西周社会并未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时期出现的烝报婚姻不能算作一种婚姻制度,也不是普遍遵守的法则,是受到社会伦理价值否定和排斥的个人行为。[11]但是在北方的游牧社会,类似于烝报婚所体现的制度则是这个社会所必须遵守的原则。游牧民族的这种婚姻制度是族内转房婚,实际上相当于华夏的烝报婚,就是“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子”。[12]在民俗上这种婚姻制度被称为收继婚制,其实就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社会中类似于华夏礼乐文化中烝报婚的族内转房婚姻,是一种制度安排,正好与华夏的伦理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在农耕民族被看作乱伦行为被否定的婚姻形式,在游牧民族却是被伦理道德所提倡的。
通过对待老人和婚姻制度相关内容的论述,可以看出游牧民族在对待老人和寡母、寡嫂态度上,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对待同一事件选择不同的价值选择,在家庭伦理价值选择方面有一定的独特性。这背后的原因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由于游牧社会生存条件是极为恶劣的,死去丈夫的妇女或者后母很难生存,社会的分裂性会强化这一趋势。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育龄妇女在整个社会中是稀缺资源,如果让这种资源浪费,就会严重威胁整个部族的生存。
四、游牧民族家庭道德生成逻辑:帕累托最优原则
社会这个复杂系统是一个自适应的系统,价值观的选择与生成也是遵循一定的规则。哈耶克的研究证明,习俗并不是天然自动拥有的东西,而是产生于许多人没有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其行为会有哪样结果的大众的各个个体的人的总和,因此习俗是无意识的人类行为的叠加累计的结果,并且能够通过遗传和模仿而传承延续下来的整个文化的遗产。[13]
习俗生成之后会产生一定的惯性,并且会固化为社群或者社会成员的常态,逐渐会变成一种规则和约定,大家都按照这个规则做事情,就会变成一种模式。人类就会摆脱霍布斯世界人人为强盗的未开化社会。[14]有许多经济学家将习俗生成理解为一种帕累托改进,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家阿罗就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社会行为的规范,包括伦理和道德的准则。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补偿。并且这一整套习俗规范可以弥补价格体制所不能提供的效率。[15]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有些习俗和信仰并不一定是纳什均衡,也并未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这些现象可以看作是习俗和道德生成中的“杂音”,并非主流的,并且一个社会当中如果“杂音”太多,可能会危害主体,造成整个社会效能的降低。
事实上,在社会中人们在选择一种社会价值的时候会产生从众的心态,毕竟人是群体中的动物,个体的选择符合社会的利益时,就会通过正反双向强化的社会机制固化为社会道德。在游牧民族对待老人的态度上,社会系统在遵循一种选择的机制,通过不断地博弈,使得老人的社会地位下降,贱老最终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婚姻制度也是选择的结果,游牧部族对待妇女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生存哲学变成了最大的真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增加部族的人口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来,妻后母和寡嫂就是现实的选择。
中原华夏族群的道德系统是通过周代礼仪的方式展示出来,这种系统与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与分封制联系在一起,男性老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最高的,尊重老人被赋予了特殊意义。这样可以和忠君保持一致性,这是因为社会是家国同构,浑然一体的,并非游牧社会是分裂的结构。在对待后母和寡嫂的问题上,中原社会奉行的一种礼仪制度的选择,其本质依然是是对于父亲和兄长的尊敬,在这里,女人是依靠男人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对女人婚姻禁忌是对死去的男人的一种态度。所以,华夏族群的价值选择对于社会总福利来讲也许不是最优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相对稳定的生产环境可以使得人们在选择时有一定余地。但是在游牧社会,严酷的生存条件就会迫使社会按照经济学的规律来安排社会生活,从而形成与中原完全不同的道德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