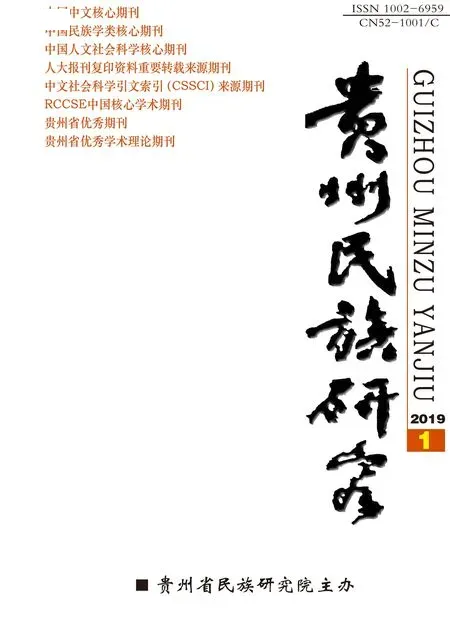西部基层法院审判窘困中的习惯法因素分析
——以彝族地区案例与电影资料为样本
2019-03-17李毅
李 毅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一、现实检视:西部地区基层法院审判窘困现象
(一)“坎上法庭”与“坎下法庭”二元纠纷解决范式冲突
在彝族地区,彝语中的“坎上”,意为“地各列托”;“坎下”,意为“地各列勿”。人们往往在地坎上方或者地坎下方围坐讨论重大事项。但凡重大的活动在“坎上”举行,而一般的则在“坎下”举行。因此,从纠纷的解决主体上划分,人们将人民法院称为“坎上法庭”,将民间的纠纷解决方式称为“坎下法庭”。而这两种不同的称谓分别代表着“官方+民间”两类解决纠纷的不同范式,所谓“坎上调解”,亦即“官方调解”,主要是指以法官为主体的代表人民法院牵头或主导下的司法调解,调解主要依据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规范,其效力为国家法律所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而所谓的“坎下调解”,亦即“民间调解”,主要是指由家支组织会议,在德古、苏易等威望之人的主持下进行的纠纷解决活动,遵守与否由双方当事人决定。
案例一:
2000 年,某乡一名黑彝S家的人到同村白彝L家做宗教法事的现场去玩。由于其醉酒后胡言,结果被L家打了一顿,36天后死亡。S家到L家兴师问罪,L家杀了10头牛、20只羊赔礼道歉,同时赔偿现金8000元。事后,L家支有1人在县上工作,遂将此事起诉到法院。结果,调解该起纠纷的德古被公安局拘留,死者的哥哥也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刑。[1]
从本案来看,案情本身并不复杂,法律关系清楚,只是“坎下法庭”的处理结果突破了国家制定法的“红线”,在发生重大刑事案件后,必须由国家制定法来规范调整的法律排他性规定,而德古仍然按照“赔命金”“赎命价”的传统习惯法方式来处理,与国家法明显冲突,既不为法律所认可,甚至还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坎下法庭”与“坎上法庭”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在民族地区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两种不同路径,二者相互并存,而又相互博弈甚至冲突。
在《马背上的法庭》中,法院审理“‘过界杀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也凸显了不同纠纷解决程序的博弈和冲突。法庭书记员阿洛的岳父姚葛(某村村长)所在的村通过“民主形式”制定的“村民公约”明确规定:“过界牛羊一律宰杀。”并将邻村过界的羊予以宰杀宴客。当邻村村民前来“讨羊”时,姚葛认为这是全村村民协商一致后作出的规定,是村民意思自治的体现,也是一直以来的传统惯例。法官老冯和阿洛均指出此项“公约”已侵犯他人合法财产权益,构成不当得利,属于明显违法行为时,姚葛无法理解法院的法官缘何反而认定自己“违法”。这些画面构成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张力与博弈,也凸显了“坎上法庭”与“坎下法庭”的在针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认知甚至对立。
(二)法院审判中“只做不写”的习惯法适用“潜规则”
从法系渊源来看,我国属于典型的成文法国家,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是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的根本原则,民族习惯法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的渊源,自然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准则。在法院审判实践中,法官往往为了化解矛盾纠纷,促进案结事了,也不会简单地囿于法律规定,往往会借鉴或沿用习惯法规则进行调解,尤其在民事调解、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纠纷案件中,从而形成了民族习惯法“能说能做不能写”的尴尬局面。尤其在当下法官办案终身负责制、改判或发回重审案件直接与法官绩效挂钩等现实考评机制语境下,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在案件审理中援引习惯法已经成为法院审判活动中的“潜规则”。
案例二:
2008 年12月,某县5名彝族青年共同打死了一名摩梭青年,公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受理后,5名被告人所在的家支均请求通过赔偿的方式协商解决,而被害人家属也想尽快获得赔偿。经各方私下商议,5名被告人的各家支均愿意向被害人家属支付11万元作为“人命金”赔偿,而被害人家属则出具谅解书并请求从宽处理。最终,法院以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了受害人家属谅解为由予以减轻处罚,以故意伤害罪对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3年有期徒刑,而各方对此结果表示满意。[2]
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涉少数民族民间习俗类纠纷案件时,注重把握国家法律和民族习惯法之间的共通性特征,灵活运用法律,既尊重民族地区的习惯习俗,又能依法裁判,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从整个法院的审判过程来看,显然其中默许或认可当地沿用习惯法方式解决矛盾,但从裁判结果来看,又丝毫体现不出其中的习惯法对审判活动的影响。
(三)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选择困惑
从功能主义视角分析,法院的司法功能主要体现为两种范式,一是法律本身所致力或追求的法律效果;二是司法裁判结果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反应。具体来讲,就是法院的立案、审判、裁定、执行等司法裁判行为对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影响,是否达到抑或实现了法律本身蕴含的预期价值目标,而这个目标除了满足法条主义或者程序正义的法律效果以外,还需要达到满足现实主义或者实质正义的社会效果。
案例三:
2005 年的一天,某县的B与A发生争执,将A刺伤,A被刺后伤重不治而亡,但两家均未报案,而是请来“德古”前来调解。经调解,德古让B的家支向A家赔偿2万元作为“人命金”并杀生赔礼后,纠纷遂得以平息。其后不久,此事被公安机关获知,遂强令A家将2万元人命金退还给B家,并将B捉拿归案。后B被判处无期徒刑,并附带民事赔偿2万元。然而,由于被告人已被判处刑罚且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民事赔偿部分始终无法执行兑现。A家为此聚集多人与B家支对峙,群体性冲突一触即发。后在县政法部门干警介入协调,并一起凑了2万多块钱给A家,该起群体性事件才得以平息。[3]
本案中,法院以及公安、检察等国家司法部门各司其职,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从法律层面来看,上述机关的行为都合乎法律规定,并无僭越违法之处。如果在其他地区,法院判处的刑事附带民事2万元赔偿款能否执行到位,仅属于法院“执行难”或者“执行不能”。然而,由于本案发生在民族习惯法浓郁的西部彝族地区,司法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中,未能有效考虑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和案件本身的特殊性,仍然以一般的法律规定行使审判职责,自然不为社会所认可,最终还得“自掏腰包”为其“买单”,也揭示了民族地区司法人员在履行职责中的诸多困难与无奈。
在《马背上的法庭》中的“兄弟分家”财产分配一案,两兄弟分家,而两妯娌之间仅仅因为一个泡菜坛子而相持不下,或许在现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个何其微不足道的案子,甚至认为这只不过是电影制作者的“小题大做”的拍摄手法而已。其实,在西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这类案件在当下仍然为数不少。因为,这类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往往不仅仅是案件的本身,而往往是为了“争一口气”,稍有处理不慎,极易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纠纷。
二、缘由解构:我国西部地区基层法院审判窘困生成因素
(一)法院审判“双重效果”的竞相交织
在法院审判活动中,任何一项裁判都应当以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为旨归,而这也往往成为法院审判活动的疑难点,这在习惯法传统深厚的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审判中显得尤为突出。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于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针对同一事项(民事、刑事或者行政纠纷)的处理或者因应之策不相一致甚至相互对立,在裁判中无法进行适用某一规则而排斥其他因素的考量。案件双方当事人并不仅仅为各自独立的实体,而其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庞大复杂的家支(家族)因素的影响,家支的另一个职能就是“大刑用甲兵”,对冲突的另一方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并且这种“冤家械斗”不仅在不同的家支之间,甚至在家支内部也可能随时发生并长期持续,正如彝族格言所云:“不维护一户,全家支保不住;不维护家支,一片被抢光。”这也使得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会在依法履行审判职能和注重社会大局稳定方面统筹兼顾,而非简单一句“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那么简单。
(二)民族习惯法在司法裁判中处于微妙地位
对西部地区基层法院法官来说,民族习惯法在具体案件中的司法适用,一直以来是一个异常敏感又不得不审慎应对的话题,总体来说处于“能做能说不能写”的微妙地位。一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尤其是在诉前调解或者诉讼中的调解活动中,较为注重使用当地习俗、民间风俗、习惯传统等习惯法方法,只要双方就矛盾纠纷争议事项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法官在裁判文书中一笔带过,只要案件审理结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实现“案结事了”即可。二是出于对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考虑,以及出于对民族习惯法干预“司法案件”、影响“审判独立”的顾忌,使得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选择上,更多侧重于社会效果的实现。这种看似相互背离而又相互依赖的裁判因素,使得法官在审判中往往采取“工具化”“技术化”的手段处理。可见在制作的裁判文书中几乎找不到习惯法的影子,更遑论直接以习惯性规范作为裁判依据的,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由此带来的诸多不便,故而有的学者将此称之为“伪饰裁判”。[4]
(三)法院“人案矛盾”等因素掣肘民众司法认同
近年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转型升级阶段,各类矛盾纠纷开始凸显,加之现在又处于法官员额改革后审判人员大量减少的过渡期,“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以及“执行难”问题等,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法院的司法公信力方面事实上一直不尽如人意,这对西部地区基层法院来讲显得更为突出。有学者曾做过专门调查,从调查问卷结果来看,西南少数民族群众认为法院在解决纠纷时存在诉讼延迟、效率低下、费用偏高、程序复杂、太讲关系、公正性不足等问题。[5]少数民族群众认为到法院诉讼的成本太高,尽管法院自身收取的诉讼费用较低,但是案件审理程序繁琐,耗时较长并且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与此相关联费用比如律师费、交通费等也较高,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讼累。相比之下,当事人更愿意选择程序简单、方式灵活、费用低廉、易于兑现等优势的习惯法解决矛盾纠纷。
三、进路优化:构建契合西部地区民族特质的基层法院审判机制
(一)兼容并蓄:坚持法律一般原则与习惯法特殊规则的调适融合
坚持宪法和法律的普适性,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是处理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关系的前置性要件和根本性准则。实践中那种忽视抑或罔顾少数民族法律传统的存在,甚至试图通过立法等外部力量来改造、摧毁、同化习惯法传统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法制建设中,从总体上看,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必须尽力沟通、理解、在此基础上相互妥协、合作。这样可以避免更大的伤害,获得更大的收益。而不是按照一种思辨的理想型模法制式,无论是强调国家制定法还是强调民间法的模式,来构建当代中国的法制。”[6]在审判实务中,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以化解矛盾纠纷为着力点,适当参照民族习惯法中的积极内容,发挥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补充性”作用。因为在习惯法传统早已根深蒂固的民族地区,原有的一整套国家法运行机制往往不能像在其他地区那样得以正常运作。就民族习惯法而言,无论是事前的警戒抑或是事后的惩处,也是为了达到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生活、维护民族秩序、促进各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这与法律制度设计的初衷也是高度契合的。
(二)多元司法:完善司法保障下的民间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指出:“尽管审判外纠纷处理与审判一样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权利实现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法律实际工作者却有一种只是把视线集中在审判制度上的倾向。”[7]尽管传统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比如,调解人员的法律素养参差不齐、调解结果不具有公法上的强制执行力(除非通过司法确认等方式予以明确)等,调解结果甚至可能与国家法之间存在冲突和背离。因此,可以立足法院职能定位,聘请优秀的“德古”“寨老”“阿妈”等“头人”作为特邀人民陪审员、民事调解员、刑事和解员、行政协调员等,参与法院司法调解、审判、执行等审执业务工作。积极参与地方综合治理,对民族村(寨)制定的村规民约、团结公约、乡约、“明白书”[8]等自律性规范的指导,将法院的司法为民工作前移到基层社会治理一线,将纠纷化解在诉讼前,矛盾解决在基层。
(三)内生动力:加强西部地区法院民族法官人才队伍建设
苏力认为,“诚然,乡民们依据他/她们所熟悉并信仰的习惯性规则意识认同和分享是另一个重要条件。法官对民间风俗习惯的下意识认同和分享是另一个重要条件。”[9]当前,西部地区基层法院在推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以及职业保障等改革过程中,在坚持抓好“规定动作”的同时,还应当注意结合民族地区特质。比如,在改革方案设计中,应当力图避免简单提高职业准入“门槛”(如学历层次、工作年限、年龄要求等),应当注重结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司法人员素质结构等特质,避免唯学历、唯资历、唯办案数量等具有普适性的“一刀切”改革模式,加大对少数民族法官的培养选拔力度,让那些既深谙国家制定法律,又熟悉民族习惯法的“双语型”优秀法官快速成长,探索构建一条契合少数民族地区特质的渐进式司法人员职业化建设之路。同时,应当加大法院人员职业保障力度,而且这种力度应当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切实增强职业尊荣感,让西部民族地区司法人才能够“引得进、用得上、留得住”,真正成为推动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