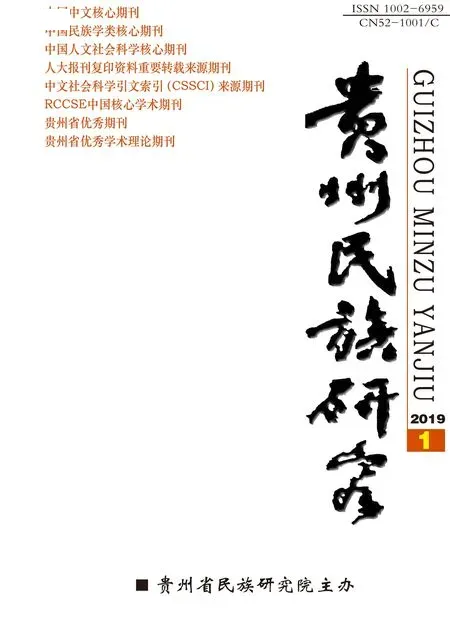民族经济治理中的习惯法透析
2019-03-17刘辉
刘 辉
(中南大学 网络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2;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安徽·合肥 230009)
民族地区传统经济治理同社会整体治理混同,使得民族经济治理中习惯法的运用同民族习惯法的社会管理如出一辙,比如,黎族群众通常依据古老咒语诅咒偷盗行为,在集市交易中黎族群众通常将自己农产品放置到寨(村)头,供路人自主选购的“拜贡”制度,就是源于黎族习惯法中宗教教义和乡约寨规。换言之,民族地区经济治理以民族习惯法为依据,在治理中“法制经济”运行机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在民族地区经济治理中少数民族群众逐渐以朴素的市场交易规则约束着群体经济活动行为,调解着民族群众之间的经济纠纷,并在民族习惯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经济治理机制,民族经济治理中习惯法的透析成为探究民族地区传统经济治理机制的窗口。因此,从民族地区传统经济治理方式入手,以民族经济治理中习惯法源头的运用和体现为依据透析民族习惯法体现,成为民族经济治理中习惯法透析的应有之义。
一、习惯法在民族地区经济治理中的具体运用
(一)基于非正式制度中自主管理的习惯法
民族习惯法在民族社会运行逐渐演化为潜移默化的,具有震慑力与强制力的非正式制度。在经济治理中民族习惯法的非正式制度影响力最为显著,特别是以非正式制度中自主管理为主的经济治理成为民族习惯法在经济治理中的集中反映[1]。首先,基于自然界的水、树木等资源的经济管理中民族群众通过禁止性、惩戒性的习惯法进行治理。一方面通过宗教教义等民族习惯法使群体对自然资源的索取进行合理规范,比如,鄂伦春族群众在树木等公共资源的管理中,主张禁止砍伐幼苗,对于砍伐幼苗的行为处以纳粮惩罚,部分鄂伦春族群众受原始自然崇拜宗教诅咒观念的影响,将公共林木砍伐治理同习惯法中的宗教惩戒关联,使民族公共资源治理逐渐法治化。另一方面,民族群众在经济治理中规定了自然万物的所有权。比如,凉山彝族习惯法以妇孺皆知的乡约寨规明确规定自然万物所有权归毕摩所有,换言之,民族习惯法在经济治理中明确规定“产权”。其次,在民族群众间的经贸集市中民族群众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习惯法作为隐性经济治理的准绳,规范着民族地区的经贸活动。比如,西北撒拉族等穆斯林群众在经济治理方面受到以伊斯兰教教义为主体的习惯法影响,在买卖交易中崇尚“诚实信赖原则”,坚持童叟无欺,在具体货物流通中则潜在禁止猪肉等关联货物的流通,且在经济活动成为买卖双方自主管理的具体反映。再者,以黎族“拜贡”、京族“寄赖”等自主管理的治理模式基本上都以民族习惯法的有机转化为依托。
(二)基于信赖机制的约束性治理
民族经济治理中通常将宗教教义等民族习惯法内化到群体意识形态当中,成为民族群体予以信赖的经济行为准则。换言之,民族习惯法在民族经济治理中主要以基于信赖机制的约束性治理为主。首先,源于民族宗教教义的习惯法以宗教法则约束着民族群体的经济行为,规范着民族群体的经济活动。时常通过宗教虔诚的践行至民族群体的商贸活动当中,一方面民族宗教教义同自然崇拜、自然敬畏相关联,禁止商贸活动买卖特定物品,比如,满族群众在集市买卖中禁止流通狗肉,并且在长期的生活成为群体具有信赖性、约束性的习惯法治理机制[2]。另一方面,民族群体将宗教教义法则延伸到经济活动中,比如:维吾尔族等穆斯林群众在经济活动中世代沿袭“诚实信用原则”。其次,民族习惯法在经济治理中通常将经济活动的法制化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习惯法的威慑力成为民族群体之间不断加强经贸活动的保障,比如,普米族群众在氏族组织的影响下,氏族群体经济行为的规范以氏族家规等习惯法为主,经济活动的规范通常由族规调整,对于缺斤少两的经济行为一般禁止其参与氏族丧葬活动,重者剥夺祭祀资格。再者,随着中原王朝对民族地区经济的管辖,以制定法为渊源的民族习惯法对经济活动治理也显得尤为重要,比如,以部落首领为土司的民族管辖政策,将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同中央优惠政策相结合,经济治理同政治信赖相关联,以中央王朝律令为主的习惯法对民族经济行为的约束也极为显著。
(三)基于民族族长元老、的经济治理
民族地区的村寨族长、元老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掌舵者,以族长、元老为中心的经济治理是民族地区经济治理中习惯法运用的民族性浓缩。一方面族长、元老在经济活动中的存在与角色扮演折射着民族地区经济治理的民族地域性特色。另一方面,以族长、元老为主体的经济治理映射着民族群体别具一格的社会组织体系。就民族地区习惯法在经济治理中运用而言基于民族族长、元老的经济治理主要表现在:一是民族族长、元老是民族经济所有制形式的掌握者。一方面民族地区普遍存在政教合一的现象,以族长、元老为首的角色掌握民族地区生产资料、分配形式[3],比如,彝族“毕摩”在原始社会公有制阶段掌握着经济成果的分配形式。另一方面,在氏族公有制经济治理中元老占有着绝对的经济主导权,比如,拉祜族村寨受“卡些卡列”制度的影响,在经济治理中“村寨头人”有着较大的经济话语权。二是以族长、元老为主体的经济纠纷的化解,换言之,族长、元老掌握着经济纠纷的裁量权,比如,毛南族群众经济纠纷则由专门纠纷化解者“匠讲”(类似于元老)处理。三是族长、元老掌握经济治理的制裁权,民族地区经济治理中元老掌握着绝对的制裁权,既能够依据民族习惯法有效地规范民族经济行为又能较为合理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民族经济治理中习惯法的透析
(一)“自然敬畏”下的民族生态经济雏形
“自然敬畏”下的民族生态经济雏形是民族习惯法在经济治理中的现代化聚焦,是法制经济与生态经济的共同体。民族地区在生态经济的治理中通常以习惯法的信仰式延伸为主导,注重民族经济治理的制度化调控。就生态经济的治理而言,一是针对民族祭祀文化、图腾文化、宗教文化忌讳下的捕猎等,民族群众在长期的自然生活中逐渐形成了自然敬畏的发展理念,比如,藏族群众忌讳对马等动物的猎杀,特别是甘南等山区藏族群众,忌讳集市买卖诱导下的过度狩猎。二是民族群众对自然敬畏的民族心理延伸到习惯法的乡约寨规中,通过赏罚惩戒的治理机制推动民族生态经济的发展。比如,鄂伦春族群众在砍伐树木、捕捞鱼苗时禁止砍伐、捕捞幼苗,同时以寨规祖训的形式鼓励群众开展“冬砍一棵、春植一株”的朴素生态经济[4]。三是鄂温克族等少数民族在经济治理中通过习惯法的形式管理群体的砍伐、狩猎行为,禁止春季砍伐树木,否则由“编户”按照州律公开处罚。总之,“自然敬畏”下的民族生态经济雏形是民族习惯法中在生态领域的凝聚与折射。
(二)“纠纷化解”下的民族经贸治理
“纠纷化解”下的民族经贸管理是习惯法在民族经济治理中具体运用的基本体现。民族经贸管理中的“纠纷化解”是习惯法视域下民族经济治理法制化的基本形态。就民族群众经贸纠纷化解的主体性而言,民族经济治理中纠纷的化解有内外部之分,以村寨家族为主要形态的内部经贸纠纷化解的治理,一般由族长作为管理者进行经贸纠纷化解。比如,毛南族群众村寨以同姓群体为主,群众之间“以物换物”的贸易纠纷化解基本上由“匠讲”处理[5],对于缺斤少两、质次量差的纠纷则由“匠讲”责令补足调换等,对于双方动手纠纷则由“匠讲”请“武相公”执行鞭责。以不同民族之间的外部纠纷则由双方元老、族长共同化解,在纠纷化解中先有彼此根据本部落族规询问彼此的缘由,而后共同处罚,比如,侗族部分村寨在族人同其他民族群体之间的纠纷实行双罚制,除按照族规处罚外,有错者还要接受元老之间调解后的处罚,个别地区甚至要给元老一定的补偿。从经贸纠纷的严重程度而言,有四种纠纷治理机制。一是以元老、族长和专门民事纠纷调解者为主的化解机制,比如,凉山彝族群体之间的简单物物交换纠纷一般由“毕摩”管理,而毛南族则由专门纠纷化解者“匠讲”处理[6]。二是以元老会为主体的民主决策化解机制。以元老会为主体的经贸纠纷化解在多数民族群体的发展历程中均有体现,比如,京族群众对于柴木买卖之间的纠纷一般由元老会调解。三是借助行政力量的纠纷化解机制。明清以来民族地区普遍实行土司制度,以政教合一的土司成为民族地区最高的行政长官,对于群体间的经贸纠纷则由土司裁决。四是对于复杂纠纷化解的“兽判”机制。民族地区经贸纠纷的化解一般由民族习惯法化解,但是往往出现难以明显裁量的纠纷,则由巫师等主持,通过概率性时间断决纠纷,比如,彝族群众在纠纷中通常利用“兽判”化解贸易纠纷。
(三)“惩戒机制”下的货物流通
“惩戒机制”下的货物流通是民族习惯法在经济治理中货物流通领域的基本反映。基于惩戒机制下的货物流通囊括民族习惯法的诸多方面[7]。一是在民族宗教教义中明确禁止特定货物流通习惯法摄入,如东乡族、撒拉族群众在集市货物买卖中禁止猪肉类的交易;壮族群众禁止青蛙的捕杀与买卖。二是民族乡约寨规中对特定货物的流通与买卖的禁止,并且对违规者进行对应惩戒。如纳西族群众在村寨石碑中明确规定“禁止买卖尚未成熟的果实”,否则禁止参与宗祠祭祀。
(四)“调解机制”中的劳动纠纷治理
民族地区经济治理中习惯法的蕴含成为维护民族经济秩序的壁垒。民族习惯法中以“调解机制”为枢纽的劳动纠纷治理是民族经济治理的基本体现。就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体制而言,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多数处于原始公社阶段,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私有制逐渐使得简单雇佣劳动成为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重要一环[8]。但是民族地区劳动关系起初受乡约文化的影响具有互助的属性,比如,怒族群众中土司等通过“瓦刷”的形式开展简易雇用劳动,佤族群众则以“珠米“(富人)官觉克”经济剥削为主,在长期的雇用劳动中劳动纠纷成为民族经济治理不可避免的现状。“调解机制”为主要形式的习惯法以调解的形式进行劳动关系调整,避免雇主同群众之间关系的破裂影响族群团结。在劳动关系调解中少数民族群众通过习俗传说,以伦理道德的准则维持群体内部的雇佣关系。比如,壮族群众通过道德神“布洛陀”的祖祠裁决化解劳动纠纷。京族的一般劳动纠纷则由“翁村”执行处罚,村寨之间的劳务纠纷则由“嘎古”中的元老商议解决。
(五)“习惯机制”中的所有制形式
少数民族群众久居边疆、山区,民族群体之间的汉化程度差异显著。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民族地区仍然保留着原始公有制、农奴制等形式。民族习惯法在民族经济治理中以其独特的非制度性规制,规定了民族经济治理的根本所有制。比如,怒江傈僳族在经济所有制形式方面大体包括个体私有、家族共同所有、家族或村寨公有等形式。随着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个体私有的逐渐扩大,以族群内部协作为主要形式的“伙有共耕制”逐渐成为傈僳族经济治理中所有制形式的基本体现[9]。赫哲族群众在灵物崇拜和家长制的习惯法静态引导下,在经济治理中所有制基本以“氏族制”为主,在狩猎中由“劳德玛发”领导,崇尚集体所有制。在汉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以封建地主阶级、奴隶主所有的经济治理体制。比如,阿坝羌族地区在食盐的流通治理中无论是土司制还是其他地主阶级都以“关盐店”形式进行所有制管制。
三、民族经济治理中习惯法的源头
民族地区经济治理中习惯法是民族社会法意志形态的体现,民族地区经济治理中习惯法的自然存在以民族群体喜闻乐见的宗教教义、乡约寨规等为源头[10]。换言之,民族经济治理中的习惯法是民族地区传统经济习俗、民族宗教教义、民族乡约寨规、家规族训等传统民族习惯法的总和。所谓民族传统经济习俗即民族地区始终沿袭的经济活动习俗,比如,撒拉族等穆斯林群众童叟无欺的诚信原则在经济治理中始终作为法律准绳。所谓民族宗教教义是民族习惯法源头的重要组成,在经济活动中民族群体通常受民族宗教教义的引导。比如,藏族群众忌讳对马等动物的猎杀,特别是甘南等山区藏族群众,忌讳集市买卖诱导下的过度狩猎。所谓民族乡约寨规、家规族训等是民族习惯法的特定性体现,比如,仡佬族崇尚祖先崇拜,在乡约寨规、家规祖训中明确规定:“对于神树附近区域进行封山,禁止砍伐、放牧。”使习惯法在经济治理中的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总之,民族地区经济治理中习惯法的源头无外乎以宗教教义、社会习俗等民族非制度性为规范。
民族习惯法在经济治理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方面民族习惯法在经济治理中的信仰上升是民族地区法制经济的建设内化与中心,并成为规范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行为底线和思想准则[11]。另一方面,民族习惯法对经济治理的原则性确立,有效地规范了民族市场经济活动,特别是自然敬畏机制下民族经济活动的抑制,推动了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使民族习惯法治理中经济领域良性机制逐渐确立,成为引导民族经济发展的牵引力。毋庸置疑,民族经济治理中习惯法逐渐将“法制经济”与“生态经济”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