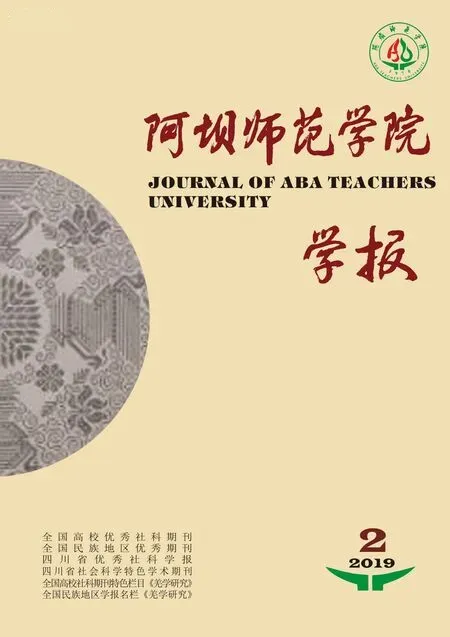羌族入黔考
2019-03-16李锦伟
李锦伟
羌族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自称“尔玛”,意为本地人。她虽然已成为贵州的17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但实际上并非贵州的土著居民。那么,她来自哪里?何时迁来?又为何而来?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虽有一定讨论,但因限于史料的缺乏,有些问题仅是简要提及,甚至有些观点难以令人信服。为此,笔者通过考证、逻辑推理、归纳分析,并结合口述史等方法,试图对羌族入黔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究,厘正一些观点,以为贵州羌族的发展找寻其历史基础。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羌族在贵州的历史和民族发展史上作用突出,在构筑“多彩贵州”文化中贡献颇大。到21世纪初贵州全省有羌族人口一千四百多人,绝大部分聚居在铜仁市的石阡、江口两县[1]51,占了80%以上,其余散居于全省各地。故本文在分析羌族入黔相关问题时就以铜仁市的羌族为讨论对象。
一、入黔羌族族源地
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受到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贵州羌族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而报为汉族。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国家民委的相关精神,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地方政府开展了民族识别和恢复部分群众民族成分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省政府于1986年批准了江口、石阡两县的羌族恢复自己的民族身份[2]533。这样,羌族重新成为贵州铜仁市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据调查,铜仁市的羌族主要有夏、姜、包、胡四姓,他们均不是本地土著居民,而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迁入至今,已经繁衍了16代。那么,铜仁羌族从哪里迁来呢?耿少将在其《羌族通史》里,认为铜仁地区的羌族就是来源于川西北地区[3]328。这一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如郭福基和杨昌文也撰文认为是从川西北的岷江上游一带迁徙而来的[4]。虽然缺乏史料的具体记载,但笔者从铜仁羌民的口述访谈中亦探得他们确是来自四川岷江上游地区。如石阡县汤山镇的夏姓羌民自称是大禹的后裔,历来供奉禹王神,以禹王为祖先神。这正和岷江上游地区的羌族有着共同的祖先信仰,由此推测本民族和岷江上游羌族存在渊源关系,认为其祖先就是从四川迁徙而来的。石阡县聚凤乡姜姓羌民在谈到自己的族源时也说自己的祖先是由四川迁入进来的。石阡县这两个乡镇的羌族均自称来源于四川,他们虽没有明确说明来自四川的哪个区域,但笔者根据古代羌族的发展史可以推断,很有可能是在川西北的岷江上游一带。历史研究表明,自西夏国灭亡后,许多羌民融入到蒙古、汉、藏等民族中,仅部分羌民依然生活于岷江上游地区。此后的元明清时期,四川的羌族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所以石阡羌民说自己来源于四川应该指的就是岷江上游一带。如果说石阡县羌民在追述其族源地还较为笼统的话,那么江口县漆树坪胡姓羌民的说法就更为具体了。漆树坪胡姓羌民说自己的始祖叫胡仁朝,他有九个儿子,胡宗礼是其中之一,也是漆树坪胡姓的直属祖先。胡宗礼之子胡云才从四川茂汶迁到湘西,再由湘西迁入铜仁,后又迁到江口县的桃映瓮稿沟胡家坡,住了四代后又迁到现在的漆树坪落业。漆树坪羌民对自己祖先的迁移路线说得也较为具体,并明确指出其族源地为四川的茂汶地区,即现今的茂县、汶川等地,该地正是属于岷江上游地区。同时,其家谱也记载:“我胡氏之源,出于安定,文德武功,代有伟人。始祖迁辰以来,流离转徙,不可胜道,殆圣朝鼎新,涵濡优渥,迄今六百余年,人繁脉固,骎骎乎有椒聊繁衍之势,故近而辰沅永靖,远而川陕西戎,渐以分疆异地。”[2]346同样说明漆树坪羌族祖先经过了辗转迁徙,就近的地方在“辰沅永靖”即现在的湘西一带,远的是“川陕西戎”即川陕甘交界的区域,也即岷江上游地区,也是自古以来羌族聚集的地区。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测江口县漆树坪羌民的族源地极有可能也是在岷江上游一带。学界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喻帮林[5]、张勇[6]、庄鸿文[7]等人,暂时未见异说。
二、羌族入黔时间
虽然贵州羌族源于四川岷江上游地区的观点是统一的,但是羌族究竟是何时迁入贵州地区的?以往学界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主要有如下三种:“元代说”“明末清初说”和“清乾嘉之际说”。持“元代说”者主要是依据上面提到的江口县漆树坪羌族的家谱记载,“始祖迁辰以来”,“迄今六百余年”,由此认为贵州羌族是在六百多年前的元代从四川茂汶羌族聚居区迁来的[5]86。持“明末清初说”者主要是依据当代羌民的口述及对其代数时间的推算,如石阡县夏姓羌族说自己祖先大约在明末由四川迁过来,已经繁衍了十一代以上,江口县漆树坪胡姓羌民说自其老祖来到铜仁地区已有十四代人,由此认为羌族从四川迁入贵州地区应是明末清初,已有300多年的时间[1]51。《羌族通史》里面也提到,明朝末年有部分羌族从四川外迁,其中包括迁入铜仁的羌族[3]328。持“清乾嘉之际说”者也是据繁衍代数估算的。有人根据《石阡县志》记载的羌族已繁衍15代人认为封建社会很多人是不满20岁就结婚,那么一代实际不到20年,由此认为石阡县羌族迁入的历史应该是300年不到。江口县漆树坪羌族只有14代人,同样也只是200多年的历史,由此否定“明末清初说”。在此基础上,他们进而认为,铜仁羌族当与乾隆晚期跟随川督和琳镇压乾嘉苗民起义的士兵有关,因为和琳为四川总督,其部队将士主要就是四川籍的,那么这些士兵中应有很大部分是属于羌族民众。在和琳去世(1796年)后,有的逃离部队,寻找偏僻之地暂时居住下来,并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这个时间距今也是200多年,与羌族迁入贵州地区的时间大体相当。由此得出贵州羌族应是来源于18世纪末乾嘉之际和琳部下逃散的一支羌族士兵的后代之结论[6]。对于贵州羌族的迁入时间,笔者比较认同第二种观点,即“明末清初说”,其余二说均存在不合理之处。先看第一种观点——元代说。这种观点单据江口县漆树坪羌族的家谱记载说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就认定是元代迁入进来的。如果按此说,根据通常所认为的二十余年为一代的话,漆树坪羌族应有30代左右了。但事实上,从一些羌民的访谈中得知,江口县的羌族发展到现在也就只有16代。这两个数据相差太大,极不吻合。再有,根据这六百多年的历史和16代推算,得到的是近40年为一代,这显然与中国自古至今的代际间隔时间不符。所以,该家谱记载的时间应该是有误的,没有尊重历史事实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故可以否定“元代说”。其次,我们再来看第三种观点——清乾嘉之际说。该说认为羌族入黔始于嘉庆元年(1796年)左右。如果按此说,距今才220年左右,按现有的16代计算,每代的时间大约为13.75年。虽然持此说者认为古代一般在20岁之前就结婚,即不到20年为一代。但提早到13-14年为一代显然不合常理,更不科学,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所以,我们对清乾嘉之际说肯定也是持否定态度。那么,唯有第二种观点——明末清初说还说得过去,与实际比较符合。根据有人对一些家谱代际平均时间的统计,可以发现每一代的时间基本是在20-30年之间,其中又以22-25年之间为最多。如果按照现有的16代推算,贵州羌族的第一代正好是在距今三四百年前的明末清初这段时间。虽然这种说法有点笼统,但总比其它二说更具说服力,更符合实际,也基本符合《羌族通史》里面提到的川西部分羌民于明朝末年外迁的观点。
三、羌族入黔缘由
在推断出羌族迁入贵州地区的时间为明末清初之后,我们有必要再试图对其迁入原因进行分析。说到羌族入黔的缘由,多数人认为跟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有关。如《羌族通史》提到,明朝末年,“羌族地区百姓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生产生活极度艰辛。”“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和明朝军队的残酷镇压和屠杀,部分羌民选择了背井离乡、离家出走。”并由此推测,现今居住在黔东北的羌民与明代后期川西北羌族地区生存状况恶化导致的人口流动有直接的联系[3]328。这一观点虽然提出羌族入黔原因当与明末动荡的社会环境有关,但是没有将其具体化。那么,羌族入黔的缘由到底具体是什么?笔者以江口县漆树坪羌族为中心进行了考察。
关于中国古代移民的原因主要跟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因素有关。首先,从政治因素来看,外出为官、谪戍、实边等均属于政治移民,但通过查阅漆树坪羌族先祖所到达过的辰州、沅州、靖州、永州等地方史志,均未见有明清时期来自岷江上游地区的胡姓外来流官,也未见有被贬到这些地方的原籍为岷江上游地区的胡姓文武官员。所以,漆树坪羌族祖先不可能是因做官或谪戍而来。再说,如若是由为官而来的话也根本不可能出现如其族谱所记载的“流离转徙”的悲惨状。另外,虽然明清政府组织了许多政治性的实边移民和“窄乡就宽乡”的移民活动,但政府是不大可能组织岷江上游的川西北地区的人民外迁的,因为明末清初是四川历史上人口丧失最严重的时期,当时政府不大可能组织四川民众的移出,相反,当时政府组织的移民绝大部分是从其它各地迁移进四川的,史称“湖广填四川”。因此,从这几个方面看,漆树坪胡姓祖先的迁入和政治性移民关系不大。其次,再从经济因素来分析,经济谋生也确是明清时期移民的主要原因,当时也确实有许多四川籍人来到湘西黔东地区经商营业,但四川籍人前来黔东湘西谋生,主要是经过两条路线,一是逆乌江而来,二是从洞庭溯沅水而来。就漆树坪羌族族谱看,显然没有经过乌江,再有其族谱记载的“近而辰沅永靖”也隐藏着其就近的迁移路线,即从永靖一带往沅州、辰州一带迁徙,最后迁到铜仁。这样的迁徙路线正好和通常的经济谋生路线相反。所以川西羌族迁往铜仁的原因应该不大可能是为着经济谋生而来的。岷江上游羌族迁往铜仁地区的原因既然和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均无关系,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和军事因素有关了。通过考诸明末清初的军事情况,还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并且,笔者推断,川西羌族迁来铜仁和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密切相关。1644年,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攻陷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后立即派军前往川西北扫除当地的明廷残余势力,因川西北羌族等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深受明王朝的残酷剥削压迫,他们见农民军过来,纷纷乘势而起,加入农民军,如威州(今汶川县境)羌族,“立即集结威州,接受张献忠的领导,响应农民军”[8]。同时,大西农民政权对民族地区采取团结、平等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更加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和拥护,更多的少数民族加入到农民军中来,其中包括许多川西北地区的羌族。比如,当时张献忠部下孙可望部率军进入川西北的羌族地区,在当地羌族的支持和配合下迅速攻陷了汶川、茂州、松潘等地,当地羌民大量加入其部队,发展了革命形势[9]53-54。可见,孙可望的部队中就有大量的川西北羌族士兵。大西政权失败后,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下和南明政权联合,转战云南、贵州、湖南等地。但不久后,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之间也出现矛盾并发生内讧,最终于1657年,孙可望在与李定国等内讧失败后率残部仓皇逃离贵阳,一路上经过新添卫、偏桥、镇远、平溪、沅州,“各守将俱闭营不纳”,“所至城门昼闭”,“有不应者”,孙可望众叛亲离,成了丧家之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孙可望决定投降清朝。行至湖南靖州,孙可望对靖州道吴逢圣说:“一路人心俱变,惟有投清朝可免。”又在临近永州的武冈遭南明追兵围堵截杀,几乎脱不了身。[10]461根据孙可望部逃亡的过程及情形分析,我们推测,在孙可望残部从贵阳败逃湘西过程中,其士兵见孙大势已去早有逃亡念头,尤其是在孙可望于靖州表明投降清庭后更是坚定了一些士兵逃散的决心,故趁着武冈(永州、靖州交界处)被围之机有些士兵就趁乱逃跑。漆树坪羌族先祖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逃跑出来并隐姓埋名,从永、靖辗转沅、辰,最后来到铜仁的。当然,大西军余部早在1651年也曾在湘西南沅州、靖州等地活动过,但当时大西军在与清军的斗争中是所向披靡、节节胜利,在自己取胜的大好形势之下一般不会出现士兵脱逃的现象。故漆树坪羌族先祖很有可能就是在1657年从孙可望残部中逃离出来的羌族士兵。并且,其转徙路线和漆树坪胡姓羌族族谱记载的“近而辰沅永靖”相吻合,即从靖州、永州一带逃离后,返回到沅州,再到辰州,流离转徙,最后来到铜仁。这一推断既基本吻合前述《羌族通史》里提到的川西羌族迁铜的原因是因军事战争、政治压迫等导致人口流动的观点,也和现今漆树坪羌民关于其先祖迁铜原因为“避祸逃亡”、“躲避战乱”的说法基本一致。另外,如果以1657年为漆树坪羌族先祖迁铜的时间,到2017年一共历经360年,根据其繁衍至今的16代人计算,平均每代人为22.5年。这也正合乎中国传统的代际间隔时间。所以,笔者推断的漆树坪羌族先祖迁入的原因当与军事因素有关,更细点说当是由清初大西军余部孙可望部队里的羌族士兵逃散而来,并且进一步推测其迁来的时间可能是17世纪中叶的1657年。
诚然,由于史料的缺乏,笔者还不能完全断定漆树坪羌族迁黔的原因和具体时间就是如上所说,但上述推断比已有的其它说法更加符合实际。当然,笔者也期待有更详实而确切的证据来证实或证伪这一观点。
四、结语
总之,通过考证与逻辑推理可知,羌族并非贵州的土著居民,他们是于明末清初时期由川西北羌族迁徙而来。在明末清初政局动荡、战乱纷争的背景下,一部分川西北羌族随军入黔、入湘,后因军事形势不利而众多士兵逃散,其中一小部分羌族士兵逃亡于湘黔边境。他们入黔之初颠沛流离,隐姓埋名,艰难生活;后在铜仁的江口、石阡等地立稳脚跟,逐渐繁衍;如今成为贵州诸多民族中的重要一员,是贵州的17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对羌族入黔相关问题进行探究,认识其迁徙史和发展史,不仅有助于贵州羌族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推动贵州民族史的研究,也有利于丰富贵州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文化内涵,促进“多彩贵州”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