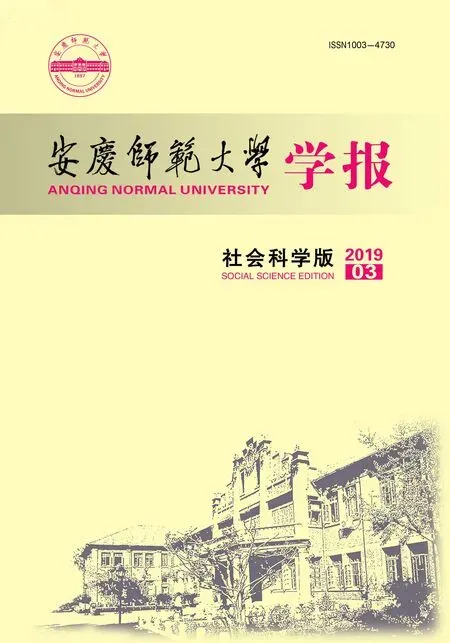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吴闿生《诗义会通》
2019-03-15潘务正
潘务正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芜湖241001)
桐城派既是文派,也是学派,在儒家经典的研究上,该派投入较多精力。然而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是,该派比较注重儒家经典的文学性研究,代表者如方苞《左传义法举要》、刘大櫆《孟子评点》、方宗诚《论文章本原》等。至于《诗经》的研究,文学性更是关注的要点。然不同时段,其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吴闿生关于《诗经》学的研究有两种著作,一是《诗经大义》,一是《诗义会通》[1]513。前者似已亡佚,后者成书于1927年。作为一位传统学者,探讨其在此时如何从事儒家经典研究,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
一、《序》与续《序》
解读《诗经》,绕不开《诗序》、毛传、郑笺、孔疏。传统学者于此大体尊之,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则欲弃之而后快。钱玄同于1921年12月7日致函胡适说:“我们是决心要对于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那么打‘经字招牌’是很要紧的事了。”在儒家十三经中,钱氏认为“谁也比不上这部有文学价值的《诗经》”,因此,得先“赶紧请它洗一个澡,替它换上平民的衣服帽子不可”[2]104。其实胡适在此前就已经倡议“以二十世纪之眼光读三百篇”[3]60,早在1911年读《诗》时,就着手“推翻毛传,唾弃郑笺,土苴孔疏”,并“一以己意为造‘今笺新注’”[4]22。为此,他从好攻《诗序》的朱熹《诗集传》、姚际恒《诗经通论》、崔述《读风偶识》、方玉润《诗经原始》等著述中汲取学术资源,形成其研究成果[5]112-127。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其言论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反响。
吴闿生少年时代曾留学日本,1912年以后还曾在新政府的部门中短暂任职,因此,其思想与桐城派传统学者有所不同。桐城前辈如钱澄之《田间诗学》“一以《小序》为断”[6]5,马其昶《诗毛诗学》“一以毛传为宗”[7]340,至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更是恪守毛传,形成桐城的“毛诗学”传统。对于这一乡邦诗学路径,吴闿生并不十分满意。然而,对于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废序”之举,他亦不能完全认同,在《诗义会通自序》中他说:“笃守而信从之(笔者按:指毛序)者,非也。一切扫而去之,抑亦未为得也。”[8]1对于《诗序》与毛传,他既不盲目信从,也不一概废弃,而是以一种折衷的眼光看待。
吴闿生肯定《诗序》、毛传的作用,认为如果不通过二者,就很难读懂《诗经》。《国风·唐·椒聊》序云:“刺晋昭公也。君子见沃之盛强,知其繁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焉。”朱熹否定小序“必为沃而作”的观点,吴氏又不赞同朱子的看法,肯定此诗刺昭“绝无可疑”,并说:“《序》末三语,尤能阐发诗人言外之意……末二句咏叹淫溢,含意无穷。忧深虑远之旨,一于弦外寄之。”由此,他感叹:“此等诗若不得《序》,则直不知其命意所在,埋却多少高文矣。”[8]101《小雅·沔水》毛传云:“疾王不能察谗”,吴氏赞赏其“能传其言外之意”,由此而云:“此经学大师所以为超卓。”[8]162在吴氏看来,毛公超绝之处在于其作为汉初大儒,“持论宏通,往往单言片词,能发诗人微旨”[8]自序,因此,其与《诗序》都有宗仰的价值。
不过,吴氏完全赞同《诗序》之处并不多见,而是往往持否定的态度。在十五国风中,他对《周南》各篇《序》深表不满,指出其弊端在于“穿凿”,在《自序》中他说:“《关雎》,三家皆以为刺诗。《芣苢》,鲁、韩皆以为伤恶疾。而《兔罝》‘公侯腹心’,自郤至已谓讥乱世之作,其不系于周初明矣。《序》乃委宛申说,悉以傅之后妃。此陋儒强经就己,以自逞其私臆者耳,曷足信哉。”具体分析中,逐篇批驳《诗序》。如《卷耳》,《诗序》云:“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对此,吴氏说:“《序》之不足信,于此最著。”并具体驳斥道:“《左传》以此诗为能官人,乃推衍而得之义……作《序》者取以说诗,又须牵合于‘后妃之志’,后妃不能官人,故必云‘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然于‘朝夕思念,至于忧勤’,终不能以强合也。复自解之曰:‘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其支离窘曲,可具见矣。”对于《魏风》七篇,他亦认为“《序》皆未得其事实”[8]95,且由《序》与诗意的不合而总结道:“凡《序》中无事实可指,推衍而为之辞者,多未足置信。”[8]94
对于《诗序》,吴氏否定更多的是所谓的“续《序》”部分。他将《序》分为两个部分,即首句与后续部分,称首句是古《序》,最能得诗之本意,而后续部分为续《序》,乃后人补作,其妄者多在于此。他的根据有三。一是《诗》之《序》有仅一句者。如《小雅·出车》之《序》云:“劳还率也。”《枤杜》之《序》云:“劳还役也。”二者均为一句,相当于《序》之首句。吴氏由此得出结论:“前人谓古《序》本止一句,续《序》与首句非出一人之作,于此尤信。”[8]146二是续《序》不符合史实。《秦·渭阳》之《序》以为康公之诗,而续《序》又云:“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诗。”吴氏认为重耳卒后七年,康公始即位,无缘复述此事。由此,他更加坚定地认为,“《序》固非出一手,妄人增为之也”[8]114。三是《序》与毛传不合。在《自序》中吴氏说:“《传》之与《序》,同出一原,必不容其有异,而今《序》《传》之不合者,往往有焉,此不独《序》之失正,即《传》亦未可尽凭。”他发觉二者不合的诗篇有《山有扶苏》《宛丘》《衡门》《泽陂》《狼跋》《四牡》《湛露》《酌》等。出现这种现象,说明毛传有后人窜入的可能,由此也可以见出《序》中存在的问题。
吴氏此种观念,有所渊承,一是家学。其父吴汝纶曾遍点诸经,《诗义会通》动辄引“先大夫”之言,可以看出家学所在。《曹·候人》之《序》云:“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曹共公与楚成王同时,然《晋语》楚成王享晋公子,即引此诗,则不可能是刺共公。因此,吴汝纶云:“此足见《小序》之诬也。”吴闿生由此引申云:“大抵《序》文非出一家,固难尽信。”[8]126可见吴汝纶否定《小序》,亦是指所谓“续《序》”而言。这启发了吴闿生关于《诗序》的认识。二是郑玄、苏辙等的《诗》学研究。《周颂·丝衣》之《序》云:“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对于《序》中高子之言,孔疏引《郑志》答张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后人著之。”吴闿生据此得出结论:“则《序》为后人所续,康成已言之矣。”[8]290其后苏辙《诗集传》大张其旨,吴氏受其影响颇多,《郑·扬之水》吴氏案云:“《序》于《郑风》各诗,多指为刺忽,朱子讥之,良是……庄公之子至多,而诗称终鲜兄弟,其为非忽固至明也。自苏子由以来,学者多谓《序》惟首句可信,以下则后儒所臆加。盖此《序》亦然。”[8]80可以说苏辙的观点对吴氏的启发仅次于其父。
在这些渊承之下,吴闿生于“尊序”“废序”之外,提出折衷的观点,以适应新的时代学术研究的需求。正如他论诗既反对老师宿儒的“泥古”,又不满新学者“不窥简编,不究音律,侈口骋臆,欲以尽易古先之成法”的“颠冥”之举,而是主张在这“世运之发皇,为旷古所未有”之际,应“融液古今,创铸无前之伟业”,而尖锐批评“泥古者不化,颠冥者妄行”,“致使天地方昌之运,亦将有所蛰滞而不行”的后果[9]卷七。说的虽是诗歌创作,亦可通之于学术研究。总的来说,他的观点虽仍是属于“尊序”一派,以此对抗新文化运动者“打破《诗经》的经字招牌”之举,维护《诗经》的经学地位,但与“泥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
二、以文义裁《诗》
传统说诗者或以汉学的训诂考据释诗之义,或以今文经学的方式探究微言大义,此两种途径均是以释经之法解《诗》;而吴闿生释诗,“一以文意为主”(曾克耑《诗义会通序》),即从文学的角度体察《诗》之创作宗旨,是以文学与经学结合看待《诗》,桐城派于经学多采取此种研究方式。这种学术路径承自其父,吴汝纶研究诸子,“一以文义为归”,因为“舍文固无以见其道”[9]卷三。正因从“文意”来考察《诗》,故吴氏说经时,尽管也用训诂之法,结合史实细绎诗意,但最主要的还是从《诗》的文学表现进行品读。《邶·瓠有苦叶》之《序》以为“刺宣公淫乱”,朱熹也以“刺淫乱”释之,吴氏少有地一概否定,他通过“味其词”,得出此诗为“隐君子之所作”,因为“若以为刺淫乱之诗,则语意不符,而神理胥失”[8]29。在具体分析中,他指出首章“深则厉,浅则揭”是“遭时制宜”;次章“济盈不濡轨”是“喻涉乱世”,“雉鸣求其牡”是“喻小人各有仇匹”;三章“士如归妻,殆冰未泮”是“喻求仕以待天下之清”;而末章“以须友为词,婉言以谢之”[8]28。通过这番诗意品味与神理揣摩,从而认定此诗为隐士之诗,非刺淫之意。其大胆否定相沿已久的观点,正是以“文意”本身为基础。吴氏动辄以“详其词气”“详味词旨”“味诗意”“察其词”之语,表明他揭示诗旨的途径。
诗语中蕴藏潜在的含义,吴闿生称之为“微文”,揭示微文是他诠发《诗》旨的主要方式。《小雅·庭燎》传统的解释是“美宣王,因以箴之”,从诗本身看,美显而箴隐,吴氏说:“诗但写勤政戒旦之殷,而箴之之意自在言外,此所谓微文。《三百篇》及三代高文多如此。”[8]161显然,“微文”即是文外之意,在他看来,这是儒家经典最主要的表现方式。通过对微文的揭示,吴氏得出的观点有时与《诗序》相左。《大雅·崧高》之《序》以为“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序》以二诗美宣王亲诸侯、任贤能,而吴氏则以为,二者都是“讥宣王疏远贤臣,不能引以自辅,语虽褒美,而意指具在言外,所以为微文深远。《序》皆未能发其义”。而这一结论的获得,主要是涵咏诗意而来。《崧高》诗数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遣申伯,路车乘马”,而之所以反复称“王命”,盖“深著王之远贤”,正如郑笺所云:“申伯忠臣,不欲离王室。”《烝民》亦屡称“王命仲山甫”,吴氏父子认为,立鲁戏、料民太原,仲山甫皆谏宣王,宣王疏远之,命其筑城于齐,所以此诗乃“深惜其去”,而非美宣王。诗之第六章语气“反复低徊”,正写出其“以直谏不容而出”的不舍之情[8]261-263。吴氏父子立足文本,从诗语中品味诗旨,揭示其中隐含的深意,在传统之见外别立新解。
当然,吴闿生通过微文,往往是为了印证《诗序》所阐发的意旨。“诗之微意,待《序》而后明”[8]50,但《序》简质,通过“微文”的方式可以为之疏证。《郑·大叔于田》之《序》以为“刺庄公”,不过后人多以此诗为颂诗。吴氏父子则以此诗是“亲爱太叔者之所为”“将叔无狃”二句乃“以微词深风太叔,非爱之之词”,作者将此句置于“献于公所”之后,“以故灭其迹”,而编《诗》者存此诗,自是刺庄之旨[8]69-70。《齐·还》序以为“刺荒”,吴氏以为“此序得诗之指”,在他看来,诗表面所写虽为“矜夸相得之词”,但“刺意自在言外”,这就是“微文讽喻”的手法[8]84。《秦·终南》亦是如此,《序》云“戒襄公”,朱熹驳之,以为是秦人美其君之辞,吴氏从微文称《序》是“得其意于辞旨之外”[8]111。以美为刺,《诗大序》称之为“温柔敦厚”,吴氏所要揭示的正是此旨。除此之外,通过“微文”能更好地理解诗的写法。后世学者在理解《鄘·二子乘舟》所写为二子已死或未死时有分歧,吴氏觉得若未死而忧念,则“其意甚浅”,而若明知二子已死,伤悼之时仍如未死忧念之言,“则诗人之所为微至也”[8]38,是一种更为深情的怀念方式。显然,这样的理解更能得诗之深处。
因为强调“微文”,所以吴氏父子对《诗》的言外之意尤其推崇。朱熹批评《诗序》解《唐·有杕之杜》为“刺晋武公”是“全非诗意”,吴氏赞同段玉裁以枤杜“特貌”阐释“武公寡特,故以起兴”,并说:“古人高文往往意在言外,如此者甚多。”[8]105《大雅·假乐》末章戒“百辟卿士”意在戒王,吴氏赞其为“古人用笔妙处”,意承其父认为的“戒王意,就朋友发之,妙远不测”,并自信地说历来解经者“皆未有明此义者”,而“古圣哲之微旨端在是”[8]243。吴氏将“微文”之妙视为“三代高文”,吕祖谦分析《齐·猗嗟》之“刺鲁庄公”云:“是诗讥刺之意皆在言外,嗟叹再三,而庄公所大阙者不言可见。”吴氏赞同此意,称此为“古人微文之妙”,而且不仅此诗,“三百篇妙处多如是”,甚至“三代以上高文大氐皆如是”[8]91。他将言外之意视为《诗经》等儒家经典最有特色的表现方式。
吴氏推崇《诗》之微文,应得自于研究《左传》的启发,他著有《左传微》《左传文法读本》等,并称此书是儒家经典中“微文”之至者[8]91。《左传微》就是“专以发明左氏微言为主”[10]1。诚如弟子贾应璞所说,经吴氏阐发,“左氏微言密旨乃得昌明于世”[10]1195。他将研究此书之法运用于《诗经》之中,属一以贯之的学术路径。
如果从《诗义会通》的成书背景考虑,则其重微文甚有深意。其时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将《诗经》世俗化,由文而重其“情理”,彻底否定其中隐含有微言大义,俞平伯云:“说《诗》最要紧的是情理,而且比较有把握的也是情理……至于微言大义,不传者多矣,臆造者亦多矣,不起作者于九京,谁与定其是非哉!”[11]111因为否定微言大义,重视情理,不仅朱熹、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定性为“淫诗”者被看作爱情诗,他们还搜集当时的民歌发表在《歌谣周刊》上,用民歌的眼光看待《诗》,由此认为:“《诗经》本来是歌谣,只有《雅》《颂》中的一部分是朝廷宗庙所用的乐曲。不幸给汉儒附会到美刺上去,竟弄成了政治的评论诗,失其歌谣的本色。”顾颉刚甚至想用歌谣去讲《诗经》,“说明起兴不必有意义”[12]70。对于这股将《诗经》往浅处说的思潮,吴闿生显然是不能赞同的,要维护《诗》的儒家经典地位,必然肯定其微文。在评析《小雅·小明》时,吴氏认为末章“无恒安处”是自慰之词,却“反若泛戒凡百君子者,此所谓‘深隐’,所谓‘微至’,正古人之高文也”[8]194,结合以上所论,他反复称道《诗》之微意是“三代之高文”“古人之高文”,推崇得无以复加,显然是针对新文化运动者的学术路径而言:他要将被拉下经典宝座的《诗经》重新扶上原位。
同时,“求微意”在吴闿生等传统知识分子看来也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方式。其《重印古文读本序》云:“文之不知,则前人之微意莫得而明,前人之微意不明,则才识无自而开,而末由变通以为世用。”[9]卷三由文探知微意,开通才识,变通而为世用,这就是他研究《诗经》《左传》《孟子》等经典的真实用意。其弟子贺培新《后序》亦云,君子“生当乱世”,不得已而“掇拾补苴”“歌三代之余音,想黄虞之治迹,冀挽世风于万一,其用心亦苦矣”;而读其书者,“以究极乎古作者之微言奥旨,以冥会乎温柔敦厚、兴观群怨之精义,而求合乎雅颂韶武之遗音”,如此,“古乐虽不可复见,而吾夫子垂教救世之本恉”,则庶几存矣,可谓深得其师著述隐衷。吴氏引《六帖》之见,认为《小雅》中《四牡》《采薇》《出车》《枤杜》诸诗皆君上之言,而反托为臣子之言,“具道其明发之怀,仳离之恨,往来之众,思望之勤,臣下之隐衷伏虑,毕达于前”,这种“微文”的效果,“真足使人截脰碎首而不悔”。由此他不禁感叹:“文章之用乃能动天地感鬼神者,凡以此也。”[8]139文章通过微文产生经世致用之功效,所以微文成为他研究《左传》《诗经》等儒家经典的核心内容及学术取向,其用心亦可谓“微至”矣。
三、桐城文法的《诗》学印证
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受到冲击的晚清,为保存民族根本,吴汝纶极为重视“文”,他说:“鄙意西学当世急务,不可不讲;中学则以文为主,文之不存,周孔之教熄矣。”所说的“文”,指文学而言,是以姚鼐《古文辞类纂》及曾国藩《四象古文》两种古文选本为代表的古典文学,他赞赏在“世乱文字绝响”之际贺涛“独以古文立教”之举[13]353。作为华夏根本的儒家之道关乎种族的危亡存灭,而此又赖文得以流传,六经之文与“中学”息息相关。同时,在儒家经典被唾弃的时代,重视其文学价值也能为之续命,尽管这是不得已之举。在此情势下,“六经皆文”的观点成为晚近桐城派的共识,方宗诚、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吴闿生等人均从文法角度研究儒家经典。而六经之中,“《诗》独以葩艳丽则著”(曾克耑《诗义会通序》),其文学性明代以来就备受关注,晚近桐城派的《诗经》学研究,文法的分析是重要的方面,如方宗诚《说诗章义》、徐璈《诗经广诂》、马其昶《诗毛氏学》等即是如此,吴闿生《诗义会通》在这方面超过前辈。
作为桐城派后学,吴氏对《诗经》文法的分析也显露出宗派的色彩,正如蒋天枢所说,该书“所附‘旧评’及采用前人评语,尚未能脱去桐城派风范”[8]308,不仅如此,吴氏本人所下按语也是如此。兹举以下数例:
一章言车,而“驾我骐馵”豫以起次章之马。二章言马,而“龙盾之合”既以起卒章之兵;“鋈以觼軜”,又以蒙首章之车。三章言兵,而“俴驷孔群”复蒙上章为文。此章法错综之妙。(《秦·小戎》顾广誉评语)[8]109
三四章借朋友作衬,七八章借妻子作衬。二、三、四章言丧乱,六章以下言安宁。第五章承上起下。(《小雅·常棣》旧评)[8]141
首章始行,次章相宅,三章寄舍,四章燕劳,五章定居,六章作室。四章所言,乃初至时于庐旅饮犒耳,说者以为落成,非也。(《大雅·公刘》吴汝纶评语)[8]244
首章先述文王之神明陟降在天,先言此者,以诗为祭文王而作也。次章言文王能施,所以造周,而其子孙之所由盛也。三章言人才之盛,文王亦赖以宁。四章言文王之德在敬,因叹天命之遐远,商之孙子若是众多,命既有归,皆臣服于周矣。五章承上言,殷士归周者,祼将助祭,而犹服其黼冔,观此,足见天命之无常也。王所进用臣,得不念厥祖乎?厥祖谓谁?谓文王也。此明告成王之词,不敢斥王,因呼荩臣而告之耳。六章复申言之,谓不可不修德以永配天命,自求多福,无恃天命而骄,殷之未丧师,亦克配上帝也。大命不易,不可不鉴于殷矣。故七章遂结之曰:命之不易,无遏止于尔躬,宜宣昭令问,又思殷之兴亡,所以承于天者,天之祸福人,无迹象可求也,当善法文王,乃获为万国所归耳。反复深切,无一字泛设。古今诸家解释未有能条畅一贯者。(《大雅·文王》吴闿生评)[8]222-223
第一条评点者顾广誉为浙江平湖人,咸丰元年诏举孝廉,以战乱不获赴召试。晚年主上海龙门书院,甫三月而卒。著有《学诗详说》三十卷。其为古文词,“由桐城而上溯震川,以斟酌唐宋,而原本史汉”[14]5,与桐城渊源甚深。《诗义会通》引顾氏之语有26条,多为释经之言,可见对其经学成就的推崇。此条评诗之文法,注重章法的错综承接,正是桐城文章讲究“言有序”的传统。第二条为“旧评”,《诗义会通》于绝大多数诗后引“旧评”以点评文法,这些评语今虽尚未能考察出其来源,然就其用力处而言,当亦是桐城后学所为。至于第三、四两条,更不用说具有鲜明的宗派特色。方苞之“言有物”与“言有序”的义法论为晚清民初桐城派继承,姚永朴以“义法”为文学纲领之首,“法”是“极变化难测,特终归于有条不紊”[15]23。姚永概亦云“行文之序,不可紊也”[16]3,故在评析《孟子》文法时,极重其条理。吴闿生为姚永概弟子,乡邦之学自然贯穿在其学术研究中。
桐城诗派自姚鼐之后好以文为诗,亦偏爱以文论诗,方东树《昭昧詹言》体现得最为明显。吴氏父子论《诗经》文学成就时,也常以文法论之。上述行文之序的梳理,很能看出这一特征,又如用来评文的术语“峰断云连”也被用于评《诗》:
此(笔者按:指《小雅·斯干》)成室颂祷之词,而其文周密详备,无美不尽。后半特申祷祝之意,而由莞簟、寝兴、占梦蜕蟺而下,尤有蛛丝马迹,岭断云连之妙。古人之圣于立言也[8]167。
(《大雅·生民》)前五章盛称后稷功德,而推本于姜嫄。后三章叙郊祀之事。第六章由后稷递入祀事,语意一贯,无痕迹可寻。先大夫曰:以上叙后稷,以下叙祀后稷,即用降种贯下,是谓岭断云连。案:此古人文法之妙也。[8]238
“峰断云连”是用来评论《史记·田单列传》“赞”与正文之关系,归有光云:“赞后附出二事,承前淖齿既杀滑王于莒及燕长驱平齐,与《世家》相为跌宕,而著齐之所以转亡而为存也。史公此等,见作传精神洋溢处,昔人云峰断云连是也。”[17]吴氏对此法极为推崇,评语中不吝褒扬。
就技法来看,吴氏于《诗经》逆笔的分析值得关注。何谓逆笔?他在一封书信中说:“凡常人胸中无此接语,而能手乃为之者,皆为逆笔,退之所云‘口前截断第二句’也。”即出人意料之语。在他看来,这种技法在“六籍经传”中“比比皆然,不可悉数而尽”[9]卷七。在评点《孟子》时反复赞叹其行文“用逆之妙”“用逆笔之妙”,评点“矢人”章时云:“起句飘忽而入,令人不知,所谓用逆之妙,一至于此。”[18]此外,方宗诚、姚永概等在评点孟子时,也对这种笔法推崇备至。在这封书信中,吴氏以《诗经》中的三首诗为例谈逆笔之妙。第一首是《大雅·崧高》,他评云:“本赠申伯者,而先言‘崧高维岳’,此逆笔也。继言‘维岳降神’,又逆笔也。第四句始倒落申伯,又以生甫及申陪衬言之,亦逆笔也。”第二首是《大雅·烝民》,他评道:“本赠仲山甫,而先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此逆笔也。再接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又逆笔也。再接以‘天监有周,昭假于下’,而后始倒落生仲山甫,亦逆笔也。”第三首是《周南·葛覃》,他于此诗逆笔评价最为细致:“归宁父母之作耳,因归宁而及污澣,因污澣而及绤,因绤而及葛覃,而其词乃从葛起,且纵极笔势,至于黄鸟灌木,其鸣喈喈,令人读之顿有高情远韵,几欲弃百事而往从游。其于归宁,则仅篇末一语及之耳。此其用逆之妙,为何如乎!”[9]卷七在《诗义会通》的按语中,除《葛覃》外,虽不用“逆笔”一词,但对逆笔之法的揭示随处可见,如《召南·行露》旧评云:“起势陡峭。”[8]1《5大雅·大明》吴氏评云:“首章先凭虚慨叹,神理至为妙远。‘天位’二句,借殷事作指点,以喝起下文,而恰与后半收束处密合无间,古今之至文也。”[8]225均特别点明诗的首句突兀而来,这其实就是逆笔。
关注逆笔,是与晚近桐城派论文重阳刚与阴柔融合的美学理想相关。吴氏之文,早期继承曾国藩及其父的主张,尚阳刚以药桐城古文偏于阴柔之不足,所以其古文“颇得气势之美”(吴汝纶评语),“真力弥满,磅礴雄浑”(贾佩卿评语);而入民国以后,则践行曾国藩“合雄奇于淡远之中”的美学理想,求阳刚与阴柔的融合,故其文“时而风霆喷薄,时而云物夷犹”(武合之评语),“局势阔远,抟捖有力,尤妙含意深婉,非徒以才气见长”(刘际唐评语),追求以阳刚为主兼融阴柔之美的境界。吴氏认为《诗经》就具有这种美,他赞美《大雅·韩奕》“雄峻奇伟、高华典丽兼而有之,在三百篇中亦为杰出之作,更无论后人追步矣”[8]265,具有此种美,在他看来就是至高无上的典范之作。而欲实现此种美,逆笔的运用必不可少。此法可以制造陡峭的气势,有阳刚之美;文中之逆笔,打破行文的正常语序,形成语句及语意的断裂,而又通过内在的意脉将上下文贯穿,形成绵邈风神,又具阴柔之美。《诗义会通》评《葛覃》最能体现吴氏的美学追求:“此诗止言归宁一事。因归宁而及绤,因绤而及葛覃,而其词乃从葛起,归宁之意止篇末一语明之,文家用逆之至奇者也。黄鸟三句,于事外起兴,与本旨无涉,而神理乃益妙远,故为文外曲致。凡此情境,皆后代文字所无有也。”[8]3此诗可谓笔笔逆,“纵极笔势”,是谓阳刚之美;又逆入“黄鸟”一句,神理妙远,又见阴柔之美。逆笔造就此诗成为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字,吴氏对两种美学范式融合的向往及对逆笔的推崇于此表露无遗。
四、《诗经》的文学史地位
与“六经皆文”相关联的命题是“文本于经”,自刘勰《文心雕龙·宗经》将文体追溯至六经之后,这种观点深入人心。晚近桐城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不仅探寻文体之源,还将经典对后世作家作品的具体影响抉发出来,如方宗诚《论文章本原》、吴闿生《孟子文法读本》《左传文法读本》即是如此。这种理路的形成是在经学受到“废经”的时代思潮威胁之际,转而凸显其文学史地位,实现经学向文学的转化,为经学提供庇护所,从而维护其存在价值的学术方式。
吴闿生引用的“旧评”中常点明《诗经》某篇的文学史意义,他肯定此种评价,并且在按语中也常做出这类判断。《诗经》显然是后世诗歌的源头,在诗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如《召南·甘棠》旧评说是“千古去思之祖”[8]14;《王·大车》:“沉郁切至,杜公《三吏》《三别》所本。”[8]65;《小雅·北山》旧评:“连用十二‘或’字,开退之《南山》诗句法。”[8]192《小雅·白华》旧评:“后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二语,从‘英英’二句化出。”[8]216从题材类型、风格、句法及技巧诸方面探究《诗经》对后世诗歌的典范意义。
在看似普通的评点中,展示了晚近桐城派的美学追求。一是吴氏较关注《诗经》在古文史上的地位,尤其是对《庄子》及韩文的影响。前者如评《小雅·鹤鸣》为《南华》之祖[8]163,《白华》旧评又云:“是篇之妙,在借喻意写正意,《南华》所祖。”[8]216《诗经》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庄子提供了艺术资源。韩愈看重《诗》的“正而葩”(《进学解》),并以之作为创作的美学标准,吴闿生及书中所引“旧评”都关注此点,如《小雅·出车》旧评:“高壮激越,发扬蹈历,处处提唱天子。退之《祭鳄鱼文》祖此。”[8]147《大雅·抑》:“此诗千古箴铭之祖。韩退之《五箴》,曾文正公《五箴》皆导源于此。”[8]255《江汉》旧评:“通篇极典则,极古雅,极生动。退之《平淮西碑》祖此,而词意不及。”[8]266《韩奕》旧评云:“首章‘缵戎’以下,古奥如《尚书》,此退之得之以雄百代者。”[8]265《诗经》与古文看似不相干,吴闿生及旧评却从中发现其与韩文的关系,而且除庄子、韩愈及曾国藩外,并未提及后世其他古文家得益于《诗经》的启发,显然是文学趣味使然。
二是特别重视《诗经》对汉赋的先导作用。“赋者,古诗之流”,班固将诗与赋连接,这一观点成为诗赋关系的经典判断。如果说班固还是粗线条勾勒的话,吴氏及“旧评”则进行细致梳理。如他们寻找出《诗经》“开汉赋之先声”的所在,在于“铺张扬厉”(《鲁颂·閟宫》旧评)[8]300;“开词赋之先声”的是“文情俶诡奇幻,不可方物”(《小雅·大东》)[8]189。这是汉赋继承《诗经》的风格,汉赋阳刚与阴柔之美,均受益于《诗经》。又如篇章结构,汉赋往往“曲终奏雅”,以颂为讽,他们认为这与《诗经》笔法有联系,《大雅·常武》旧评云:“召公以德可常武不可常,故先言兵威以快其意,卒陈戒词,言乃易入。汉赋本此。”[8]268再如技法,汉赋最喜将平凡之物夸大为神异之物,吴氏以为此亦源于《诗经》,其评《周颂·振鹭》云:“以似为真,汉赋多学此种。”[8]280所论即此种技法。至于具体篇目,吴氏亦偶有触及,如评《小雅·斯干》:“旧评‘如跂’四句,古丽生动,孟坚《两都》所祖。”[8]167《车攻》:“‘四黄既驾’八句,尤为舂容大雅,王者气象,孟坚《东都赋》之所自出。”[8]159班固《东都赋》折以法度,颂扬王朝,在气象上与《车攻》有同工异曲之妙,二者间的渊源不言自明。
三是点明《诗经》与辞赋尤其是楚辞、抒情小赋之间的关系。如风格,《邶·绿衣》旧评:“哀艳,《离骚》所祖。”[8]22如创作心态及艺术风貌,《小雅·节南山》按语引何一碧评云:“此与《正月》《桑柔》等作,忠爱迫切,词繁不杀,苍茫百感,惝怳迷离,意无端绪,语无伦次,并是《离骚》之祖。”[8]171吴氏评《大雅·召旻》云:“贤者遭乱世,蒿目伤心,无可告愬,繁冤抑郁之情,《离骚》《九章》所自出也。”[8]271再如技法,《小雅·正月》旧评云:“正喻错杂,已开《离骚》门径。”[8]17《3小雅·大东》吴氏评云:“后半措词运笔,极似《离骚》,实三代上之奇文也。”[8]18《9邶·终风》引姚鼐评云:“后二章即屈原《渔父》《卜居》之权舆。”[8]25至于后世抒情小赋源于《诗经》,吴氏亦有所涉及,如悲情,《豳·东山》旧评:“‘果臝’六句,写凄凉景况,《芜城赋》之祖。”[8]13《4豳·鸱鸮》旧评:“通篇哀痛迫切,俱托鸟言,长沙《服赋》所祖。”[8]132如女性举止的描写,《卫·硕人》吴氏评云:“生动处《洛神》之蓝本。”[8]50《郑·有女同车》旧评云:“‘将翱’句,《神女》《洛神》诸赋所祖。”[8]74。
吴氏并未全面评点《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而是主要就其与辞赋及庄子、韩愈、曾国藩古文之关系立论,这显然受时代心理及审美取向的支配。
首先,时代心理。清朝灭亡,吴闿生虽曾在新政府中任职,不过这并不能消除其遗民情怀。在评析《小雅》诸篇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亡国之悲,他反对小序以“刺幽”释《弁》,以为是“同姓宴乐之词”,并从末章体会到“忧危之旨”,由此断定此诗“为乱世悲愁之作”[8]204。他将《离骚》与《小雅》关联,主要是在哀艳之类情感基调上的相似。而这类情感,最能触动其作为遗民的隐忧。不过,根据“声音之道与政通”的理论,他对此类趋于阴柔的风调又怀有戒心。对于清代以来的宗宋诗风,他深表不满,因为“宋体诗以淡莫微眇相夸尚,英思壮采屏斥都尽,非不诡隽可观,而去质厚峻雄之境日远”[9]卷五。而若“壮往感激之意气”受挫,则“遭时多故,国势亦晻忽不振”[9]卷五。显然,一方面,《离骚》哀艳之情能打动其敏感的心理,另一方面,从国运出发,他又呼唤“质厚峻雄”“壮往感激”的篇什,因此在重视抒情辞赋的同时,又向往汉大赋及《庄子》、韩文、曾文的刚健瑰玮境界。
其次,审美取向。吴汝纶评析桐城文风得失,指出其特色在于“气清体洁”,而不足则是缺乏“雄奇瑰玮之境”,即偏于阴柔而阳刚不足。有鉴于此,曾国藩“以汉赋之气运之”[13]51-52,形成“宏肆雄放,光焰熊熊”[9]卷五的风格。因尚阳刚,故韩文亦受重视,曾选《经史百家杂钞》录韩文12篇,居诸家之首;《四象古文》太阳气势中选韩文12篇,亦居诸家之首;马其昶撰《韩昌黎文集校注》,均意在以韩文救桐城之阴柔。同时,桐城传统亦重《庄子》,钱澄之著《庄屈合诂》,姚鼐著《庄子章义》,曾国藩对此书情有独钟,吴汝纶谓“往时写藏曾文正《四象古文》目录,《庄子》中多节钞”[14]172,今本此书少阳趣味之下钞《庄子》五整篇及十小节。其“独嗜”《庄子》,在于“庄生之恢诡恣睢”[19]18,而“恢诡”正得益于比喻的运用。正因如此,吴闿生在其父教导下,于《庄子》、汉赋及韩文用功颇多,故在品评《诗经》时,能领悟到其对诸家的浸润之功。正如他所云:“桐城之义法,固不免隘矣。有志乎文者,要必源本六经,泛滥于周秦诸子,屈宋之骚,马扬之赋,左、《国》、马、班之史,瑰奇伟丽,汪洋恣肆,夫亦极斯文之大观也已。”[9]卷七从对《诗经》的评析中,亦能看出他的文学趣味所在。
综上所论,吴闿生《诗义会通》在《诗经》学史上虽算不得鸿篇巨制,但因其成书于特殊时代,对诗的解读中蕴含着特殊的情感与学术意旨,浓缩着桐城派的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因此,其书又不失为一部独具特色的《诗经》学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