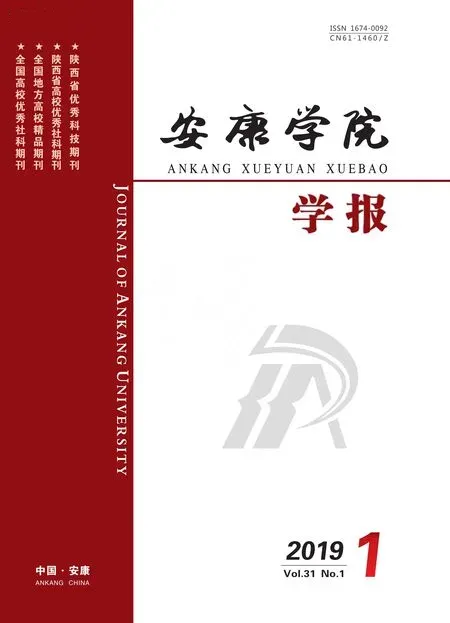“北妹叙事”中的姐妹镜像
——以吴君的小说为例
2019-03-15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2012年深圳作家吴君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者认为,吴君的小说展现了来深圳“淘金”的外省人的生存命运、生活状态和心理情感,塑造了真实、鲜活的城市新移民群像。作家以悲悯的情怀聚焦城市化进程中被忽略的人群,直面社会之痛、人生之艰、人性之暗,揭示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1]。吴君以平和、细腻、温婉的笔触塑造了诸多“北妹”形象,聚焦女性打工者这一弱势群体,力图破解南方女性打工者的心灵密码,探寻女性精神被遮蔽的重要层面,丰富了“五四”以来以女性为写作对象的内涵。
一、“北妹”——难以摆脱的身份枷锁
“70后”作家盛可以于2004年出版《北妹》一书,一经面世,“北妹”一词就立即引起了大众的关注。读者们发现漂泊一族中除了“北漂”“沪漂”外,还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叫作“北妹”。在《北妹》里盛可以对“北妹”的理解是:广东人认为广东以北都是北方,那些地方来到广东打工的女孩被广东人称为“北妹”。吴君延续了“北妹叙事”的题材,并且在她手中“北妹”群体的概念被扩大。在《复方穿心莲》一文中她将所有说普通话的外省妹都叫作“北妹”,“北妹”一词颠覆了教科书上以秦岭淮河以北为北方的概念,这一具有歧视性的称谓背后隐藏着诸多耐人寻思的意味。
吴君笔下来到深圳的“北妹”,大多都是来自穷苦的家庭,她们的长相、打扮、语言、习俗等都有着鲜明的“乡下人”特征。如何摆脱“北妹”身份的枷锁是所有“北妹”都需要面临的人生难题。尽管她们竭尽心思融入这个城市,大费周章地藏好“乡下人”的尾巴,但是真正的城里人一眼就看破了她们这些小把戏,让她们感受到无法言说的屈辱。在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北妹”个性被湮没,人格被扭曲,尊严被丢掉,成为都市文明中没有自我特色的“符号”群体。
吴君习惯从现实的、发生在身边的日常生活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题,从平常人的生活琐事中描写和刻画人物。平常中见真章,在生活的琐碎中更能凸显“北妹”身上沉重的身份桎梏,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北妹”在城市中生存的艰辛与无奈。《复方穿心莲》中方小红说“荷兰豆”在她们北方也有,叫作“扁豆”,但是遭到全家人的质疑,“这种东西北方绝对不可能有,你们北方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菜呢”[2]25,同为“北妹”的阿丹为了迎合方小红的婆家,昧着良心说了谎。以为嫁给本地人就能摆脱“北妹”身份的方小红,连亲吻自己孩子脸颊的权利都没有,因为婆婆认为她的脸脏。虽说方小红在众多“北妹”眼中是已经“上岸”的人生赢家,但是事实上方小红仍然处于“食物链”最底端,身份得不到认可,地位无法提高,甚至连保姆都可以瞧不起这个外省妹。文中的另一个“北妹”阿丹用尽所有的手段去争取一个深圳户口,对所有有点权势的人都谄媚巴结,不惜献上自己的身体,在自甘堕落中又清醒地知道,在众人眼里自己只不过是一条任人蹂躏的母狗。她的懂事能干得到方小红婆家的称赞,但在她走后全家人都换上了丑陋的嘴脸,甚至用恶毒的语言去诅咒这个讨好他们家的“北妹”,甚至对整个“北妹”群体都不屑,丝毫不顾忌同样来自北方的媳妇方小红。《富兰克恩》中潘彩虹为了工作,隐瞒了自己已婚并育有一子的身份,她陪酒、陪睡拼业绩,对老板庄汉文忠心耿耿,一路血泪爬到了酒店经理这个位置。潘彩虹倾尽一切去讨好庄汉文,为的是深圳的户口、儿子的学费和房子的首付。卖力过度出现了副作用——连和丈夫亲热时冒出来的都是庄汉文的脸,夫妻关系逐渐破裂。老板庄汉文对潘彩虹的忠心和能力大加赞赏,可是仅仅是因为潘彩红有利用的价值,用“深圳户口”诱惑潘彩红为他卖命,事实上他绝不会为潘彩红去争取一个户籍的名额。最后潘彩红惨遭毁容,老板庄汉文弃之如敝屣,潘彩红梦醒之后无路可走。
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中《迁徙的终点:从土壤地板到中产阶级》提道:“对于乡下移民而言,晋升中产阶级并非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是历史上的常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期间,这种现象在欧洲和北美的城市历历可见。”[3]北妹们怀着这样的“深圳梦”,希望跻身成为深圳的中产阶级,她们为此付出血泪、承受社会方面的压迫,她们成了被城市攫取、掠夺的对象。在吴君的小说中这些“北妹”大多没有美好的结局,时代的洪流将这些弱势群体冲上岸边,却没有人记得她们也曾为这个城市的崛起贡献过力量。
“户籍问题”是许多“北妹”越不过去的一个坎。盛可以的小说《北妹》中村长只为处女办暂住证,李思江献出了处女之身才换来了薄薄的一张暂住证。随着时代的进步,“北妹”们面临的户籍问题没有那么严苛了,但是得到深圳户口对于她们来说仍然是个棘手的难题。解决户口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嫁给本地人,方小红即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摇身一变成为本地人的。方小红也许是沾着些运气的成分,因为她之前是个教师,婆家基于优生学的考虑才会让一个外省人嫁入他们家。然而成功移民的方小红不过是从一个牢笼掉进了另一个牢笼,生育是她最大的价值,她在这个家只是作为一个生育机器而存在。阿丹为了得到一个深圳户口,在吃尽一切苦头后求仁得仁,最后借着怀孕嫁给了一个深圳人。潘彩红因为有家室的缘故,只能靠自我打拼,在她做出了全方位的牺牲、价值被完全压榨后,被老板无情地抛弃。“北妹”在“吃人”的城市中,姐妹之间的关系也被极度地扭曲,“利己主义”风行,世道崩坏了人心。她们像是掉进蜘蛛网的虫子,越挣扎越喘不过气。
为了融入城市,“北妹”做出了太多的牺牲,城市却没留给她们一席之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北妹”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在城市中处于失语无根的位置。吴君用剥洋葱的手法,揭开人物的每一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神情背后的伪装,暴露内心真实的阴暗,一层一层往里剥,直到灵魂最深处。虽然没有剑拔弩张、刀光剑影,但是“北妹”的生活在作者犀利的笔触下无处可遁。
二、镜中姐妹——两个女性的对立
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林幸谦教授认为:“女性得以在同性关系之间,找到远比异性关系更多的影响力。这显示出,女性视彼此为她们被男性抹杀/压抑的替身。在此状况下,女性充分利用男性中心论中女性遭受父权法则贬压的机会,进一步贬压那些比她们更为弱势的女性。更何况,在同行的竞争背景下,女性在压抑的生活中,常把身边的女性视为与其争夺权位和男人的对象。”[4]吴君在“北妹叙事”的作品中基本都会设立两个女性角色之间的对立。两个出身相同、经历相似的女性在冷冰冰的城市中惺惺相惜成为姐妹,但又是同在深圳这个独特的环境下,两个女性都把对方当作威胁的天敌,不惜用阴损的手段去陷害对方,最终两败俱伤。
“五四”以来女性作家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大多是正面积极的形象,如凌叔华《绣枕》中的大小姐、丁玲《梦坷》中的梦坷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苏雪林《棘毛》中的醒秋等女性形象。许多女性作家不敢面对传统社会中女性的阴暗意识,但吴君在她的作品中刻画姐妹情谊时没有落入乌托邦式的情结中。她展现的不再是诚信、勤俭、仁和的传统中国女性特征。对爱情坚贞、对命运坚韧、对信念坚持,这些都面临种种挑战。她们也不一定是社会美德的坚守者、践行者,但她们仍然是女性自我价值探索的先驱者、实践者,也是社会进步的参与者、推动者。吴君的作品透过这些有特殊烙印的人物,反映了在新世界、新环境、新生活中女性成长的不寻常经历和思想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其破解了身处南方物质社会中的女性打工者的一段段心灵密码,探寻了女性精神被遮蔽的重要层面,丰富了“五四”以来女性写作的内涵。
《复方穿心莲》中设置了双线女性人物:一个是嫁给了本地人的方小红,一个是还在苦海中沉浮的阿丹。方小红对阿丹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优越感,她过上了阿丹梦寐以求的生活:嫁入了深圳人的家里,做起了本地人的媳妇,再也不用每天叫外卖,不断地更换出租屋,还有保姆伺候。然而,方小红的生存状况和卖淫女阿丹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她们在这个社会同样没有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方小红活在一个外壁富丽堂皇,内则阴暗逼仄的“牢笼”里,但她不愿意离开这个姐妹们钦羡的“牢笼”。方小红不是没有试图反抗,她发现丈夫出轨后尝试过一次出走,可是带着孩子试探性出走的方小红最后又不得不返回。没有一个人关心她的出走,全家人皆是为她的丈夫开脱。阿丹清楚地知道方小红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她还是追求过上这种看似富足安稳的生活。她对方小红怀有一种羡慕和仇怨的心理,多次在现实中委曲求全却求而不得后,阿丹把怒气撒在了方小红身上。她故意陷害方小红,告知方小红婆家方小红寄钱回家,把方小红寄给同学的信也交给他们,以此让方小红在婆家备受屈辱。她向方小红揭开婆家温情脉脉的面纱,逼着方小红去看清自己嫁入了一个腐朽已久的家庭。
《念奴娇》中两个对立的女性是皮艳娟和嫂子杨亚梅。同样基于优生学的考虑,皮艳娟一家几乎倾家荡产娶回了师专毕业的杨亚梅,而娶杨亚梅的钱是皮艳娟用青春甚至是鲜血换来的。皮艳娟一家的主要收入是来源于被赶到南方打工的皮艳娟,出卖皮肉挣的钱为的是把钱寄回家让哥哥出人头地或者找个好老婆。全家人一边用着皮艳娟用身体换来的钱,一边又对她不耻,连家都让她少回。风风光光嫁进门的杨亚梅和皮艳娟形成鲜明的对比,小镇里知识分子稀有,嫂子成了他们一家的荣耀,杨亚娟没有为这个家庭做过什么贡献,全家人却把她当成“女神”供着。皮亚娟痛恨自以为有文化的嫂子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她的鄙夷,讨厌她一副指手画脚、指点江山的神情,她无奈地发出呐喊:“你们用的可都是我的钱啊!”在这样畸形的关系下,皮艳娟选择了对全家人进行报复。她一步步按着自己的计划把嫂子杨亚梅拉下污潭当陪酒女,可真的把嫂子拉去陪酒的时候,皮艳娟内心充满了挣扎,站在夏天的房间里打了冷颤,害怕带自己嫂子出来跟别人鬼混会遭天谴,但是很快报复的快感湮没了她的良知,她享受杨亚梅在她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为能够拿捏杨亚梅的情绪而洋洋得意。皮艳娟设计了这一切,终于轮到她看着杨亚梅堕落的样子,轮到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提醒:“杨亚梅,你不要乱七八糟好不好?”“真是好笑,你这样乱七八糟,也配做别人的老婆、母亲、嫂子”“别忘了你是家里的形象”[2]115。
还有《樟木头》里的陈娟娟和方晓红、《十二条》里的曹丹丹和江艳萍、《皇后大道》中的陈水英和阿慧、《富兰克恩》的潘彩红和阿齐等都属于二元对立的女性叙事。吴君与以往作家描写的底层人物不同,不是着重刻画底层人物的苦大仇深、水深火热的生活,而是更注重人物在精神层面的复杂性。她注意到了同为底层人物之间精神的龌龊、狭隘之处,这种复杂性主要从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和两位女性细腻的情感中表现出来,情感的不断累积,两位女性之间势必会有一场爆发。在爆发中她们将生活中的不满和怒气都撒向对方,在激烈的撕战后是两位女性的言和。她们压抑了太久,无处发泄,最后只能从同类身上找到发泄口。像杨亚梅最后和皮艳娟说:“其实我已经和你一样,你全看到了,有没有知识能怎么样,谁也不要看不起谁。有了这些事吗,你我就平等了。”[2]120阿丹嫁给本地人后打电话给方小红的道歉:“方小红,我其实有个事情对不起你……这两件事,一直压在心里,现在,说出来,我终于可以好受了。”[2]28阿齐对潘彩红说:“还以为会开心呢,呵,没想到我这种人也会失眠。”[2]200
“两个为梦想来到深圳的女孩,在各自的轨迹中行走。在某一刻相遇,成为心灵相通的朋友也成为彼此生命中的天敌。她们牺牲爱情、尊严、青春和梦想,只为兑换一张深圳永久的居住证。”[2]239两个女性承受着同样的苦痛,不拔刀冲向伤己之人,而对反身向同类插刀。“底层的陷落”凸显的是城市对世道人心的崩坏,深圳宛若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了人性之恶。
三、姐妹殊途同归——幻灭
吴君在访谈中说道:“心力角逐后,不过是殊途同归。”[2]239“北妹”们的共同结局指向——幻灭,“深圳梦”被现实无情地碾碎。深圳是一个男女失调的城市,男女比例一比七,不断会有年轻貌美的“北妹”涌进这个城市,“北妹”间竞争不断增大,城市给老“北妹”的机会也愈来愈少。没有“上岸”的“北妹”,也许这辈子都无法成为梦想中的城里人。摆在她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离开深圳,回到农村;二是继续在深圳过着“边缘人”的生活。所有的结局在故事开头就已经写好,无论她们选择哪一条路,结局都是“幻灭”。
在吴君的笔下,都市是病态的,都市里的人也都有病,他们都不快乐,不幸福。“北妹”们不惜代价,甚至舍弃亲情、尊严、贞洁,目的就是要在都市立足、扎根。《亲爱的深圳》中的光鲜白领张曼丽,保持高冷的姿态游走在都市。她眼里似乎只有两种人,对她有帮助的和不相关的。她可以对帮她搬东西的保安笑语盈盈,却对家中病重的老父亲避之不及,甚至他的死让她觉得解脱。她为自己捏造了一个处于中上层社会的家庭,因为这让她能够在都市中光鲜立足,受人高看。她努力与自己贫苦艰难的过往人生划清界限,但是抹不掉那段岁月在她身体上留下的痕迹,“外表光鲜,苦在里面”。离家出走到深圳打工的程小桂,努力学习都市人的口吻、生活方式,并以自己越来越像城里人为傲。为了保住得来不易的写字楼保洁工作,她回避与丈夫李水库的关系,甚至言行中充满了对他的鄙夷;她教丈夫如何放弃夫妻关系,以获取深圳人的身份,成为名正言顺的城里人……然而,小说的最后,作者转用饱含柔情的笔触,剥掉程小桂坚硬的外壳,露出她被城市割裂的伤痕累累的身体和心灵。作者以此唤醒读者重新认识这个人物作为女性弱势的一面,使得小说前面耗费大量篇幅塑造出的那个坚硬的女性形象变得有血有肉,生动起来——都市不给任何人喘息和脆弱的机会,适者生存是唯一的法则。《念奴娇》中,为了供哥哥读书,皮艳娟只身一人来到南方打工,“想家的时候,她会哭。直到哥哥没了工作,全家人也来到这座城市,她才不哭了”[2]105。被包养的日子让她获得了短暂的轻松和幸福,也很快就让她失去了所有。在这个冷酷的都市,她想尽办法给哥哥安排工作,得到的依然是全家充满势利的埋怨,于是带有报复性的唆使嫂子杨亚梅走上了从陪酒陪唱到被包养的路。小说的最后,留下的是一声怅然的叹息,为这个都市中艰难反抗又不得不屈从的那些女性。
四、结语
吴君认为作家应该具备更敏锐的社会神经,对于底层问题的关注不应只停留在物质层面,而应关注更深的精神层面。她的“北妹”形象展现了现实主义写作的高度,通过日常琐碎诉说“北妹”们无法摆脱身份枷锁的无奈、对金钱和名利的渴望、被社会机器压榨的伤痛……吴君以现实主义题材勇敢地呼应了急剧变化的都市社会,“北妹”群像深化了都市女性写作的文化内涵,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女性写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