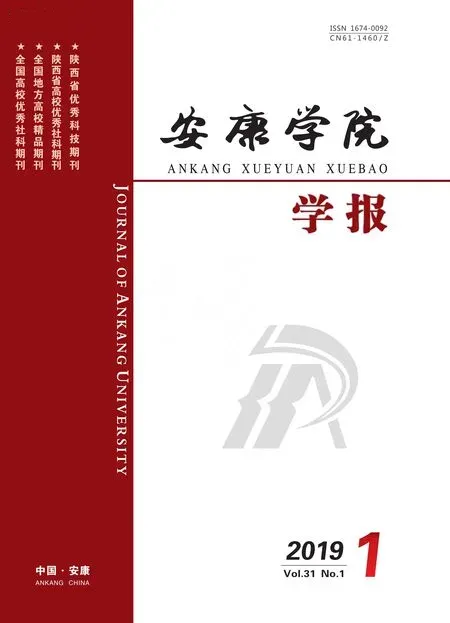叙事伦理学视域下的《丹东与妓女》评析
2019-03-1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叙事活动从古至今都不是孤立的、单纯的、形式主义的“文字游戏”。每种叙事活动的背后,都必然会牵涉到对伦理观的探讨。那些通过语言或者非语言手段将某个事件记录下来的行为,其实只是叙事活动的浅层含义,而叙事的深层内蕴始终绕不开对伦理问题的追问。且先不论旨在宣扬某些总体性的价值观念的宏大叙事,即便在后现代语境之下不少被高度解构的文本,在它们看似支离破碎的表面之下,其实也蕴含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个体生存境遇的人文关怀。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引子:叙事与伦理”中阐述了对“叙事伦理学”的见解:“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1]引子4据此,在叙事伦理学的框架之下,首先被关注的应当是叙事活动本身,要先了解故事中所叙述的那些关乎个体命运的事件,并且剖析叙事者在叙述过程中采取什么手段讲述故事,继而再去深入发掘故事情节以及叙述手段背后所试图反映的道德及伦理层面上的考问。简言之,在叙事伦理学视阈之下,文学表达应该表现为一种从叙事到伦理,而不是伦理观先行的态势。
一、复叙事:基于原叙事的突破
刘小枫认为:“现代伦理问题的确尖锐地出现在为数不多的一些现代叙事思想家讲的故事中,探讨现代性伦理不可能绕开这些叙事观望到的个体生命的伦理深渊,而探讨的方式只能是复叙事。”[1]引子11所谓复叙事,它的核心环节依然离不开叙事,但是复叙事并不意味着将前人创造的既有叙事再简单、机械地复述一遍,而是需要复述者凭借一定的叙事技巧,在原有叙事的基础之上作出突破,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叙事关系。
概括而言,《丹东与妓女》①刘小枫的《丹东与妓女》一文,最早刊载于《读书》杂志1998年第4期,后被收录于刘小枫的个人文集《沉重的肉身》中,但后者较之前者有较多增补及改动,两个版本存在一定差异。本文所评析的《丹东与妓女》是收录于《沉重的肉身》中的版本。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方面,作者对毕希纳所创作的剧本《丹东之死》进行了深入剖析,分析了剧中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二人之间的对立冲突,此外还对剧中的一个次要角色——妓女玛丽昂的形象也作了一番解读,由此揭示了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关于“自由”的伦理观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作者把毕希纳比作一位“思想的刑事侦探”,并将他撰写《丹东之死》的过程比喻成“破案”。借助文学式的叙述,毕希纳成了作者笔下半虚构式的人物,故不可以把他跟历史中的毕希纳完全等同。至于在《丹东与妓女》中所叙述的毕希纳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创作剧本《丹东之死》的过程,则变成了作者企图向读者讲述的故事。因此,假如将《丹东与妓女》仅仅解读成是对剧本《丹东之死》的文学批评,却忽略其中极为关键的叙事性,那么距离其精髓似乎还存在一定距离。
之所以说《丹东与妓女》并非一篇单纯的文学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在复叙事的过程中,添加了不少虚构性的元素在其中,增强了主观建构的故事性,却淡化了作为批评的客观性,而且这样的处理手法在文中比比皆是。例如,在毕希纳撰写《丹东之死》剧本和后来染病致死这两件事之间所建立的“人为联系”,就比较明显地反映了这种叙事特征:
毕希纳写完这宗思想疑案的案情报告书后,精力耗尽,身体变得极度虚弱,本来他的身体很好(不然怎么能干革命),完全可以抵抗那场偶然的伤寒。结果,二十四岁的毕希纳发高烧死了。其实,毕希纳死于一场内在的(思想上的)伤寒,一场因看到近代自然权利的自由伦理的底蕴而引发的伤寒。[1]32
刘小枫对毕希纳的死因所下的判断——将撰写剧本与感染重病这两件本无因果关系的事件联系起来,如果结合史实来看,或显得有失妥当。对此,毕希纳的翻译者、研究者李士勋也曾就这个问题提出过严肃的批驳①参阅李士勋《质疑刘小枫博士的〈沉重的肉身·丹东与妓女〉》,东方论坛,2010年第6期,第63-72页。在其第一部分“关于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之死”中,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史实证据,驳斥了刘小枫对毕希纳死因的臆测。,并表示“那种误导读者的臆测,纯属小说笔法”[2]63。诚然,李士勋站在历史考据的立场,秉承还原历史真相的精神,他对《丹东与妓女》提出的质疑并不是无理的。然而,刘小枫这种“歪曲历史”的做法真的是疏忽所致吗?采用这样的叙述方法是否“别有用心”?
归根究底,这还是离不开贯穿《沉重的肉身》整部文集的复叙事手法。由于刘小枫已经在文集的引子中强调过,他所进行的只是复叙事,所以在《丹东与妓女》一文中,他只是尝试讲述有关毕希纳撰写《丹东之死》这段经历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丹东与妓女》一文中很多看似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叙述,如果当成是“故事”而非“历史”来解读,也是无可厚非的。正如《沉重的肉身》引子部分所提及的,“讲个人命运的叙事,是原初的伦理学”[1]引子6。《丹东与妓女》的出发点,其实并不立足于对历史寻根问底,而是试图在突破旧有的伦理观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复叙事的方式赋予原有叙事新解,站在与现代个体的精神气质更为吻合的立场,从而更加合情合理地探究现代人的伦理问题。
除此之外,在刘小枫的文学观念中,似乎一直非常强调文学对个体生命独特体验的关切及书写。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一文中,他曾说:“文学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渴望在场的肉身在者的忧心和关怀。它在属于个体的肉身存在的言说中救护无辜不幸者和犯罪的不幸者成为人”[3]。这种文学观念的形成塑造,或与他早年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事实上,在刘小枫的不少文章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对十年“文革”的反思。《丹东与妓女》一文,正是围绕人民民主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博弈而展开的思辨。因此,虽然这篇文章叙述的是关于西方历史及文学的故事,但某程度而言,放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之下,也足以引发深刻的社会性思考。
二、由“身体”引发的自由伦理博弈
李士勋认为:“毕希纳通过这出戏揭示了罗伯斯庇尔打着为革命与共和国利益的旗号,滥用职权、玩弄自由、民主、道德等概念,操纵法庭和利用假证、伪证,采用各种卑鄙手段,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政敌置于死地的全过程!——这才是历史剧《丹东之死》的意义之所在。”[2]69应该说,这种解读是站在将《丹东之死》看成一部严肃的历史剧的立场上展开的,批评者综合考察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事实、政治气候、社会现状等因素,并且将毕希纳也视为历史的忠实考察者这样一个身份,从而对剧本《丹东之死》作出较为合理的阐释。然而,《丹东与妓女》一文似乎并非旨在对历史真相追本溯源,作者更多是企图讲述关乎个体生命感觉的故事,目的是深化伦理层面上的思辨。
在《丹东与妓女》中最直观反映出来的被反复讨论的伦理学问题,无疑便是两种自由观的碰撞。刘小枫通过详尽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以罗伯斯庇尔的立场为代表的“人民民主自由”(积极自由)同以丹东的立场为代表的“个体自由”(消极自由)这两种自由伦理及其背后所牵涉的政治观和国家观之间的博弈:
罗伯斯庇尔一方依照卢梭主义的提案建立以人民公意和道德一致为法理基础的伦理国家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丹东一方则以为,应以承认个体的感性偏好及其差异为国家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如此国体就是自由的个体民主的国体……丹东与罗伯斯庇尔在国家制度问题上发生了龃龉,一个要建立能体现出个体肉身曲线的美或丑的国家,另一个要建立用人民道袍把个体肉身遮起来的国家。[1]17-18
结合史料来看,罗伯斯庇尔是卢梭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他对人民民主的高度推崇,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卢梭的思想中探寻到理论根源。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贯彻了鲜明的“主权在民”政治理念,并提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把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接纳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的社会公约思想。换言之,就是将人民公意上升到社会道德及意识形态的层面,并将其置于个体意志之上。
对此,刘小枫不仅在《丹东与妓女》中对“人民道德”作出了概念性的阐述,指出:“人民成了美德的公意符号,在人民的公意道德中,个人的价值偏好必须得到矫正。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必须放弃自己个体的价值偏好,不然就不能成为共和国公民”[1]8,事实上,在《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一文中,他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阐述:
任何社会存在样式都是一种语言的样式,因而,可以通过对某个意识形态话语的考察来看这一问题。例如,所谓“自绝于人民”——“人民”一词具有巨大的道义迫害力量,凡不能被认同为“人民”者,就是应该被消除的个体存在。“人民”一词的道义迫害力量,首先不是得自于其数量上的不可推算性,而是其道义色彩和总体性,正是这两个特点表征出全权社会中意识形态话语的一般样式……在“人民”这一称谓中,人本身——每一个体的肉身存在并未在场。正是这种情形,使个体存在悄悄地失去了生存的正当性和处身性。[5]
由此可见,人民民主在追求某种总体性的公意道德的同时,实质隐藏着对个体造成压迫的风险性。人民民主伦理所倡导的总体自由,很有可能会扼杀个体的自由。正如哈耶克所言:“自由要求允许个人追求他自己的目标: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的共同目标束缚的人。”[6]这就反映出个体自由所追求的价值,恰好与人民民主自由所追求的价值存在着一定矛盾。回到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以及剧本《丹东之死》本身,虽然罗伯斯庇尔与丹东在革命事业初期是合作无间的战友,但后来由于丹东似乎逐渐意识到人民民主伦理中存在着巨大的道德压迫力量以及令人可畏的一面,于是与罗伯斯庇尔逐渐产生了分歧。
然而,《丹东与妓女》中所展示的人民民主自由与个体自由及其所牵涉的国家观,二者表面上看似相互抗衡,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实质上这两套观念却又“本是同根生”。一方面,由于对自由的实现方式存在着不同理解,所以导致了治国理念的差异;另一方面,对于自由与否的最根本出发点,其实在于如何掌控身体的主导权上,因此这个源头是相同的。所以,原本在《丹东之死》里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政治争斗,在《丹东与妓女》中则增添了象征的意味,变成了对由“身体”这个根本原因所引发的两套伦理观之间的冲突的隐喻。
据此,对于妓女玛丽昂形象的深入剖析,在《丹东与妓女》中就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意义。事实上,在剧本《丹东之死》中,妓女玛丽昂只是个非常次要的角色,在全剧四幕共计三十二场戏中,玛丽昂仅仅出现过大约半场戏的时间①玛丽昂只在《丹东之死》的第一幕第五场出现过。。然而,刘小枫却敏锐地察觉到玛丽昂与丹东之间的契合,他发现了“丹东只是把妓女玛丽昂当作个体自由伦理的极端个例,以此向罗伯斯庇尔的人民民主国家构想挑战,以个体的享乐欲望、具体的感性偏好抵制人民的道德公意和抽象的共同体良心”[1]18。暂且不论妓女行业的存在,到底与单纯追求个人肉体享乐还是社会不公所造成的道德沦丧哪个因素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妓女”与“身体”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隐秘而直接的联系,却是无可置否的。在《丹东与妓女》中,玛丽昂所肩负着的妓女身份,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因为无论是肉体上的快感还是痛苦,这同样源自身体本能的两种不同感官体验,以极为微妙的方式对立统一在了这个符号之中。
在西方思想界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受到“灵”“肉”二元对立思想的深刻影响,将“身体”置于主体性的地位所展开的伦理层面的探讨,无疑是存在空缺的,往往更倾向于把身体作为意识的附庸来看待。但是从尼采开始,再到后来的福柯,从现代主义的开辟一直到后现代主义的延续,对于身体主体性的关注程度都有所提高。正如汪民安所言:“从尼采和福柯这里开始,历史终于露出了它的被压抑的一面。一切的身体烦恼,现在,都可以在历史中,在哲学中,高声地尖叫。”[7]或者这就可以尝试解释,为什么刘小枫在《丹东与妓女》中,很有必要通过复叙事的手法,再去重建新的叙事。因为只有突破《丹东之死》剧本原有的历史观的局限,突破过去普遍将《丹东之死》单纯视为历史剧的传统批评观点,而将剧本中长期被隐藏、被忽视的由“身体”所衍生出的一系列伦理学问题,重新置于当下的语境中加以发掘,才能凸显其价值和意义。
三、悬而未决的伦理困境
如果从《丹东之死》的剧情本身来分析,剧中丹东放弃任何辩解、逃走、自救的机会,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断头台,这个结局看似是罗伯斯庇尔以及他所坚持的人民民主自由伦理观的压倒性胜利。然而,在剧中的第一幕第六场里,罗伯斯庇尔却也对自己所坚持的立场有过迷惘和质疑:
为什么我们总是盯着那一个呢?圣子耶稣确实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被钉上了十字架,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客西马尼花园里厮打得头破血出,可是谁也不能用自己的创伤解救别人。——我的嘉米叶啊!——他们都离我而去了——到处都是荒凉和空虚——只剩下我孤身一人。[8]
针对剧中罗伯斯庇尔的这段独白,刘小枫在《丹东与妓女》中先是指出“这天夜里,罗伯斯庇尔也撞见了虚无”[1]29,继而尝试进一步解释剧中的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各自所面对的虚无的成因:
罗伯斯庇尔与丹东撞见虚无的方式不同。丹东觉得上帝对这个世界实在多余,想要没有上帝的生活,结果撞见虚无;罗伯斯庇尔觉得过去的上帝无能,不能真的救人,便把老上帝驱走,自己成为上帝之子,结果撞见虚无……如今,这只神义之手被斩断了,罗伯斯庇尔和丹东设想出不同的人义性的自由方案来承负身体偶在的悲惨,发现承负的只是一个最终会化为虚无的身体。[1]29
由此观之,在剧本《丹东之死》中所反映出来的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各自所坚持的两种不同价值立场,刘小枫通过《丹东与妓女》,展示了这两套伦理观各自演变的轨迹——它们不仅出发点相同,都是源于对如何消除身体的痛苦而展开的伦理探索,尽管实现的手段不同,但最终的命运竟是殊途同归,二者的终点都指向了虚无主义的悲观乃至绝望——脱离了“神义性”而用“人义性”手段所得来的自由,由于失去了精神寄托,一旦身体毁灭了,那么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复归到虚无状态。
假如顺着神义性与人义性的分歧这个思路深究下去,必然会延伸至有神论和无神论这两种立场之间的争辩。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其实隐含了刘小枫的预设立场。他发现了在神义性的救赎缺席之后,无论是丹东还是罗伯斯庇尔,他们各自企图借助人义性的手段去拯救肉身的尝试都是徒然无功的。由此推测,刘小枫在情感和价值取向上,实质上是倾向于借助神义性的方式去实现肉身的救赎的。然而,对于彻底的无神论者而言,又显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承认这种有神论的立场。于是,在《丹东与妓女》中反复展示的两种自由观之间的对立,随着复叙事的不断深入,最终指向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神学立场上的根本差异,而这种差异所带来的伦理学困境,目前似乎仍停留在无解的状态之中。
除此之外,前文曾提及过,刘小枫将毕希纳撰写剧本《丹东之死》与后来染病致死这两件事关联到一起,实属文学虚构的表达方式。但如果往更深一层思考,选择这样的叙事方式到底目的何在?其实,《丹东与妓女》中所谓“致命的伤寒”,已经超出了身体疾病的范畴,它与历史上毕希纳的真实死因甚至毫无关联,只是作为文学形象的毕希纳在这个故事中的结局。“伤寒”在这里被赋予了强烈的隐喻意味,暗示了毕希纳在创作《丹东之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人类伦理的难题却又无力提出解决方案的困境。而且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作者刘小枫在复叙事的时候必须面对却无法给出标准答案的困惑,这也是现代人所处的伦理困境。
四、结语
在《丹东与妓女》中,作者刘小枫通过独特的复叙事手法,重新讲述了关于毕希纳的个人经历及其剧作《丹东之死》的故事,展示了两种源于将“身体”置于主体性的地位这个基点的思考,并具体表现为“人民民主自由”与“个体自由”两种自由伦理观及其所衍生的不同国家治理观念之间的冲突,最终又同样指向了神学层面思辨的两套价值观之间的对立统一及其背后悬而未决的现代伦理困境。作者在文章里似乎并没有正面提供一个明确而圆满的解决方案,但他至少在叙述毕希纳及其剧作《丹东之死》的故事过程中,展示了这种现代人无法逃避的伦理困境,提供了让更多人愿意正视并深入探讨它的对话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