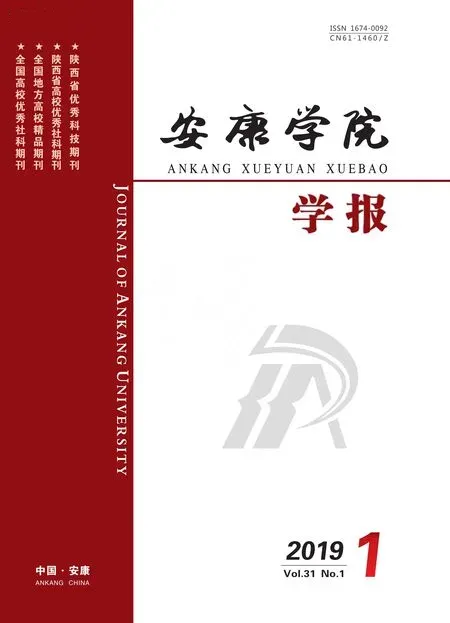论萧红小说的散文化特色
2019-03-15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一、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传统
小说在我国虽不像诗歌那样影响广泛而深远,但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从神话、传说经由笔记、传奇直到明清时代兴盛的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源于对“书场说话”气氛和故事性的强调,我国小说形成了区别于西方小说“情节中心”的模式。新文学运动以来,与“个性”“自我”一类彰显时代潮流的理念、范畴相呼应,小说叙事开始出现情绪化、心理化倾向,其发展则是散文化风格的叙事渐成模式。具体而言,即缺少戏剧性,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浑然天成。作品中浓郁的情感充斥其间,于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传达作者的意图,但并不排斥在文章中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也不否定情节的发展。这种变化是对变动中的时代的呼应,也是对变动着的时代的表现。
以散文化风格为标记的小说家主要有鲁迅、郁达夫、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他们的创作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一个重要的审美传统。来自白山黑水的东北作家群中的萧红,以其女性身份和突出的创作个性,也成为散文化小说创作领域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存在。
鲁迅可以算是散文化小说的创始人。“五四”时期主情主义的文学浪潮也影响到了鲁迅,他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渴望揭露国民的痼疾,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种创作动机的最终实现有赖于鲁迅自身的文学才能。他幼年接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具备了一定的传统文学素养,加上鲁迅本人有着强烈的乡土文化意识,带着对人类问题的终极关怀,创作出了诸如《社戏》 《故乡》等作品,都以淡淡的乡愁笔调描述了浙东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以《故乡》为例,当“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满心的憧憬却被现实撞得粉碎。魂牵梦绕的故土早已改变了模样,文章尖锐地指出农民在生活中的麻木与退化,闰土终于还是恭敬地喊“我”一声“老爷”,小时候那个充满活力的少年已被磨平了棱角。鲁迅并没有着力营造激烈紧张的矛盾冲突,即使对闰土性格的转变,也是以抒情笔调刻画出来的。
郁达夫是20世纪20年代浪漫抒情小说的代表人物。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发表的《沉沦》就是对自我心灵的真实揭露,开创了“自叙传”小说的写作。采用这种文体,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其童年经历在长大后的余响。幼时家庭的不幸以及精神的痛苦造成了他自卑脆弱、忧郁的内倾型性格,因而当文学这杆利枪出现在他面前时,便外化为强烈的自我情感表现;另一方面,他留学期间喜欢阅读日本“私小说”的作品,并且深受屠格涅夫“多余人”形象的影响,以上这些都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沉沦》为例来分析这种小说,会发现文中始终贯穿一条情感线索,那就是“我”的苦闷、自卑,是“我”作为身在异乡的弱国子民,渴望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回国后,《茑萝行》 《迟桂花》延续了浪漫抒情风格,这种小说虽然少了传奇色彩和戏剧化的情节,却更有生活化的气息。另外,他的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如《沉沦》结尾主人公发出的:“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1]正是作家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表现;《春风沉醉的晚上》对烟厂女工陈二妹的同情关照,体现了作家对于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蕴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关照。郁达夫将自我感情熔铸于文本,以真实的情感感染读者,叩击读者的心扉。
废名的作品洋溢着诗化、散文化的特色,意境的营造使通篇有“唐人绝句”的韵味。同时作品也浸润了佛、道、儒三家思想,尽管这些思想使文章读来有些晦涩。具体来说,儒家思想在废名心理结构上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观察人生中。而当现实中的痛苦无法解脱时,他便转而求助于佛道思想。其佛教思想的形成有着更为深厚的根源,废名生于湖北黄梅这个禅宗思想浓郁的县城,佛教禅宗追求美与自由,注重感性思维,强调灵感直觉,对于废名心理的形成有很深的影响。并且他与周作人交往甚密,周作人也深谙佛理,这两方面都促使废名在文章中自觉运用禅宗思想,如对三姑娘、陈聋子的形象塑造,体现了他理想中的美好人性。道家追求无为而治、自然隐逸,从《竹林的故事》中对三姑娘爸爸的死的描述可以窥见,他不是大写人的悲伤,而是将其描写为一种自然行为。这些都使文章于和谐宁静中有空灵,在美好人物形象中品出“美文”的味道。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代表,自称“乡下人”的立场赋予了文本深厚的乡土意识;他的文章还体现了“自然即美”的唯美主义倾向;《猎人笔记》的抒情笔法与巫楚文化的影响在其作品中也若隐若现。作为一个流寓他乡的漂泊者,无所归依使他渴望精神上的还乡,文章充满乡野的平和质朴之美。他以对湘西世界的诗意重现、对“人性之常”的赞美迥异于鲁迅、郁达夫等人。最能代表其风格的是湘西题材小说,尤以《边城》为最。小说描写了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应是小说的重点,但细细读来,文中对两人的爱情描写得很少,而对外祖父的笔墨似乎更多,读者只能在寥寥几笔中找寻他们的爱情发展线索。对于傩送、天保的性格,也是从别人的口中才有所了解。傩送不要磨坊要渡船,作家对此正面描写不多,读者亦只能在只言片语中感受傩送的专情。总之,在人物关系和情节结构上,小说写得很散,但却隐伏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对于人性、人情的赞美,带有乌托邦色彩。这种“形散神不散”的散文化手法出现在小说中,使小说具有了散文的精神。
汪曾祺提出:“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我一直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2]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延续了20年代以来的散文化小说传统,如在《受戒》 《大淖纪事》中营造了一种清幽淡远、韵味无穷的意境。这种写法与他在西南联大时师从沈从文有密切关系,但更多的是他自身的性格所决定的。他有着深厚的书画功底,并且曾从事戏剧编辑,这些都培养了他的观察兴趣。他以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童年生活的回忆,酝酿出一个美的氛围,在文章中表现为对素朴、率真人性的真诚赞美。如《受戒》就从独特的视角,讲述了和尚明海与村姑英子之间的一段恋情。和尚不再是正襟危坐的传道士,在他们身上保留了世俗情趣,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明海与英子的恋情显得格外真挚。文中语言也富有韵味,结尾段“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3],这些语句描绘了一幅苏北风土的画面,给人以诗的美感。
二、萧红小说散文化的具体表现
萧红的作品中,最能代表其散文化风格的首推《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是萧红生命后期的代表作,当时她流浪在距家乡千里之外的香港,带着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写出了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及生活状况,表达了对人民“无主名”的愚昧和黑暗社会现实的否定。更为重要的是,文章采用了散文化风格,这使萧红的情感表达更加感人,对于《呼兰河传》这篇有着强烈抒情色彩的小说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萧红小说的散文化风格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儿童视角
用第一人称叙事并不少见,若在第一人称叙事中选择运用儿童视角,数量便会减少一部分,如果不流于童话故事的模式,那就会少之又少。《呼兰河传》便是集合了上述特点于一身的作品。文中始终以年幼的“我”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幼小的孩童自然无法理解大人的世界。基于这样的常识,“我”的眼中出现了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以隐晦的文笔写出了呼兰城人们的愚昧昏庸。在“我”的眼中,世界很荒诞,在陌生化的描写中写出了世界的本真状态。
文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小团圆媳妇被打得害病,人们说她是鬼上身,只有“我”觉得她很正常,并且和她玩玻璃球;有二伯偷东西被人发现了,与他同阶级的人嘲笑戏弄他,而“我”却很理解他,并央求他不要把“我”的事告诉妈妈;王大姑娘嫁人后,人们说她那样坏,一定不是好东西,“我”发现人们对她嫁人前后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都是大人们不愿意承认的,但在小孩子这里,却可以肆无忌惮地加以展示。她什么都不知道,但看到的、说出来的却比大人更加真实,这种反差,就鲜明讽刺了成人世界的虚假和愚昧。
选择儿童视角,是萧红的无奈,更是她自觉的选择。萧红的文学创作曾得到鲁迅先生的悉心指导,鲁迅先生创作的《社戏》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都运用了儿童视角,这对萧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萧红笔下,这种手法的运用得更为成熟。这种视角在描写“我”与祖父的关系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祖父是非常爱“我”的,所以任何幼稚的举动在祖父眼里,都是值得爱怜的,萧红把这种感情还原到了极致,让我们也能感到那笑盈盈地祖父的慈爱。在后花园里,“我”与祖父一起栽花拔草;祖父还给“我”烧过美味的小猪和小鸭;当祖父在讲解“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时,“我”的害怕恐慌,祖父的忧郁哀伤,在萧红笔下,都显得非常真诚感人。
(二)场景叙述
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是按照情节的发展或者人物性格的变化来叙述。如茅盾的代表作《子夜》描写了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上海商界的沉浮,以他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斗智斗勇为线索,展示了他从兴起、挣扎,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以觉新的性格变化为线索,表现觉新由最初朝气蓬勃的青年,转而沦为封建社会的帮凶,期间他不断地动摇挣扎,直至第三部开始彻底的觉醒。按这样的思维来看《呼兰河传》,很难清楚地概括它究竟写了什么内容,这是因为它使用了场景叙述的方式。
这部小说以空间结构的变化来安排全局,一是写呼兰县的总体外貌,例如有东二道街、十字街、各种小巷;二是讲述小城人民的精神面貌,包括各种请神、祭神仪式;三是“我家的后花园”,写童年萧红与祖父的生活;四是从后花园转向“我家”的正门,写了拉磨的、漏粉的、赶车的几户人家;五是写小团圆媳妇的悲剧;六是写“家族以外的人”有二伯的故事;最后一章可以说是一个“光明的小尾巴”,写冯歪嘴子与王大姑娘结婚生子,在妻子死后,冯歪嘴子不顾旁人指点,拉扯孩子,坚韧生活的故事。
如果把文章分开来读,就会发现每一章都是一篇优美的散文,都可以当成一个个小故事来读。例如第二章写呼兰县的盛举,有娘娘庙大会、放河灯、跳大神,这些铺衍出了东北地区的风俗画面,虽不乏愚昧的成分,却充实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七月十五这夜生的孩子受到指责,但要是有钱那就另说;女子指腹为婚,常酿出悲剧;娘娘庙里的女人雕塑得很温顺,老爷庙里的男人很凶狠,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所容……
(三)文脉设置
文脉,大致相当于线索,不是先行布设来的,而是天性流露,尽管可感却不可见,着重说的是“形”的方面,体现到文中就是灵动不羁、洒脱、行云流水这类形式感方面的风格。《呼兰河传》中时间、空间、情绪意识不断跳跃,排列组合,看似毫无章法,其中却始终贯穿着萧红怀乡恋旧的情绪。
萧红本身是一位非常感性的作家,一生都在极力追求爱与美,虽在短暂的生命中有过一时的欢愉,但总体来说,却是始终求而不得。当她在生病期间,提笔写《呼兰河传》这篇巨作时,情感自然而然就渗透在作品中了。身逢战时,只有记忆中的呼兰河才能抚慰她备受创伤的心灵。这部写给自己的作品完全靠感情驱使,看似不成熟,但作家随着自己感情的变化,自如地书写,别有魅力。
依靠感情连缀文章,自然不同于规约下的正统文字,章与章的连接不合逻辑,却暗合作家思想的流动,下笔成文,往往就是记忆中的生活琐事。急欲袒露自己的心意,常常文不达意,但细细想来,却是情理之中。这种本能的表达,源于萧红感知世界的特殊方式,她为人任性天真,渴望理解与自由。这种矛盾表现在她的文章中,主要是不按常规套路,文体的选择也不同于他人。语法结构的重置在文中随处可见,段落的设置时长时短,短句重复出现。文章常常使用方言俗语,情节发展上没有强制的因果联系,以上种种都使文章呈现出行云流水、不饰雕琢的潇洒美。
(四)语言表达
为了抒情的需要,文章也保留了大量的方言土语。“毛子人”“火烧云”“团圆媳妇”“包米”这类词语在文中多次出现。词语的使用也通俗易懂,例如“白亮亮”“混沌沌”等。“了”字不断出现,符合儿童的语言特点,在描写火烧云时,有这样的语句,“一会红堂堂的了,一会金洞洞的了”[4]106,眼前似乎可以活现出一个活泼的儿童。
修辞在文中屡见不鲜,比喻、拟人的使用更为频繁。如描写老头走在结冰的马路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4]84;“花开了,好像花睡醒了似的”[4]131等。再如“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4]157,这句话初看很不合理,颇有什克洛夫斯基所言“陌生化”的意味,但将“鲜明”与“荒凉”加之对比,更能显示出粉房里无视生命的愚昧。文章中还不断出现“荒凉”“寂寞”的字眼,如“这院子是很荒凉的了”[4]152、“我家是荒凉的”[4]154,这种反复虽然单调,却将心灵深处的声音充分渲染了出来,可以想见萧红内心的悲凉,似乎可以拧出作家情感的汁液来。
即使感情凝聚至此,萧红笔下的表达还是很含蓄的,如第二章中的那段文字:“听了这声音,许多人终夜不眠,若赶上下雨的夜,则更为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4]112。这反映了身处不幸中人们的迷茫、困惑,却也是身为作家的萧红寂寞心境的表达。萧红并没有放肆怒号,也没有凄凄惨惨戚戚,而是用不动声色的文字将自己的寂寞传达给了读者。
三、萧红小说散文化的内在蕴涵
萧红的作品不仅因艺术形式上的追求而使人着迷,更因其内容上的深刻而研究者众多。她的作品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强烈的自由意识、深重的寂寞情怀,有别于其他作家的作品,读来每一篇都很有分量。萧红的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晰,所以在本文分析中也涉及她的散文创作。
(一)鲜明的女性意识
萧红曾经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身处这个群体,她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种种恶意,临死之际,写下了“半生受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正是鲜明的女性意识,她才能道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一现实。
出于这种认知,萧红笔下塑造了一大批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形象。她们善良、温柔,却有着非人的遭遇,男人把她们当作发泄、生育的工具。在这里,萧红撕下了笼罩在男性身上的面纱,他们不再是含情脉脉的觉新、觉民,而是冷酷的刽子手。如《生死场》中的金枝在未婚前抱着与成业幸福生活的愿望,匆忙出嫁,但等待她的却是与成业嫂嫂乃至所有妇女同样的命运,她在几个月之后也开始恨男人了。月英曾经是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有着温柔的目光,可是现在这些全都消失了,在她瘫了之后,丈夫开始还替她治病,在治疗无果后,便对她不管不问,好像“一个人和一个鬼”生活,进而折磨她,月英眼珠、牙齿变绿,下体生蛆,连被子也没有,生不如死,最终棺材葬在山下,寂寞地死了。生育原本被奉为神圣的行为,但在这里,生育却沦为一种刑罚,即将临盆的女子,“带着满身冷水地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5]39,女性在这里完全失掉了自己的地位,只能畏畏缩缩地活在男性的威权下。
这些男性显然不是英雄,他们碾压着女性的命运。在这里,萧红极力解构男性的中心地位,男性不再勇敢无畏,他们只敢在家庭中装腔作势。王婆的丈夫赵老三当初组织“镰刀会”,还算有骨气,但仍不及王婆,王婆找来老枪,教赵三怎样装火、上炮,她显得比自己的丈夫更有能耐。赵三失败,坐了监狱后被放了出来,他完全失掉了男性的骨气,对东家感激涕零,终日念叨着地主的好,并且感到自责,开始深深地忏悔,从“起初看来还像一块铁”,变为“后来越看越是一摊泥了”[5]34。就是这样的一些男性,他们本身没有力量,可在封建势力和传统观念的习惯下,他们控制着女性,并将女性带入了死亡。萧红将这些男性与女性形象进行鲜明对比,猛烈抨击男性的丑恶,企图冲破旧时代强加给女性的桎梏,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
(二)强烈的自由意识
在三四十年代风云激荡的文坛,许多作家选择了战争、为政治服务的题材,萧红却反其道而行之,将眼光放在了远在东北的呼兰小城。在作家们不断学习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宏大建构小说的同时,萧红却以散文化小说另辟蹊径,她声称“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这些都说明在一个弱女子身上,同样有着不流于世俗的愿望和强烈的自由意识。她毕生都在歌颂自由、追求自由,同时鲁迅先生对于封建礼教的批判,启蒙民众的立场也成为萧红创作的“影因”。这在她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反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性别压迫,她孜孜不倦追求的启蒙、试图唤醒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正是自由意识的一部分。
鲁迅先生对于《生死场》曾有这样的评价:“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6],东北人民在生活重压下的抗争,以女性的口吻说来,更添韵味。在文中,吸引我们的是一系列女性群像,在麻面婆、金枝、王婆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人的愚昧和觉醒。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5]3,在她的身上,人的属性被埋没,只留下低级本能的动物性,她无知愚昧,不会抱怨,逆来顺受,是另一个阿Q。金枝和王婆与麻面婆相比,可以算是觉醒的人。金枝在经历婚姻不幸、品尝世情冷暖之后,由最初的蒙昧,发展至恨男人,最后恨中国人,不能不说,她对于世界有了先进的认识。王婆是具有抗争精神的女性,在得知丈夫组织“镰刀会”后,她教丈夫练枪,取得了与丈夫同等的地位,让他也很佩服。得知儿子死后,刚烈服毒自尽,自杀未遂后,更加按自己的性子生活,之后,鼓励女儿为哥哥报仇,自己也加入了抗战的队伍。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反映了萧红对于女性的殷切希望,也继承了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主题。
《呼兰河传》中大泥坑子酿成很多惨剧,人们却不思修缮;面对摇晃的屋子,住户反而无视生命;王寡妇的悲剧成为人们的谈资;小团圆媳妇的惨状彻底暴露在民众眼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被旧习惯、旧观念所束缚,缺乏反抗的能力,丧失了人的主体性。这些惨剧的发生,都是由于民众丧失自由意识、没有作为“人”的自觉,因而无意识地参与了一场场“谋杀”,自己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三)深重的寂寞情怀
萧红一生无爱、无家、无根,加上性格上的任性而为,始终不被人理解。茅盾曾有这样的评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7]萧红经历了多重的寂寞,最后殒没于香港浅水湾。“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现在的我们已无法还原她的苦难,姑且品评作品这一“达芬奇密码”,窥一斑而知全貌。
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呼兰河传》的诞生便是萧红寂寞童年的写照。这部作品写于萧红最寂寞、最痛苦的时期:鲁迅先生去世、与萧军的感情破裂、与端木蕻良的错误结合,再加上疾病的折磨,使她渴望觅得一个安身之所。但逃到香港后,那里却变成了她的香消玉殒之地。在《呼兰河传》中,她极力回忆自己的故乡,渴望在故园中找到一方净土,可当她落笔时,家乡也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大安慰:祖母有洁癖,“我”故意弄脏她的窗纸,结果被针扎;“我”顶着水缸玩,被父亲踹了一脚;继母对“我”恶语相向;能给“我”温暖的只有慈爱的祖父,可是后来祖父也死了,把人间的温暖与爱全都带走了。
寂寞是萧红作品的主色调,《商市街》是青年萧红的寂寞写照。《商市街》主要以她在青岛和萧军的生活经历为内容,写二人在艰难中相濡以沫的生活。可萧红还是寂寞的,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使他只把她当作需要保护的孩子,萧红在家庭中只是他的出气包、佣人。萧红自己也想找一个工作,但她晚出未归使萧军大发脾气,大喊“有了职业,连爱人也不要了”[8],最后广告员的梦碎了,萧红只能蜗居家中,百无聊赖。萧军要求萧红这样做,可他自己也没有做到,在《他的上唇挂霜了》中,萧红这样写道“好像很久捉不到的鸟儿,捉到又飞了”[9],萧军留给她的只有背影,每每让萧红生出自己是“完全停止的机器”的想法。幸而写作可以缓解她的寂寞,但即使是这样,萧红的作品也没得到萧军的肯定,个中滋味只有萧红自己知道罢了。
四、结语
作为一个时代新女性,萧红不仅在人生道路上走出了不同于常人的轨迹,在文学上也标新立异,在30年代的文坛算是旁逸斜出的一支。但无论其行为表现如何乖张另类,性格上有任性、不成熟等类似缺陷,可以确信的是,她始终怀着对文学无限热爱的赤子之心,从她身患重病仍笔耕不辍就可以看出,而这足以让人肃然起敬。真正理解了萧红,才能看懂她笔下的悲与苦、爱与恨、无奈与坚持、倔强与脆弱……
著名学者葛浩文说:“萧红有她的特殊性。作为一个新女性,她在中国当时的社会中寻求独立的人格,要遇到外部的压力和她自己内心的矛盾。”面对这些,她选择的方式是小说的散文化,这是其个人生命形式的转注式呈现。她用率真的儿童视角、亲切的语言表达、真实的自我书写,再现自己的心路历程。
出于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初衷,她选择了自由地表达。她不愿讨好读者,选择了个人话语;为了追求自由,一生都在流浪;并且接受鲁迅先生的指引,倔强地反抗压迫。这种自由意识难能可贵,但终因没有做好万全准备,加上萧红过分局限于个体生命体验,很难被人理解。另外,她选择的儿童视角,相当于怀旧,是她的一个灵魂向度,也是她从现实出走的一个路径,是难以融入社会的任性、天真。可以认定萧红的心理本质是基于童心的自由意识,体现在文本上则是在她的主要作品中,围绕着童年记忆、祖父在世时候的那个呼兰小城是她的原点。这个空间性的想象方式投射在作品中,就是她“散文化”的全部秘密。也就是说,她并非是一个自觉的文体追求者,而是在做率真的自我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