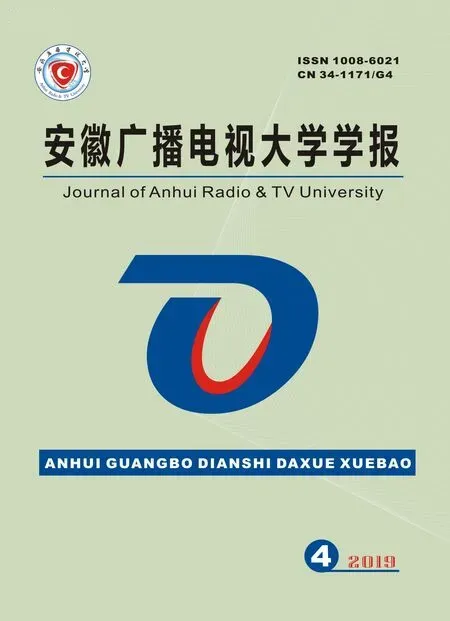《夏伯阳与虚空》的经典性与大众性
2019-03-15郑晓婷
郑晓婷
(首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9)
一、佩列文文学创作30年
1989年,27岁(1)关于佩列文的出生年份,另有1960和1967两个说法,在此以维基百科上的1962年为准。的维克多·佩列文发表处女作《伊格纳特魔法师和人们》(Колдун Игнат и люди),直至最新力作《通往富士山的秘密风光》(Тайные виды на гору Фудзи,2018),30年来,作家佩列文几乎从未间断过自己的文学创作,为世界各地的读者奉上作品逾50种。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年轻的佩列文就被公认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30岁一代人中最著名、最神秘的作家”,他的成功就被冠以“佩列文现象”“佩列文问题”“佩列文时代”,作家本人和他的作品也几乎成为 “культовый писатель”(极受公众喜爱的作家) “бестселлер”(畅销书)的近义词。与他的名气相当的是他的神秘性,在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原野上,佩列文绝对是最神秘的幻影。在信息化的当下,佩列文鲜与外界接触,仅以几次网上论坛和电话采访为主,最新的访谈也停留在2010年。当笔者以“佩列文文学创作30周年”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时,网络上一片寂寥。佩列文真的完全消失在了作品背后?还是曾经的轰动已成为过眼云烟?笔者更愿意相信,佩列文的作品真正成了进入文学史的经典,他不再依靠任何包装和效应博取关注。
年轻、神秘的佩列文,他的创作轨迹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生发惊人的一致。在经历了形成和确立两个阶段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取得“合法化”地位,年轻的后现代主义在文学风格多元化的“后”苏联时期成为最受瞩目的思潮和流派。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名义上是从西方引进的,实质上是十足的俄罗斯现象,文学批评家亚·格尼斯甚至提出公式“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先锋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佩列文从一开始就被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好像他本人及其思想是西方的舶来品,像可口可乐一样,然而,时间最终证明佩列文是一个纯粹的俄罗斯小说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经典作家兼思想家,类似于托尔斯泰或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2]。佩列文早已预见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本质无异于“吞食死去文化的肉”,在短暂的喧嚣之后,回归理性的人们意识到后现代主义相对于本国社会是异质的,出现了“俄罗斯文学的后现代主义刚刚赢得合法身份,人们就开始兴高采烈地为它送葬了”这一奇特历史现象。无论佩列文本人如何戏仿俄罗斯文学经典,他的血液里流淌的还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蓝色血液。
佩列文的长篇小说《夏伯阳与虚空》诞生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由“热”转“冷”的时期,但它并未被后现代主义的泡沫掩盖,反而助推佩列文成为真正的“经典作家”。这部小说一经推出便受到广泛关注,1997年佩列文凭借该小说获“朝圣者奖”(премия Странник-97),2004年在我国出版中文译本,2015年被美国导演托尼·彭伯顿改编成电影《佛的小指》。小说《夏伯阳与虚空》拥有众多标签。佩列文自豪地称这部小说是“世界文学中第一部发生在绝对虚空中的作品”,评论家亚·格尼斯称它是“俄罗斯第一部佛教—禅宗(2)禅宗是佛教家教派之一,主张顿悟。小说”[3](дзэн-будд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和“朝圣小说(роман-паломничество)。通读完这部小说,读者也很难判断小说究竟发生在哪一时空领域,结尾处主人公奔向的内蒙古究竟是哪里,读者按照惯用思维是无法把握小说主旨的。
二、精巧·永恒·传统——《夏伯阳与虚空》的经典性
1997年,谢·科尔涅夫第一次将佩列文称为“经典的后现代主义者”。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和叶夫盖尼·涅克拉索夫就佩列文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给出了很高评价,“他自己就是个流派和思潮,犹如谢拉皮翁兄弟和绿灯社”[4]。如此,就“佩列文是否属于经典?”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评论家和作家们就给出了较一致的肯定意见。而《夏伯阳与虚空》这部引起很大反响的长篇小说,就是奠定佩列文文学影响力的重要作品。如同小说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完全发生在虚空之中的小说”,“虚空”不仅是小说主人公之一,还是佛教教义所阐述的“涅槃静寂”状态,因此,亚·格尼斯称小说是“俄罗斯第一部禅宗小说”。
这部小说的经典性体现在其形式、内容、思想和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上。首先,该小说在形式上是设计精巧、非常完满的“圆形”结构。小说的情节是铺陈于两个时空,单章内容的背景是1918-1919年红军部队,圣彼得堡颓废派诗人彼得·虚空偶遇苏联红军指挥官夏伯阳并成为后者的政委,夏伯阳帮助虚空认识到世界的虚幻性,其中还涉及虚空爱慕的女机枪手安娜、夏伯阳的副官科托夫斯基、伺机夺权的富尔曼诺夫;小说双章的背景是苏联解体后(1991-1992年)莫斯科郊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虚空与“就是马利亚”(3)本文译文均引自郑体武所译的《夏伯阳与虚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谢尔久克、沃洛金等病友接受医生铁木尔·铁木罗维奇的针对“伪人格分裂”的集体治疗。所谓“伪人格”就是病人无法接受苏联解体语境下的自身,例如,马利亚的性别倒错、谢尔久克“酒狂状态下的自杀及漫游综合征”、沃洛金对极乐世界的追求,其中虚空和谢尔久克倾向于东方的“出世”哲学——佛教,就是马利亚和沃洛金倾向于西方的“入世”哲学,这便是对俄罗斯时而与西方、时而与东方炼金术式的联姻的隐喻。看似两条完全平行的时空主线,在虚空出院之后交织在一起。单章的结尾是虚空在安娜、夏伯阳之后跳入“乌拉尔”(俄文“绝对之爱的相对之河”的首字母缩写形式),双章的结尾是虚空自象征着惶恐不安、物欲横流、毫无出路的世界的精神病院逃出,奔向象征着虚空的内蒙古,所以这“一入一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主人公真正进入虚空。小说的两条时空主线和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最终完全重叠,形成一个圆,圆的内部是虚空。不同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荒诞不经,佩列文总能在当代文学语境中以其朴实形式和纯净文体令人惊奇。
其次,从思想内容上来说,佩列文在其小说中提出了比永恒更永恒的问题。如果说传统的俄罗斯文学善于从人的精神和道德层面提问,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么佩列文已经将问题从人道主义的层面提升到了存在层面,而且问题的答案不是单一的。在《夏伯阳与虚空》中,佩列文不仅借助佛教教义“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缘起论教义回答了关于人生的本原问题、人的认识能力的问题、世界的本体论问题和关于彼岸世界的问题。还辅之以西方思想经典,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世界万物都是对某一个完美理念的模仿,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众多理论。所有这些哲学思想都是服务于一点的,即向主人公和读者论证“世界是幻象”“除了我的意识一切都不存在”。这是两位主人公反复对话的思想核心。评论者一致认为佩列文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形而上学特征,他的作品是引人入胜的,恰到好处的哲学穿插与悬念迭起的平缓叙述保持着平衡。
最后,佩列文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艺术的继承者。按照小说的叙述顺序,佩列文先后提到数十位俄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艺术家,19世纪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捏克拉索夫、纳德松、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布宁、夏里亚宾,20世纪的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勃留索夫、阿·托尔斯泰、纳博科夫、巴尔蒙特、索洛古勃、索罗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梅烈日可夫斯基,大卫·布尔柳克、布留洛夫,甚至还有中世纪的圣像画家鲁布廖夫。前面已经提到的两条时空主线让我们想到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佩列文也曾坦言自己很喜欢这部作品,曾被深深打动。佩列文有选择地借鉴了布尔加科夫的叙述原则,也将自己的主人公置于不同的时空,但佩列文更进一步,他的主人公不仅可以在两个时空维度自由穿梭,在小说的第七章佩列文还制造了第三时空,主人公虚空在黑男爵荣格伦的带领下进入阴间——瓦尔哈拉宫。佩列文将主人公置于三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再次证明“世界即幻象”,不同的世界只是我们意识的反应。除了结构上的模仿,在人物形象上我们也可以找到佩列文对布尔加科夫的继承,例如颓废派诗人彼得·虚空就是苦苦求索的大师,黑男爵荣格伦就是无所不能的魔王沃兰德,佛陀夏伯阳与耶稣同样充当精神导师的角色。
1918-1919年是小说的叙事时空之一,所以佩列文很自然地将诗人虚空放入20世纪初白银时代的背景之下,虚空成为众多诗人的同时代人。佩列文在小说中援引的诗歌深受帕斯捷尔纳克和勃洛克的影响,在音节、韵律和风格上能够发现佩列文对二人的模仿。例如,勃洛克的诗剧《滑稽草台戏》和散文《俄罗斯花花公子》中的主人公具有双重人格,他们关注祖国和人的命运、揭露现实的空虚,同时具有佛教信徒和苏联红军政委双重身份的虚空与他们是一致的。
三、杂食·游戏·解构——《夏伯阳与虚空》的大众性
佩列文的文学创作始于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如火如荼的时期。德里达提出“世界即文本”的公式,从而一反亚里士多德以来“文本如世界”的文学规律和法则。在世界这个大的文本海洋里,作家可以任意撷取他所需要的文本,文学与现实的界限就变得模糊起来。鲁德涅夫在《二十世纪文化辞典》里把“否定真实性”当作后现代主义一个“基本原则”,“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这样的流派,它公开承认文本不反映现实,而是创造新的现实,甚至更确切地说,创造许多互不依存的现实”[5]。后现代主义颠倒了文学创作“源”与“流”的关系,否定唯物主义观点。这便是佩列文在小说《夏伯阳与虚空》中表达的思想核心。
在佩列文那里,后现代主义永远都不是抽象的概念,甚至也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不存在,所以创作那样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如同吞食已死文化的肉。佩列文的读者包括中学生、老兵、扫院子的人、研究者等,其作品受众之庞杂、广博使其作品一度被冠以“地摊文学”(ло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的标签。
佩列文作品的“对应性”和“杂食性”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经典也具有大众性。所谓“对应性”就是作品映射当前社会政治状况。《夏伯阳与虚空》创作于1996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思索何去何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已不仅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思考中心,几乎成了决定每一个俄罗斯人命运的关键节点,精神病院中的四位病人就是很好的体现。
“杂食性”则体现在知识体系的庞杂,涉及领域十分宽泛,既包括严肃的政治话题、文学艺术、哲学探讨,也包括大众的娱乐消遣及多种形式。这从小说涉及的各色人物就可见一斑,前面已经提到佩列文在《夏伯阳与虚空》中提到了20多位俄国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另外还提及政治人物有列宁、捷尔任斯基、格·拉斯普京、亚历山大二世、伪德米特里二世、尼古拉二世等。而小说中涉及的外国作家、哲学家、艺术家更是五花八门,其中有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英国作家莎士比亚,英国画家约翰·康斯太布尔,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德国作家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奥地利诗人勒内·马利亚·里尔克,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英国哲学家休谟、贝克莱,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黑格尔、莱布尼茨、康德、叔本华、埃哈特、尼采,德国政治家伯恩斯坦,法国医学家、星占学家诺斯特拉达穆斯,瑞典哲学家斯维登堡,挪威作家汉默生,美国演员阿诺德·施瓦辛格,中国思想家老子等20多位。深谙东方文化的佩列文还虚构出一些人物,例如,作者以“庄周梦蝶”为蓝本,衍生出一个从事革命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庄杰梦见自己化身蝴蝶。让主人公之一的谢尔久克结识日本“平清盛集团公司”的川端织田,并在后者的影响下剖腹自杀。
在这部小说中,不同场合下饮料可分为波罗的海茶、家酿伏特加、波尔图葡萄酒、荷兰酒、日本米酒等,中国轿子、宝剑,日本和服、木屐、灯笼、匕首等独具异国风情的物件应有尽有,仿佛佩列文的小说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超市。这种被福柯称为“中国式的百科全书”系统是对西方古典的一般系统的瓦解和颠覆,能够映照出西方现代思想体系自身的局限。
小说《夏伯阳与虚空》的大众性还体现在多重解构上。一,对苏联意识形态、神话、文献、制度的解构(“精神病院”);二,对大众意识、思维定式的解构(“世界即幻象”“一切皆虚空”);三,对俄罗斯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的解构(颠覆“永恒女性”——“所有女人都是母狗”[6]);四,对人和历史的解构(“历史也不存在”)。佩列文把“与虚空的独特对话”作为自己最主要的艺术手法,创造出尘世(科托夫斯基的)和佛教(夏伯阳的)两个世界模型,在如梦人生和时空转换中自由解构,利用梦境、毒品、游戏、笑话、大众传媒、虚拟世界等形式组织自己的文本结构,从而为吸引最广泛的读者受众创造基础。在说到小说的体裁界定时,佩列文更愿意将其称为“思绪遄飞”。
佩列文吸收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创造出具有“对应性”和“杂食性”的“大众文本”,艺术形式和内容的不确定性、多样性都达到最大化程度,为最广大读者受众所接受。
四、结语
“大众性”与“经典性”本是文学作品两种截然对立的文本风格,但在佩列文的长篇小说《夏伯阳与虚空》这里,两者不再泾渭分明。小说《夏伯阳与虚空》是作家与虚空对话的最典型的作品之一,其中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探究显示出佩列文延续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决心和追求。禅宗的唯识论、西方哲学思想的理念论、俄罗斯文学中的神秘主义都是构成《夏伯阳与虚空》形而上色彩的重要因子,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佩列文是某一宗教或哲学思想的信徒,如同作家所说,这些宗教和哲学思想只是作品的标签[7],真正引导人们认识自身、从纷繁的烦恼中解脱,或许才是作家的真正目的,作家心目中的“内蒙古”。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夏伯阳与虚空》是一部兼具经典与大众调性的小说,作家以独特的写作手法提出人类生存境遇的永恒思考,而读者可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大众性”解读,这或许是小说成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