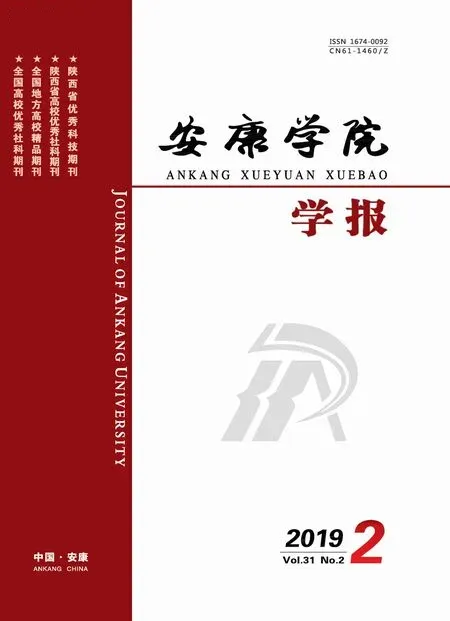文化资本视野下的爱情书写
——从《蜗居》看爱情中的资本消费
2019-03-15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爱情是一种以性为纽带的给予,它源于身体或者是性,但是又不被性和身体本身所控制。它是一种给予,那个给予本身而并非给予者自身,所以爱情是一种平等、自主、自由的相互成为对象的爱情游戏。”[1]然而,这种爱情观念在现代社会似乎不再完全适用,无论人们先天拥有的条件和资源是否相同,在爱情来临后,他们的婚姻必定伴随着不可避免的资本交换和消费等活动。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两个爱情个体的结合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平等、自主、自由,否则我们在平日里就不会屡屡听到有关婚姻财产诉讼的案件和新闻。从本质上说,阶级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条件上的不均等都是必然存在的,这种情况会激发人性潜在的善与恶,对爱情的走向也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同马克思提道:“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因为货币所交换的不是特定的性质,不是特定的事物或特定的人的本质力量,而是人的、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所以,从货币持有者的观点看来,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或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2]
一、当下社会中的资本消费式爱情
当代关于现实生活的话语主要体现的是个人强烈的消费欲望与有限的经济能力之间的落差,在爱情中的表现即在婚姻形成之前的消费欲望和经济能力的权衡。无论是资本充裕的中产阶级还是传统概念下的名门富豪,都逃不过资本的裹挟。他们一方面利用已有资本获取所需,如文化资本。布迪厄说:“文化资本是指包含了可以赋予权力和地位的累积文化知识的一种社会关系。”[3]这一阶层的人们已经在社会中拥有了基本的权力和特殊的地位,并且以文化为基本能力,他们日常的获得和输出几乎都是以文化为基础,所以文化资本在这一阶级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也难逃被资本利用的命运,这是资本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当然他们的爱情和婚姻也必定掺杂了资本的性质。资本的消费会促进爱情的发展,同时也会不同程度对它产生阻碍。物质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享受在某些层面上可以相互转化,有时候精神上的满足可以弥补物质上的匮乏。作为爱情个体,当我们被爱情包围的时候,可以忽视资本条件,因为爱情的欲望超越了物质的欲望。但是,当情感的欲望消退时,物质的欲望便会卷土重来。我们可以在一无所有时遇到爱情,但很难在一无所有时形成婚姻关系。通常赞成裸婚的爱情个体大都能够很好地保障自己的生活,因为当对方不再为你负责的时候你仍有足够的能力保障自己,这就是资本的力量。
现如今,许多人在效仿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咖啡馆、西餐厅、健身房这些名词已经不仅仅是它们本身的意义,而是作为资本的标志和文化的符号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现象的出现代表了人们对资本的崇拜和向往。中产阶级的爱情或者婚姻相比无产阶级来说有更大的自由度,爱情双方受到较少的物质条件制约,对资本迷恋和需求更少,很难在双方关系中产生经济上的依赖,他们作为更加独立的个体在爱情中更富有自主性——没有了资本和物质的制约,感情中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交流,物质条件于婚姻而言不再无比重要。而缺少资本支撑的婚姻或者是双方的资本不均衡时,爱情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婚姻中除了情感的寄托,还有现实相切的不同程度的资本牵连,这就会使婚姻有名无实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一旦爱情个体之间的依附关系发生破裂,解除婚姻关系就会引起一系列与情感无任何关系的经济纠葛,而结果往往让双方两败俱伤。事实上,这种结果早已潜伏在婚姻开始时,因为以获取资本为目的的爱情很难脱离资本对其的影响。如今离婚率的居高不下或多或少都与爱情双方之间的利益有关,资本可以产生爱情也可以消融爱情,精神的力量有时比物质强大百倍、坚不可摧,而有时又不堪一击、轻触即破,爱情与资本的关系在物质化的社会中变得愈加复杂。虽然关于爱情是否已沦为资本社会中一个庸俗空洞的符号的问题依旧值得商榷,但是爱情已经无法脱离资本的控制而单独存在,反而如同鱼水般互相依赖、互相制约[4]。
二、文学作品中的资本消费式爱情
消费时代的来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大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但值得注意的是,物质的富足并不等于人们的精神层次也已经进入到更高的境界。在资本聚集的发达城市和地区,贫富差距异常显著,拥有巨大资本的少数社会群体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导致数量庞大的普通大众在共享资源时变得捉襟见肘,原本就分配不均的资源变得更加失衡。这种情况使底层大众的竞争愈加激烈,很多普通人在被淘汰的边缘挣扎。小说《蜗居》的出版以及同名电视剧的播出引发了奋斗在一线城市的普通人的强烈共鸣。除了生活中的巨大压力无处排解之外,工作的回报也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这就加剧了一些新的社会现象在物质社会的产生。旧的生活形式不能完全满足丰富的物质条件和消费资本,新的生活方式顺势而出,这些新事物使得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逐渐发生变化。各种资本的消费都在吸引着人们的注意,物质获得不断地在没有满足和暂时满足之间循环,从而导致人们欲壑难填。人们对商品的渴望不再是以使用为目的,而是欲望的扩充。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在迅速占有后会立即对这些商品失去兴趣,人们追逐的目标永远没有终点。
《蜗居》中展现的各个人物形象都在物质主宰的消费时代中彷徨失措,走走停停,一路寻找、一路失去[5]。海藻和海萍都属于社会底层大众,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毕业生,但是要想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立足,难于上青天。海萍毕业后在一家外企工作,但收入完全不能满足生活支出。由于收入微薄,只能住在环境恶劣的廉价出租屋,左邻右舍无不是斤斤计较的市井小民,长时间生活在那种环境中使得他们变得市侩,这与当初的梦想南辕北辙。她原本可以回到家乡安安稳稳度过自己的一生,虽不会大富大贵,但可以拥有一个温馨的家庭,过着安逸的生活。然而作为有学识有追求的新青年,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和现代文明的洗礼,面对发达城市丰裕的物质文明生活的吸引,当然会渴望成为这里的一分子,也希望可以享受这里更高层次的生活。因此,她毅然选择了留在上海,同无数与她一样的人一起打拼。他们有着同样的追求和理想,并且执着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奋斗出脑海中描绘过的样子。她付出了所有她能付出的,当现实离当初的样子越来越远时,她开始疑惑和失望,并且明白了上海这种不现实的城市,注定不属于穷人。最后她不得不通过妹妹海藻,凭借市委秘书宋思明的帮助才得以安身立命,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在这过程中所有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次,不知道她是否还会如此执着。在这个故事中,海藻与宋思明之间的这段感情所带有的资本价值解决了所有因资本而出现的问题[6]。这段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感情无论其初衷和结果如何,都是以欲望的满足和资本的诱惑为开端。如果海藻和宋思明之间可以称得上是爱情的话,那海藻与前男友小贝之间的爱情应该更加纯粹。而这段感情的最终瓦解正是因为资本的需求与资本的供给不再平衡,小贝无法满足海藻在物质上逐渐上升的需求,导致这段感情最终破裂,其实他们早就应该明白无关资本的爱情是根本无法存在的。海萍虽然努力了,但她最终明白,努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她也应该知道自己与宋思明之间,如果没有海藻作为纽带,是根本没有结识的机会。他们身处两个不同阶层,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集。她会一直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根本不会有人关心她的处境,因为她所代表的群体是这个社会最庞大的组成部分,即使必不可少却也无关紧要。
杨晓莲在《消费时代与建构现代新感性》中对“消费时代”进行了阐述。她认为,所谓“消费时代”,是指消费主导生产、生产围绕消费的时代,商品生产者不得不揣摩消费者心理而不断对商品进行创新的时代[7]。现在人们更多的是追求消费本身的社会意义,比如消费行为的超前观念,即无论是否有足够的购买力,都要用各种手段和方式满足自己过度的欲望,无论手段是否正当、方式是否合理。这种不健康的观念就是《蜗居》中为我们建构的一个同时具有丰富物质条件和过分消费欲望的商品消费社会,它真实地还原了当今社会的某些现实状态。不仅展示了琳琅满目的名牌服饰、豪华汽车和奢侈住宅,还表现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平民大众的生活不易、举步维艰[8]。作品用这种方式将大众带入真实的环境中,使观众感同身受。这些其实都是现实的差距和欲望在满足和不满足间不断变化引起的社会现实问题,欲望的满足就是物质的满足,同时也是资本的积累。因此,在消费时代,任何欲望都可以通过消费理念而转化,在绝对的物质资本面前,爱情可以被消解,因为物质欲望的满足感会远远超过爱情所带来的愉悦。这已经与爱情在精神领域所体现的真善美和情感的独特表现形式背道而驰,因为社会性质已悄然改变。
三、消费时代的社会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相较于原来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爱情观在不同阶级、性别、文化背景下的体现越来越多样和复杂。同时,信息传递更加迅猛,西方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日渐被大家接受和吸纳,爱情的消费理念尤其在80、90后甚至更年轻一代人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个体的表现逐渐变成群体的展现。资本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无须赘述,它以无比迅猛的速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可以拿来消费的已经不仅仅是金钱资本,还有文化资本、劳动资本、身体资本等各种资本的表现形式。多样的资本表现形式决定了多样的资本消费方式,这些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程度和多样性程度所决定的。婚姻作为爱情的最终表现形式被视为一种对爱情的保障,但现实却让人们对这种“保障”提出了巨大的质疑,人们对婚姻的诚信度越来越低,只剩下白纸黑字和精神上自欺欺人的虚假寄托。
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资本的发展速度,其中娱乐产业的资本味道尤其浓重。从理论上讲,多大的积累和投入就会换来多大的回报。作为娱乐产业中的主角,偶像明星本身就是最大的资本所有者,爱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时被赋予了比普通人群更大的资本价值。其实爱情本身并不被关注,只有当“爱情”成为社会话题时才可以引起大众的关注,或者说只有当爱情被拿来消费时才会变得有价值。相反,普通大众的爱情根本无人关心,因为它并不会产生可以创造资本价值的话题。资本的产生并不仅仅局限于爱情的初始阶段,它存在于爱情的整个发展过程,包括婚礼的形式、婚后夫妻相处之道以及下一代的出生等等,只要发生对象是具有“流量”的偶像明星,就足以产生富有资本的话题性。然而,尽管作为资本所有者,明星并不是这场资本游戏中获益最大的参与者,最大的获益者永远都是资本操纵者。爱情在资本市场变成了获取资本的工具,对于现在拥有更多资本的人来说,无论是商业巨贾还是中产阶级,他们爱情观念中的消费意味日渐加重。资本的消费活动几乎伴随着他们全部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用工作中资本的消费模式来解决现实生活问题已经变成他们的惯性思维[9]。在这种爱情体系中,女性绝大多数成为被消费者,资本的消费关系导致了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人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10]
在人性被物质化、幸福被具体化、理想被现实化、爱情被货币化的当今社会,马克思的交换与消费理论会更加详尽地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否接受这种理论和方式,精神物质化后,物质的交换与消费一定会越来越多地被运用。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性质不断地发生微小而影响巨大的转变,现代社会更多的是建立在消费理念的基础上,物质与精神消费无处不在,消费主义也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在飞速发展的今天,更多事物会被替代,生活方式也正在改变,我们必须用更加积极和包容的态度去面对日新月异的多元化社会,资本交换和消费必定会更多地伴随我们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