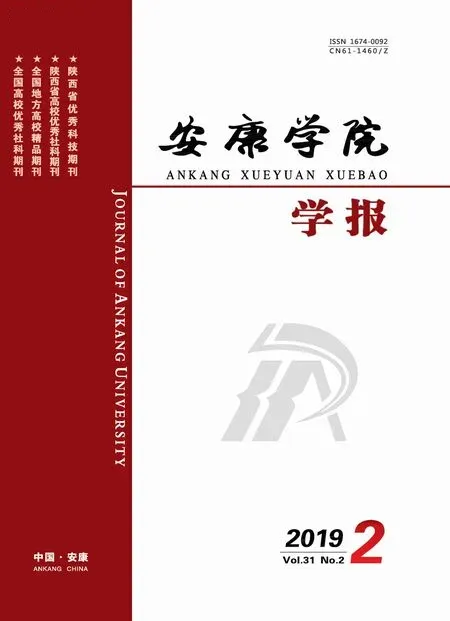“轻描淡写”的苦命人
——读贾平凹的小说《带灯》
2019-03-15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贾平凹的作品总是能够探触到人们生活最真实的一面,特别是对底层农民生活的描写。然而,人生百态,一生一死,都逃不过欲望针尖。生命演绎最真最细处往往是在最底层的生计者,就像自然界的蚂蚁、蜘蛛、蝉、蒲公英和萤火虫,以及那泥土里再普通不过的小花小草。贾平凹的《带灯》是一部关于描写秦岭山区乡土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以一位力量弱小的女性为主角,刻画出了樱镇上最鸡零狗碎、最藏污纳垢,也是最为真实的农民日常生活,映射出了中国乡土农民生存状态中的一些问题。
关于《带灯》,许多论者将它视为一部零时差创作的“问题”小说。主人公带灯被视为是拯救樱镇农民的一位伟大、崇高的女性形象,或者说是菩萨,是佛祖,是樱镇人的希望。而笔者认为带灯这个人物也是樱镇村民们同一群像中的一员,他们都是无法改变自己悲苦命运的弱者。从这个角度才能真正了解这部小说呈现出的最本质和最本真的农民生存境况。在叙事艺术方面,黑框小标题、短信体引人注目,因为这样的叙事文体是贾平凹之前的创作中不曾出现的。有论者把它称为散文化小说、笔记体小说,它像古代传统的章回体小说,更具随笔的味道,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加入与延续”[1]。对于叙事形式的变化,贾平凹本人也自称是受《旧约》的启发,有意寻求经典化[2]。那么贾平凹为什么要努力寻求小说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呢?这种改变在《带灯》这部小说中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除了作者提到的“怕读者读久了心烦,必须不停分小节,让读者有个空间”[3]以及受《旧约》启发之外,还有《带灯》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更重要的本体性因素。
一
小说《带灯》借樱镇镇政府的一个特殊部门——综治办为窗口,向读者展示了樱镇村民的生活。综治办就像树的枝干,樱镇农民便如树枝上的叶子,一片片散开来呈现他们生活的百态。带灯是综治办的主任,自然也就成为小说叙事的焦点,成为展现农民本真生活的一把钥匙。评论家吴义勤认为,将带灯这个人物作为“以个人的肩膀,以个人的身躯拯救她的伙伴们,去帮助那些底层的弱势群体,那其实夸大了她的能力……我更愿意把她仅仅看作一个特殊的个体,这个个体最后也被命运压垮了,成了一个疯子”[4]。笔者认为带灯这位综治办主任与千千万万农民一样,他们身上映射出的更多的是对命运的囚禁和身不由己,而不是救世的菩萨和试图改变樱镇人的希望之灯。
“小说中的人物如同一个挂衣架,有助于小说家十分方便地将各种事物‘挂’上去,从而让我们了解到一个社会的时代风尚或一个地域的民俗风情。”[5]155带灯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作者没有专注于告诉读者这位女主人公的外貌、性格,而是通过她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世界,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并通过人物活动对樱镇人民生存状态进行全方位的展示。带灯毕业于农校并且主动要求分配到基层工作,她的善良和聪慧使她保持着清醒,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为贫苦贫知的农民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最后她得了夜游症,分不清现实和梦幻,但她所关心的仍然是农民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带灯不习惯镇政府人的做派,“越来越要求着去下乡”[6]15,她在每个村都结识有老伙计。带灯有心向镇街广仁堂的陈大夫学习号脉配药方,下乡时也顺带给山村里人看病。贾平凹笔下的带灯始终拥有一颗悲悯之心,也正是因为她的工作性质,让她更多地了解山区村民的真实境况,作为一个女人的爱与善,就像小说中写的“咱们还是要善,善对那些可怜的农民,善对那些可恶的上访者,善或许得不到回报,但可以找到安慰”[6]208。上访是小说中的一部分,也是综治办抓的主要任务。王后生是樱镇有名的上访者,他不但为自己上访,还替那些在大煤矿打工得病的人上访,甚至写了樱镇引进大工厂污染环境的上访材料,四处寻人联合签名上告,被镇政府的几个干事凶残地暴打,最终妥协。王随风连年上访,上访上得成了神经质,跑到县政府大门口喝农药,“村长一脚踢在王随风的手上,手背上蹭开了一块皮,手松了,几个人就抬猪一样”[6]79,连夜将王随风抓了回去,而带灯听说她男人生病,便叫上陈大夫一同去看她男人。带灯在综治办工作,每天接触的人都是些不讲理的人,调解的事也是些难缠的事,但她说:“我有时说话直了对方是泼皮无赖让我无法忍受,但我总看到他家人或亲人有闪光人性之处,让我有心退让”[6]170。
带灯看到了农民的可恨之处,他们为一丝一己的好处不饶人,也看到了他们的卑微、可怜,更了解了他们本性中善良和温暖的一面。带灯把自己当作乡下人的亲人,每当蔬菜、山果成熟的季节一到,就会有村里的老伙计打电话或让人捎话给她:“樱桃下来了来吃樱桃呀”“新麦下来了来吃捞面”“再烙个囫囵子呀”[6]160。有的专门挖了老山药送来,还有的特意留了大红柿子、五味子让她吃。带灯下乡去村子里解决抽水机的问题,在村口被告状人拦住了路,双方吵过了之后,告状人却把带灯和竹子送到了河边才离开,以致带灯并没有觉得受委屈,而是反过来对竹子说:“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像风吹着田地一样,人气还是一股梢地向着正经一边的”[6]151。作者塑造的农民群像中,带灯似乎一直是那个永远清醒的人,对待山里的这些可怜人永远是菩萨心肠,怀有一颗怜悯之心。与镇政府的其他人不同,带灯能真正与农民融在一起。她始终在用真心和她仅有的便利帮助他们,像一个举着火把的领头者在漆黑的森林中带领这些苦命人找寻些许光明。但这并不能说明带灯的崇高、伟大,是菩萨、是佛样的降灵,因为她同这里的人一样,属于这个群像的一分子。他们都是苦命人,都在为自身的命运争取着抗争着,只不过带灯在这个群像中是唯一更加清醒的人,对他们是满腹的同情与怜悯,她尽自己最大努力来帮助这些同她一样的苦命人、边缘人。
此外,从小说里的“闲笔”中也可以发现作者追求的是一种更为普世性的东西,凸显的是“乡村世界的日常生存样态”[7]。小说中展现更多的是生命存在的形态,农民有着种庄稼的自由,自食其力、衣食饱暖,但正是农民与土地的相依,使他们与不可抗拒的自然世界有着独特的关系和情感,而带灯同山里的农民一样,都有一种孤苦、无依傍的归宿感。
萧乾认为自然描写是“写作目的之一个”[8],它会使小说里的“文字不再是呆板的铺陈。色在舞,形在舞,山水不仅是背景,是氛围,而且成了故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联着角色的性格,关联着角色的命运”[8]。通观《带灯》这部小说,贾平凹书写的自然之生灵,如樱镇家家户户的农民,他们都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与土地里种的庄稼一样靠着天意吃饭、生存。小说中“樱镇是县上的后花园,是秦岭里的小西藏”[6]144,是秦岭三大驿站之一,这里“空气好、水质好、风光好”[6]144,带灯和竹子下乡累了就喜欢躺在山坡上睡觉,“竹子也常想,如果带灯是山上的树呀草呀,那她是树和草之间跑动的什么小兽”[6]98。作品中自然性叙事意蕴浓厚,众多类似自然意象出现在小说中形成了一个意义的张力场,不仅展示了秦岭大地的自然风韵,也增添了小说叙事的自然美与诗性美,蕴藏着叙事主体对秦岭及秦岭之地山民的丰富情感。尤其是在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中经常提到自己在山上、野外看到的景物,如“蜜蜂嗡嗡嗡地响,小鸟在吵,沟涧上一位说话只是半语的农民在垒石畔不时地胡喝两声,像林子里偶然的怪鸟的直叫”[6]85;“两边的山狭窄得伸手可及,山的顶上是一片晴天,清爽的水有情有义地留过我,一朵蒲公英悄然飞来,而鱼儿游过了青蛙产下的那一摊卵后又钻进了野芹的水草丛中”[6]124。镇政府大院不离不弃的白毛狗,樱镇人最不缺的虱子,带灯的草药和她关心的人面蜘蛛,总是把自己看作山上的一株草、一只鸟儿、一只蝉儿、一颗被遗漏的核桃。作者有意给他所描绘的大自然的动物和植物披上一层凄苦、悲凉的外衣,然后借带灯之口说出。奇妙的是,“带灯”自身也是一只萤火虫,“火焰向上,泪流向下”[6]350,还有一直陪在带灯身边的“竹子”,不都是作者寄予人物以大自然的寓意吗?这些人物的命运如同小说中的植物、动物都挣脱不了大自然以强食弱的生长规律。作者给予她们“天地间的真精神”[9],有着善良、美好的向往和寄托,也有暂时无法摆脱的困境,对于山村农民的生活境况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改善,农民生活有了明显变化,但是农民尤其是山区生活的人们与土地、与天气的关系仍然是紧密相连的。小说中不断出现的“天气预报”,是带灯每天晚上不会错过的电视节目,她说看天气预报就是在看天意。冰雹算盘珠子一样大,秋后要收获的苞谷全没了指望,只能重新打算,再撒一次粪,再耕一次地,种上别的种子。遇上天气大旱,大旱过后就是洪灾,泥沙覆盖了农田,冲毁了河堤,老树连根倒。有的村民见电线杆被冲倒,去捡电线,被电线打死。有的躲大水跑上了山,又想起墙缝里的三百元钱,跑回去拿钱,没被洪水冲着,却被雷撵着劈了。作者在此写出了一种普遍的人世感和生存法则,不仅是山里农民,所有人面对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威力时,都显得那么弱小。
“蚂蚁和人一样为了生计在劳作着”[6]121,山里的农民为了利益争斗得“你死我活”。樱镇建大工厂,给那些需要搬迁的农户赔偿,人们得到消息后便连夜疯狂地栽树,甚至出现了许多没有根的树;因为灶土,巩老栓与王老五吵架躺在巷口不起来;张膏药为儿子坟前的几棵树与儿媳吵架、上访,要挟带灯要政府赔偿;元家薛家为圈河滩建沙场打架出了人命……山里的人们不缺乏善良和聪明,也不乏丑陋与险恶,黑乎乎的土地里会生长出各样颜色的花草。贾平凹对陕南山村人永远怀着一颗悲悯之心,通过小说中的自然叙事与农民生活常态的叙事,写尽了山区农民生活的真实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平等的自然价值观念。带灯在镇政府的身不由己,对农民的怜悯、无奈以及山里农民的身不由己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悲悯的意味。但她还是说:“农村人真正可怜,但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在农村,因为在农村能活出人性味,像我捂酱豆很有味道但具体每个豆子并不好。”[6]184作者以主人公带灯这个具有诗性的女性人物和樱镇形形色色的农民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命运的悲剧感、不确定性以及“对于现实的一种无能为力的感伤”[4],这也是作者对人世间一切生命最真切的感悟。人像那些幼小动物、本草植物一样都是大自然的生灵,处在底层的农民与自然关系尤其紧密,面对生活的困境,他们表现出了最强劲的生命力量。由此,我们也可以读出作家自身的生命观和“一种异乎寻常的艺术表现功力”[7]。
二
自《带灯》出版以来,这部作品的写法备受关注,与之前的《秦腔》 《高兴》 《古炉》等小说有着不同的叙事方式和叙事风格。贾平凹说:“《秦腔》 《古炉》是那一种写法,《带灯》我却不想再那样写了,《带灯》是不适那种写法,我也得变变……你总能寻到一种适合你要写的内容的写法。”[6]361“创作之所以是创作,创是第一位的,作是第二位的,一切无定式,一切皆扑腾。”[10]那么,贾平凹力求在小说《带灯》中采取不一样的叙事手法的原因是什么?作家在寻求新的叙事方式的同时又潜藏着怎样的主体情感呢?
首先是小说中看似纷繁杂乱的黑框小标题。作者在不断地分小节,而且每节内容长短不定,上下节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中间常常穿插对生活、生命的感想等随笔。初读时像是作者进行的一次田野调查与随笔记录,整体显得很散乱、随意,“故事情节淡出,语言更为简化,一改小说经典的文本叙事,转而为散板漫流甚至闲聊式的生活言说”[11],轻描淡写,只是娓娓叙来。但这种充满散文化结构意味的叙事文体,正适合《带灯》所要表现的农民杂乱、纠纷不断的生活内容,恰恰能反映作品中乡下农民和带灯的现实生活环境。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由这一个个让人纷乱,没有头绪的鸡零狗碎的日子构成的。所以说,作品的叙事形式、叙事结构与它的叙事内容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而且会超越“具体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12],这也是小说结构本体力量的体现。文本中有小标题“樱镇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6]37,作者花费大量篇幅将这些问题一一详细地叙述了出来,如林坡纠纷、宅基侵占、道路修建补偿、霸占树木等矛盾,这些问题都牵扯着农民各家的切身利益。集市上买柴禾、王中茂家过喜事、陈小岔闹镇政府、谁又喝了农药等等,被单独列出的“县志里的祥异”[6]72更体现了农民的命运随着天气的阴晴转化而潮起潮落。常年上访无果的朱召财、王随风,可怜的杨二猫、十三个妇女,贫苦女人给自己的丈夫过生日、张膏药被烧死在家里、大矿区死人、老伙计的死、带灯的疯等等,作者有意将这些故事题材各自独立,分成或长或短的小篇幅,没有掺杂个人的情感,只是把底层人的现实生活状态一一展现出来。“所写的都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体悟的东西,它没有了那么多的抒情和优美,它拉拉杂杂,混混沌沌,有话则长,无话则止,看似全没技法,而骨子里还是蛮有尽数的”[13]。这一客观叙事的声音之中还夹杂着“人面蜘蛛”“当归”“观蚁”“埙”等某种具有隐喻意味的物象渗透于文本之间,有效地调节着小说表达的主题意义。作者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技法,用相对独立的小标题一一分解了故事情节的紧密度,客观地描绘出农村、农民、弱势群体的生存面貌,也让笔者想到了由刘震云小说《我不是潘金莲》改编的同名电影。小说是一部上访题材的作品,导演和编剧在将这部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同时添加了一些技巧的元素。当电影镜头向观众打开时,人们看到的只是屏幕中心明亮的一个被艺术化了的圆形小窗口,周围全是黑色。编剧和导演只是在给观众客观地展示一个农村妇女上访的过程,观众也只能透过屏幕中心的小窗口“偷窥”到一个农村妇女艰难而且没有成功的上访之路。镜头周围其他什么也没有,完全是黑色,但也正因为是黑色的,让观众有了想“偷窥”黑色部分的欲望和联想,它肯定是藏有与透明镜头下一样精彩的内容。美国小说学者塞米列昂说:“文体是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拨开生活的浓雾,为揭示其本质意义所做的努力。”[14]电影窗口的技巧正如小说形式一样都是对生活的客观叙事,“淡淡地来写,但是隐藏的是激烈的事情”[3]。《带灯》所表现的正是作者对秦岭山区农民真挚、深切的感情,流露的是作者对秦岭大地上生活的人们无限的关注与爱。
“为了表达作品的‘内容’我们寻找‘形式’,为了获取形式我们得求助于‘结构’,为了形式结构我们得讲究技巧,而为了掌握技巧我们最终得了解小说的读者。”[5]207贾平凹在小说《带灯》中采取了分裂的叙事技法,一是带灯的工作与樱镇农民的生活内容;一是带灯的精神世界,即她经常跑到河堤上读书和给元天亮写信。前者是客观冰冷地展示、叙事,后者是浓浓的散文化式浪漫抒情的语言。从文本和读者的角度出发,为避免读者阅读的枯燥无味,作者采取了相对平衡的策略,给读者留下了空白和思考,同时在审美方面也为小说增添了不少魅力。但一切技法都是为作品的题材内容和作家的主体思想情感服务的。作者以发短信的形式,又借带灯之口向读者展示了秦岭大地的自然美好,表达自己对农村、农民的一种亲切的情感。尤其是处在综治办这样的工作环境,带灯仍然能保持着安心读书、思考的习惯,不觉又使读者生发出对乡村自然风光的向往。短信的书写不仅是对带灯形象的一个补充,更与前文笔者所说的,作者赋予小说人物某种自然意蕴的含义相应和,可以说是贯穿整部小说创作的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手法。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中不仅有对樱镇山水风光、花草植物和野生小兽的赞叹,也饱含了对自身命运身不由己和对农民生活困境深深地哀怜与同情。带灯说:“冬天不是树叶不发,是天不由得,夏天不是树叶要绿,是身不由己。”[6]119“每次我都依依惜别地觉得自己觅到了出路,谁知道每次还是恍恍惚惚如困兽八面突围。”[6]202带灯也向元天亮诉说樱镇农民发生的或美好或龌龊的泼烦事,如某某媳妇不会生育遭人们讥讽,村民骂村干部做事不公平,也讲某家女人怎样给丈夫过生日,山坡上恢复了小庙,“方圆的苦命人都来磕头上香”[6]140,祈求苍天的护佑……这又是作者叙事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被孙郁称为《带灯》的“闲笔”,而“闲笔”里饱含着更多的温暖和真诚,“温润之美与包容之爱亦人间生态的一部分”[9],然而生命的脆弱也隐藏在这美好之中。小说这种双重结构的安排使作品有了很强的立体感和生命感,使评论者在解读其潜在意义时,更强烈地感受到作家寄予其中的一种命运的悲凉感。
总之,作者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乡村世界农民生活样态的画卷,凸显了乡土大地上生命存在的常态。他们的生命犹如土地里的庄稼、麦穗,受着大自然的恩露,徘徊在社会的底层和边缘。笔者认为这也是贾平凹写《带灯》要抵达的一个生命层次。写本文之时恰逢贾平凹新作《山本》出版,这又是一部秦岭山地史诗性的长篇著作,被称为“鬼才”的贾平凹又一次冲破了创作的“火山口”,“让天使和魔鬼再一次敲门”[6]362,让读者再一次领略秦岭大地的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