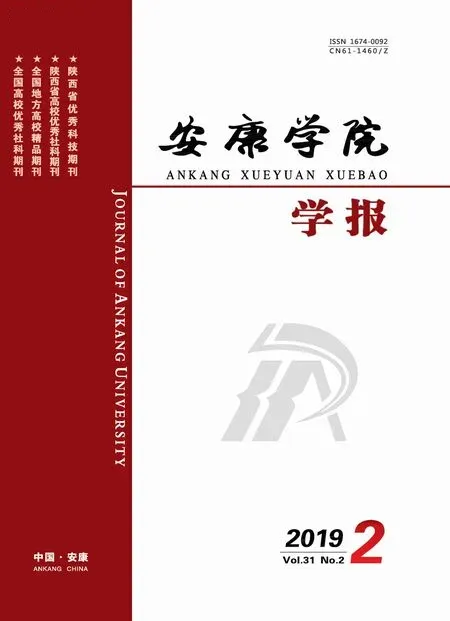历史·世相·美学
——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读札
2019-03-15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山本》是贾平凹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与之前的《古炉》 《老生》一起组成了他的“秦岭志”新历史小说三部曲。《山本》原本起名就是《秦岭志》,作者一是认为容易和《秦腔》相混淆,二是为了读来上口,后改为现名。“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1]522《山本》却不仅仅是写山的一本书,虽然记录秦岭地区的草木记、动物记是贾平凹写作的初衷之一,但绝对不是写作《山本》的全部意义。因为文学不是历史,不是政治,更不是动植物学。文学不管怎样关注历史、政治、自然、博物,写得似“秦岭的百科全书”[2],最终使之成为文学而不是其他的,还是因为它写了历史中的人和人性。所以我们认为,《山本》固然写了历史,写了战争,写了秦岭地区的动物植物,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但其根本还是在于表现历史中的世相和人心。
一
《山本》中有三个耐人寻味的物象:铜镜、黑猫和皂荚树。铜镜是井宗秀在陆菊人那三分胭脂地下的古墓中所得,被视为宝物珍藏,后作为信物赠给了陆菊人。后来井宗秀“成事”了、自我膨胀了,陆菊人将铜镜交还井宗秀以示劝诫,希望他“见了铜镜能回忆起铜镜的来历,会明白其中的意思”。贾平凹精心选择铜镜作为陆菊人和井宗秀二人之间的信物是别有意味的。唐太宗曾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铜镜意象在小说中就成了人心、历史的镜鉴,从历史中可以看到未来,从人心中可以看到善恶忠奸。陈思和也指出小说中铜镜、陈先生和宽忍师父的功用分别为:“以铜镜立戒指向过去,以救世行医指向当下,以宗教慈悲指向未来,三界均有指点。”[3]黑猫是作为陆菊人的陪嫁一起到涡镇的,“头是身子的一半,眼睛是头的一半”[1]18。它有着预知祸福的能力,心中有鬼或行为不端者就会在它的眼中看出森煞。它就像一个神秘的幽灵,一直扮演着陆菊人守护神的角色。皂荚树“长在中街十字路口,它最高大。站在白河黑河岸往镇子方向一看,首先就看见了”[1]3,是涡镇的地标式植物。它结的皂荚没人敢摘,因为身上长刺,而且它有个神奇的功能:能够识人德行,只有德行好的人经过,才会自动掉下来一个两个。井宗秀为了修钟楼将它移栽,它就在一场大火中烧成木炭,涡镇似乎也就失去了皂荚树精魂的护佑,最后也在炮火中化为灰烬。这三个物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着神秘的洞察人心、鉴别品行的镜鉴作用。理解了这三个物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贾平凹《山本》中写上世纪20年代秦岭地区历史的意义。其目的在于用强烈的史鉴意识,接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史传传统,以历史风云烛照出动乱苍茫年代里的世相和人心,这也是贾平凹设置这三个核心意象并在作品中反复渲染的原因。
然而,从历史到文学的转化并不是没有难度,贾平凹也因此犹豫过。《老生》后记中说:“写起了《老生》,我只说一切都会得心应手,没料到却异常滞涩,曾三次中断,难以为继。苦恼的仍是历史如何归于文学,叙述又如何在文字间布满空隙,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4]291在写作《山本》时,他也有同样的困惑:“《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了构思,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材料,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1]523贾平凹的困扰主要在两点,一是如何处理野史与正史、主流意识和作家创作意识之间的冲突;二是如何完成历史到文学的转化。关于第一点,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没有私心偏见”地“说公道话”。这多少受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便,成一家之言”人文史观的影响。写作《山本》时他想的是:“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意识形态有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要求,写作有写作的责任和智慧。”[1]523他自觉承担着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即使写作可能有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地方,但也不能不说,不能不写。关于第二点,他在《老生》和《山本》后记中都提到了“流在秦岭山顶上的河”,这是他“感觉的河”,他进而领悟到:“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好了,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是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1]525贾平凹找到了他写历史的方法,那就是尊重历史的精神,用自己钟情的人、事、物来重造一个属于自己“个人化”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只属于他的历史,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这个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是李平凹或张平凹”,是“看山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新境界[1]524,也是他的“新历史小说”的“新”之所在——“通过强调偶然性因素,构造时空破碎的历史图景,引用‘反英雄’的写作叙述策略,采取闹剧和讽刺剧的情节化方式,以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取代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进化论史观”[5]。
贾平凹是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百年发展历史,又是如何看待革命和英雄人物的呢?《古炉》写了古炉村“文革”的一段历史,目的是想搞清楚:“如果‘文革’之火不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点起,那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却怎样使火一点就燃?”[6]《老生》的四个故事分别截取了游击战争时期、土改、人民公社和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历史阶段,表明了作者对革命的态度,“我的《老生》在烟雾里说着曾经的革命而从此告别革命”[4]295,原来写革命历史是为了“告别革命”;到了《山本》,只写了上世纪20年代秦岭地区以涡镇为中心的国民政府军、红军游击队、土匪逛山以及各类地方武装之间的军事斗争和人事纠葛,意旨似乎又进了一步,那就是——“告别英雄”。小说中有文字表达了作者“告别英雄”的英雄观,井宗秀为了替死去的哥哥报仇,将仇人抓来剜心掏肝,十分残忍,陆菊人就慨叹:“我嫁到镇上也十多年了,来的时候镇上是穷,人也整天吵呀骂呀也打架,那算是个日子,但这些年生活是好了,到处是血,今天我杀了你,明日我又被人杀了,谁都惊惊慌慌,谁都提心吊胆,这人咋都能成这样了!陈先生说:人是十二个属相么,都是从动物中来的。陆菊人说:那你看着啥时候世道就安宁啊?陈先生说:啥时候没英雄就好了”[1]496。陈先生是小说中儒道精神的代表,他认为涡镇乃至整个秦岭地区争斗仇杀的根源,都在于人身上的兽性,而他、宽忍师父、陆菊人则是涤荡掉人性中罪恶、唤醒涡镇人善真一面的救赎力量。《老生》和《山本》都表达了在历史长河中个人(包括英雄人物)和时代渺小的思想。《老生》后记中说:“匡三司令是高寿的,他晚年荣华富贵,但比匡三司令活得更长更久的是那个唱师……没有人不死去的,没有时代不死去的。”[4]294《山本》后记中也说:“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使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依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1]523《山本》更表明,在历史中真正能永恒的、有力量的、值得铭记和书写的是山河,是爱。至此,贾平凹用三部历史小说完成了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的书写。《古炉》和《老生》写齐了各个历史阶段,而《山本》又对20年代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秦岭地区的历史做了重写,这种重写是属于贾平凹个人的,是来自民间立场的。正如陈思和所说:“文学创作起源于民间,在被士大夫文化改造之前,它是走在后一脉野史的源流之中。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最为绚烂的成果,就是作家重归民间的自觉,贾平凹和莫言为佼佼者。”[3]
二
了解了贾平凹对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些看法,我们再来关注《山本》中的这一段历史表现了怎样的世相和人心。那个世道是如此的动荡不安:“那年月,连续干旱即是凶岁,地里的五谷都不好好长,却出了许多豪杰强人。这些人凡一坐大,有了几万十几万的武装,便割据一方,他们今日联合,明日分裂,旗号不断变换,整年都在厮杀。”[1]6这虽写的是秦岭地区,但又何尝不是中国有史以来战争动乱时期的共同写照呢?井宗丞是秦岭地区最早发展的共产党员,为了筹措经费,出主意让人绑票他爹,导致他爹自溺于粪窖里。这在涡镇人看来就是纲常败坏,“没世事了”。在革命年代里,这种革命后辈以惊人的勇气和剥削阶级的父辈们决裂甚至成仇的故事并不少见,因此井宗丞的这种行为不缺少历史事实和政治伦理的基础。作者在此所要表现的是革命对人伦道德的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反复重演的,又是很难修复的。除了基于革命目的的道德伦常破坏,对金钱和权力的争夺也带来了世相的颓败。无人主政时期的涡镇,群龙无首,地方权贵间必然明争暗斗,吴掌柜和岳掌柜之间的争斗就是对地方话语权的争夺。陈先生说:“算起来,拐弯抹角的都是亲戚套了亲戚的,谁的小名叫啥,谁的爷的小名又叫啥,全知道,逢年过节也走动,红白事了也去帮忙,可谁在人堆里舒坦过?不是你给我栽一丛刺,就是我给你挖一坑。每个人好像都觉得自己重要,其实谁把你放在了秤上?”[1]50这无疑是对中国人世相的精准概括。《山本》中吴掌柜和岳掌柜的明争暗斗、井宗秀兄弟和阮天保之间的殊死搏杀,都是对旧时中国人世相和人心的具体而生动的反映。
权力、地位对人的心性改变,体现得最集中最明显、也是作者最着力刻画的人物是井宗秀。客观来说,未“成事”前的井宗秀本性善良、心思缜密、待人诚恳。对待善待自己的人,比如陆菊人、杨掌柜以及从小玩到大的一帮兄弟,他很懂得报恩。他最初能力的显现是在处理父亲井掌柜的后事上,拿回父亲卖地的钱安抚集资的乡亲,表现得冷静理智、有勇有谋。在杨掌柜送给自己的三分地里,发现了古墓,变卖古董完成了翻身的第一笔原始积累,他也表现得毫不张扬、低调隐忍。在陆菊人告诉了他那三分地的来历和暗示玄机后,他也没有说出发现古墓的事情。得财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谋个做画师的活计,这样才可以花销得来的钱财,不至于招人怀疑。可以说,他走的每一步都是精心盘算、稳妥周全的。当陆菊人终于告诉他三分胭脂地的秘密后,他视陆为命中贵人,尊称为“夫人”,一生敬爱有加;对于送给自己埋父之地的杨掌柜,始终尊敬爱戴,奉为义父;对从小玩到大的发小杨钟、陈本祥、苟发明、唐景、巩百林等人,也是一路关照提携,兄弟情深;对于自己的哥哥井宗丞,虽也有怨恨,更有政治派别的分歧,但毕竟血浓于水,始终牵挂于心,得知哥哥惨死,经多方打听消息,最终抓来仇人为兄复仇。
总之,除了陆菊人,井宗秀应该是小说中最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作者毫不掩饰对他的偏爱,说他“从来不说一句硬话的,可从来没做过一件软事啊!”[1]82这已是极高的评价,因为这正是贾平凹的朋友对他自己的评价。但同时,井宗秀对背叛自己的或与自己为敌的人,也从不心慈手软,显出他性格中阴冷、毒辣、残忍的一面。他的媳妇孟家大女儿与土匪五雷有奸情,他便使计将其淹死在水井里。为了除去五雷,他又利用小姨子挑拨五雷和二当家王魁的关系,虽然杀死了五雷,但也导致小姨子结局悲惨,死于非命,岳父也因此而发疯。对阮天保派来挖自己祖坟的士兵,更是将他们活埋在城墙内。他请麻县长联系国民党军12师联合剿灭了阮天保的保卫队,却也学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架空麻县长,成为涡镇乃至平川县的独裁者,与之前的史三海、阮天保并无二异。井宗秀的畸变应始于他联合麻县长剿灭土匪五魁,自己当上预备团团长之后,从此变得血腥残忍、刚愎自用,连陆菊人的话也听不进去了。陆菊人告诉他王成进团长抢人家女儿:“这不是和土匪一样吗?”“井宗秀脸却一下子黑了,说了句我知道了。扭头就走了。井宗秀还从来没有在陆菊人话未说完就走开的”[1]341,这足以说明他连最信任最倚重的人的批评意见都听不进去了,变得独断专行。之后又借改造街巷之机大兴土木,盖钟楼、戏楼,搜刮民财,保护涡镇的独立旅成为危害地方的一霸,走向了自己之前反对的对立面。井宗秀这个人物形象的演变说明:一个失去权力制约的地方领袖,就如同一只脱缰的猛虎,必将成为一股无法控制的破坏性力量。而金钱、权力正是会激发出他们心性中的残忍、冷酷的恶魔性因素。
如果说在井宗秀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善恶混杂、人性复杂,那么在陆菊人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中善良、温情、执着、坚强的一面。“《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块木头或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1]525战争虽然占了《山本》很大的篇幅,但写战争是手段却不是目的,是为了表现人心、人性、人情,旁及文化、风物,才写如此动荡的时代。除此之外,陆菊人和井宗秀之间特殊的情爱关系,也是小说着力表现的一个情节。雷达先生很早就敏锐地发现,“贾平凹的模式中的轴心是一‘情’字”。他同时指出,写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传统,如同曹雪芹、汤显祖、孔尚任的作品那样。[7]笔者认为这是很有洞察力的发现,至于写情的好与坏,则可能意见并不统一。如黄平就认为:“贾平凹并不擅长写‘爱情’,他的所有作品里没有一场真正的爱情故事,他擅长的是对‘爱情’的‘旁门左道’(并无贬义,原文注)的处理,比如《废都》的偷情、《白夜》的滥情、《高老庄》的婚外情以及《秦腔》疯子引生那畸形的感情,他曾经试图以‘爱情’为主题,但是合乎逻辑的,《病相报告》成为他最失败的作品。”[8]在笔者看来,贾平凹不是写不了“真正的爱情故事”,这可能和他独特的爱情观或人性观相关,也可能由他独特的秉性偏好决定,不是不能,而是不愿。笔者更认同陈晓明的“性情”说:“他的人物总在文化体系边缘行走,人们时时处于僭越伦理道德的危险境地……似乎只有非法的反常的情欲关系,才能显现人的‘性情’,才具有复杂的文学意味。”[9]《山本》中的爱情描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贾平凹的情爱画廊。如果说《废都》写的是无爱之性的话,《病相报告》则写的是无性之爱;如果说《秦腔》中引生对白雪和《带灯》中带灯对元天亮的一厢情愿是爱的话,那么《极花》则写的是强迫之爱。以上的爱情书写确实都有畸异甚至变态的成分,但是《山本》中井宗秀与陆菊人的情爱与以上皆不相同。他们的情爱(因为道德的约束无法有性爱)却是真正建立在彼此欣赏、惺惺相惜,颇有知音意味的基础上,如王春林所说:“与其说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是一种‘绝美的爱情’,莫如说他们俩是惺惺相惜彼此相知的精神知己更准确些”[2]。《山本》的爱情书写是对作家之前情爱叙事的有力补充,至此,人们再不能说贾平凹不会写真正的爱情,即那种建立在人格平等和心灵相通之上的爱情。小说中的陆、井二人不是没有结合的机会,在陆菊人的丈夫杨钟中弹去世,井宗秀也死了媳妇之后,按理说这两个彼此欣赏、互相牵挂的人是可以结合的。之所以没有,一方面是彼此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杨钟是井宗秀的发小兄弟,杨父又对宗秀有恩;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更深层的原因:井宗秀将陆菊人视若地藏菩萨,他是不愿用世俗的婚姻毁掉自己的信仰。排除井宗秀后来的人性畸变不谈,他与陆菊人的情爱是颇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心理的,发乎情而止乎礼,缠绵悱恻也能当机立断。小说中有一段陆菊人说二人关系的话,表明她已从两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爱“执迷”中解脱出来,真正“悟”了。她说:“一个人对一个人器重也好,喜欢也好,感到亲了,自己就会发现自己的能力……有时也想,我待你亲什么呢,其实还是待我的想法亲,在杨家十几年了,我有一肚子想法,却乱得像一团麻。现在我是把这团麻理顺了,我才知道了我要什么,什么是能要来的,什么是要不来的,也就理顺了我该咋样去和人打交道咋样去干事。”[1]321可以说,《山本》中的情爱书写是对《废都》无爱之性、《秦腔》一厢情愿之爱、《极花》强迫之爱的反拨,它更真实,更纯粹,更接地气,也更中国化。
三
《山本》在小说美学形式上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开头。类似于《百年孤独》式的预叙开头:“陆菊人怎么能想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1]1这个开头为全书奠定了基调:以陆菊人的回忆展开故事,并且弥漫着神秘的宿命气息。小说中关于风水、龙脉、梦占等神秘事件更是为那段历史蒙上了重重迷雾。全书采用了主副双线结构,从陆菊人八岁被许给开寿材铺的杨家做童养媳写起,以陆菊人和井宗秀的情爱纠葛为主线,以陆菊人和陈先生在涡镇废墟上的一段对话作结。“一部长篇小说,以陆菊人始,以陆菊人终,这一人物形象对于文本完整性所具有的重要结构性功能,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事情。”[2]另一条副线写井宗秀哥哥井宗丞在游击队和红军的经历,最后两条线汇合一起,井宗秀在和红军的两次交锋中先胜后败,涡镇毁于炮火。
其次,《山本》的结构更加混沌、圆融,整体感更强。《古炉》共分为五部,分别为冬→春→夏→秋→冬,完成一个季节的轮回。《老生》也有简单的章节,四个故事实际就是四章,这之前有“开头”,之后有“结尾”。《山本》则没有明确的章节,只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意义单元间用虚线隔开,似乎更符合贾平凹对小说整体、大气、混沌的追求。从小说和中国古代元典之间的关系来看,《老生》在每个故事中间加入了老师对《山海经》的讲解,使故事和经文形成一种互文关系。《山本》也有《山海经》的影响,不过这个影响已化为血肉,融入小说的肌理。从动物性中看出人性,这是《山海经》;从人性中看出动物性,这是贾平凹的《古炉》 《老生》 《山本》。如同贾平凹在《山本》后记中所说:“随便进入秦岭走走,或深或浅,永远会惊喜从未见过的云、草木和动物,仍能看到像《山海经》一样,一些兽长着似乎是人的某一部位,而不同于《山海经》的,也能看到一些人还长着似乎是兽的某一部位。这些我都写进了《山本》。”[1]526《山本》中井宗秀属虎,就故意学虎的做派,之后又有剥人皮、活埋人、剖心挖肝等血腥举动,具有了虎的残忍、冷酷;陆菊人喜欢蟾,是背负责任、隐忍坚强的化身;杨钟似猴,杜鲁成类狗……《老生》中拴牢是牛,裹上牛皮就卷起来,白河说:本来就是畜生么!墓生觉得自己是竹节虫……贾平凹受中国天人合一传统思想和民间朴素的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在其对历史书写中,将人性的变异用具象的动物形象体现出来,其呈现的美学效果和莫言的《生死疲劳》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老生》的结构由于写了四个彼此并不关联的故事,显得并不整体合一,所以就用了《山海经》和活了百年的老唱师将它们串联起来。那么,《山本》的结构相对更有整体性,因为时间集中,就写了上世纪20年代这一个历史阶段;人物集中,以陆菊人和井宗秀的情感纠葛为主线;地点集中,主要在秦岭地区最大的镇——涡镇。而在小说内部,作者也采用了一些办法使节与节之间联系更紧凑,这应该是借鉴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写法。比如说上一节末尾写:“却意外得到一个消息:井掌柜死了!”[1]10下节就写井掌柜如何被绑票又如何被勒索走了众人集资的银子而自尽。又如,上节末尾写:“井宗秀好久没有想到过井宗丞了”[1]43,下一节就写井宗丞在游击队的战斗经历。这种类似于顶针修辞的写法,使每一节似断实连,形成一气呵成、气韵畅通的审美效果。
此外,不能不说《山本》的语言更加老辣,主要体现在不动声色的言说中,有更多的言外之意可供读者品咂。只写出事实的一部分,事实的整体和背后的许多东西并不明说,交给读者自己去品味。据说贾平凹家里挂着海明威的画像,表明他对海明威简约有力的语言是欣赏的,对著名的“冰山理论”也定不陌生。而这种写作理论与中国传统绘画计白当黑的画法颇能相通,对中国画论颇多关注的贾平凹不会不有所领会。如小说中写到五雷搬进了井宗秀家,一天街上有人叫卖饸饹,宗秀媳妇说:“他爱吃饸饹,我去买些”[1]74。这里的一个“他”字就暗含玄机,不称名只说“他”,表明井宗秀媳妇没拿五雷当外人,而丈夫就在旁边,不考虑丈夫的喜好,却记挂着五雷的喜好,也难怪小说写道:“井宗秀知道媳妇所说的他是指五雷,心里多少有些不美,却也不好说别的”[1]74。读者和井宗秀一样,都能感觉出两人关系的不正常,所以宗秀才会觉得“不美”,但读者和宗秀一样并无实据,所以宗秀也只能是“不好说别的”。之后有一段写井宗秀回家,“到了家,前院没人,门道里放着一篮子青菜,鸡在那里乱鹐,撵走了鸡,去桶里舀水熬茶喝,桶里却也干着。提了桶到后院井里打水,便听到后院上房里有说话声,以为五雷和王魁他们在里边,并没在意”[1]101。井宗秀和媳妇住前院,五雷住后院,前院没人,宗秀理所当然认为媳妇不在家,而且门道里放着一篮子青菜,说明媳妇离开的时候比较匆忙,起码是中途离开的。但“这时候媳妇从后上房出来”,猜想此时宗秀心中定是又疑又怒,疑的是媳妇在后上房到底干啥,怒的是媳妇太没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世人都明白此情理:丈夫不在家,媳妇和客人定是要有所回避的,她不但不回避,还主动往上凑,丈夫撞见了还镇定自若,这只能说是仗着五雷的武力撑腰,色胆包天了。这时小说又两次写到媳妇出来见到丈夫时“低了头”,一次写低头并不让人奇怪,两次提及就有深意了——媳妇一定是脸上有什么痕迹不愿让丈夫看见。之后的情形就更加印证了宗秀和读者的猜测,“井宗秀进了上房,房里都是烟气和酒气,五雷好像才洗了脸,西间屋里的洗脸盆里水溅湿了地,而酒肉却摆在东间屋的床桌上……”这里的“却”字,也暗指了媳妇说的是假话:“他要喝酒的,我给端了盘卤肉”,仅仅是喝酒的话,五雷或宗秀媳妇是都没必要洗脸的,这一段落的结尾写道:“井宗秀没有说话,便去熬茶。往常茶熬成琥珀色正好,但他熬了半天,熬得黑乎乎的,像是药汤,筷子一蘸能吊线儿”[1]101。这里简单的两句话,细心的读者却能读出宗秀此时内心的万丈波涌。“没有说话”,是没法对媳妇表示怀疑甚至发怒,他知道五雷是什么样人,任何怀疑或撕破脸皮都可能带来灾祸,但以他的脾性肯定也不能容忍这种羞辱和背叛,这为后文的设计杀妻埋下了伏笔。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贾平凹的这种写法是颇得中国古典小说神髓的,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时说:“吾尝遍观今人之文矣,有用笔而其笔不到者,有用笔而其笔到者,有用笔而其笔之前、笔之后不用笔处无不到者。”[10]这样讲究语言用词准确且具含蕴的写法在古典小说中并不鲜见,如《水浒传》第三回,写鲁智深在五台山当了四五个月的和尚,肚子饿得干瘪,正在想酒吃,“只见远远一个汉子,挑着一副担桶,唱上山来,上面盖着桶盖,那汉子手里拿着一个旋子(温酒的器具)”。金圣叹就批道:“二语之妙,正是索解人不得。盖桶上无盖,则显然是酒,有何趣味;桶上有盖,则竟不见酒亦未为奇笔也。惟是桶则盖着,手里却拿个酒旋,若隐若跃之间,宛然无限惊喜不定在鲁达眼头心坎,真是笔歌墨舞。”[10]贾平凹在《山本》中的一些笔法,正是用有限的语句表达出超出语句本身的大量“言外之意”,这或许就是金圣叹所说的“趣味”“奇笔”和“笔歌墨舞”了。
《山本》是贾平凹的第三部新历史小说,考虑到他有一组题材写三部的习惯(如商州三录,改革三部曲等),这会不会是他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终章呢?《山本》以历史洞察人性的现代历史、文学观念为出发点,以民间流传的神秘意象为贯穿全书的线索,写出了一个不同其以往作品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建立在平等、尊重、信任、扶持基础上的情爱理想的追求。在小说结构的圆融、语言的老辣方面颇得古典小说美学的神髓,这也正体现了作者对“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