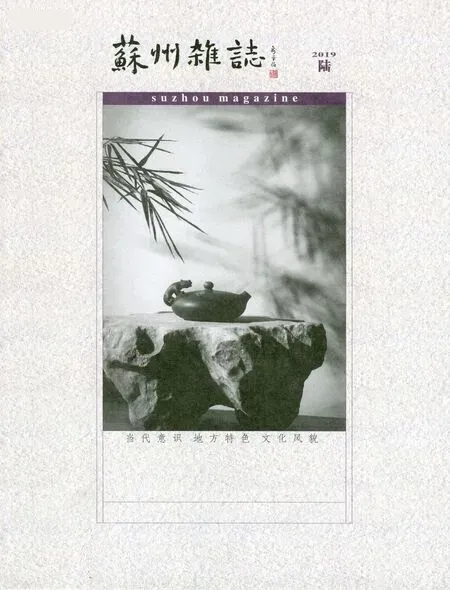郑逸梅、黄转陶舞文惹祸
2019-03-14黄恽
黄 恽
吴江名士费仲深,本来住在混堂弄,后来购得桃花坞屋,修葺整理后住了下来,现在在桃花坞就有了费仲深故居,钉了木牌。不过听人告诉我,费仲深树蔚,现在被文保所改了名,称费仲琛了。如果人有灵魂的话,我想费氏之魂恐怕在桃花坞会找不到自己的家,以为已经被一个名叫费仲琛的鹊巢鸠占了,而实际不过是被现在的专家改了名字。
作为苏州士绅,费仲深是个火气很大的人,因为和张一麐等人意见不同,曾大闹矛盾,二十年代中叶之后,曾发誓不再管苏州的事了,从此深居简出,啸傲林泉。他有个号叫韦斋,就是因为火气大的缘故才自己起的。过去有许多叫佩韦、佩弦的人,譬如《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朱自清性缓,就是现在所说的慢性子,就叫佩弦,用以均衡一下,让他遇事不要那么迂缓,动作和反应快一点;而费仲深,自号韦斋,韦是古代一种鞣熟的皮,韧而软,用以提醒自己不要轻易发怒。这里不妨再说一个人,翻译家傅雷,他也是一个火爆脾气,一触一跳,照理说也应该起个号叫佩韦,孰料傅雷起了个号叫怒庵,好像变本加厉似的,其实不然,庵也可写作安,怒而安,也即止怒也。可以这样说,一旦发火,就想到怒,想到怒之不妥,并以此制怒,进而止怒。中国文字有点奥妙,也有点游戏,本是文人股掌间的玩物,一玩就从仓颉玩到了现在,很有趣。
野马跑得有点脱缰了,收一收,再说费仲深吧。
费仲深对苏州文人中的郑逸梅、黄转陶两人最恨了,这不怪费仲深火气大,得怪郑逸梅和黄转陶自己舞文惹了祸,起因都与“袁公主”有关。

原来,费仲深和袁世凯的“太子”袁克定是连襟,娶的都是吴大澂的女儿,费仲深和袁克定又是亲家,他的儿子娶了袁克定的二女儿(当时戏称公主)。费、袁当年联姻,在古城苏州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袁家的嫁妆奢华名贵,数量极多,浩浩荡荡,抬了一条街,苏州万人空巷,喧传一时,看客中就有郑逸梅。

别人都是满满艳羡的眼光,偏偏郑逸梅独具只眼,他别的没多关注,看到了嫁奁中的一件大玉玦。他给《上海画报》写了一篇文章,叫《嫁奁中之玦》(载1926 年第74期),对这块玉玦大做文章:
“袁芸台(袁克定)之女公子,下嫁于费氏,早已喧传吴中,而各报上又竞载其奁物之奢华靡丽,历历如数家珍,而独有一物,未之述及。厥物为何?曰玦是也。玦为玉质,色泽綦古,想亦数百千年物,固可宝也。然余以为奁物中可罗列诸珍,而独不当有玦。夫玦者,圆而缺也。盲传:‘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遂有金寒玦离之叹’。观此则可知玦之为物,不宜于点缀美满姻缘矣。”(笔者按:成语盲传腐史,就是指《左传》和《史记》,这里专引《左传》,原文是“左传云:晋太子申生帅师,晋侯佩之金玦,狐突叹曰:金寒玦离,胡可恃也。”其实也见《史记·晋世家》)
郑逸梅是补白大王,像笔者一样好弄笔墨,一生中写了很多著作,但文章容易惹祸,只顾逞一时笔墨之快,祸机也正伏于此。人家兴兴头头地结婚,你却暗示这个婚礼不吉利,是何居心?简直迹近诅咒了。
固然,郑逸梅也有他的道理,苏州人迷信,讲究谐音,玦音诀,诀别也,在吴语中则读作缺,而这玉玦的形状也是圆而有缺,这对于婚礼之圆满无缺来说,确实有点不够吉利。如果以苏州人的观念来说,似乎隐伏着:或男女双方死一方,或离婚,或双方不圆满等诸多意味。自古《荀子》有“绝人以玦”的说法,所以在传统观念中,玦又意味分离、翻脸、断绝的意思,正像鲁迅说的,中国人喜欢自己骗自己,孩子满月,如果有人说这孩子总有一死,道理是对的,但要被人吃“生活”(打也)。生活中很多事情,不能挑破,一挑破,事主的心情就会大受影响,势必迁怒到这个说皇帝没有穿衣的孩童身上,这回,郑逸梅正好充当了《皇帝的新衣》里这个孩子。
人家的大喜事,被郑逸梅这么一说,还刊发在发行量甚大的《上海画报》上,心头就有了阴影,合家不快。袁家是北方人,或没有这样的忌讳,只知扎台型,爱女儿,讨好亲家,嫁奁倾其所有,多多益善,哪知道江南苏州的“苏空头”会这样想这样说?作为公公的费仲深一看该文,一团高兴,也顿飞往九霄云外,简直气破了肚皮,也顾不得什么韦斋之韦了,只想打郑逸梅一顿,方泄心头恶气。然而,碰上这样的苏州文人,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咬牙切齿,恨恨不已,这时韦斋的号倒有点多事了。
郑逸梅在上海,从朋友处知道自己的一篇小文闯了祸,一时也不敢回苏州,生怕费仲深找人打上门来,难以收拾。
很多事情,当下难过,事后也就释然了。好在这对新婚夫妇敬老爱幼,相敬如宾。
不料几年后又来了一件更可气的事。这回不是郑逸梅了,而是另一个星社同人黄转陶。黄转陶别名猫庵,喜欢养猫,抗战结束后,辗转到香港发展。
原来苏州人的家长里短有个发布的场合,叫做茶馆。不但富家子弟,生意中人,官场公职人员,甚至家奴仆佣,每天早晨都喜欢到茶馆喝茶聊天,新闻记者,特别是小报记者,全靠茶馆里流传的消息来填补报纸的空白。
1926 年8 月10 日,黄转陶在茶馆里听大家在传,费家的仆人说,袁公主开电风扇触电了。黄转陶一听,这是绝好的社会新闻啊。触电,那还了得,一定是没命了。于是,他也没细打听,第二天,小报上就有《公主触电》的新闻,认为袁公主一命呜呼。
这里把刊发在《上海画报》(1926 年8月11 日)上的报道录入如下:
小报告
袁克定女公子,今春适费仲深之次公子,时甫半年,日昨因开风扇触电逝世。(转陶)
黄转陶这一番合理推测,搞得苏州很多与费家有亲的人家大起惊惶,纷纷去电或亲临探问。事情的真相则是,袁公主触电事诚有之,麻了一下手指,受了一吓,并没严重的后果。
费仲深这一气,哪还能抑制得住,大喊来人,拿我的片子(即名片),报警局告以造谣诬陷之罪。
早有人暗地通知黄转陶,黄转陶见机不妙,也来不及多想,马上叫上黄包车,快快,往火车站。
黄转陶连家人也来不及通知一声,就这样一溜烟跑到了上海租界,躲了起来,很长时间都不敢重履苏州。
黄转陶之“桃(陶)之夭夭”(谐音逃之夭夭),一时成了苏州文艺界的谈资,都说噱是噱得来,比说书先生讲的还要精彩。
两次事件中,文章都刊载在《上海画报》上,它的创办人是毕倚虹,周瘦鹃在该报任编辑,这些短文大概都是通过周瘦鹃的手在报纸上出现的。
《上海画报》上有一个署名瘦鸥(当是秦瘦鸥)的人,讲他文字生涯中,因为舞文贾祸的事也不少。此文叫《文字厄志感》,刊载于1928 年初,他历数自己文字生涯中惹出的祸端,摘录如下:
愚酷嗜弄笔,尤爱作游戏文字,年十四五即致力于此,至今迨六七年矣。其间若为《快活》作爱情小说而触怒某戚,竟至绝交。又为某君草滑稽寿词,而被某巨公所忌,险致丧身。近则因《福尔摩斯》而涉讼公庭,久久弗解。此仅其大者也。他若琐屑之交涉,未发之祸端,犹在不及举与不可知之数,文字之祸,真可畏也。
可见舞文弄墨,还需审慎第一。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当尊重事实,率尔操觚,往往弄出祸患来,不容易收场。就郑逸梅和黄转陶来说,他们两个都一时间回不了家乡。
这两件事都与费仲深有关,也可以从中看出费仲深与新闻记者、苏州文人之间的关系在某个时期存在着一点不够和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