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断案
2019-03-13叶介甫
叶介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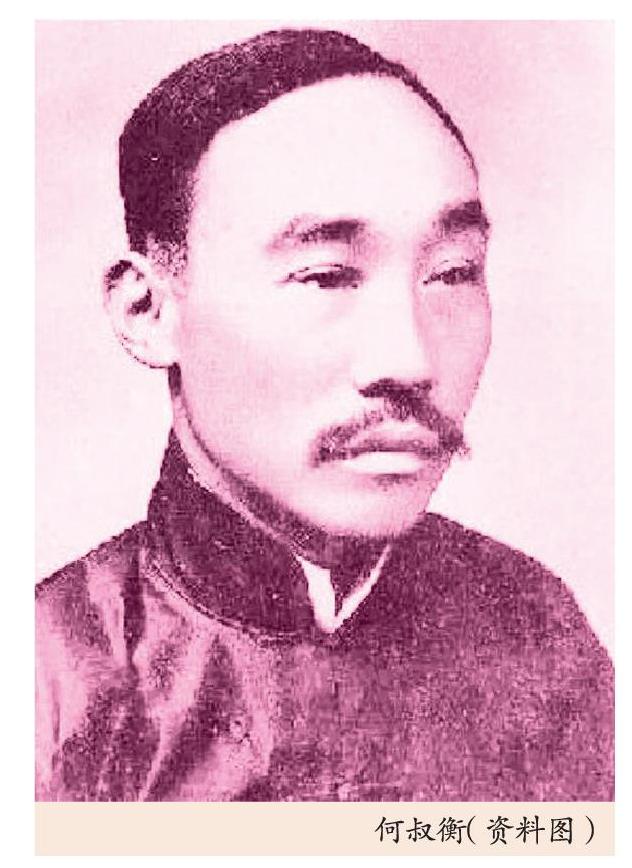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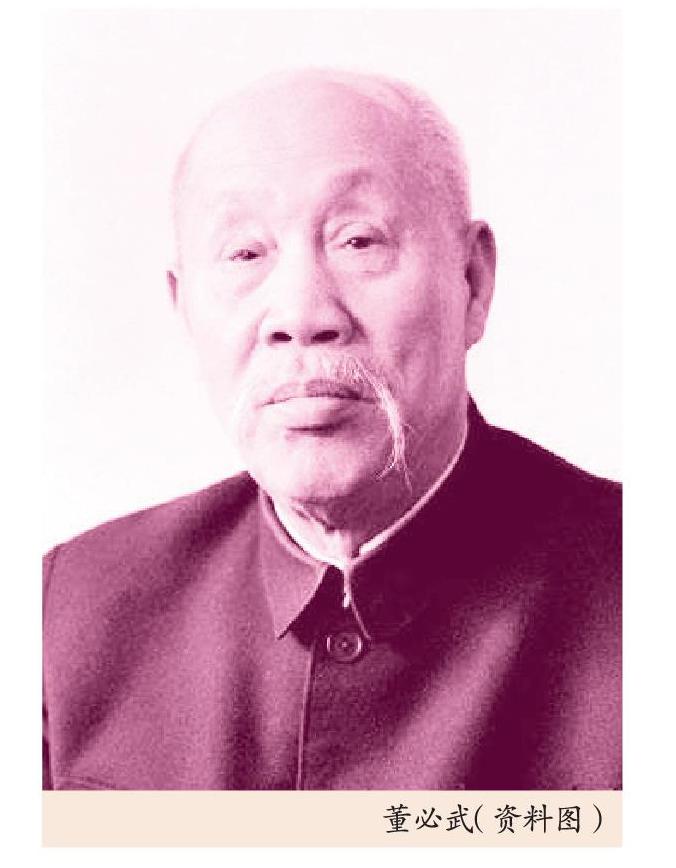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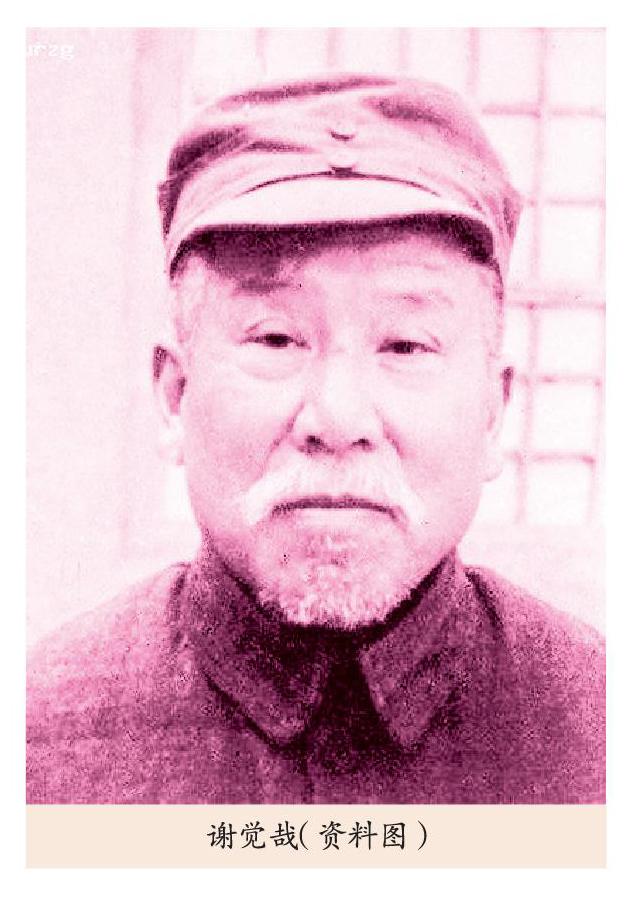
革命老人何叔衡、董必武、谢觉哉是被人们尊为中央“五老”中的“三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担负过司法工作,并且在司法领域都有独特的创造和建树。从中央苏区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他们在各个时期都参与了立法工作,在司法审判工作实际中,处处体现司法为民的观点。他们以身作则,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切实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努力争取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司法权利,深受大众好评,被人们誉为人民司法制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何叔衡,1876年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讲习班,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志同道合,成为最好的朋友。1920年冬,他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他与毛泽东一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他在中央苏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随后又任内务部代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毛泽东高度评价他的革命精神和工作能力,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他在福建上杭县水口镇小径村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为牺牲同志默哀的名单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大家莫不为这位在党内被尊为“五老”之一的革命长者的牺牲而深感震惊和悲痛。
在中央苏区时期,何叔衡主持临时中央政府检察、内务和最高法院工作时,凡属检察、民政、司法等方面的工作,都由他主管。在工作中,他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何老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何叔衡主管的工农检察机关有七八十个干部,常分批轮流下到各地,检察各种贪污、违法乱纪、失职渎职的行为,调查落实各种控告材料。每批人员下去前,他都要详细交代应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不能对群众耍态度,要搞好和群众的关系,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每批下去的干部回来后,他都要亲自听取汇报,下去的干部有什么事做错了,他就指出错在哪里,今后应注意什么。他对干部要求严格,但他批评人不是疾言厉色,而是和风细雨,耐心教育。
1931年11月,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在苏区党代表会(通称赣南会议)和1932年8月党的宁都会议上相继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对此,何叔衡十分不满。在工作中,他对“左”倾错误的某些作法进行了抵制。当时,在过“左”的肃反政策的影响下,一些省、县司法机关的干部认为,多判死刑保险。何叔衡主管司法,对下面报来审批的案件,总是仔细审查,反复推敲,凡是认为不够判处死刑的,均不予批准。
1932年5月26日,何叔衡在审批瑞金县苏裁判部第二十号判决书时写道:“关于朱××判死刑一案不能批准,朱××一名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根据口供和判决书所列举的事实……是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7月7日,他对江西省苏裁判部省字第二号关于温××、余××等六犯并案分别判处一案的批示中写道:“余××判处死刑暂时不能批准,因余的罪状不很明白……原判发还……暂作悬案,待接到你们详细报告之后再作决定。”10月10日,他在给会昌县苏裁判部的指示信中说:“第二号判决书主要是些偷牛偷鱼的事,至于与反动土豪通信,到底通些什么信,发生了什么影响,未曾证明,不能处死,需再搜查反革命证据或发现反革命的新材料可以复审。不过,主审人要改换。”
但是,何叔衡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从不心慈手软。1932年秋,瑞金县黄柏区的干部和群众揭发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有严重问题。他立即派干部进行调查。随后,又亲自到黄柏区了解情况。结果证实,陈××确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罪恶累累、民愤很大的恶霸地主,并任过“民团”团长。他毫不犹豫、排除各种阻力,立即将陈××依法逮捕。经过公审,排除各种阻力,将其枪毙。
何叔衡在审判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罪证确实,量刑準确,重罪不轻判,轻罪不重判。对当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指责他为“严重的官僚主义者”,何叔衡并不畏惧,说:“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1933年10月,他在审批江西省苏裁判部第一八二号判决书关于王××判处枪决一案时,仔细审查了判决书中关于王XX犯罪的全部材料,认为其只有少量贪污公款一项是属实的,其他各项或者是任意夸大的,或者是无法落实的。10月10日,他对这个案件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对全案材料所列举的事实一一做了分析,指出原判是“过‘左的判决”,“王××只是贪污公款(量少),不见有反革命重大行为,处以死刑,是非常失当的,应改为监禁一年,剥夺公民权一年”,并在批示中指出除所贪污的财物收缴回公家外,“原判宣布无效,希即照批示执行”。
何叔衡能不顾政治压力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但从不固执己见,而且知错即改。他在对干部的处分问题上,也曾作过某些错误的决定。但是,当别人指出后,他就立即予以改正。一次,他错误地批判了几个干部,这几个干部不服气,把详细情况书面报告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并请主席阅后转给何叔衡。何叔衡看后亲自找到这几个干部做检讨:“我当时不了解情况,现在看来你们没错,我错了。”这几个干部听后很受感动,非常钦佩他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
1980年,诗人萧三为纪念何叔衡赋诗一首:矍铄老翁何叔衡,十二人建党立殊勋。做事不辞牛荷重,感情一堆烈火熊。生平能谋尤能断,赤胆忠心无与伦。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型。
董必武:“随处留心观察”
便是“绝大本领”
董必武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法学家,是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位受过正规法律专业教育并从事过律师职业的人,是党内坚决主张实行法治的第一人。他长期从事我国法制建设的领导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法制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杰出贡献。1996年,江泽民在董必武110周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了董必武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董必武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有指导意义。”
1955年1月,湖南省人民法院上报的有关绥宁县人民法院错判“放蛊”案件的报告摆到了董必武的案头。所谓“放蛊”,是指心怀恶意的妇女把蜈蚣、乌烟虫等毒虫用火烤焦,碾成粉末,藏在指甲内,然后偷偷弹到别人的饮食中,食者即“中蛊”,几个月或几年后就会死去。据说“放蛊”的妇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杀人缘由,只因若不“放蛊”就心情烦躁。这类案件错判的经过,都是由于有人怀疑某个妇女“放蛊”,村干部就发动群众对她进行批斗,甚至捆绑吊打,迫使妇女承认后,由乡政府移交人民法院。绥宁县人民法院的办案人员对这种迷信传说深信不疑,在不做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对被指控的妇女定罪判刑。
错判的“放蛊”案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与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初步建立我国法律体系有关。这次大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5部重要的法典后,董必武被选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到任后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推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大力改善新中国审判人员的审判作风。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指示,各级人民法院严查审判作风问题。一查,问题还真不少,一些地方审判员的审判作风不正,严重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顺利实施。比如,湖南省人民法院在1954年年底对省内各地法院进行彻底检查时,就发现1951年至1954年8月,绥宁县人民法院先后受理了25宗“放蛊”案件。湖南省人民法院经过深入调查,查出14人是被蒙冤判刑的。错判的“放蛊”案件一经发现后,立即进行了纠正和平反。董必武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认为这一案件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绥宁县人民法院错判“放蛊”案件,典型地反映了审判人员中存在的先入为主、不深入调查、诱供甚至刑讯逼供的错误审判作风。
1955年1月21日,经董必武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此事,并转报了湖南省人民法院《关于绥宁县“放蛊”案件的检查报告》。这一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2月1日,毛泽东批示:错判“放蛊”事件,不过是不良作风表现在若干案件上面而已,应使重点放在改善作风。3月12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上述报告,并发出改善司法机关审判作风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发动全体司法人员对自己的审判作风进行深刻的检查,反对逼供信的审判作风,提倡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判作风,以避免错判案件继续发生。
“放蛊”案件报告中共中央后,董必武的心情并不轻松。如何对各级法院的审判人员加强教育,引导大家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形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办案作风,这是他不断思考的问题。考虑再三,董必武想到一个办法。他指示有关人员把古今判案中一些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案例编成一个小册子。在编辑过程中,董必武特别交代,要将《聊斋志异》中的《折狱》的一则故事编进去。
这则故事讲的是清朝顺治年间发生在山东淄川县境内的一件事:淄川城西崖庄村里有个小商人被人杀死在半路上,隔了一夜,他的妻子也上吊死了。商人的弟弟就告到官府。當时淄川县令叫费祉。他亲临现场去察验,见死者裹在布袱中的五钱银子尚在腰上,知道并非为财所杀。召集乡民询问情况,也问不出什么头绪来。但他对谁都没动刑,也不拘留一个人,而是让他们各自回家,不要耽误农活。半年后,差役因交纳赋税事逮捕了几个人,内中有个叫周成的,一到公堂就十分害怕,当时表示愿意交纳赋税,说着便从腰间布袱中取出银两,交给费县令。费祉收验了银两后,问:“你家住在哪里?”周成回答住在某村。费祉问:“你家距西崖有几里?”周成答:“五六里。”费祉又问:“去年被杀的商人是你什么亲戚?”周成答:“不认识这个人。”费祉听后勃然怒道:“人是你所杀,还说不认识!”认真一审,周成果然认罪并详细交代了杀死商人、逼死其妻的经过。衙门里的公差都惊叹费县令破案如神,可是不明白他是如何破的案。费祉说:“辨明案情并不难,重要的是要随处留心。我在验尸的时候,见商人的布袱上绣有万字花纹,周成的布袱上也有这种花纹,出于同一个人所绣。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又说不认识商人,而且神色惊慌,语无伦次,我就断定商人可能被他所杀。”在《折狱》中,作者蒲松龄称赞费县令“‘随处留心之言,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也”。
1955年5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司法座谈会上,按董必武的指示,将编有《折狱》故事的那本新出的小册子发给参加会议的各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各司法厅(局)长和部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并要求他们组织所在系统的审判人员学习。这本收录了古今断案经典故事的小册子,对全国司法人员树立良好的审判作风很有助益。
1956年2月8日,董必武曾亲自为这本册子写了一段题词,专门谈到了《折狱》中费县令“随处留心”的办案作风。题词说:“重证据不重口供是我们人民审判员进行审判时必须遵守的原则。但仅仅遵守这一原则是不够的,人民审判员还必须从案件的各个侧面观察,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发展,才能作出比较客观的判断;最忌的是粗枝大叶,漫不经心。这里选择的聊斋有一篇折狱后面采了费祉先生几句话很好。费先生说:‘事情没有什么难办的,总之,要随处留心观察就得了。‘随处留心观察便是绝大本领。”
谢觉哉:
“我们绝不可草菅人命啊”
谢觉哉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谢觉哉历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秘书长、司法部长、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审计委员会主席,为建设根据地而不遗余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法制建设、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11月,中央西北办事处司法部成立不久,省裁判部送来“王观娃死刑案”,要谢觉哉批复。谢觉哉反复看了卷宗,提出了一系列可疑之处:“王观娃的罪到底是什么?当了几年土匪有什么事实?今年抢人抢了些什么?在何处抢的?抢的情形怎么样?怎样动员人去当土匪的?都是哪些人?”他指出:“王观娃各种事实情节都没有说清楚,案卷报告上看不出来,这样马马虎虎,怎好来判他的死刑?”于是,他拿起毛笔,重重的写了4个大字:“无从下批。”
省裁判部根据谢觉哉的批复,重新审判,结果对王观娃以“无罪释放”结案。
谢觉哉在办案中,注意保护妇女权益。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很长,对妇女的压迫最深最重,使妇女和男子不能平等,因此在司法工作上应该注意保护妇女的权利。
延安安边县发生一起人命案——丈夫杀死了妻子。早先,这个被杀死的女同志就来延安告状,说男人对她不好,要求离婚。谢觉哉亲自接待了这位女同志,亲切地向她讲了许多夫妻和睦的道理,要她与丈夫和好。
女同志听了谢觉哉的劝解,回去了。但丈夫毫无悔悟之意,骂她“闹自由”都闹到延安去了,更加粗暴地虐待她。女同志忍无可忍,又多次到县司法机关要求离婚,因为司法机关有的人有封建思想,不保护妇女权益,该离也不判离。女同志无奈,二闯延安。谢觉哉向县司法处批示:“应准判离。”女方高兴地回去了。
可是,过了不久,县司法处报来这个案子,谢觉哉翻开案卷,大吃一惊,报来的不是判离案子,而是报请核准死刑案:那个丈夫将妻子杀死了!
谢觉哉愤然批示说:“应该离的,不判!如判离了,可救两条性命。”他认为,这是司法人员不坚守职责和判案水平低所致。他强调要注意保护妇女权益,是因为人民的司法制度不同于封建王朝的司法制度。
1961年,谢觉哉已经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在各地法院出现了电报报案的情况。谢觉哉针对这个问题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一定要看案卷,否则,何必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呢?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了就不能再安了,我们一定要对人民高度负责。”
当时,云南报来一个案子,案由是一个50多岁的地主分子利用毒菌毒害社员。谢觉哉先看了各级法院的意见,都认为这个地主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判死刑,接着他详细地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如下几个疑点:第一,她是和大家一起在山上捡菌子,无人能证明有毒的菌子就是她捡的;第二,菌子的毒性有多大,为什么有人中毒、有人没有中毒,缺乏鉴定材料;第三,这个地主分子是有意去捡毒菌还是无意?如是故意的,大家叫她吃时,她完全可以选些无毒的吃以掩盖事实,而她并没有这样做。
谢觉哉想,地方法院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草率判决,有没有因为被告是地主分子而推论是她有意作案的因素呢?为慎重起见,谢觉哉指示将案卷退回,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调查后,再把材料送来。
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派人重新调查,证明这个地主分子根本分不清菌子有毒无毒,也找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毒菌就是她捡的,当时她自己之所以没有吃,是因为捡菌子时,她自己留了一些在家里,煮熟已经吃饱了,并没有其他原因。于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由死刑改为无罪释放,并向最高人民法院写了检查。这一错案得到纠正后,谢觉哉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看案卷,因为这是提高办案质量的关键。
1961年3月,谢觉哉对张志远强奸案提出了怀疑。张志远1950年参加革命,后随当时的西北卫生部民族医疗队到甘肃省天祝县自治区从事医务工作。1952年12月,天祝縣人民法院判决他利用驱梅注射工作之便,强奸一位藏族妇女,因此判刑10年,投入监狱。这个案件经过三级法院(包括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判决,但张志远一直不服,曾3次上诉。谢觉哉接到张志远的申诉后,认真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对审判员说:“此案存在三大疑点。一是张是个医生,判决书上认定他利用驱梅注射之便进行强奸,难道他不知道梅毒的传染途径吗?二是事情发生在妇产科诊疗室,光天化日,人来人往,难道真的可能吗?三是一个人判了10年刑,已坐了8年牢,还不断申诉,应不应该考虑他有冤屈的可能?”
谢觉哉的分析对审判员很有启示。经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派一位有经验的女审判员同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同进行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天祝县是藏族聚居的地方,发生案件时还未土改和镇反,牧主粮户(即牧主兼地主)是当地的当权者,而与本案有关的院长、区乡长、民兵队长等不少是牧主粮户的代理人。由于他们都反对土改,牧主粮户的老婆便利用一个不懂事的13岁幼女制造事端,捏造冤案,目的是要把医疗队赶走。
根据上述调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又组织天祝县人民法院进行复查核实,最后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撤销原判,对张志远给予平反。接到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为张志远平反的报告后,谢觉哉语重心长地说:“从冤错案的数量来说是很少的,只有百分之几,但对一个蒙冤的人来说,却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百啊!对冤错案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解决当事人一个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挽回不良的政治影响,不可疏忽。”
事后,谢觉哉又叫有关同志打电话问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是否已经放出来了,工作是否落实,工资是否已经补发?”直到这些问题全部落实,他才放下心。
1962年5月,谢觉哉视察西安。他从抽调的案卷中,发现一个关于王为明被判无期徒刑的案子。案卷里写道:王为明趁我党整风之机,先后向毛主席、周总理及人大常委会等写了十几封信,咒骂我党革命领袖,攻击各项政策,给章伯钧去信献策将农工民主党改为“农民民主党”等,因而判处王犯有期徒刑10年。王犯不服上诉,法院改判王犯有期徒刑20年。投入劳改后,王犯不服,抗拒改造,西安市坝桥区人民法院又增刑4年,变为24年。该犯仍然不服,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写“控诉书”,控诉中央领导人放纵下级干部滥用刑法侵犯人权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判死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改判无期徒刑。
谢觉哉仔细看完案卷中的全部材料,认为案子判得有问题。他说:“宪法规定,人民有通信自由。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有什么罪,为什么反映问题就要判刑呢?而且判得这样重。人家又没有什么行动,这样做对广开言路有什么好处?”他主张改判无罪释放。
但是,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和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的人怕别人说他们右倾,持有不同意见。谢觉哉没有以上级压下级的方式处理问题,而是组织大家讨论,并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也摆在桌面上。通过反复的争论说服,大家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将王为明由无期改判无罪释放。但承办此案的同志仍在案卷上注明:“这是谢觉哉在这里讲的,这个案子判错了所以要改。”事后,谢觉哉意味深长地说:“为什么这样写?就是准备反右倾的时候,反不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