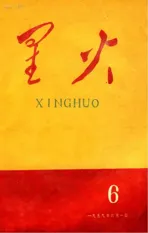疼痛的肋骨
2019-03-11○田宁
○田 宁
一
酒石酸美托洛尔/苯磺酸氨氯地平
辛伐他汀/呋塞米/孟鲁司特钠
氨茶碱/氯雷他定
包醛氧淀粉胶囊/百令胶囊
…………
五年时间里,我每月两到三次前往本县人民医院,排队挂号,找医生,请他们为我开这些药。不是给我,是给我父亲。我没问题。但我拿不准我是不是真没问题。我想没人能保证自己没问题。我记不住这些药名,尽管我已经面对它们整五个年头,这些名字对我来说依旧只是一堆汉字符码,冰冷,陌生。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父亲的病痛?能否让父亲离死亡稍微远一点?我不清楚。日复一日,我从医院取出这些药,让母亲督促父亲按时服下。看着父亲饭量正常,恢复对母亲端到桌上饭菜的百般挑剔,抱怨现实,强撑面子,起码精神还行,我对疾病或死亡的忧虑有所平息。
因为说不出药名,我请医生点开父亲过往的开药记录,告诉医生这种药开半个月,这种药开一个月。一个月太多,不给开?上次都可以,现在不行?我问医生。医生不看我,他的眼睛盯着电脑屏幕,脸色说不上是视死如归的平静还是视死如归的淡漠。我想了想,说,不行就开半个月,半个月就行了吧。医生说可以,不过他是呼吸科医生,只能开治疗哮喘的那些药,治疗高血压和慢性肾衰的药他开不了,我得重新挂号,另找医生。我拿着父亲的医保卡,回到人头簇拥的挂号大厅,站在往来的人流里,我想了想,决定剩下的药还是下次再开。
父亲得的是高血压、慢性肾衰和哮喘,眼下的症状是双脚浮肿,无力,举步艰难,行动稍微剧烈就呼吸带喘。是否还有其他病,难说。看起来没有,也许检查一下就有了;今天没有,保不齐明天就有了。就像他的肾衰和哮喘,突如其来。
五年前的那几日,父亲的双脚开始肿胀。我们一开始没特别在意,以为只是一般的水肿。父亲坚信是早些天下暴雨,房间进了水,身体跟着受潮,体内湿气太重,只要去除湿气,浮肿就会消下去。十余日过去,父亲的脚肿丝毫不见消退,腿脚却越来越绵软无力。有人建议我们带父亲去医院做个检查,图个心安。我们觉得有道理,带父亲到医院,量血压,抽血化验,尿检。检查的结果是,重度高血压,肾功能衰竭,不马上治疗,发展下去就是尿毒症,得做血透,如果继续恶化,就只有换肾,再不然就是,等死。
后面的话医生没说,但意思摆在那里。我和大哥看着父亲的化验单,陷入短暂的惊慌和面面相觑。主要是想不通。父亲此前有高血压,但父亲一直吃降压药,血压一直维持在正常水平,怎么就又上去了?还是重度?肾衰又是怎么回事?我们询问父亲,才知道十多天前,父亲去镇上卫生院量了一次血压,医生告诉父亲,他的血压正常,父亲却理解成他的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于是断了降压药。然后,父亲的血压一路走高,然后在高血压的作用下,肾功能衰竭。就这样。
医生建议父亲立刻住院治疗,但父亲不愿住在医院里,他闻不惯医院里那股味道,洗漱麻烦,晚上安排陪床也是个问题。何况,内科病房满员,父亲的病床安排在人来人往的走廊,父亲夜里根本无法入睡,而父亲腿脚无力,夜里上个厕所也不方便。于是父亲住院治疗的这段日子,大哥每天开车把父亲接到医院,我在医院陪父亲打点滴,一上午四五瓶药水,滴完药水,大哥再将父亲送回老家。其时正是暑假,学校里没什么事,我每天一早起来,就到医院等候。扶父亲乘坐电梯上五楼,等候护士量血压,回答医生关于父亲屎尿的提问,关注药水注射情况,扶父亲上厕所,记录父亲的尿量,按铃叫护士换药水,将父亲的两条腿搬上病床,和父亲说话。医生过来,按压父亲的双腿。还好,父亲的水肿略有消退,完全恢复虽然已经不可能,但如果坚持长期服药,基本能保证不恶化。也就是说,只是肾衰,暂时不会恶化成尿毒症,父亲不用做血透。
二
我挂断电话,收拾好教案,向学校请了假,骑上电动车直奔医院。四月初,已是暮春,南方小城到处绿意葱茏,骑在车上,暖风迎面吹来,我心里没起任何悲伤或恐惧的念头。我想的是,先去医院,看情况。这时已近中午,如果事情不要紧,就去女儿的学校接女儿放学,回家吃饭,午休,下午回学校。
是侄女安打来的电话,安在电话里说大哥正在医院里,门诊五楼内科病房,是前一天晚上住进去的。安在电话里语调平静,那就表明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很可能,大哥只是疼得没办法忍受,于是住进了医院。这和一个月前母亲的电话不同。一个月前母亲在电话里尖声痛哭,说大哥刚才离开老家准备返回县城的时候,突然向父亲和母亲跪了下去,大哥说怕到时间不能够拜别父母,先把头磕了。母亲哭着说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他这是要取我的命,有病就要赶紧治,你向学校请好假,快去看你大哥,陪他去医院,你现在就去。母亲的哭声凄厉而绝望。我站在教学楼之间的天桥上,没止住突然喷涌的眼泪。
我熟悉门诊五楼内科病房。两年前父亲就在这里治疗他的脚肿。我上楼,找到大哥的病床。大哥坐在病床上,脸色灰白,嘴唇干裂,身上插着几根管子,旁边放着血压与心率测量仪器,仪器发出尖利的嘀嘀声响,上面闪动红色的数据。侄女安坐在一边,看着床上的大哥。安突然站起来,用一根棉签沾水涂抹在大哥的嘴唇上。
大哥看见我,嘴唇动了动,一滴水从他嘴唇上滴下来。安从病床边上抽出一张纸巾,拭干大哥下巴上的水滴。大哥重新闭上眼睛,没说话。安说他已经说不出话。为什么不让你爸躺下来?我问安。他躺不下,他背上长出一个肿包,一躺下就痛,不能呼吸,喘不停,他已经从昨晚坐到现在,没睡觉,没吃东西。安说。
大哥身上插着管子,已经从昨晚坐到现在。我立刻明白了大哥脸色的灰白和嘴唇的干裂。我问自己,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办。我会立刻去死,我对自己说。但大哥的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我意识到这个事实,意识的某个地方突然裂开一个深幽无底的黑洞。
我站在大哥的病床前,听见仪器的滴滴声传进耳朵里。我离开病房,来到走廊上。我想找医生问问情况,但我找不到医生。我想上厕所,但我没必要上厕所。我想找点事情干,可我干不了任何事情。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想打个电话,但我不知道该打给谁。
大嫂不在病房,安说她回家做饭去了,等下就会来。医生建议可能要转院,午后就转,转到赣州附属医院,大嫂得回家收拾住院生活用品。我转头四顾,看见到处都是病床,走廊上,病房里,和两年前一样。病床上都躺着病人,只有大哥坐着。他坐着,在夜里,他没办法躺下入睡,他的目光越过所有人的头顶,是不是看清了更多东西?是否看清了亲情、爱情和其他各种人情,在他突然莫名得病的这两年里如何纠缠不休?他是否看见死亡,这种他早在一个月前就瞥见的东西,再次敲打生命这堵危墙?如果可以选择,他是否会选择另一种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他是否终于明白,生命这东西,真没我们想的那么强大,有时候一根手指,就能让它轰然倒地?
我和安坐在大哥身边,不说话。安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大哥涂抹一次嘴唇。大哥闭着眼睛,胸口起伏。有时大哥睁开眼睛,他的眼睛里一片灰白。
仪器的滴滴声忽然变得急促,尖锐的声音响彻整个病房。大哥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他睁开眼睛,看着安,嘴唇颤动。你想说什么,爸?安把耳朵凑近大哥的嘴唇,我听见几个微弱的词语断断续续从大哥的嘴里出来,我听不清。
几天后的晚上,大哥的遗体已经被送进殡仪馆,我们在老家为大哥守灵。天下着雨,我和安坐在门口,看雨从屋檐上滴下来。安说,大哥那天用尽他生命最后全部的力量,是为了对她说,以后,凡事,要靠,自己。
大哥比所有人都提前看见了自己的死。
三
我感觉出血了。希在黑暗里说。
我睁开眼睛,突然变得无比清醒,从沙发上腾身坐起,按开灯,看见希穿着睡衣,手扶着肚子,站在客厅中央。我看向墙上的挂钟,时间接近凌晨1点。
我们马上去医院。我说。
希换衣服,我拿起她早就准备好随时能提走的袋子,查看她的病历、医保卡、她近几次做的B超和其他检查结果是否都在里面。女儿在睡觉,呼吸平静。我们担心女儿醒来发现自己一人独自在家会害怕,让餐厅的灯亮着,将两人手机中的一部放在灯下的餐桌上。她已经八岁,会接打电话。将来的事谁都说不准,没人能说得准人的一生中会遇到什么意外情形,但是最起码,她可以打电话。我这样想。
街上空无一人,深夜的南方小城除了风,只剩暗黄的街灯。十字路口信号灯闪烁,偶尔有车辆穿过。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握紧方向盘,把车速放缓。还好。希回答。她坐在后视镜照不到的地方,我看不见她的脸。
挂号,问诊,做B超,抽血,验血。深夜的医院不复白天的喧哗,一片安静。这是八月初,节气已近立秋,夜风中隐隐有一丝凉意。我和希坐在化验室外面的长凳上,看风吹动院子里那几棵香樟树,树叶发出细密的沙沙声响。周围寂静无人,B超室的女医生被我们敲门叫醒,做完B超又关上门睡觉去了。化验室的女医生被我们叫醒,正在灯下操作仪器。邓希,女医生的声音在夜里突兀而尖锐。我闻声站起,从玻璃窗口接过化验单。女医生打出一个哈欠,从里面把灯关上。
胎盘前置。我不懂这类术语,只知道它的意思,危险。大出血是最糟的情形。几个月前,负责产检的老医生对希说。也有人没事,有人年龄比你还大,从发现胎盘前置到孩子生下来,一点事没有,还是顺产,这个概率是存在的。我明白,这个概率是存在的,就像大出血的概率也存在一样。我向来把灾难发生的概率分成百分之零和百分之百两种情形:灾难没发生,百分之零;发生了,百分之百。别的概率没意义。只要不出血,就没事。老医生说。如果出血了呢?我不知道我在问谁。
出了血,就得保胎,胎儿还没足月,生下来很危险。接诊的女医生一边填住院单,一边说。谁更危险?大人还是孩子?我问医生。都危险,先住下来,看B超,羊水不够,胎盘遮住子宫口,不多,但存在危险,有可能大出血,一旦大出血,我们会按程序抢救,但是,任何事情都有意外,你们现在就要面对这种意外,你是家属?在这里签字。
是各种风险告知,各种死亡的可能。死亡?一瞬间,我仿佛掉进了一个时间的深洞。我伸出手,想抓住什么东西,可我抓不住任何东西。出意外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听见自己在问。我同样不知道自己在问谁,上帝,还是眼前的女医生?这个我们不能确定。女医生说。你得签字,签字我们才能接收病人。
希坐在诊室的长凳上,看着前方某处。她在想什么?35岁的年龄,踩着高龄产妇的下限,用一个母亲的执着希望再要一个孩子。我们得让女儿有个伴,将来凡事有人商量,才不孤单。她说。我承认,她是对的。就像我在这一刻,面对眼前的风险告知,没有人告诉我,签还是不签。我感到无限孤单。
希终于在病床上躺下来,药水一滴滴滴进她的身体里。我只能相信药水会起作用,会止住血。我握着希的另一只手,把耳朵贴在她的肚子上。他现在很安静。希说。安静就好。我抬起头,看见窗外天色已经渐渐变亮,外面的街上响起车声。接下来我得回家,叫女儿起床,把她安置到朋友家里。得找人去献血,女医生说,要预备1600毫升。我对1600毫升没概念,也晕血,但得去做。得打电话给希的姐姐,告诉她希的情况和各种可能的风险。得收拾好住院用品,做最坏的打算。风险一旦成为现实,那会是一连串的事,我不确定自己能否一一面对。
四
父亲的病床斜对的那间病房房门敞开,那个男人常常两手交叉抱在胸前,散淡地靠在门口,或者搬一张凳子坐在门口,看手机,看走廊里来往的人。病房里断断续续传出一个老人的呻吟,男人要么不理,要么转头朝向病房,高声说,要死就快去死,哼哼有个屁用,告诉你没人来看你,除了我,没有人。男人看我在看他,说,快死的人就这样,想吃这个想吃那个,他以为他是谁?有张床给他躺着等死,已经几好。男人踢开凳子,起身到走廊的尽头,点燃一根烟。老人的呻吟接着忽断忽续。
开水房在走廊尽头,我给父亲打开水时路过病房,看见里面一共三张床,两张空着,空床的病人多半和父亲一样,没事在家,打针输液时才出现在床上。靠墙的床上躺着一人,上半身挡在墙后面,看不见,只能看见两条腿,脚尖朝上,枯瘦,骨头突兀地挑起皮肤。
几天后有张病床空了出来,我把父亲转进病房,不再在走廊上守着父亲输液,此后没再看见男人,没再听见老人的呻吟。老人是不是在那几天死去,不清楚。他是否实现了关于吃或被探视的愿望,也无从得知。某天我再次经过那间病房,看见靠墙的病床上已经换上另外两条腿,陪床家属是个女人。女人看着床上的病人,眉头紧锁。
父亲搬进病房,邻床是个老人,家住附近。老人脚肿,两条腿肿胀如鼓,上面布满黑褐色的斑点。老人没人陪同,自己提一只袋子,一个人来,输完液,又一个人走。老人说话喘气,但很健谈,父亲和他有一句没一句说话。渐渐相熟,知道老人姓蔡,说起来与父亲的一名战友同村。于是聊起更多人和事,谁死了,谁没死,谁也快死了,等等。
父亲对死不陌生。那年夏天,父亲在晒坪上突然轰然倒地。我们以为是中暑,送医院,才知是脑出血小中风。我们兄弟几个轮流照看父亲。有天晚上我陪父亲,我看见,惨白的灯光下,生命像阵风,几日前都还强悍的父亲,还呼呼喝喝的父亲,和母亲争斗不已的父亲,转眼就成了一具沉默衰朽的残躯。几天后,父亲从昏迷中醒来,算和死亡擦肩而过。医生说,这次命大,只是小中风,再来一次,就没这么简单。
数日后的某个早晨,我扶父亲走进病房,发现老人已经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老哥好早,父亲说。老人侧头看了父亲一眼,两眼重新盯着天花板,没说话。过了片刻,老人说,死又怎么样,七十多了,什么没见过,死就死好了。我和父亲一时愣在那里,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老人第二天就没再来,留下一张空床,等待下一个人补上。这是医院,生和死,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生还是死,如同翻转一块硬币。
医生进来,为父亲量血压,按压父亲的双腿。情况不错,父亲的血压降了下来,肿胀的双腿稍微消退,复原已经没可能,但可以出院。以后坚持用药,不喝酒,不抽烟,不大量喝水,能多活几年。
我问医生,能多活几年?这哪说得准,医生说,也许一年两年,也许五年十年。我不知道医生懂没懂我的意思。父亲嗜酒,嗜烟,嗜茶。是不是因为嗜酒导致高血压,难说。要父亲彻底戒酒,没可能,少喝点可以。彻底戒烟也不大可能,从此不抽得太凶,问题也不大。但父亲这辈子都泡在茶里,一得空就茶不离手,一壶喝空立马满上一壶,限制父亲喝水,是要推倒父亲七十多年建立起的生活,基本没可能。所以,如果只是为了活命,这个不能那个不能,多活一年和两年,五年和十年,有什么区别?说到底,父亲接下来究竟该为谁而活?
五
能熬过今晚,就没事。那名医生从重症监护室出来,扯下口罩,露出一张微胖的脸。情况不太好,背上那个肿块,可能会要命,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打开监护室的铁门出来,把我们,我、安和闻讯赶来的姐和姐夫,招呼到墙角,用不轻不重的声音,为我们带来希望,也把我们推向绝望。
监护室外面是几张凳子,大嫂中午收拾好的住院用品散放在凳子周围,像一堆无用之物。大哥没能转去赣州,他无法躺下来,血压不稳,哪怕最轻微的颠簸都可能致命。医院征得大嫂同意,安排大哥转到重症监护室。
大哥被推进监护室的那一刻,大嫂就开始低声哭泣。她靠在椅背上,哭泣,一边催促安通过铁门向里面张望。去看着爸爸,给爸爸加油,你去,快去啊,你去给爸爸加油啊,让爸爸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一起来,给爸爸加油。大嫂的啜泣渐渐夹入昏乱的呓语,从午后,直到深夜。
我们站在监护室外面,等候消息。ICU的铁门像堵墙,隔着生死,隔着希望与现实。在等候的间隙里,我们说起两年前大哥突然的肺结核,说起大哥在市医院艰难而漫长的治疗,说起大哥的病始终无法确诊,长期的发热与疼痛原因不明,说起大哥偷偷吃下的那些镇痛药,疑点重重。我们还说起鬼神的力量,老家房屋的风水,门口不祥的深井,等等。大嫂的哭声从旁边的接待室传出来,尖细,隐约,不绝如缕。
哭声后来变成了嘶哑的呼喊,那时已是凌晨三点。医生从监护室出来,扯下口罩,露出疲惫的眼睛,对我们摇摇头,说按规程,他们继续抢救半小时,半小时后病人没反应,就放弃。大嫂伸出手,朝着门口的方向在空中抓挠。安,快去,叫爸爸回家,我们回家,你们不要抱着我,你们抱着我干什么,你们这些人,你们,抱着我干什么,安,你怎么站着不动,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大嫂的嘶喊最终变成了哀求。姐从后面环腰抱住大嫂,眼睛看着地面,一动不动。
两个小时前,一位老医生从监护室出来,说大哥背上那个肿块得彻底清除,他们没这个技术,得从市里叫医生上来做手术,当然这笔钱,我们得另外付,我们同意的话,他们就安排叫人,一个小时医生就能到。医生说,从大哥被送进ICU,他们就一直在组织抢救。老医生向我们说起溶血,说起脏器衰竭,说起手术哪怕成功,病人也可能因脏器衰竭死亡。
凌晨两点,一个年轻人在侧门一闪,进了监护室,片刻之后,年轻人在老医生陪同下出了监护室,身上已经穿上白大褂。年轻人告诉我们手术的关键,已经出现溶血,这些我们不懂。我们只听懂了风险,大哥可能死。我们把包好的钱递给年轻人,年轻人把钱装进口袋,进了监护室。之后不久,年轻人同样在侧门一闪,他已经脱下白大褂,从侧门离开。
在这里,生命脆弱而偶然。我听见,浩大的夜风从远处吹过来,拍打低处的云层、城市的楼房和树。风吹进窗户,卷起地上的纸屑。一个偶然出现的陌生人能改变什么?他的身影来去匆匆,我怀疑,他们其实更知道,当生命的大门缓缓关闭,一切都是必然。
大哥的遗体被推出铁门,他进去的时候坐着,出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担架车上。安看见大哥,身体滑向地面,痛哭。我和姐夫一左一右扶着她。我看见,大哥的双眼紧闭,再也不会睁开。我意识到这一点,左边肋骨一阵刺痛,我弯下腰去。大嫂在接待室里的哭声已经嘶哑,姐抱住她,不让她出来。
殡仪馆的人来了,为大哥穿上寿衣。大哥的身体被不断翻转,后背露出那只挖开的血洞。你们轻一点,别弄疼了我爸。安哭喊道。我们跟在大哥的遗体后面下了楼。殡仪馆的车等在门口,我们烧化香烛纸钱,风卷起纸钱的灰烬。大哥的遗体被搬上车,然后车门关上。
一个生命这才完全堕入黑暗。
六
剖不剖?你们商量好,要快。女医生扫了我一眼,尽管一脸不悦,但她已经没时间继续训斥我们。我的建议是马上剖,流血太多,产妇和胎儿都极度危险。叫你们静卧,你们偏要走动,还上下楼,搞成这样,出了事你们自己负责。女医生还是没忍住。我走进待产室,掀开隔帘,看见希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几缕头发贴在她脸上。床下是希脱下的衣物,被血浸透的衣物一片殷红。旁边的仪器在测胎动,声音像闷鼓,又像呼呼风声。
刚才我们从家里回到病房,希说要上卫生间。我放好坐便器,扶她坐好,关上卫生间的门出来,听见希在里面一声呼喊,我拉开门,看见卫生间里一片血光。这是大出血?我不知道。但我能想象,血如何倾泻而下。一片血光里,希浑身软下去。
一个月前的保胎,她的孕情其实已经大为好转,没再流血,羊水恢复正常,胎位没问题,胎盘上升了一点,尽管只是一点,医生说,乐观一点,不排除顺产的可能。我们松了一口气,想只要能撑到足月,必要时就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还是高兴得太早。一星期前,希再次流血,我们立刻住进医院,还是保胎,止血,打针,催肺泡成熟。医生说希必须静卧,不要轻易走动。正是九月初,天气炎热,医院里晚上蚊子成群,风扇对着吹,又怕着凉。这是产科病房,孕妇的呻吟叫喊和婴儿的啼哭此起彼伏。希住到半夜,在床上辗转反侧,没法入睡。她终于熬不住,提出回家。医生说保胎离开病房,太危险,但希坚持回家。之后希白天输液保胎,晚上回家,一连几天没事。直到这一天,血从她身体里喷涌而出。
剖不剖?我问希。希抬眼看着我,不说话。我知道她意思,胎儿没足月,生下来危险。可她要孩子,哪怕不要命。自从确诊胎盘前置,几个月以来,让我深夜从梦中突然惊醒坐起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时刻?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剖。我终于决定。我拿出手机,打电话给姐,告诉她希要生了,让她立刻过来。胎儿没足月,生下来就得进保温箱,我忙不过来。女医生和护士进来,把希推出待产室。
产房在住院部四楼。医生从窗口递出风险告知,我拿起笔签下名字。我没看内容,看了又怎样?希被推进产房,大门重新关闭。我和姐在产房外等候。我知道,希会先被麻醉,失去痛觉,然后在腹部剖上一刀,取出孩子,缝合,留下一道疤痕。我还知道,四楼上去是五楼,五楼是重症监护室。一年前的夜里,大哥在那里死去。我说过,在这里,生和死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产房里传出婴儿的啼哭,产房的铁门拉开,护士推着婴儿车出来。是个男孩,护士高声说。我迎上去,看见婴儿车里是一团皱缩的皮。他在啼哭,手脚乱动。他的哭声响亮,像受够了委屈,终于可以哭出声来。大人呢?我问护士。大人没问题,等下就出来,护士说。
姐留在产房外面,我把儿子送到新生儿科。医生提起儿子的脚,称重,量身高,做标记,放进保温箱。我回到产房门口,产房里没有声音,没有医生匆忙进出,没有仪器发出的尖锐的滴滴声。我不着急,我坐下来等待。
七
后来有一天,大嫂对我说,她后悔当初把大哥送进重症监护室。我明白她的意思。面对生死,我们什么时候该用力,什么时候不能勉强,不一定能由着自己。如果能站远一点来看倒好了,站远了看,单个生命会融入无数生命,个人的悲喜会消释得无关痛痒。可你没法站远了看,你身在其中。
所以将来的某一天,我会对我儿子说,好好活,你妈生你的时候,差点把命丢了,就冲这一点,你也要珍惜你这副身体,这是对你妈起码的尊重。你不是你爸你妈的私人物品,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由你自己决定,但前提是,当你准备伤害它时,先想想你妈。同样你要记住,你妈生你不容易,你不能长大了,就把你妈往死里气,你要敢这样,我第一个收拾你。
将来的某一天,我也会对希说,考虑到我们的年龄差,正常的话我会死在你前面,第一你别哭,每个人都有一死,时间迟早而已,像草木荣枯,没什么可哭的,管自己好好活。第二别让不相干的人碰我,不能把我翻来覆去,像翻一堆沉重的肉,也别往我身上插管子,我只希望干净体面地死去。第三如果我还能动,我希望你拉着我的手,挑一个地方坐下,让我安安静静回想这一生的爱恨和悲欢荣辱,看着它们在眼前烟消云散,就很好。
近年来,我的胸肋常常无端疼痛,严重时像根尖刺插进胸口,我站着,疼痛会让我突然弯下腰身。一位老中医为我把脉,说我脉相虚浮,是肝气郁结,痛在胸肋,此后凡事看开一点,朝好处多想一点,对病有好处。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做起来却不容易。那些生命里看过的生老病死,经历过的绝望和哀痛,要完全消化,不是那么容易。比如去给大哥上坟,当所有人都离去,我留在最后。我抚摸大哥粗粝的坟头,咬住嘴唇,不让哭发出声音,那时我听见,我的肋骨发出一声尖利的脆响。
看来,平复关于生和死的情绪,我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