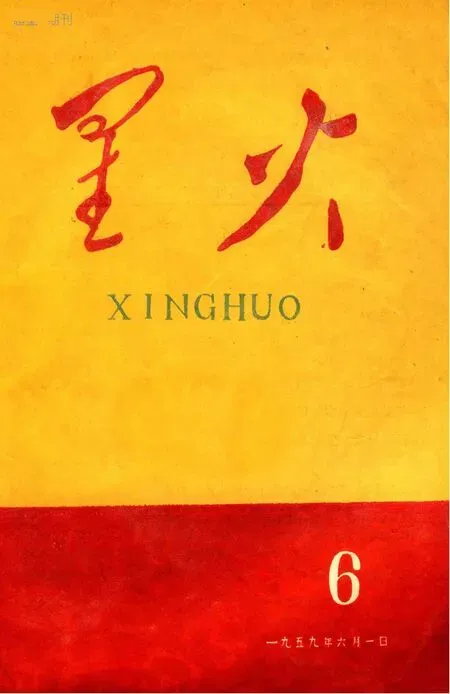旷野的耳语
2019-03-11籽落
○籽落
以日以年,我行其野;蔓草连天,如亲如诉。
1
与我上班的地方相邻,有一片旷野。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每隔几天去那里走一走。最初只是为了找个地方散散心,过滤一下几天来淤塞的情绪渣滓;后来,慢慢演变成“采诗”,我把脚步交给午后的光影,像是一名古代的行吟者;再后来,旷野给我的,就远不止这些了。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警龄:十年;工作地点:监狱。你不必讶异。对于一个工作如此封闭、单调又繁复,目之所及都是栅栏、电网的人来说,一片旷野的出现是值得感恩的。
单位东接高速公路,往西走三公里就是公园和城市,它们一个通往时尚、繁华、生存、社交,一个用来满足我的远行。以我每天上班的民警办公楼为圆心,往北方向的半径分别是:高墙、服刑人员改造场所、高墙、旷野;往南的半径分别经过:民警备勤房、家属区住宅、场区外的家属菜地、村庄、旷野。工作解决了我的稻粱谋,承载了入世的担当,而旷野盛放的,是那些在人群中的欲说还休,轻谧的治疗与修复。
时代里的浮躁因子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有自己寄托和疏通的方式。我身边的女孩们,有人清晨在阳台上面向朝阳做瑜伽;有人在一个钟头精致的化妆中消弭烦恼;有人乐于在老电影中体会岁月诡谲,时光轮回;有人在厨房虚度,研制现磨咖啡或缤纷的小点心。烟,酒,茶,奢侈品,古玩,旧物,爱情,物与人,无非是用来承担内心积攒已久的焦虑。而我,每次带着满身的火焰,只有往旷野中跑,往深草里扎,像一头饥饿的豹子。
通常是午后,当然如果是太阳暴烈或者风骤雨横,有要紧的日常事务,我就必须调整时间。我脱下警服,换上轻便的衣鞋,背上小包,带好相机,出门往左,行经一段香樟与银杏交叉的树荫,八百余步后进入路旁的村庄,涉过稻田,菜地,鱼塘,野松林,踏入旷野的腹地。这样的启程多年来我不厌其烦。
2
说来,我眼中的这片腹地,与中国南方村落里的大部分旷野并无太大区别。当然,于我而言,当工作和生活的鸡毛琐事应付不过来时,一片寻常、开阔和沉默的土地是够用的,然而腹地深处却有着浆果般多汁的体验。
第一次进入旷野,是九年前一个夏日的周末。我刚结束与朋友们的不欢而散。本来约好逛超市,再下午场唱歌,车停在闹市区的商场门口,我却突然闷在里面不愿出来,念叨着雪花片一样纷飞的工作资料、见鬼的加班就一阵头皮发麻。入世的喜悦和天蓝色警服的荣耀没持续多久,我已被盘根错节的事务搅得神经衰弱。
这样的时候,一次小小的放纵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朋友的慰藉也似乎隔靴搔痒。和大家告别后,我独自返回。像一个沉重的油罐,百无聊赖地进入这片旷野。
车辆的呼啸渐渐消失,野草在脚底蔓延,各种鸟啾虫鸣在头顶、在脚下,在看不见的角角落落旁逸斜出。我带着满身的火气大步暴走,来不及仔细辨认这些声音部落的方向。直到走在稻田间的空旷大路上,脚踩着雨后黏腻的泥泞,抬头望见辽远而未曾被高楼割断的天空,视野随地平线无限延展……那一刻,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放松与踏实。
就像一个人的思维只要不是太僵化,遇见对的东西,总能激活新鲜而美好的知觉。比如吃到鲜净的蔬菜,或者淘到一本好书,让人感觉瞬间连接上了时间深处隐秘的信号。我告诉自己,对的,这个地方是值得信赖的。
3
乐曲逐序进入低音部,密帘拉开。亲爱的旷野,每当这个世界露出它粗暴、狰狞,或者模棱两可的面目时,总是在我触足可及的地方,替我和现实拉开一段适宜的距离,为我梳理凌乱,怀柔炊烟一般袅袅升腾的哀伤。
旷野深处究竟有什么呢?
三小片野松林;
一大片野草与杂芒错织的原野;
几块百来平方的池塘;
几十亩不规则的稻田;
数百畦大大小小的菜地;
无数条土马路、蛇形小道以及田埂。
稻田像一口口炖锅,从一片漠漠平滑的绿渐渐煮沸为一湖金黄;
草丛间轻摆一小截腐木,瓢虫家族一厘厘行进,耗费秋日暖阳;
芒草反射层层阳光通往远方,一头小牛崽在璀璨中满地撒欢儿;
“凿破苍苔地,偷他一片天。”蓝天倒映池水,水面上几只灰鸭子,如在天空中凌波微步;
冬日大小道旁林立姿态各异的枯枝,随手可入瓶插花,有贾科梅蒂雕塑里的嶙峋;
村庄里,不断有人建红墙琉瓦的小高楼,另外一些数十数百年的老房子,因无人打理变得破败,在岁月吹拂中渐渐剥落,长满野蕨和青苔;
一蓬蓬不知名的花朵如粉白炸弹,蜜蜂军团一群群进袭,将其引爆。一只白色小柴犬路过,竖起耳朵,半晌未发出一声吠喊;
断壁颓垣处,乱花迷眼:蓟、臭牡丹、母菊、白檀、野蔷薇、益母草,乃至数不清的无名之辈,再微小的花粒,到了属于它们的季节,都在拼尽全力地绽放。
…………
我像是一个流浪者,又像是一个归乡人,总是轻易地激动,感怀,目瞪口呆。时间开始行走得缓慢,让人渐渐回到一种肉身的、温润的状态,像一个恢复喘息的孩子。
4
生活却并非历历分明,不会因为遇见一个好人,一件好事就一劳永逸。它布满了细节和褶皱,枝条横生。具体的事项尚有办法缓冲和调节,糟糕的是,在不短的时间里,我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怀疑,厌倦,甚至叛逃的念头。
记忆中有一次为了工作放声痛哭,是独自坐在办公室加班到凌晨,我给父亲拨了一通电话,对这个地方一阵抱怨:严肃、压抑、起早贪黑,罪犯是有期徒刑,连死缓都有机会减刑,只有我们是真正的无期……习惯了回之以正能量的父亲,只是在话筒那头留一小片沉默,任由我一波胜一波地咆哮。
谁没有过闪光的理想呢?在风华年少的时候,我曾一次次想象着丢下一切羁绊去流浪地球;我还憧憬着能在舞台上闪耀,活着不就为了炽烈燃烧吗?当看见朴树在后海带着乐队唱《猎户星座》,人们渐渐围过来,像被音乐带入一个久违而美好的漩涡时,我还是忍不住感动得热泪纵横。
谁不曾梦想着成为生活的英雄?
而我的工作呢?即使在兄弟队伍中,与电视镜头里公安民警惊心动魄的抓捕,法官扣人心弦的审判相比,我们注定是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封闭、枯燥、高危和寂寞。在舞台上闪耀就不要想了,想像徐霞客、余纯顺那样壮游?说的是南辕和北辙吧?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规划着离开这里。去哪儿都行,开个书店,或者丢下一切跑去西藏支教,最次,考到其他的公务员单位去。
希望一次次在规划表上破灭,我原封不动地站在这里,时间在特殊的语境里持续推进。儿时的故事,看起来真的是骗人的。
童话里,勇士斗败了恶龙,人们过上万事大吉的生活;神话中,孙行者变幻七十二般招数,无计可施时,自有各路神仙显灵,令魑魅魍魉现形。故事里没有讲,现出原形后怎么样了?关住了肉身,是不是就锁住了罪恶?故事里没有讲,他们也要吃饭、睡觉,会生病,会思念,有一天他们还将回到人们中间;故事更没有告诉过我们,有那么一群人,每天陪着他们等太阳升起,看星月落沉,需要走过怎样一段动荡的心路?
…………
不堪重负的时候,我只有旷野。最初的邻村及其腹地已经不能满足双脚了,那就往更深处,炊烟依稀,绿芜升腾处迈进。
5
事实上是,不论哪个时辰,与我同时出入这片旷野的,都没超出过十个人。越往深处,人就更少。我常如入无人之境。他们零星、寥落地出现。除了高草中迎面走来的荷锄老农,从不曾对视过的菜地里的妇人,一些来回路过的村里人,我还曾三番四次邂逅过一个打扮得非常雄性的女生。
她短发方脸,约莫着二十来岁,每次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哭。有一次,她边走边哭经过我时,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之后,狠狠掐了我一把。走近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精神失常者。尴尬的是,她也是我目前唯一发现的,和我一样被人投以怪异目光,漫无目的的陌生人或闯入者。
我时常会回想起她的眼光,就像小孩子受了责备,要把这份委屈告诉全世界。也许我不该贸然给一个人下定义,往深里看,我和她不过是程度不一的焦灼症患者。对的,我是一名头顶盾徽的人民警察,这并不代表我就金身坚固,永远向阳。
娱乐至死的雾霾同样笼罩在这个群体头上。我们也会深夜睡不着,清晨丧失动力去迎接新的朝阳;我们很难好好静下来吃一顿饭,总是心事重重;我们没办法耐着性子好好读完一本书,不相信它能给眼前的烦恼带来哪怕短期的平复。于是我们打开手机,一遍一遍地刷朋友圈,用足够抓人眼球的词句,营造一种存在得挺滋润的假象;或者干脆瘫软在沙发上,淘宝、微博,以主人翁的心态对当下的热门话题进行一番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当我们再次像鳄鱼一样把头从沼泽里拔出来,似乎觉得内心的焦躁得到了缓解,但又如此深刻地感到虚空。除了视网膜的老化与超负荷,镜中的自己,灰扑扑的,像一枝没有根系的植物,水分一点点蒸发,飘散,无迹可寻。
日子白白流淌,心却如入无物之阵。不知有多少人拥有这青春,却重复着同样的心路,上班,下班,吃饭,锻炼,带孩子,睡觉,活得像一个完全正确的公式。看似正常,却总觉得哪里有蹊跷;看似平静,却时常感到海啸暗生。我问自己:我自己的核心呢?如果此刻死去,有什么能代表一个独一无二的我?
当然,也有人并不感觉有什么异常。他们紧紧拥抱着生活,未发出过一声疑问。而我,需要被丢到时间之外。
6
旷野无言。千百年来,它就这样停留在这里,也并没有什么不寻常,无非是一片红枫叶落在地上瑟瑟,我把它捡起来轻握在手里;一枝芦苇伸向天空光影摇晃;微风过后,樟树林的细碎小花飘落如雪……赋予它意义的,无非是行走其间的频率与时间。
一个把傍晚的散步献给它,希望多呼吸几口新鲜空气的人,和一个把每一天的隐秘思索呈现给它的人,感受是不同的;一个住在城市,偶尔前来体会乡郊野趣的人,和一个对星辰大地有着深切乡愁的人,获得的启示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人,最初拿着相机行行摄摄,到后来有了和它一样缄默的眼睛,不可同日而语。
广袤的绿意与空旷清洗着人的眼睛,在这里,人的嗅觉和听觉也变得较以往更敏锐。或者更恰当一点:那些细微的事物暗藏在深处,命令你清空头脑,全身心地专注。如果一个人,愿意花上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日,走进旷野,保持这种专注,就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那枝叶间跳动的小鸟,簌簌飘落的花粒就是你自己。没错,你可以感觉自己身躯无限缩小,小成一只鸟的形状在唱歌,再小成一颗花粒的重量在坠落。
我曾和朋友Y分享过这种心绪。“一切都是我们的外化。”他神色淡泊有笑意。当下我脑中某个部位似乎猛然间被打通了,是的啊,目之所及,天光云影,草木枯荣,都是我啊。许巍唱,“我们是山之子,我们是风之子”。我们已经有多久记不起自己是大自然的孩子。只有被它映照、激活,生活的质感才得以真正诞生。
继续往深处,行走,行走,不在意荆棘扎破皮肤,泥土溅满鞋裤,直到远离世俗与人群的喧嚷,脱下条条框框的束缚与羁绊,感受到一种充足的:静。是的,静,如同一颗明矾,沉淀心湖。在持续而巨大的寂静中,渐渐理清,什么是身外之物,什么是真正的珠宝;什么可以设法解决,什么需要静待时间。静极生慧,佛经一语中的。安静生出一种平和与明朗,让人置于其中,一点点敢于解剖自己,再一点点敢于俯视黑暗,然后,转身,回归,准备煤炭,为爱和微笑发电。
在旷野中行走久了,就恍惚觉得自己是古代赶路的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在时光中赶路的人,似乎都曾穿越而来,接受一片旷野的检阅。旷野中储存了多少人的心灵档案呢?
人们急于建设城市,或者改造村庄,有一些村庄空着,一些郊野得以荒蛮。真是奇怪啊,它如此荒芜杂乱,却让心感觉到四平八稳。打理它的人是谁呢?他在哪里?为什么我两手空空而归,却觉得被喂饱?
7
今年三月末的一个夜晚,我和朋友L在他古村的工作室小聚。那时雨已经下很久了,从冬天下到春天,天潮潮地湿湿,一点没有要停的意思。他架起炭火,我们围炉而坐。在雨水中快要发霉的心事,这个时候开了闸,兴起处他聊起自己的一些“特殊体验”。
“你知道吗?我常感觉到有精灵,”忆起儿时的往事,他变得越来越健谈,“小时候我跟爷爷住在山上的窑洞里,一到夏天的晚上,万籁寂静的时候,我就听见精灵在外面,在树叶上,在风里面穿梭,对了,就像宫崎骏动漫里的龙猫!”我安静而体贴地听着他将此类情景一一道来,不时点头回应。
“你发现,在日常生活背面有一个神秘的场。”我停顿了半晌。炉火里烤的红薯熟了,发出清香,我们分别钳出一个,抬起脸继续交谈。“对,很真切的场,只是长大后,渐渐弱下来了。”
这一晚,我们聊到把他刚买来的一袋木炭都烧光了,茶水接连换了两壶。我脑海里反复与他描述的星光满天的夜晚,深山的窑洞,还有那一阵轻灵而神秘的脚步共情。绿野仙踪,对的,我在旷野里,不也发现他留下的蛛丝马迹吗?不过我所遇见的,不是L口中轻盈的精灵,是一个更有威仪、更沉穆的所在。
旷野,当我们轻声念出这个词,上颚缓缓往口腔深处退,思绪和舌尖便会接着往时空的无限深处延伸。诗意,辽远,新鲜又荒莽,包罗万象又单纯如一。
8
如果命运有扩音器,那最可能出现的地方,一个是医院,另一个就是监狱吧。医院是病痛引发人哲思,所以有了史铁生关于生和死的一系列深度逼问与追索。而监狱,是把一个人所有身外之物拿走,并把他推进一道深渊。
据说《等待戈多》在美国一所监狱上映的时候,引起了服刑人员龙卷风似的反响。剧中渺无人迹的荒野,孤零零的枯树,戈戈和狄狄语无伦次的对话,日复一日循环往复又毫无期望地等待,得到了他们前所未有的高度共鸣。贝克特制造了一种从形式到内容,从语言动作表情到情绪乃至灵魂的虚无、荒诞和悲凉感,与他们的遭遇深深契合。
在这样一种心境的深渊中,名和利自不用说,来自整个社会的舆论压力,两手空空,人情冷暖一夜尝遍。左边是奴役,右边是等死,前方是虚妄,后方是罪恶,乃至对作恶心态的习以为常、寸步难移,所有的等待可不就像贝克特笔下的那两个流浪汉一样徒劳?
但自由总是相对的。作为民警的我们何尝不是禁锢重重?作为服刑人员的他们何曾彻底丧失过自由。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傍晚,我带着一群孩子在监狱大门外的空地上玩“老狼老狼几点钟”的游戏,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院子里,几乎同时,墙内响起一阵整齐的踏步和嘹亮的歌声。那一刻,我抬头看见月光高悬,清寂不语。我忽然想,在所有宏大叙事、神秘猜测和人们暧昧的言语背面,无处不在的栅栏内部,他们终归要把日子过回日常。没错,月光同样照耀在这里。
清风的吹拂如是,花朵的盛开如是。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适应了一名监狱人民警察的角色和节奏。当真的有机会离开的时候,竟有了些不舍,甚至慌张。是的,罪恶与救赎,自由与束缚每天都近在咫尺地上演。我发现,我守着一座黑漆漆的宝藏。
我关注的是,面对这一大群特殊的病人,直面阴郁的底色和改造的日常,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思维,才能在日常中传递威严?神性与兽性对峙,慈悲与私欲博弈,我们需要具备怎样的内心力量,才能让光源充沛?
9
村庄日渐异化,像一只渐渐颓败的兽,只有风和植物欣欣蓬勃;人们成群结队出走,留下更多的沉默给故土。在村庄,死去的人比留下来的活人多。
旷野中,墓地几乎出现在任何你所能想象以及无法猜测的地方:稻田、菜地、马路边、房前屋后、村委会门口、祠堂对面……活人在意的是活人的活法,并不介意与死去的人共处,相较于生存而言,这并非大事;再加上此地多平原,少山丘,平地上又到处建新房,难免与墓地狭路相逢。村里人讲究风水,觉得这是吉利。
印象中,有一次在大片芒草地旁走着,乌云压境,仿若世界末日。环顾茫茫,空无一人,只有沿路几座散落的坟茔。那时我想到了自己的死。有一天我也会和他们一样,委身于小小的椁木,变成一堆白骨,甚至白骨也无,发不出一丝声响。生与死,距离如此之近。死亡,这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像野草一样裸露于大地。我忽然不那么害怕它,就像不害怕衰老。我害怕的是,自己来人世只是稀里糊涂打了个卡;我害怕年轻的时候从没有放飞,也不曾为什么而奋力燃烧过。
真的有幽灵吗?目前没有任何确凿的科学证明,人离世后是真的像风中的灯笼,一吹就灭;还是留下灵魂在我们无法探究的维度游荡。但可以推断的是,如果真的存在幽灵,那他们势必因为脱下了欲望和执念,因为对纷扰红尘的不在场,而有了纯粹和理性的质地。真的有什么可以不朽吗?为什么有的人在生时就具备了幽灵的特质?
在风吹草动的细节里,我有时也能捕捉到他们的线索。在竹篱围住的一朵豌豆花上,纷飞三两黄蝶,我和陶渊明不期而遇;在野草深处,我读懂了鲁迅先生的题辞,以先生同样的姿态,守望地下熔岩的迸发,几度挥泪如雨;临水而站,我感受到了卡夫卡的紧张与用力,试图撇开偏见与谎言的淤泥,触摸到坚硬的礁石——我们所处的现实生活本身……还有更多没有名字,辨认不出朝代的幽灵,衣着敝旧,神情落拓,一个个穿越历史的尘埃,从旷野中走来,对我招手。
会不会真的是这样,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道时空的口子,一个wifi连接口?然后在某些微妙的契机,会有亡魂穿越时光的魔道,从一片草一朵花一条河上醒来,与你相认?我可以笃定的是,他们身上携带着我的,遥渺的乡愁,一种类似于前世今生的东西。
10
时代迅猛地发展着,我们的头顶每天都像被一台大型搅拌机飞速地翻腾,难有一丝蔚蓝。这是一个最不缺“神”的时代。人们似乎越来越推崇一种独立、享受和洒脱的生活模样,仿佛有了这样的生活就达成了一种高配的理想。男神女神们只需要盘腿而坐,拈花微笑,就有无数人趋之若鹜。
通透,对这样的词语我总是持有一种本能的怀疑。当拨开潮流、消费、人设、流量、包装的层层泡沫,终还是抵达让人无比眼熟的那两个字:名利。天下熙熙,食色性也。“神”屹立的稳固度,区别只在于包装的精细度,有的拙劣,有的高端,而有的神不知鬼不觉。人群攒动的热搜和论坛里,售卖着一筐又一筐瓤红皮绿的瓜。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幻灭感格外丰富的时代?
回到最初的问题:有什么是真正不死的吗?有人开始适应荒凉与虚无,投入剧目中的表演;也有人不死心,被远方似有若无的信号所诱惑,走进深山、走进大海,走进繁华的都市;当然也有人和我一样,走进旷野。
旷野,从万古洪荒中铺展而来,历经了朝朝代代的兴衰,被烈日炙烤,被风雨暴注,被野火焚烧,今日依旧将怀抱无限敞开着,生生不息。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这颗星球上始终留有一片片旷野,拽住时间的脚步,让生命接受天道人心的审问。神不轻易降临,幽灵却不吝啬登场。
旷野中的人,如果有幸可以和一位幽灵共情,也许,可以生出一种幽灵的视角——跳脱一具肉体,一层关系,一段历史,一颗星球,回归一个最朴素的命题:秩序。神存于秩序之中,秩序存在人的心里。在追逐唯美和轻盈的时尚里,总还需要有那么一些人,逆流而上,把崇高和严肃这样老掉牙的字眼刻在心上,践履躬行。
我终于明白:比扮演通透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独立从何而来;比获得多少更值得借鉴的,是我们能以多少良知、怜悯和魄力来填充自己的生命。
忽又想起了小时候,那个扎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每一年的四月,她都要行经很长的一段原野走到外公家。大人们在前面聊天,谈正事儿,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里像是放飞的鸟儿,一会儿把枯枝折断,将鼻子贴近深嗅它的芬芳,一会儿为出岫的一朵白云心旌荡漾。童年,似乎就是在大人们交在后背的手和她不断迷失、追赶的那一段又一段田野的距离。
时间过去很多年,她再一次被召唤进一片旷野。脚步不复儿时的雀跃,曾经提出的疑问,也没有得到全部的解答。只是每一次从那轻柔的耳语中归来,她都觉得,呼吸得到了再一次均匀,行走尘世的步调得到了一次微小的修正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