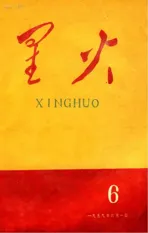秘 境
2019-03-11○蔡瑛
○蔡 瑛
1
没想到,我会被一个梦绑架。
我梦见父亲,他独自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形神衰瘦,面容枯槁。他看着我说,妹仂,我病了,你怎么不来看我?父亲的眼睛像一口枯井,周身散发着腐朽的气息。父亲,在他去世之后,一次又一次,以枯萎的病体,进入我的梦。
父亲生病之前,特别生机勃勃。他看书,练字,晨跑,写作,行走有风,说话利落,笑声洪亮,吃起东西来嘎嘣脆,健康得像个年轻人。头一年,父亲陪母亲去上海检查肠胃病,我也随同。那次上海之行,父亲照顾迁就妻女,全程拎包打头阵,全程精神抖擞,像一个骑士。以至于,我只顾着紧张母亲的身体,完全忽略了他。
父亲生性良善,见着谁都客气,和煦,春风满面的样子。父亲还爱笑。我没有见过比父亲更温暖明亮的笑容。他的笑容很充分,很开阔,甚至很纯真,眼睛眯成弯缝,皱纹漾开,面容舒展,露一排灿烂的白牙。笑着的父亲,很像是一个老人,又像是一个孩子。父亲牙齿很好,整齐洁白,嚼再硬的食物也不在话下。他常以牙齿为傲。如果再多活些岁数,到七十,八十,甚至九十,父亲依然会是个耳聪目明贪吃爱笑的可爱老头儿。
那时候,我从没设想过父亲的病态。可当他突然走了之后,我所有的梦里,全是他的病体。我的梦里,只剩下衰弱的,苍白的,被死神紧紧拽住的父亲。
我知道,肯定是我的记忆在哪里停住了。就像一条搁浅的船,它兀自停留在那,动弹不得。越是挣扎越是深陷。
我写了很多关于父亲的文字,可我从来没有写到那个晚上。我有意回避它,像回避一条毒蛇,一场病痛,一个谎言。可是,越回避,它越缠着我不放。每一个有着类似场景的夜晚,它都会无声无息地来到眼前。我完全无法控制,我的记忆,偏执,任性,死死地纠着那个夜晚,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我的梦逼着我要对它做个交待。
那天,父亲身体里的癌细胞发了狂。父亲痛得无法抑制,我给他服了吗啡,仍然止不住痛。父亲的身体在疼痛面前,像蛇一样,蜷缩着,扭动着,颤抖着。我们度秒如年,乱了方寸。傍晚,我们决定送父亲去县医院打杜冷丁。德保伯摇头说,看这情况,不好再折腾了。我虚弱地坚持,得止痛啊。得想办法呀。我固执地扶起痛成一团的父亲,给他编造童话,爸,我们得去人民医院,去打一针就不痛了。父亲巴巴地看着我,他一直那么信任我。我们分了两辆车,两个女婿一辆,去打前站。另一辆,二妹开,坐我和父亲、母亲。父亲安排在前座,前座可以放平,方便父亲躺着。临行时,母亲突然说怕晕车,想坐前排,便换坐了女婿们的车。妹妹开车,我坐在后排照顾父亲。车一路颠簸,颠得人五内俱焚。父亲躺得一点也不安分,像做戏法一样,一会躺下,一会起身,动静大得反常。我一只手托着父亲的头,一只手握着父亲的手,他的每一次动作都牵扯着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亲安静下来,安睡一会,顺顺利利地到达医院,顺顺利利地止住疼痛。天色渐暗,我心头一片焦黑。父亲突然问我,妹仂,到哪了?我含糊地说,快了,快了。父亲不再说话,像是被刚才那句问话累到了。但他仍是止不住折腾,躺下,坐起,躺下,坐起,像是身体里面藏着一只横冲直撞的魔兽。
车拐进往县城的公路后,父亲突然安静下来。路不再颠簸,两排的路灯明亮齐整地迎过来,像一个温暖的拥抱,又像一个明朗的预言。我突然发现父亲的神色有点不一样了。他像是要睡去了,他的眼睛半睁着,暗沉,浑滞,像口枯井。他张着嘴,喉结艰难地蠕动,仿佛喉咙深处藏着一个欲言又止的秘密。我意识到,刚才父亲反常的举动,是在与濒临的死神抗争,他已经尽了所有的力气。我对妹妹说,开快点,快点!爸好像不行了。妹妹说,姐,我不敢开快,我的腿在发软。我顾不上接她的话,我得跟父亲说话。我说,爸,你别睡呀,咱们聊聊天吧,你看老三老五还没回来呢,你儿子都还没结婚,咱家好多事呢,你不能不管啊,你要耐心点,坚持住,马上到医院了,到医院打一针就好了。我们来倒数一百个数。100,99,98,97……
我的声音在我头顶上嗡嗡作响,像盘旋着一架失衡的飞机。我听不见自己在说什么了。我感觉自己像一摊烂泥。我想逃开,想看别处,可我还是看到,那双眼睛在一点一点地黯淡,燃尽。我闭上眼睛……
我不确定父亲是在哪个时刻走的,我也不确定我在哪一刻放开了护着父亲的手。我只知道,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怯懦,惶恐,逃避。我面对至亲的死亡,面对生命的终极真相时,像一个在战场上畏缩脱逃的衰兵败将。在某一刻,我甚至怨母亲,她没有跟我们同一辆车,她没有陪父亲最后一刻,她把这种境地独留给了我。
我的父亲,在我草率的决定下,在我虚弱的手中,在去往医院的路上,匆匆去往另一个世界,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到了医院,大家把父亲抬往急救室,一阵忙乱与哭喊。我不敢看父亲,我蹲在急救室门口,全身发冷。随后赶来了几个管事的亲戚,叫了一辆货车,帮忙买了草席,爆竹,将父亲抬上货车。我们几个跟父亲一起坐在敞开的后车厢里。夜半,满目漆黑,一片死寂。几声爆竹,冷不丁地,像过气演员谢幕时稀拉的掌声,愈显出一份凉薄。父亲躺在草席上,终于不再折腾。几个亲戚在哭丧,嚎着嗓子,说些凭吊的话。母亲也在哭。母亲是知识女性,年轻时与父亲生过嫌隙怨怼,老来相互扶持和睦融洽,却好景不长。母亲的哭丧也随了乡俗,哥呀哥的拉着悲切的唱腔,说些前尘往事与来世今生。母亲连名带姓地喊了父亲一辈子,临了,道出一声亲昵的哥来,那人却是听不到了。
我很恍惚。这样一个深夜,我们坐在一辆货车上。这辆货车的后车厢里躺着我的父亲。静默,枯瘦,冰冷。万事皆休。远处有灯火,有狗吠,有人在梦呓,有人在狂欢,有生命在呱呱落地,也有生命就此终结。我第一次,如此真实地嗅着死亡的气息。它如此平静,如此平淡,像身旁的风,像眼前的夜,像扬起的尘土。它仓促得让人措手不及,轻飘得让人无所适从。我看着父亲,那个原本热火朝天生活着的父亲,成了我脚边一具无声无息没有面容的身体。他的情感,他的记忆,他的执念,是什么时候统统从这具身体上撤离的呢?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他对尘世怀着无比的善意与感恩,怀着无比的热爱与留恋,可世界顷刻就把他抛弃了。我感到无比悲凉。
那个夜晚之后,世界依旧前行,我记忆里的某个点却静止了,它停在了那一刻。后来,在很多个类似的夜晚,坐在某辆车上,四周静谧,路灯桔黄,突然地,我就回到了那个晚上。父亲的病体与遗容在眼前交错。每一次,我都着急地想要推开它,擦掉它,替换它,我想把那个晚上从我的记忆里彻底抹去。我努力地去回想生病之前的父亲,在院子里打理花草的父亲,在厨房给我们包米饺子的父亲,大包小包扛着行李将我们送到村口的父亲,晨跑的父亲,吃东西嘎嘣脆的父亲。我还拼命去回想,从前的从前,因为我的任性追着要揍我的父亲,因为我剩饭罚我跪的父亲……那些父亲,有时慈爱,有时严厉,有时可爱,有时可恶,却都鲜活,生动,可亲。我死命拉住他们,跟我的记忆较劲,可那个晚上的父亲轻易就覆盖了他们,虚弱而执拗地立在我的眼前。
父亲用了一辈子来让我理解与深爱,却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颠覆与定格了我的记忆。我一次次跟我的记忆讲道理,你怎么这么偏执,这么残忍,我是如此爱他,我的父亲,他是那样一个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是一个努力要活得阳光活得体面的人,是一个拥有这世上最温暖最明亮的笑容的人,你为什么,偏要记住那个他最不愿意让人看到的灰暗枯萎的时刻。我说得那么真挚动情,让我自己泪流满面,可记忆听不进去,我打动不了它。
它一意孤行地进入我的梦。
2
一条污水沟突然闯进我的梦。是的,一条污水沟张牙舞爪将我围困,我惊惶地醒来。
我们大概都做过一些奇形怪状的梦,它们面目暗黑,气息诡异,看起来与我们的日常毫无关联。但细究起来,也许是一条通往记忆的秘径。
我的村子,原先很脏,到处污水横流。八十年代,是常有的吧,村子里到处是各家的茅厕,粪缸蓄了半满,还来不及挑走,下场雨,粪水便自溢了出来。地上,沟里,下不了脚。我家也有砖厕,在后院。我总是到邻居桂保叔家的坐厕解手。坐厕,当然是坐着的,粪坑用木板隔起,搭一条座板,后面撑着两根木棍,八字型,不但可以坐,还可以半躺。家里人多,活也多。趁着上厕所的工夫溜个号,拿一本琼瑶或金庸,一坐便是大半个小时。那个时候,上厕所简直是美妙时光。那个坐板,被无数的屁股磨得光滑圆溜,很人性化了。除了茅厕,还有猪栏。我家前前后后都有猪栏。猪栏里除了猪,当然是猪粪。猪吃得多,也拉得多,粪满为患,遍地横流。
我不知道,这些景象,是不是一条污水沟的隐秘支流。
我曾经在我的一篇散文《房子,房子》中写到我老屋不同寻常的后门。要交待一条污水沟的来龙去脉,必须说起它。从我有记忆开始,我老屋的后门便是堵着的。邻居紧挨我家后门盖了一间猪栏,堂堂地将我家后院占了大半。猪栏离我家后墙的距离,我没有实际测量过,童年的我,四五十斤的干瘪丫头,侧起身子刚好能过。因为常年见不到日头,那里阴暗潮湿,墙体生满湿癣般的青苔,脚底下也常积有污水。污水的来处复杂可疑,有雨水,潲水,粪水。积久了,就成了一条污水沟。
后院是我的秘密花园,因为那里有一棵柚子树。柚子树是祖上留下来的。那棵柚子树芬芳了我的整个童年。夏日,柚子树舒展着臂膀,在后院中间撑起一片清凉。我拿本书,踮着脚穿过污水沟就去了后院。午后,大日头下的村子有些倦怠了,它闭上聒噪的嘴巴,渐渐地,呼吸平缓,鼾声细微。只有几只知了和远处的货郎仍执拗地扯几嗓子,知了,知了。卖货咯,卖货咯。催眠曲般,愈显出一份深深的静来。偶尔一阵风过,叶子嗦嗦几声,抖落大把花香。我坐在柚子树底下,捧起书,一切的声响都虚无了。那自然不是一个极好的阅读场所,猪栏在侧,绿头苍蝇在粪缸里抱团取乐,间或飞出来透透气跟我打打招呼。可谁也干扰不了我。我沉醉在书里,在柚子花香里。柚子花的香气,质朴,纯净,清雅,遮蔽了一切污浊。
父亲极珍视这棵柚子树。父亲三岁没了父亲,母亲改嫁后,只有祖母与这棵柚子树陪着他成长。他以这棵柚子树为坐标,盖屋设院,一点点地,给他单薄的生命开疆辟土,开枝散叶。柚子树是他生命的见证。后门堵住之后,父亲极少去后院了。但柚子的香味总是引诱着父亲,为了摘一个熟透的柚子,父亲像个孩子一样,夹着身板,一寸一寸挪着步子,淌过污水,翻山越岭般,从自家后门穿到后院。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记得我家后院的那棵柚子树,而把后门那条暗无天日的污水沟给忘记了。好像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它怎么可能会在一个小姑娘的心里激起波浪呢?
我在父亲走后,突然梦见这条污水沟。它在我心里无声翻涌,腾起巨浪。对父亲而言,它绝不是一条寻常的污水沟,它是人性的暗处,生活的暗处,命运的暗处。
小的时候,模模糊糊的,没有太多具体的记忆了。也许是,它们并没有多么明媚美好,我的记忆不屑于去记住它们吧。回想起来,全是一些灰扑扑的画面。大多数是雨天,雷声阵阵。大雨滂沱。闪电将天空炸开一个又一个口子。父亲一脸阴霾。外婆在唠叨。母亲在抽泣。邻居伍保和他四五个兄弟们乌央央地站在自家院子里,朝着父亲指手画脚、恶言恶语。伍保的女儿,和我一般大的春花,靠在门边上,斜着眼睛看我。我很想去跟他们对骂,还想去跟春花干一架,可我喉咙里总像塞住了东西,手脚也软软地提不起劲,憋屈得不行,也跟着母亲嘤嘤地哭起来。父亲蹲在厅堂抽烟,沉默不语。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父亲,总让我感觉有点孤独,还有点软弱。而我,竟也好像遗传了他的软弱。
那些争执,欺凌,是为着什么?年少的我并不完全知晓。后来才明白过来,是因为地。争地,也是争气,争命。
听母亲说,当初邻居在我家后门盖猪栏的时候,父亲几天都吃不下饭,像患了一场大病。村里辈分最长的锤子爷爷看不下去,拄着拐杖过来,一字一声地对伍保说,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欺孤凌寡!欺孤凌寡呀!!可有什么办法呢,父亲势单力薄,争不回祖宗的地。他生命中无端横亘起一条污水沟,让他不得不夹起身板走路,夹起身板做人。
几年后,村里一些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邻居一家也迁居景德镇。村子渐渐有了些变化,有些田地荒了,却次第长出一栋栋新楼。父亲突然要盖楼房,不容分说的样子,我不知道父亲为了这件事暗自存了多少心力。因为要绕过猪栏,辟开后院,他甚至做出了一个决定,砍掉那棵柚子树。父亲用了整整一年,推倒老屋,伐掉老树,在原地基上盖了一栋外观清秀可以打开后门的楼房。父亲在前院种上花草,栽上铁树,生活终于一点一点顺着父亲的意愿,有些扬眉吐气了。花甲之年的父亲计划着他的美好晚年。他这一辈子,被命运所负,让境遇压着腰板,一直憋着一股劲比别人更攒劲地活,好不容易活舒坦了,没想到,又被身体给负了。
父亲最后的时光,一直在书房里忙着给村子修谱。父亲退休在家,能写,有闲,又足够热心,是村子修谱的不二人选。父亲说,退休了,要一心一意为村子做点事。他每天一个人坐到书房里,抄抄写写,乐此不疲。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想给自己写个传。要让子孙知道咱家的历史,父亲说,不管你们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都不能忘了祖宗,不能忘了来时路。我有些不以为然,一个普通人,好好的,写什么传?父亲走了之后,我才回过神来。我有一次特意去父亲的书房,想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里找寻父亲的遗迹。那些成堆的稿纸里,全是一个蔡姓村庄的前世今生。他将他最后的心力与爱,交付给了这个给了他生命与伤痛的村子。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症,让父亲的后半生戛然而止。父亲没有为自己留下片言只语,仿佛他这一生了无遗憾。
今年回去的时候,村里已经没有了一点土路,地上更是看不到污水了。村里还添了垃圾运载车,每天准点唱着歌儿在村里游晃,每家每户都自觉地将垃圾提出来,交给它统一运走。母亲随我们进了城,家里的房子没人住了没人稀罕了。只是,每次回家,一打开门,那些灰暗的陈年旧事随着父亲的气息扑面而来,像一条汹涌的河流,让我喘不过气来。
梦,是记忆的秘密通道。无论是父亲的病体或是一条污水沟,都是我内心深处的隐疾。它们之间充满了关联,切皮连肉。我很少在文字里写到我的村子,对于它,我并没有太多明朗的记忆,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对它没什么深厚的情感。我重新审视我和它的关系,是因为父亲。我是父亲的女儿,也是村子的女儿,我和它永远脱不了干系。我的故土情结,是父亲用生命的终结来唤醒的。终结,意味着接续,意味着新的开始。我的梦,让一条污水沟,把我带回我的村庄,带回我生命的源头,一定是父亲的意思。他让我记着一条河的过去,记着一条河的本质,也记着一条河的生生不息。
为了覆盖与安抚我的梦,我将父亲生前所有笑着的照片摆满我的视野,客厅,书房,QQ空间,微信朋友圈。我随处都能看见父亲的笑。父亲的笑容,让我踏实,安宁,让我相信世间所有的美好与永恒。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儿子笑起来的样子像极了他外公,眼睛眯起,牙齿闪耀,一张脸,晴空一般明亮。他是个特别爱笑的孩子。他长相并不随外公,竟完全随了他的笑容。这个发现,让我鼻子一酸,心里溢满了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