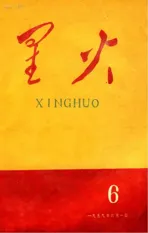一根角铁的生活
2019-03-11蒲素平
○蒲素平
一
父亲在玉米地里劳动的时候,他自己就成了一颗玉米。我在工地上劳动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是一节钢铁。坚硬的、粗糙的、无语的,一切用在钢铁身上的词都可以用在我的身上。
久久地立在工地上,直到自己也分辨不出来哪个是角铁,哪个是我自己。
角铁与角铁的命运也不同,比如有生存在室内,穿着精致的衣服,一生文文静静,不被风吹雨淋。有的一生在野外,见风淋雨。我看见一根角铁在夜晚被露水打湿,露水珍珠一样缓缓划过角铁的皮肤,慢慢湿透它,它不言不语。一根角铁,被大风吹动,被雨雪袭击,被阳光暴晒,它不言不语。其实作为一根角铁,它知道自己的使命,站在哪里都是一种选择,不一定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但不管怎么说,选择了就意味着使命,意味着一种坚守。这一点, 我们许多人比不上角铁。
一个人做出选择,往往有各种理由后悔,但角铁能找出理由后悔吗?能自动离开它的位置吗?不能,除非一种结果,就是它报废了。谁愿意无辜报废自己呢?不管是人,还是角铁,还是任何一个事物,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延长些再延长些。
在工地上,一根角铁夹在许多的角铁中间,被人从汽车上用撬棍一拨,哐一声卸下来,砸在同伴身上或地上,发出单调的声响。从此,一根角铁开始了自己一生的路。
英雄不问出处,不管一根角铁它过去经过了怎样一个成长过程,现在被卸在了塞外的工地上,它知道自己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是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它被一只手拿起来,看了看编号,被另一个人扛在肩上,走出几米远,咣的一声扔到土地上,砸起一小点狼烟。
几根角铁在工地上堆放着,一个人迈过去,忙别的事去了。角铁成为工地的背景,一个人走过来,又走过去,一个人和角铁习惯了成为彼此的景深,照出彼此的映像。
一根角铁被一只手拿起来,被一颗螺丝穿起来和另一根角铁连接在一起。它的周围是一节又一节的角铁,大的,小的,薄的,厚的,它们和螺丝连接在一起,组装成一基铁塔,站在旷野,站在山巅,站在生活里。
一根角铁,就这样淹没在更大更多的角铁之中。从铁塔下走过的人,分不清这根和那根角铁的区别,它们看起来似乎都差不多,只不过大小和位置不同而已。平原上、山尖上突然就增加了一基铁塔,一只飞过的鸟觉得很新奇,绕着铁塔飞来飞去,后来就把巢筑在铁塔的横担上。鸟从路边捡来小树枝,从铁塔下捡起小小的细铁丝,然后开始编织,像我们小时候编织梦想一样,编织出了一个精美的鸟巢。甚至一只从南方飞来的候鸟,认错了标志,耽搁好长时间后,飞向了铁塔旁边的村庄。
之后,铁塔成了候鸟飞行的标志。
一根角铁,在荒凉的工地上扎根,接受夜的黑,风的冷,雨的淋,也接受阳光的照耀,鸟的赞美。角铁从不知道孤独,角铁组成铁塔之后,铁塔担起导线在肩的重任,一种叫电的东西开始通过导线传输过来。每每阴雨天或大雾天的时候,从铁塔下经过,或站在导线下,便能听到刺啦刺啦的放电声。
这时候,有人会多看铁塔几眼,会发出赞叹声,嗬,这家伙真威武!瞧瞧,这电声响的!一脸的敬意。
这时候,每一根角铁都直起了腰,每一根角铁都咬紧了牙齿,角铁知道自己决不能因别人的赞叹而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更不能躺在地上享受赞誉。
四季的变化,在角铁的眼里,周而复始,自动轮回着。
有一天,我去检修铁塔,先绕着铁塔转一圈,用大扳手突然在铁塔的身上当当地用力敲几下,然后侧耳听听有没有呼啦呼啦的声音。就像一个医生用听诊器放在人的胸口,微微闭着眼,侧耳听。如果铁塔某个部位传来呼啦呼啦的声音,就说明有的螺丝松了,听出大概哪个位置的螺丝松了,我就得找到松了的螺丝,用扳手拧紧。我一边拧着螺丝一边观察。过去曾经锃亮的角铁,几年后变成了灰褐色,但依然棱角分明,依然腰板挺直。
我抚摸着角铁,依然冬天冰凉,夏天烫人。
在工地生活久了,我常常想,也许我也就是一根角铁,一根短短的,在人群中默默无闻又沉默寡言的角铁。在风中迎接风的吹,在雨中迎接雨的淋,在阳光中灿烂,在春天里开花。
在工地生活久了,慢慢的角铁的生活似乎就成了我的生活,角铁的性格就成了我的性格。
这说不上好还是不好。
二
据说坚硬的东西因缺少柔和,而不愿意扎堆,或者说因彼此的坚硬和独立,很少能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但角铁除外,角铁生下来就是为了互相支撑,就像树枝,枝与枝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生下来就是为了长出树叶,为了在天空舒展自己。
在工地上,角铁,一根一根被组装在一起,它们互相服务,互相鼓励,高处的、低处的,水平的、横向的,对于角铁来说无所谓,反正都是彼此撑起来,成为一基铁塔。这一点与人不太一样。在一个群体里,不同的人总是有着不同的面孔,不同的地位。
在工地上,我看见一根角铁踩在另一根角铁的肩上,这一根角铁正骑在那一根角铁的头上,一根角铁和另一根角铁拉着手。夜晚来临时,角铁在不停地诉说。
当成吨的角铁从铁塔厂出发,被火车运来,被汽车运来,被拖拉机运来,被卸在一个荒山上,这个荒山方圆几十米的地方就叫工地了。四周的石头寂寞地望着天空,多少年了?石头自己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石头多少年没见过除了荒草之外的其它事物了,石头突然多了邻居,石头有点小兴奋。
一个人寂寞久了,会不自觉向往另一个人的到来,这方面人与石头大约一样吧。
一些草正在干枯,一些草被角铁压在身下,时光由亮变黑,变锈,变得斑斑驳驳。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战胜不了时间。角铁能吗?角铁知道自己也不能,角铁能的就是一旦成了铁塔,就要像一基铁塔的样子,扛起责任,完成自己的一生。
我常常想,一根角铁究竟要怎样才能敞开心扉让更多的人理解?
一根角铁在荒山上渐渐陷入深思。
三
不远处的山脚下,一辆卡车突突突地开来,卸下一堆角铁。一个人拿着一根撬棍,这儿拨一下,那儿拨一下,用足够的耐心让一切变得整齐。
一根角铁站起来,又躺下,后背冲着另一根角铁,另一根角铁就沿着他的脊背,啪,啪,啪地走过去,角铁将走向哪里?
其实角铁知道,自己被运到这里,就是要组装成一基铁塔,不管大角铁还是小角铁,都将通过螺丝的串接而成为一个新的生命。角铁排着队从工厂里走出来完成自己的使命,角铁将按照图纸的安排,重新进行组合,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呢?
一只手摸索着角铁身上的编号,一个人在大声地喊着编号,一些角铁的位置被重新定义。
角铁与角铁之间的连接需要一颗或几颗螺丝,需要一把扳手一扣一扣把螺母拧紧。拧一下,一根角铁就与另一根角铁的距离近一些,几把扳手一起拧时,更多的角铁就以一种新的姿势连在了一起。
你支撑着我,我支撑着你。
你扛起我,我扛起你。
角铁和角铁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坚强的团队,成为一个铁的拳头。
一根角铁挺挺自己的腰,在风中,在无垠的旷野。
生活呢?没有铁塔之前的电,是弱小的,是不禁风雨的。最初的铁塔也是小的,比如35千伏的铁塔,单薄、矮小,甚至有点弱不禁风、羞羞答答的,后来到了110千伏、220千伏、500千伏、750千伏,今天到了特高压——1000千伏,不管是身高还是能量,都与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完美匹配。有人说,特高压的发展提升了中国能源战略,从重要序列上讲与原子弹和宇宙飞船并列,甚至比前两项更加令人振奋,因为它普惠了亿万家庭。能为普惠亿万家庭的事尽一份力,是一件光荣的事,我这么想,不知道角铁是否认同。
每想到此,我站在铁塔下时不由得会收腹吸气,会仰望点头,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自豪。
在工地的日子,我最喜欢春天踩在冒着热气的土地上,踩着刚刚钻出地面的小草。毛茸茸的,踩在上面,心情别提多高兴了。我一边唱着小曲,一边踩着小草走向铁塔。有时我是去组装铁塔,有时是去检修铁塔,有时什么也不干,就是想去看看铁塔,看看曾经被我抚摸过无数次的角铁,看看它们历经风雨之后的样子,和它们说说话,或者什么也不说,就是单纯地看看。
其实也不是单纯的看看,我有自己的使命,比如观察,比如记录。一个老农到自己的庄稼地里转转,不仅仅是为了赞叹自己的庄稼;一个农学家到自己试验田里,不仅仅是为了看看风景。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在的使命和外在的快乐。
我用力晃晃铁塔,铁塔一动不动。一根根的角铁,各就各位,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角铁就是这样,值得我们学习。
四
在工地组装铁塔的日子久了,我对每一根角铁,每一颗螺丝都生出了感情,对每一根角铁都反反复复地抚摸,好让每一根角铁都感到我的在意。
在意不在意一颗螺丝、一根角铁,它们是能感受到的。比如有时累了,烦了,疲倦了,拿螺丝或角铁的手就显得随意,充满了怠慢。这时候,往往本来容易安装的角铁就开始在风的鼓动下扭动起来,很难顺当组装在一起,像一个不配合穿衣服的孩子;一颗螺丝常常从手里无端地滑落,扑通一声掉到了地面上。这时候我知道得调整自己的情绪了,要把自己弄得高兴一点,快乐一点。人一旦快乐了,拿角铁的手就会专注许多,就会亲切柔和许多。
角铁有时像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感觉十分敏感。
横着、竖着的角铁,在工地站立着,一些施工的旗帜在工地上飘扬,高高低低的,令人瞩目。
一些人,在工地上走来走去,像戏台上的武戏,忙碌而充满了斗志,每一步都踩着鼓点,看着忙乱,实则有序,井井有条。
没事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长时间注视着角铁。
而角铁沉默着,冷静地面对一切。
更多的时候,我和角铁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互相支撑着站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一天又一天。任凭风吹雨打,任凭岁月流逝。
有时想一想,在阳光下闪着光的角铁把自己交给了我们,就像爱恋的女人把自己交给了我们,这是多么重的责任啊!我常常暗咬牙齿,我得把自己当成角铁中的一员,尽管有时我做得并不好,尽管常常感到疲惫不堪。我的队长常说,和角铁打交道久了,你就会成为一节角铁,成为了一节角铁,你就知道角铁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角铁在工地上被组装的人固定在一个地方,我们轻松地安排了角铁的一生。
谁又安排了我们的一生?
成为一节好角铁,不易啊。我们得学会珍惜,比如既然一生与角铁相遇了,与一个朋友相遇了,与一个女人相遇了,就要相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既有缘,必相惜,必在意,必有情。用一颗满含深情的心去感受一根角铁,一颗螺丝,一个朋友,一个女人。感受每一天的相遇,用一颗心去理解,去爱所有相遇的人和事物。
五
我习惯于太阳落山之后,抓紧这小小的间隙再干上一阵。这时候太阳的余晖在西边的山后红着,一些树的影子正在回归树本身,一些鸟在空中飞来飞去,它们在做着一天最后的活动,大地正在趋于安静。
干完最后一点活,从几十米高的铁塔下来或从几米深的基础坑里爬上来,用力拍拍身上的尘土,把工具一股脑放到拖拉机上,坐上去,突突地回住地。
拖拉机一路爬行在乡间无人的道路上。树们开始窃窃私语;两边的庄稼在打着盹,似睡非睡;一些炊烟在空中互相绞缠着,分分合合,升起又消失;几只大小不一的狗趁着主人忙于做饭,结伴在村庄里转来转去,好像在巡查什么。
一路上,拖拉机上聊天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有时又飘得很远,一部分撞到树的身上,返了回来。
走着走着,远远近近村庄上的灯光,就开始毫无保留地照着一切。灯光其实多么像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道它能照多久,不知道它有多明亮,也不知道它何时熄灭,但我们看见灯光就感觉到生命的存在和希望的存在。
灯光,在黑夜里亮着,照着一些树啊,房子啊,照着我模模糊糊的意识。世界变得虚幻起来,安静、辽阔。
当黑暗彻底淹没时,我们就到家了,其实就是到了住地,就是我们租住的房屋,那里有食堂,有宿舍,有好酒。
而此时,拖拉机上一准有人在梦乡里出出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