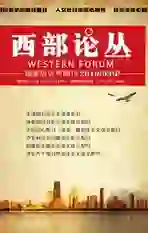“爱奥尼亚谬误”
2019-03-08廖瑞
廖瑞
摘 要:“里格斯诉帕尔默案”,法官厄尔在审理该案时援引了法律原则——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并结合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对抽象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法律。法律规则和经过严谨论证的法律原则结合适用于复杂疑难案件中,这不仅是权衡利弊的需要,更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
关键词:里格斯诉帕尔默案 法律原则 解释法律
若道德价值优先于法律施行,道德价值必定隐含于法律之中,这是对于道德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于法律权威性的尊崇。法律原则突破法律规则适用,法官必须负有论证义务,“原则在效力上高于规则”作为没有论证的推理前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容小觑的。[1] “里格斯诉帕尔默案”,是在适用法律规则遇到瓶颈时而援引原则的典型案例。
一、问题的产生:他能获得遗产吗?
1880年8月13日,富朗西斯·帕尔默立下遗嘱约定其孙,即埃尔默·帕尔默继承其大部分财产。十六岁的埃尔默·帕尔默常年与其祖父富朗西斯·帕尔默共同居住生活,也知晓其祖父所立遗嘱的内容。婚后的富朗西斯·帕尔默有试图改变遗嘱的明显迹象,埃尔默·帕尔默为此毒杀其祖父以期待尽快获得遗嘱中的财产。帕尔默的杀人行为可依法裁判,但埃爱默关于继承其祖父遗产的主张是否可以成立呢?
厄爾法官援引法律原则——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最终判决帕尔默因杀人行为被剥夺继承权。法律条文与社会价值的碰撞,追求合法性的努力变成徒劳,这不意味着合法性命题是虚妄的。[2]道德价值的评判在法律论证的过程中是有意义的,对于法条的苛刻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立法意图的束缚。
二、法官的睿智:“针尖对麦芒”
解释法律是用哲学的方法说明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本问题,其不同于对法律文本或法律相关具体事实的法律解释。[3] “里格斯诉帕尔默案”,厄尔法官拥有比格雷法官更多的支持者,厄尔法官的意见也彰显在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
(一)厄尔法官: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
规则文本是刚性的,对于问题的考虑具有局限性,价值判断和裁量自由往往伴生于柔性原则的适用。[4]《遗嘱法》的制定是为保障立遗嘱人能够有处置其可继承财产的自由,但继承人为获取遗嘱利益而杀害被继承人的行为绝不会是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故意杀害被继承人,应剥夺其继承权,这应是可以被立法者认同且是当时法律文本所缺失的规定。遗嘱合乎法律的形式程序,被继承人去世后,继承人可以依据常规的法律文本的解释请求执行遗嘱。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并不限于法律条文本身,法官被允许根据法律和具体事实而作出“合理解释”。法律解释是综合性的判断,需要语言文字的表述,获得确定的法律结论并保证法律的适用从而表现出对具体解释的思考。[5]法官享有衡平的权力,任何人却又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法官也无法严惩一个自杀流血的抑郁症患者。立法者基于国家利益以及考虑到社会的整体价值去制定法律,法律文本并不能完全体现道德。
遗嘱在立遗嘱人死亡后发生实际效力,依据“里格斯诉帕尔默案”需要考虑以下问题:第一,不能确定帕尔默一定在其祖父之后死亡,也不能确定其祖父不会更改遗嘱。第二,帕尔默为获得遗嘱利益而杀害其祖父,其可以被允许享有犯罪后的成果吗?第三,暴力夺取他人财产已被法律明文禁止,帕尔默的杀人获财的行为显然不能被认可的。厄尔法官认为:正义和自然法则对人是具有一定约束效力的,制定法没有对此作出规定不是源于立法者的疏忽,法律原则应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帕尔默有在其祖父去世之前就丧失继承权的可能,其不能通过犯罪行为而获得财产。厄尔法官的说理不是针对于案件事实,案件事实并没有太多非议,法和理的论证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格雷法官:法律是沉默的
判决不是基于道德而作出的,法律已经给出了限定范围。遗嘱的设立和撤销、更改等都已由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在已有法律文本的基础上使用衡平法理裁判,这是对于法律的蔑视,对于自由的无极限扩张。个人自由处置自己的遗产的行为需要有安全保障,个人的自由是以遵守国家制定法为前提的。立法机关对其设置了相关事项的约定,并加以各种特定条件的限制,帕尔默仍是享有权益的。案件的矛盾在于立法的缺席,立法的缺席不承认可以对正义规则进行“临时修正”。格雷法官认为,帕尔默因犯罪行为而失去获得遗产的权利需要法律来宣告,哪怕是以法律之名来撤销或修改遗嘱。制定法并没有关于撤销或更改遗嘱的规定,遗嘱的撤销或是修改需要外在的一些行为证明。在客观事实层面,帕尔默的祖父并不存在重新订立或撤销遗嘱的外在行为。虽然可以推测帕尔默祖父有重新订立遗嘱的意图,但其意图并不是法院判案所依据的客观事实,意图不能否定事实。
三、上下求索:“爱奥尼亚谬误”
“爱奥尼亚谬误”的核心观念是,所有问题都必然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并且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区别原则上是清晰可辨的。[6]解决案件的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是由法律内部给出的。法律原则的修改周期明显短于法律规则的修改,法律原则的适用也是对于法律的遵循。碰撞法则的构建,不是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敌对,而是建立起二者的亲密联结关系。“爱奥尼亚谬误”应适用于法院裁判,同时期内同案不同判是很难具有说理性的。笔者认为,这里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并不是对与其不同意见的完全否定。制定法的演进需要辩论,“唯一正确的答案”是必要的,其对于公众秩序的稳定以及对于国家政策的价值导向都是不可缺的。
注 释
[1] 林来梵,张卓明:《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从规范性法学方法论角度的一个分析》,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2] 何海波:《何以合法?对“二奶继承案”的追问》,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
[3] 谢晖:《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4] 张卓明:《用原则断案时的论证义务——以“里格斯诉帕尔默案”为例》,载《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5] 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6] 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