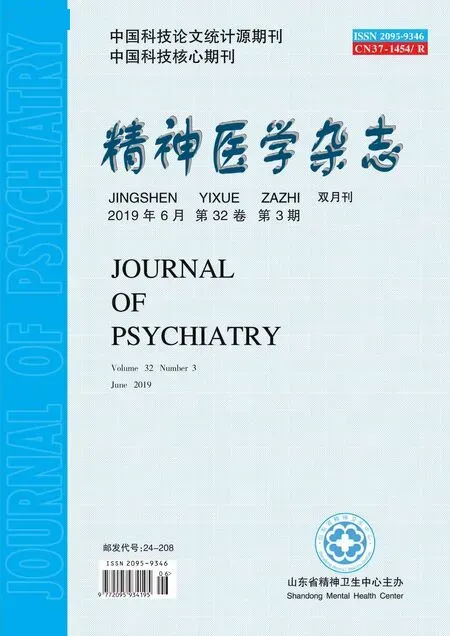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相关认知神经心理学理论及研究进展*
2019-03-05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一种在临床上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其症状主要在学前出现,主要表现为与年龄不相称的注意力缺陷、活动过度、行为及情绪冲动,并可共患学习困难、破坏性行为障碍(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 DBD)等其他精神障碍。ADHD的患病率一般报道为3%~5%,国内患病率为5.7%[1],全球各个国家地区均有本病发生,但可能因为使用的诊断标准不同使患病率各有差异。患病的男女比例为(4~9)∶1,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男女患者的症状表现有所差异、ADHD相关研究中女性未得到与男性相同的重视等原因,很多女性患者在目前的诊断系统中未得到适当的诊断与治疗。在ADHD的病因与发病机制方面,较为认同的观点是ADHD的发病来自基因与环境的共同作用,但具体病因仍不明确。
ADHD的认知神经心理学在近十几年内一直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为病因学研究、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了数量可观的理论基础。本文简要概括了ADHD认知神经科学主流观点,并分析它们在基础和临床上的应用价值及优缺点。
1 抑制缺陷模型
Barkley RA[2]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抑制缺陷的理论模型。此模型认为ADHD的首要缺陷是反应抑制不足,这种不足涵盖了抑制的全部三个方面:第一是抑制由事件引发的首先出现的优势反应;第二是根据得到的反馈停止正在进行的反应,以得到一段可供作决定的延迟时间;第三即保护该延迟时间及在此期间内的自我导向行为,从而继续完成任务(抗干扰)。这三方面的缺陷随后引发了四种神经生理学上的执行功能缺损,包括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情感-动机-觉醒(Affect-Motivation-Arousal)的自我调节、语言内化(Internalization of Speech)以及行为重构(Reconstitution)(即行为的分析与综合),再向下游使机体运动控制和流畅性受损[2]。临床表现上可见ADHD患儿注意力难以集中、多动冲动,相比于非患病儿童更话多、制造噪音更频繁等。简而言之,此模型认为ADHD患者的注意缺陷是其行为抑制和干扰控制能力受损在自我调节和执行功能上的表现。Barkley RA这一模型启发了大量相关的试验研究,Go/No-go任务、停止信号任务等多种研究范式结果的相对一致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此模型的合理性[3]。但也有学者的研究发现,单凭反应抑制缺陷不能区分ADHD儿童及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CD)儿童[4]。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ADHD抑制缺陷和执行功能损害的研究数量众多。近年研究发现ADHD儿童在Simon任务、抑制冲突任务和停止信号任务中的错误率均高于对照组正常儿童[5],在Go/No-go任务、Stroop任务的表现上ADHD儿童也逊于正常儿童[6],提示患病儿童抑制功能上有明显缺陷。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者发现高智商对ADHD的操作性执行功能有保护作用,特别是在工作记忆、转换和流畅性方面较普通智商ADHD儿童受损程度要轻[7];而在实验室条件之外,有研究使用执行功能的行为评定量表(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s,BRIEF)测量高智商ADHD男童的生态学执行功能,结果显示8个因子均有明显而广泛的功能受损[8]。但并非所有ADHD儿童都存在所有方面的执行功能缺损,国外新近研究发现,89%患该病儿童表现出至少一项的执行功能缺陷(其中62%存在工作记忆损害,27%存在抑制控制缺损,38%设置转换受损),只有35%的患儿表现出两项及以上的执行功能缺损[9]。由此可见,虽然国内已广泛接受抑制缺陷理论作为ADHD儿童研究的理论基础,但国外已有许多学者对反应抑制不足的核心性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大量补充观点。
2 厌恶延迟理论与双通道理论
1992年,Sonuga-Barke EJ等[10]在试验中观察到ADHD患儿表现出一个普遍现象——他们总是选择一个即时的奖励而非一个需要等待的奖励,即使后者使他们的获益更多——根据这一现象提出了“厌恶延迟”假说。此模型的核心即ADHD儿童避免延缓自己得到满足,他们偏向选择即时满足是因为对任务中总体的延迟时间更敏感和反感,从而想方设法使其最小化。ADHD儿童不是不具有等待的能力,而是他们首要考虑的是时间长短因此不愿意等待[10,11]。另一方面,为了使估计时距(Experienced Length of Time)更短,患儿会做出被家长或老师认为冲动、无组织的行为[12,13]。这一模型提出后被学界广泛接受,有学者认为ADHD的儿童在时域处理上存在缺陷,神经影像学研究也发现ADHD患者的小脑半球体积比正常人缩小,而新小脑环路对呈现准确的时间关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此观点[14]。厌恶延迟模型还同时涉及了环境与患儿父母在其中的作用[10],但Sonuga-Barke EJ亦承认有很多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进行。如奖励前与奖励后延迟的关系、ADHD儿童对是否值得等待的时间长度评估等。
2002年,Sonuga-Barke EJ[15]对原来的厌恶延迟理论提出了补充,不再否认抑制缺损在ADHD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厌恶延迟和抑制缺损是ADHD两个相互独立的机制。抑制功能的不足与多巴胺系统的中脑皮层至皮层控制中心的投射分支有关,导致了运动与思维的失调,此为思维运动失调通道(Dysregulation of Thought and Action Pathway, DTAP);厌恶延迟这一动机风格(Motivational Style)则与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相联系的奖励通路,以及童年早期所处环境有关,此为动机发展通道(Motivational Style Pathway, MSP)。这一双通道模型涵盖范围更全面,对后续的ADHD核心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15~17]。
国内在这方面研究数量较少,有结果显示ADHD儿童在选择延迟任务1(CDT 1)中得分与正常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选择延迟任务2(CDT 2)中则无统计学意义[18],提示此病患儿的确存在显著的厌恶延迟。另有一项针对ADHD倾向儿童的研究表明他们在延迟任务中的时距估计比对照组儿童更长,同时高唤醒积极情绪能缩短ADHD倾向儿童的主观时距[19],Barkley RA等[20]经过20余年的纵向研究进一步发现,ADHD混合型患儿的时间判断能力受损,且此缺陷会持续至成年早期,即便其ADHD症状已经缓解,也可能影响到ADHD患者的活动组织以及驾驶机动车、过马路等日常行为的安全。
3 认知-能量模型
Sergeant J[22]的认知-能量模型被认为是相较于抑制缺陷理论、厌恶延迟模型等而言更具有综合性的解释,强调揭示ADHD不同于其他发育障碍的特异缺陷[21]。此理论将ADHD的认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处于最下游的是编码(Encoding)、中央处理(Central Processing)和动作组织(Motor Organization),研究表明ADHD儿童的反应组织存在缺陷但前二者相对完好;第二个层次是能量库(Energetic Pools),包括三种成分,分别是觉醒(Arousal)、激活(Activation)和努力(Effort),在这个层次,ADHD主要与激活有关,同时也涉及到努力;第三个层次是管理/执行功能系统(Management/Executive Function System),与计划(Planning)、监控(Monitoring)、错误的察觉和纠正有关。Sergeant J等[22,23]强调,有别于抑制缺陷和厌恶延迟模型,认知-能量模型认为ADHD核心缺陷既是“自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的,注意的加工过程不但涉及如前额叶这样的顶端结构,也与皮层下结构有关。综合Go/No-go任务、大脑血流研究以及动物模型实验等结果,Sergeant J认为ADHD的核心不是抑制功能的绝对缺陷,而在于患儿获得的能量不足以支持其很好地保持注意并完成任务,此过程发生在努力能量库,同时,激活能量库的不足使患儿不能很好调整状态,后续有基于成人ADHD的研究发现状态的调整与左脑功能相关[24]。本模型能帮助学者和临床医生更深入地从多方面了解ADHD,也为日后的科研探索和疾病诊疗提供了新思路,尤其是在ADHD与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CD的共病研究方面。国外研究发现高唤醒水平能提升ADHD患儿的认知水平[25],但在国内对此理论进行的讨论和研究都比较少,余雪等[26]的研究发现ADHD儿童在中、高唤醒水平下正确反应的被试内变异性降低,但对抑制功能无明显改善,可能提示能量库在此病的发病机理中并不比抑制缺陷占据更核心的位置。
4 “冷”“热”执行功能
基于执行功能相关的观点和大脑前额叶皮层功能差异,Zelazo PD等[27,28]明确提出了“冷”执行与“热”执行的概念:背侧前额叶(DLPFC)涉及的是“冷”执行功能,即抽象的、非情景化的认知方面;“热”执行功能则与眶额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OF/VMPFC)有关,指的是认知中带有动机或情绪色彩的决定和目标设定功能。在既往的研究范式中,如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WCST)、Go/No-go任务、Stroop任务等考察的都是“冷”执行功能。与之相比,对于ADHD儿童“热”执行功能的研究则起步较晚,爱荷华赌博任务、剑桥赌博任务和饥饿驴子任务等考察的都是“热”执行功能。一项历时2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即便随着年龄增长ADHD患儿的症状有所减轻,他们各方面的“冷”执行功能缺损是持续存在的,且这种缺损与患儿性别不存在相关性;在“热”执行功能方面,患病女童的做决定能力相对于正常女童是受损的[29]。以往通过赌博任务等对ADHD儿童的研究显示他们倾向于作出风险性更高的决定,尤其是在决定的结果是模糊不清的时候[30],提示他们存在“热”执行功能的缺陷,但Antonini TN等[31]经过研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以往的研究存在外部奖励,在缺乏外部动力(如奖励或金钱)的试验中,儿童作出高风险决定的倾向便被减弱了,这可能与ADHD奖励机制上存在缺陷相关。同样,Van Cauwenberge V等[32]也未在研究中观测到ADHD儿童存在显著的情绪调节缺陷。
近年来,国内“冷”执行功能和“热”执行功能的研究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尤其在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领域,用于探索儿童青少年各阶段的认知发展特征。在精神病学方面,此理论常用于研究儿童青少年的行为障碍和发育障碍,有研究发现“热”执行功能障碍是DBD患儿的核心缺损[33]。在ADHD领域“热”执行功能研究数量不多,一项使用简化的N-back任务、趣味游戏任务的试验发现ADHD可能并不存在特异性的“热”执行缺陷,反而在趣味任务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体现了患病儿童缺乏内部动机、容易受外界奖励影响的特征[34],这个结论与Antonini TN等[31]的发现有相同之处。但2018年一项研究显示ADHD儿童的“冷”、“热”执行功能均落后于正常对照组,且差异随任务的复杂程度增加而增大[35]。这样相互矛盾的结果可能与“热”执行功能中动机与情绪卷入的两面性有关,它既能一定程度上补偿患病儿童“冷”执行功能缺陷,但也会使患儿在任务中做出高风险的决定。总而言之,在“热”执行功能的测查上,由于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等的不同,各国学者也未能达成一致的共识,ADHD儿童的“热”执行功能仍待进一步探索。
5 小结
ADHD作为一种对患儿的生活和学习各方面都造成重大影响的慢性疾病,正越来越受到家长、学校乃至全社会的重视,纵观国内外对于ADHD的认知神经心理学研究,虽然每一个理论模型都有其特征和优缺点,但不妨碍学界将它们广泛应用于基础研究和临床诊疗当中。抑制缺陷理论是目前在国内接受和使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模型,除了用于单纯的认知研究之外,常常还与电生理、神经影像学等方法相结合,共同研究ADHD的疾病发展特征或治疗前后指标改变。例如,皮质-纹状体-丘脑-皮质环路(Cortico-Striato-Thalamo-Cortical Circuits)将执行功能与神经科学紧密联系起来,研究ADHD患儿的思维与情绪问题的调节机制[36,37]。还有学者将其扩展到对健康被试的认知功能测查中,Linssen AMW等[38]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健康人群使用哌甲酯后可以观察到工作记忆、处理速度、言语学习与记忆、问题解决、注意力/觉醒这几个认知维度的提高。这些研究对探索ADHD的发病机理、寻找相对客观的诊断标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抑制缺陷理论把ADHD的核心简单归结为抑制不足引发的执行功能损害,而没有深入讨论非理性因素及儿童所在环境在认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发现反应抑制的不足可能并不是ADHD的特征性缺陷,难以用其将ADHD与另外的儿童发育或行为障碍区别开来,使这个理论模型显得较为片面和单一,其所用的研究范式(如停止信号任务)也缺乏针对性[39],遭到了后续很多研究者的质疑和批评。厌恶延迟作为早期的ADHD认知行为理论,经过后续的改进演化成双通道模型,已发展得比较完善,国内外众多相关研究也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实证支持。此模型同时讨论了ADHD儿童在等待情景下的情绪反应是如何塑造了他们的动机风格,并强调了患儿所处家庭、社会环境在其认知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Sonuga-Barke EJ当时并没有进一步发掘两条通路之间的联系,而认为它们是相互独立的机制。Low AM等[40]考察了成人ADHD患者在使用哌甲酯治疗后厌恶延迟的变化,发现治疗前后的自评量表得分提示有改善,但DeFT测试结果无明显差异,提示认知功能与症状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更深入的探索。认知-能量模型则建立了一个更具综合性的理论框架,强调ADHD认知的过程既是“自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的,但此理论在国内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关注,它作为一种提供了新思路的综合性模型,也有待多学科、多种手段的联合攻关,对理论中的各个能量库进行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试验研究,明确其在此病发病机制中所起的具体作用。最后,虽然“冷”“热”执行功能的理论并非专为ADHD一种疾病提出,但近年引起了该领域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此观点讨论了两种执行功能在ADHD患儿中的特征,从另一角度解读了ADHD的注意缺陷、多动/冲动的典型症状,此观点对ADHD的行为矫正训练及患儿家庭教育有重要的启示。目前国内“冷”“热”执行功能相关的研究正在起步,但立足于ADHD的试验仍然较少,且虽然“冷”执行功能缺陷在ADHD儿童身上得到了较多的实证,对于“热”执行功能是否存在特异性的损害研究者们依然莫衷一是。待学者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挖掘后,相信本理论会对ADHD的临床诊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不难看出,ADHD的认知神经心理学模型正逐渐从单通路发展到多通路,并越来越多地着眼于抑制缺陷外的其他功能障碍,也逐渐把听觉、视觉等知觉能力纳入考察范围[41],或考虑此类缺陷来自于神经系统中的某些物质供应不足,如乳酸[42,43],为这一儿童常见神经发育障碍的一系列症状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从病因学出发,无论是哪一个理论模型,它们都将与脑科学结合得更紧密,与神经影像学、电生理学、神经生理学、遗传学等学科一起共同解释ADHD的发病机理和特点;至于临床治疗方面,认知功能作为可以通过量表评估和认知测查考察的指标,将为评价ADHD治疗效果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途径,例如,可以通过特定的认知测查考察不同药物对ADHD患儿认知功能各个维度的作用,从而为了解药物特点及临床用药个体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或是对比药物与非药物干预对ADHD认知功能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制定该病的综合干预策略。无论如何,ADHD认知神经心理学方面的发展都会对基础研究及临床诊疗有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