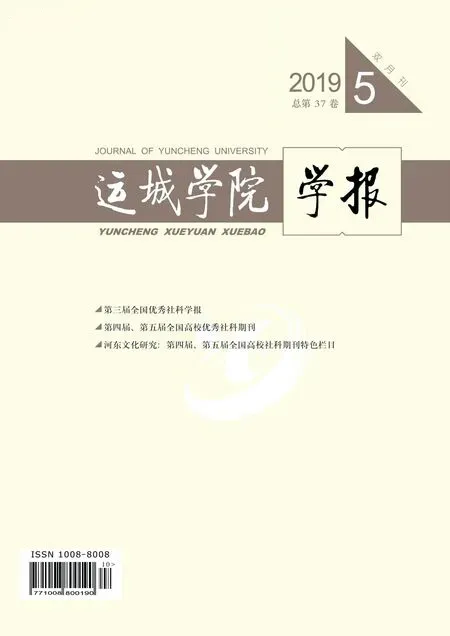柳宗元、刘禹锡天人关系论之革新
2019-03-05杨瑞冬
杨 瑞 冬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唐代之前儒家的天人关系经历过复杂的变动。先秦时期,“天”是一种高于社会的人格神存在,具有神秘之天的特征;孔子之后,天仍是至高至善的存在,人事制约于天,但此时孔子更注重人事的重要性,天的神秘性逐渐被人文性取代,才有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魏晋唐代,儒学经历了一个低谷,在儒、释、道三家文化交织的背景下,儒学已被注入了新的内容。柳宗元、刘禹锡参加的改革失败后被贬,仕途境遇相同。二人相处友善,世称“柳刘”,常以书信切磋,柳宗元写下《天说》《天对》以及《答刘禹锡天论书》等,对天人关系做了新的探讨。柳宗元批判了韩愈的天命论,刘禹锡则进一步发挥韩愈之立场,作《天论》探讨天人之际。二人于韩愈之后,相较韩愈思想来说,其天命思想不完全针对政治或佛、道思想,更多是从儒家思想本身出发,作有关“天论”的探讨。
众家皆将柳宗元、刘禹锡作为中唐时期儒学的重要节点。张岂之认为,柳宗元和韩愈同属儒者,但是柳宗元却以儒为主,融合释道“在融会贯通上走得更远,更多地接受了佛学和老学的东西”,柳宗元能继承初唐包容开放的态度,相较韩愈将儒学一味地抬高,使“儒、释、道的关系则深化到了义理上的兼容。”[1]280-290刘禹锡便是在柳宗元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化的补充。侯外庐、杨荣国从唯物主义角度分析韩、柳的世界观,杨认为柳宗元、刘禹锡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批判汉儒以来的神学目的论,刘禹锡的论证则使他们共信的无神论思想走向一致。[2]205-209侯认为二人“在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史上也有其创造性的建树和特殊的历史地位”。并且二人都试图将其建构的世界观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3]212任继愈梳理唐代社会状况和思想的冲击,认为“天与人,命与我的讨论,由来非一日”,到了中唐时期思想矛盾的尖锐,“道家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儒家就必须就此作出解答”,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便“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也是对前代天人关系争论的小结,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就采取了新的形式。[4]520-534众家皆从当时社会上“三家”冲突的角度分析柳、刘的思想,本文从二人天论思想本身出发,在儒家思想发展的背景下,看柳、刘天论思想于儒家天人关系思想进程中的地位,乃是在中唐时期发生的一场由天及人的思想革新。
一、柳宗元的天人相预
神学目的论以及各种世俗迷信虽曾受到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东汉王充和南北朝时范缜等人的尖锐批判,却由于统治阶级统治利益的需要,天论又在唐代得到了新的发展。针对这种现象,柳宗元则提出了“天人不相预”的命题,对此种“天能赏罚”的神学目的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柳宗元认为天并非万物的主宰,也非秦汉以来神学家所言的创世主,而是“自然”,“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5]80摆脱了天对人的束缚,人事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天,强调的是天的自然属性。
1. 柳宗元与韩愈“天”观念之争。柳宗元针对韩愈的天命论做出了针对性批判。韩愈认为,“物坏而虫生,元气、阴阳坏而人生”[7]442,人产生之后又进一步破坏阴阳元气所造成的和谐状态,所以衡量人的功过的标准在于是否保护自然,即“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7]442天能根据人对阴阳的作用,产生功、祸的判断,“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7]443并施与赏罚奖惩。韩愈认为,人身处自然天地之间并且人的活动能作用于天地,但是他也认为,相对的天是有意志的,天可以奖赏那些能保护自然者,惩罚那些祸于自然者。这样一来,人生的苦难还是天对人错误行为的报应,天还是独立于人存在的有意识的权威者。柳宗元不赞成韩愈这种天有赏功罚祸功能的说法,为“折韩退之之言”[5]443而作《天说》。
2.柳宗元的天论。首先,天是可以认识的。柳宗元认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5]443天虽然很大,看似让人捉摸不透,但是也和瓜果等能被人感知和了解的小事物一样,是能被人直观感受的真实存在的具体事物,有颜色、有温度、有方位。既然能被人感知了解,就像瓜果一样能被人利用,而非反之,“瓜果”能利用人。他说:“天地,大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5]443。韩愈能认识到,所谓“赏罚”这是人类的社会性结果,是个人实施社会性行为所造成的自然存在的事物,哪怕是大到人不能完全接触到的天地都不能对人做任何干预。
第二,为了进一步论证天,即宇宙万物造始者和本原的问题,柳宗元以《天对》回答屈原《天问》的问题,说明世界没有一个超验的神秘力量来主宰。他说:“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易可盲焉!各黑听眇,往来电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5]365否定了那些关于天地开始以前的荒诞传闻,指出世界不过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构成,世界万物的变化并不神秘,就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宇宙的本原即是元气,是由一元混沌之气冲荡变化而成,昼夜、明暗的交替,万物从混沌蒙昧中产生,发展变化,又复归于息灭,都是元气的运动所致,元气才是唯一的存在,根本没有造物主。“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5]365既然天地是自然而然地存在和运行,根本不可能有外来的创造者,天地就只有自然性,没有神性,就为“天人不相预”论奠定了基础。这就把万物变化看成物质世界间的自然运动,从根本上否定了由外在神灵主宰宇宙万物的天命论。
第三,在天人关系上,柳宗元得出“天人不相预”的结论。既然天是一种具体的事物,植物等非人的生长就在于阴阳变化,而人是不同于植物和其他动物的,人可以组成社会,制定法律规则,构成和谐秩序,形成符合人性的规律,可称之为人道。柳宗元认为要论证天人关系首先要分清此。他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言,“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与人为四而言之者也。馀则曰: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5]816既然“天道”是自然规律,“人道”是人类社会规则,天道是阴阳变化生成与发展,人道是按照人的本性制定,那么天道、人道彼此独立、平等而互不干预。
柳宗元的元气自然观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元气,自本自根、无始无终,其“天人不相预”思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都具有客观规律性,但天道的运行是无意识的自然之变,而人类的社会活动才是有意识的作为,强调人事的重要性,阐明了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活动才是关乎社会治乱和人事成败的决定性因素。[8]32柳宗元的天论思想是发挥东汉以来对儒家思想神秘化批判的基础上,并借鉴了荀子、王充的天人关系论,更加强调天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二者的严格区别,试图消解神秘学说对儒家思想的控制。
二、刘禹锡:“天人相预”的深化
刘禹锡赞同柳宗元对韩愈的驳斥,但认为其未能详尽论述天人关系,于是作《天论》。
1.辨析历史上对“天”的两种解释。一种是“阴骘之说”,“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徕,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5]443-444承认天有意志,认为善恶有报应,祸福有前兆;另一种是“自然之说”,否认天有意志,认为天、人各有自己的职能,天道不干预人事,事物背后“是茫乎无有宰者”[5]444。前者主要指汉代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等,后者则主要指黄老之学和王充等人的思想。刘禹锡显然已把无神论与有神论、目的论与自然论的天人观明确地区分开来了,反对“阴骘之说”而成“自然之说”,并发挥“自然之说”,将自然与人的关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肯定人在自然的中地位。
2.“相胜相用”说。在自然界,即天道中,万物平等生存,优胜劣汰。但是人类社会则不然,人类社会有一整套与道德和法治相适应的善恶是非准则。人之道就在于能利用自然规律,耕种生存,并以人为尺度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即“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5]445刘禹锡认为,“人道”与“天道”是有区别的,天人之间既相互争胜,又可相互利用。“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5]444人有人之能,天有天之能,人与天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合一,也不是简单的相分,而是“交相胜,还相用”。对自然规律的无知,会导向天命论;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则会否定天命论。从人类历史的长过程来看,天并不一定能胜人,而人则一定能胜天,这就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推向“人定胜天”的高度。由于人类智慧善于创造,能制定和执行法规,与天争胜且能利用自然赋予的有利条件,从而建立起人类社会的纲纪。
3.刘禹锡的社会观,来自天人“交相胜”。他认为,社会治乱可分为三种状态:法大行、法小弛、法大弛。在法大行状态下,人能胜天;在法小驰状态下,人天关系混乱;在法大弛状态下,人天关系颠倒,关键还是在人。关于“人胜天”,他提出三条根据:第一,“法大行”时人能胜天,刘禹锡认为,当社会政治清明、法制完备时,人的主观能动性往往能得到充分地发挥,此时人可以胜天。相反,当“法大弛”时,社会政治昏暗,法令不行,必然是“天胜人”。刘禹锡强调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法令的实施情况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意义,这是很有见地的。第二,在是非分明、贤者在位的条件下,即“圣且贤者先”的条件下,则“人胜天”。相反,在是非混乱、单靠强力从事,即“强有力者先”的情况下,则“天胜人”。第三,“理明”时,“人胜天”。在刘禹锡看来,任何事物都受客观规律的支配,人只要能认识和利用规律,遵循规律,又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可以胜天。相反,在“理昧”的情况下,人们不能认识客观规律,只能盲目地受必然性所支配,往往表现出“天胜人”的情况。所以,天人之间总是“交相胜,还相用”的。刘禹锡还认为,“理昧”正是有神论立生的根源。
在刘禹锡看来,“人胜天”的种种情况,都取决于人的主观努力,天不一定胜人,“人诚务胜乎天”,而人则一定胜天。刘在理论上的贡献,首要的是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继承和发展了荀子以来的优秀思想传统,概括了当时的科学成果和生产经验,一定程度上把自然和社会按其固有的特点区分开来,并试图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把自然史和人类史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等按照辩证思推的途视来加以考察。[9]32刘禹锡在天人关系上的观点,既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既强调“天人有分”,又看到了天人的统一性;既强调了规律的客观性,又重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从先秦以来的“天人之辩”,由柳宗元、刘禹锡在理论上作了出色的总结,使天人之论在中唐时期呈现新的面貌。
三、柳、刘“天”思想形成的原因—兼论思想之同
中唐时期,举国上下莫不怀念盛世之年,渴望大唐再度中兴,众家士人提出各种学说以求振兴国家。韩愈高举儒家道统,排斥佛老,反对政治变革,反之,刘柳二人则顺势三教合流,求新求变,要求政治上的变革以及思想上的革新,关注现实政治,这也是二人共同的思想特点。
柳宗元、刘禹锡二人的人生境遇颇有相似之处,二人同年进士,投身政治活动,赞同政治革新,生活上是为挚友。官场上,支持政治变革,柳、刘二人共同面临劫难和冲击。当柳宗元展开对韩愈的论争后,刘禹锡也加入了这场关于“天”的论争,并站在了柳宗元的一方,二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刘二人被贬为边州司马,政治活动上的失败使二人对中唐之复兴的愿望落空,面对现实的冲击进行思索,则注重儒学理论的辩证和开新。韩愈利用儒学是注重其权威的维护和重树,当韩愈高举道统,反对政治革新,实则宣扬天人感应的有意志之天时,柳、刘二人便从自然之天对其予以驳斥。柳、刘二人认识到如果天是有意识的,那么自己维护的社会革新运动为何走向失败?政治上的倾轧、社会矛盾的尖锐让柳、刘二人对有意志之天产生了怀疑。
佛、道在唐朝的发展,使得儒学受到冲击,韩愈便高举“道统”大旗,大力宣扬孔孟的“天命观”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等,维护儒家正统思想统治地位,以驳斥佛老。柳宗元、刘禹锡却适应“融合”的潮流,吸收批判佛老思想。在艰苦的贬谪生活中,仕途的冲击使柳、刘二人思索人生的意义,试图摆脱社会遭遇的冲击,便从佛中悟出了无神的人生理论。刘禹锡认为万物都是“乘气而生”,认为“空”并不是绝对的“无”,“空者,形之希微者也。”[5]448其间充满着细微无形、难以用感官感知到的“气”。在他看来,“空”和“无形”都统一于物质性的“气”。“气”这种物质实体虽然不可直接感知,但却可以“以智而视”,即用理性思维来把握。柳、刘虽不是赞同佛教思想,但是也在对韩愈思想的批判基础上,客观审视佛教思想的有益成分,以补充进其思想之中。
从外缘因素和内在理路的角度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论思想,不仅是对现实生活进行理性的反思,还从学理上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发展作了适应时代的修正。
四、结语
“天人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思考命题,中国人对“天”的信仰,自商周甚至原始社会以来就有不同的表征,但周公、孔子对文化大传统进行伦理化、道德化的理性改造之后,天的信仰便有了人文特色,更具理性化,关注现实社会,然而对天的神秘性信仰以及其神圣地位认知,却不是很容易消解。中唐时期,因为儒学地位下降,外域文化和本土新文化的突起,对儒家传统文化造成重大冲击,以至不得不进行转化,而转化的关键即为社会所用。韩愈便走了从维护天的神圣性出发,探讨天人关系。然柳宗元、刘禹锡经历了现实遭遇后,对现实和神圣性的文化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质疑,在对“天论”的讨论过程中,加进了“人论”的内容,这是天论思想发展至中唐时期的一场革新。但其“天人关系”之论调并未很好的延续后代,甚至宋明理学更是将儒家思想中的伦理性固化,至于唐宋之际的思想特色之变革,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