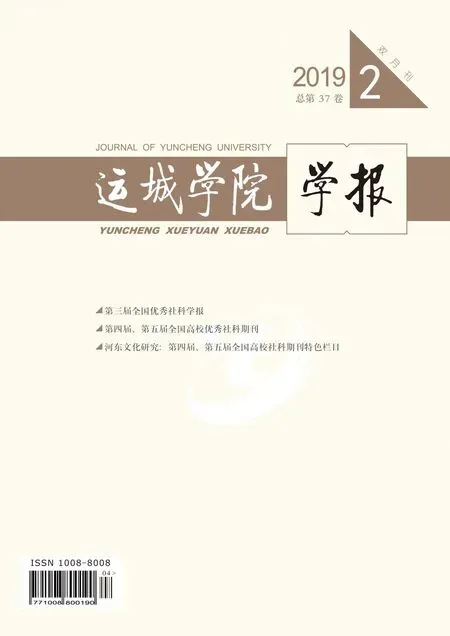北朝社会的文体认同和文章四体
2019-03-05李德辉
李 德 辉
(湖南科技大学 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基地,湖南 湘潭 411201)
一、北朝社会的文体认同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地域有一地域之文学。北朝文学除了人所共知的时代性地域性外,其内部还存在着一个文体认同问题,即什么样的文体才是北朝文人重视的主流、正宗文体的问题。这一问题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提到研究层面上来,但却实实在在构成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北朝,文士采用的诸种文体之间,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而是有着重要性程度区别的,等差分明的。北朝的文体认同,其一表现为文体的身份认同,即一种文体是否能够被社会认同为正宗和主流的文学样式。其二表现为文体的社会接受度,即这种文体世人能否普遍重视,作者众多,成为一个时期的代表性文体。这在唐以后诸种文体都已成熟,各有成式和典范的时代,不是一个问题,但在三至五世纪的北朝,却很成问题。那时候,很多文体都还处在萌生和成长状态,文体规范还未形成,写作技巧不为士人所掌握。而且即使是在文学相对发达和先进的南朝,各种文体也不是齐头并进,等量齐观的。在重实用,讲功利的北朝,差别就更显著了。特别是中古前期的北方,士人心目中所认同的文学,和今人理解的就有很大的距离,就是和南朝也有明显的不同。最大的差异,一在体裁样式的选择和运用,二在文学风格的辨析和认同。风格认同简单直接,史上都有明确记载,只须略加辨析即可,体式认同则要复杂得多,牵涉到文体的文学性和实用性,文学观念的时代、地域、人际差异。过去我们对南北文风的差异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而对北朝的文体认同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认识,更缺乏专就北朝公认文学体裁的专题论述,研究未能落实到具体的文体上,和北朝社会实际结合不够,本文即由此而发。
南朝文学秉承汉魏传统,以诗赋为文学的主要样式,文人的才情主要用在诗赋上。北朝则不然,对笔的重视明显要高于文,不押韵的笔社会认可度较高,社会上用得最多最普遍,是文士的成就、特点所在。而他们理解的笔并不是像南朝那样无所不包,诸体之间差别不大,同等重要,“统该符、檄、笺、奏、表、启、书、札诸作……凡文之偶而弗韵者,皆晋宋以来所谓笔类也。”[1]而是有选择的,偏向于那些纪实性强的有用之文。衡量文学的标准,不是看它写得好不好,优不优美,而是看它是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用,有用性和时效性是其重要的考量标准。一种文体,如果能够直接服务于时政和社会生活,那它就是有用的,否则就是无关紧要的。创作的目的性、功利性强。对于作为文学正宗体裁的诗赋虽然也重视,但是觉得体性较虚,偏于抒情,脱离实际,很多人既不能认同,也不够擅长。从这种文学观念出发,北人认为,只有诏令、史传、碑志、书檄才是真正重要的文体,平日的才情主要用在了此四体上,取得的成果也主要在这四个方面。
此四体有两个显著的共同点:一是非虚构性特征,即不是凭借飞腾的艺术想象,采用虚拟的方式构造情境,主要就是用纪实之笔写现实之事,直接服务于实际生活需要,不反映人情和人性,不展现士大夫的心灵世界,只写生活中的真人实事,文学的政治性、事务性、时务性强。二是非抒情性,即不以个人抒情写志为目的,而以叙时事、写时人为主,内容比较具体、实在,容易理解,是四种主于叙述的实感较强的文体。
魏晋南北朝成熟和通行的文体多达十多种,为何北朝文人格外重视此四体?主要缘于此四体既社会需要,能“切时用”,又精心结撰,不乏藻采,文体温厚,风格笃实,有语言形式之美,是所谓“篇翰”[2],适合了北朝文人对于文学作品构思和技巧的创作需要。换句话说,原因在于文体用途和社会需要能够适配,又不缺失最起码的文学特性,故为时人所重。下面试图从四个方面来论证北人心目中的文学四体,揭示北朝文学创作的独特性。
一是史志目录的记载,可以看出文体的主次轻重。《隋书·经籍志四》别集类,北朝文集从魏孝文帝到庾信,共十九部,文体上以文章为主,诗赋极少,有很强的偏好。其中诏令处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当为北朝文章中居于首位的第一体。《隋志四》总集类著录北朝诏令总集八部:宗幹《诏集区分》、佚名《后魏诏集》《后周杂诏》、李德林《霸朝集》、佚名《杂诏》《杂赦书》《皇朝诏集》《皇朝陈事诏》。又常景延昌初,受敕撰《门下诏书》四十卷,其他像这样皇帝下诏,臣僚专为某种文体编撰的北朝总集就绝少了,相比之下,凸显出北朝对诏令的重视程度。《旧唐书·经籍志下》总集类和别集类的情形跟《隋志》差不多。总集方面,有温彦博《古今诏集》三十卷,李义府《古今诏集》百卷,皆编于唐初,汇编的是先唐诏敕,其中有很多北朝诏诰。别集方面,有《后魏高允集》《宗钦集》《李谐集》《韩(显)宗集》《袁跃集》《薛孝通集》《温子昇集》《卢元明集》《阳固集》《魏孝景集》《杨休之集》《邢子才集》《魏收集》《刘逖集》《宗懔集》《王褒集》《萧撝集》《庾信集》《王衡集》。与《隋志》相比,只是书名的改变、卷数的增减及个别作者文集的增加而已。卷数都寡少,超过二十卷的不多。析其文集的文体构成,发现有限的篇幅,还被诏令和碑志、表疏、书檄占去大半,诗赋所占的比重不大[3],偏向性明显。不像南朝,各体文字皆备。
二是史传、子书和石刻提供的证据,昭示了北朝文人对此四体的认同。史传方面,《魏书》《北史》《北齐书》中有大量的例证,其文体的排列结构就是碑诔书檄等杂笔,诗赋只占少部分。北朝最有名的文学家邢邵、魏收、温子昇,虽然为文各有所好,但总体不出实用文的范围。邢邵长于章表、诏诰。温子昇最长碑志,全不作赋。邢邵虽有一两首,又非其所长,魏收则唯以章表、碑志、诏命自许,此外文体,视同儿戏,北齐初的重要诏命、军国文词,皆其所作。北魏前期名家高闾,好为文章,但其三十卷的文集中,所收为“军国书檄诏令碑颂铭赞百余篇”,文风与高允近似,后称二高,当时所服。邢虬写作的三十余篇文章,体裁是碑颂杂笔。袁翻孝昌中与徐纥俱在门下省掌文翰,著文笔百余篇,擅长的也是诏令奏状。魏孝文帝好为文章,有大文笔,马上口授。但他所擅长的大文笔,主要就是颁布政令的诏诰,偏好性极强。史称自太和十年以后诏册,皆帝之文。韩显宗上疏,亦极力称道帝“耳听法音,目玩坟典……文章之业,日成篇卷”[4],平日所留意和致力者,在于诏令等政治性文体。而《颜氏家训·文章》所载,更全面、直接地指正了北人所长的文章四体及其地位高下,文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根据文体政治地位的高低和对社会的有用性来排列,先列地位最高的诏命策檄,其次是事关国政的奏议,第三是个人文章,最后才列诗赋。总之是以“朝廷宪章,军旅誓诰”为重,“陶冶性灵,从容讽谏”为轻。原因就是前者能“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后者属个人抒情,“行有余力,则可习之”。颜氏的这种观念,在北朝颇有代表性,足可显示出北人心目中的文体轻重和地位高下。此外还有石刻提供的证据,也很实在、有力。中华书局《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及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三书所记的墓主生前所撰文体,也是诏令书檄史传碑志为主,极少提到诗赋,而往往以文章、文笔、文翰来统称,排序上往往是书檄、诏令、碑颂三体连排,显出文体的主次先后,这些都跟南朝和唐代有异。
三是文学总集提供的证据。这些文体,还是六朝隋唐总集的常客。唐初许敬宗编的大型先唐总集《文馆词林》中,就有魏孝文帝、节慜帝、孝静帝、北齐文宣帝、孝昭帝、魏收、阳休之、温子昇的诏敕,高允、魏收、薛道衡、李德林的碑颂。《文苑英华》中此四体比重尤大,诏敕从卷三八○到四七二共计一百七十三卷,下分数十个小类,檄移占七卷,碑诔志墓表行状从卷八四二到卷九七七,占一百三十五卷。三部分合计,约占《英华》的三分之一。《英华》虽是宋人所编,但效仿的是《芳林要览》《类文》《文馆词林》等唐人编的总集,其编撰体例、文体观念都是承自前朝,并非宋人新创。而且因为汇编的是自梁陈到五代的作品,里面有相当多的北朝诏敕、碑志。故《英华》所录的这几类文章也部分反映了北人的文学观念。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朝部分也可看出这种文体构成,其中诏令、奏疏、碑志、书檄比重最大,其他文体不能相比。温子昇就只有诏令、表疏、奏状、碑铭各数篇,其他称为名家的源怀、高允、高祐、邢峦、阳固、魏收、邢邵、崔瞻的情况也差不多。不仅有归属的作品多为诏令、表疏、碑铭,就是阙名的残文,文体也是诏书记颂铭,这又从文献存传反映了文体的社会接受度,说明当时认可的就是这些文体,表明了当时文士的侧重点。
四是隋唐宋类书中的大量实例,彰显出文体份量。《北堂书钞》卷一○二艺文部,列有诗赋颂箴连珠碑诔哀辞吊文。卷一○三艺文部,列有诏敕章表书记符檄,排序都很靠前,表明重要性程度要高于其他文体,并且每个标目下都有相应实例佐证。《艺文类聚》中载录的主要也是诏敕、碑志,其中属北朝的碑文是为太尉、司徒、司马、司空、尚书令而作,出自名家之手。寺碑尤有特色,北朝作家较多。名文有卷七六周王褒《善行寺碑》,卷七七后魏温子昇《寒陵山寺碑》《印山寺碑》《大觉寺碑》《定国寺碑》、北齐邢子才《景明寺碑》《并州寺碑》。《太平御览》文体部分,依次为诗、赋、颂、赞、箴、碑、铭、志、诏、策、诰、教、檄、移、露布,几乎每个文类都有北朝实例。
这种排序不仅表明了文体的位置先后,也反映出古人文学观念跟现代的差异。现当代是以文学性强弱为标准,古人则以文体为文学。在中古北方,这种观念尤其强烈、鲜明。判断一篇作品是否为文学,不是看写得优不优美,而是根据体裁,体式上属于时人心目中的文学作品,那就视为文学,否则就不承认。诏令、史传、碑志、书檄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而且和社会生活及政治需要有紧密关联,既有实用,又有地位,所以被认为是高层次的文学。大概在北朝人心目中,所谓大手笔,主要就是指诏令、碑颂、书檄这三体实用文,外加作为专书的史传。北朝史传虽是专书,各有体例,但从散文史和文章学的研究角度看,也是历史散文、传记体裁,政治地位和文学层次都很高,作者极多,名家辈出,加以重在叙事,比较务实,和政治的关联紧,故历来是北朝文学的重点,多数北朝文章名家都修过史。唯有奏议和表疏,北朝文士虽然也作过不少,但是文体过于普通,各朝都有,无时代特色,故本文弃置不论。诏令虽则各朝也有,但是对北朝而言有特殊的意义。北朝格外重视诏令,把这种政务性公文当成了文学的最高层次对待。北魏献文帝和孝文帝甚至亲自写作,“诏令殷勤”[4],形成一个皇帝亲自草诏的传统。从北魏到北周,几乎每个皇帝都有这类文章。保存在《文馆词林》弘仁本的残文,就有二十多篇诏诰是北朝八位帝王所作。为了草好诏诰,遴选本国最好的文章作手专职写作,魏收、邢邵、温子昇、李德林,即是作诏的高手,社会声誉极高,所作诏诰本身也不乏文学性,故当另眼看待。
二、北朝的文章四体
(一)诏令:北朝文学的最高典范
诏令古称王言,是以帝王名义发布的行政命令,乃一朝的国政所系,有重要意义。且其撰写各自有体,强调文采和气势,要求措辞得体,用语精炼,写作要求很高,北人极为重视。围绕诏令的撰写,集中了北朝文坛的多数名家,形成了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献积淀。开展对此类文体和文献的研究,意味着把北朝最重要的政治-文学类文献纳入研究视野,其意义不言自明。目前学界对唐宋诏令已有了较好的文献汇编。先唐方面,文章总集中也有不少。但所做工作为文献辑集,并非文章学研究。目前北朝文章研究日趋深入,唯独没有从文章学角度提出的北朝诏令研究。古代文学研究一向重纯文学,轻应用文。诏令受此影响,着力一向不够,北朝诏令研究尤缺,然而又是北朝散文的重头,忽略了它,就是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缺项。此前学界对北朝诏令的文献详情、发展简史、文体演变、代表作家并不清楚。古代正史目录自《隋书·经籍志》到《明史·艺文志》,除《新唐书·艺文志》外,都是放在集部,历代混编,并未区分南北。至《四库全书总目》见其体尊重,方升入史部,单独成类,曰“诏令奏议类”。这一做法虽是着眼于诏令的地位,但也提醒我们,这种文章确有独到价值,当特别对待。在目前各种文学研究都在趋深的情况下,尤需大力加强。
魏晋南北朝随着台阁制度的发展,诏令的撰写日趋精密。早在梁代,草诏就成了专门之学。《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著录的诏令已达三十多种,还出现了《梁武帝制旨连珠》这样的断代诏令选集,北朝亦有《诏集区分》这样的通代诏令分类选本和《门下诏书》这样的专书,可见至迟在北魏中期,草诏已成专门之学,其地位不是奏议可比的。古代奏议虽多,但一般臣僚都写,并不复杂,毕竟只是常行文体。诏令则为文章之极致,负责草诏的中书舍人亦为文章之极选。很多北朝文人都汲汲于斯道,把自己锻炼成出色的王言作家,以适应社会需要。在北朝,擅长作诏的有魏收、邢邵、温子昇、崔瞻、李德林、卢思道等,都是当时的所谓“大才士”,其文学声誉和业绩与草诏一事很有关系,从中就可看出诏令对作家声誉和地位确立的支撑作用。《北齐书》载,邢邵为文,长于章表、诏诰。孝昌初,与黄门侍郎李琰之对典朝仪。自明帝之后,文雅大盛,邵文章之美,独步当时。毎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永安初,累迁中书侍郎,所作诏诰,文体宏丽。其北朝文学名家地位的取得,“北地三才”文学并称的获得,与他善作诏诰章表就有直接关系。另一名家魏收,其才名也在修史和草诏二事上。《魏书·自序》及《北齐书·魏收传》载,魏收最初被朝廷录用,就是靠了有草诏之才,为文敏速,以表现出众而迁官散骑侍郎。孝武帝初开始草诏,“文诰填积,事咸称旨”。到北齐神武帝时,已号为“天子中书郎,一国大才”[5]。“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协睦。时昕弟晞亲密,而孝昭别令阳休之兼中书,在晋阳典诏诰,收留在邺,盖晞所为。收大不平,谓太子舍人卢询祖曰:‘若使卿作文诰,我亦不言。又除祖珽为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词士也,闻而告人曰:‘诏诰悉归阳子烈,著作复遣祖孝征,文史顿失,恐魏公发背。’……每有警急,受诏立成。或时中使催促,收笔下有同宿构,敏速之工,邢、温所不逮。”[5]以诏诰为文学的代表,著作(修史)为史学的代表,从中可见诏诰在北朝文士心中的正宗地位,更可见出名家成长与草诏一事的关系。诏书本身就行文简洁,语气错综,笔力雄健,有辞藻气势之美,文体堂正,加上政治地位极高,故最易获得世人认可,博得文士青睐。由于地位高,分量重,对撰写者的要求也极高,不仅要措辞得体,行文有法,而且得为文敏速,能够应付紧急事态。不具有这样的才能,就是不称职,不会被录用。所以北朝社会文士虽多,草诏的高手却没有几个。他们认为,唯有这样的诏诰写得既快又好的文人,才是“一国之大才”,其他人都当不起这个称誉。前述《北齐书》引文中魏收所说的“文”“史”还有特殊的含义,不是今人理解的文和史,而是指撰文和修史这两件北朝文士看重的大事,关系到文士的地位、声誉,是指职务、官位。但从中也可看出,在北人心目中,诏诰属于文学门类,著作属于史学门类,对文人都重要,二者能居其一,即可称为文士。《北齐书·文苑传序》:“天保中,李愔、陆邛、崔瞻、陆元规,并在中书,参掌纶诰。其李广、樊逊、李德林、卢询祖、卢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独擅其美。河清、天统之辰,杜台卿、刘逖、魏骞,亦参知诏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诏旨。其关涉军国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逊、李德林、薛道衡,为中书侍郎,诸军国文书及大诏诰,俱是德林之笔,道衡诸人皆不预也。”[8]引文中的文翰、文章多指军国文书、朝廷诏诰。文中提到的北朝名家也都是草诏高官,帝王亲近,管司机密,其成名与任职有密切的关系。负责草诏,撰写重要的时务性文体以应急,诏诰一出,士林传诵,他就能迅速成名。这也表明在北朝文人看来,唯有诏诰才是最能代表文学创作高度的文体,能获得社会认同,存国之颜面及文士之体面,类似这样的地位和作用,其他文体就不能相比。由此看来,首先是诏诰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其文学地位,其次是其文学品质决定了文学价值。诏诰都经名家写作,仅以词华之美而论,也是盖代的。
其中重要诏书所记乃军国大事,不容丝毫马虎。《魏书》卷一二载,孝静帝将禅位于文宣帝,诏书就是事先作好的,禅代之际,即将预先写好的诏书交付大臣杨愔进于帝。卷一九中载,元顺在宫中为官,所作诏书文辞优美,同僚嫉妒。高道穆为中书舍人,元颢逼虎牢城,或劝帝赴关西,帝以问道穆,道穆反对,其夜到河内郡北,帝命道穆秉烛作诏书数十纸,布告远近,于是四方知乘舆所在。温子昇为中书舍人。庄帝杀尔朱荣,当时赦诏皆子昇之词。阳休之性疏放,齐受禅时修起居注,坐诏书脱误,左迁骠骑将军。表明北朝诏令皆军国大事,事关机密,择人慎重,且文辞优美,音调抑扬,世人看重。从正史行文提到的频率和排序,也可看出主次先后。崔?博学有辞藻。自中兴迄孝武帝,诏诰表檄,多?所为。祖珽文章之外,又善音律。帝虽嫌其数犯刑宪,而爱其才技,令直中书省,掌诏诰。魏收北齐武成帝崩,掌诏诰。文宣帝天保十年十二月,召于御前立为诏书,宣示远近。李德林北周初从驾至长安,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武帝谓群臣云:“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6]高闾永明初为中书令,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崔瞻以才望知名,天保中为司徒属,杨愔欲引为中书侍郎,时卢思道直中书省,因问思道曰:“我此日多务,都不见崔瞻文藻,卿与其亲通,理当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词之美,实有可称。但举世重其风流,所以才华见没。”愔云:“此言有理。”[5]便奏用之。崔衡天安元年,擢为内秘书中散,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多出其手。李敷为秘书中散官,以聪敏,内参机密,出入诏命。常景普?初,除秘书监,以预诏命之勤,封濮阳县子。徐纥以文词见称,世宗初,除中书舍人。清河王怿以文翰待之,仍领舍人,军国诏命,莫不由之。时黄门侍郎太原王遵业、琅邪王诵,并称文学,亦为纥秉笔,长直禁中,略无休息。前述引文中的文词、文辞、文翰、文笔、笔札,主要就是指的诏诰、书檄等服务于时政的实用文,按照今人理解,文学性贫弱,称之为文书或者更加妥当,当恰恰是这些文士的特色和亮点所在,彰显了和南朝文学的显著差异。
(二)史册:北朝文学的另一重心
修史是北朝重视的另一件大事,史书也被北朝文士当成正宗和主流的文学体裁,而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著述。为了修好史书,从北魏起,即在内廷设置有专业史官——起居令史,负责记录人君言语举动及每天的国家大事,每行幸宴会,则在帝之左右。后又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领之,而隶属集书省。北齐别置起居省。北周以春官外史掌此事,以为国记,旨在彰邦国之美恶,申褒贬之微旨,为惩劝之大法,著为典式,垂之后裔,事关重大,从文字表达到人事叙述都有很高的要求。史书在北朝所占据的文学正宗地位,正是从它和政治的紧密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由于史书所记事关褒贬得失,史官司笔削之任,所以用人也很慎重,写作上尤其讲究,重要事件记载皇帝甚至会亲自过问。为了撰好国史,仿效晋代官制,在秘书省成立著作局,有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专职修史。围绕此事,聚集了北朝最优秀的文人。北朝知名文学家,修史的占去一大半。崔浩、崔光、李彪、高祐、高闾、邢邵、魏收、温子昇,就都是著作局培养出来的著名作家。最初的名家为道武帝时秘书郎邓彦海,著《代记》十余卷。接着为名臣崔浩,著有《晋后书》五十余卷。此后撰录国史的有崔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享、黄辅、游雅、高允、高祐、程骏、李彪、崔光、李琰之,皆以秘书官参著作事,各有成书数十卷。此后名家名作则有邢峦《孝文起居注》及崔光、王遵业的补续本,温子昇主修的《孝庄帝纪》,王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北齐天宝中,由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书。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让、裴昂之、高孝幹等助撰,成《魏书》百三十卷,形成今本《魏书》叙事繁富,史文繁重的著述特点。
跟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北朝修的是当代史,前代史并不在修撰范围,听由文士私撰,亦不算犯法。因为当代史的编撰,关系到本国的名人高官甚至在世人物,这就涉及很多方面的敏感问题,写作上有更高的要求,审核也会更严格。最起码,记载史实要齐备,重要人物和事迹不能漏略过多,褒贬人物必须合实。出于这样的写作要求,同时也是因为不同于南朝的修史观念,北朝文人修史,记载史事特重细节,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逐一叙述,不像南朝史书,叙事简略,遗漏甚多。
这就形成了北朝史书善于叙事,有《左传》之风的写作特点。叙述务求详尽,资料翔实,史事繁多,文风古朴,不事藻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南北文学观念不同,北朝人对待史书的写作重于叙述,注重细节,不重文采,不事修饰。另一方面,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述,乃是因为“文各有体”[7],是史书所用文体本身的原因,“此等著作是‘笔’,以叙事为宗,不得不减损雕绘,非北人与南人异。”如魏收《魏书》,“叙事佳处,不减沈约《宋书》;‘笔语’当为大宗,而为‘秽史’恶名所掩。”[7]观其本纪和列传,叙述之详尽,资料之丰富,远非南朝诸史可比。以篇幅而论,《南齐书》《梁书》《陈书》三书合计,字数也才略微超出《魏书》。全书所记人事极多,语言精练,对话生动,有各种不同的叙述手法。既重视记事,也重视写人。不仅写人物,还记语言,记战争,表世态。写人方面尤有特色。通过描写、对话、行动、外貌来写人,还通过专传、合传、类传来写人。同一个家族人物,多为家传或类传,重要门第、家族,自北魏初到北齐初,叙述几无遗漏。多者子孙宗族至数十人,颇似家谱家传。每篇传记皆搜括史料,铺陈细节,史文繁重,连篇累牍,内容之丰赡,跟南朝史书的叙事简略,文字粗疏形成鲜明的对比。名臣传记叙述尤详,动辄数十页,读来不胜其烦。这种感觉,是读唐以前史书所少有的。一般来说,宋以后正史内容繁重,唐以上史书叙述简略,唯独《魏书》反其道而行之。不仅魏收,整个北朝史书都有这个特点。东汉到南朝,史书的编撰是以文字简约为高,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善于叙事,长于概括。北朝则不然,不是以文字的简约来定史书的优劣,而是强调史事、人物记述的无遗漏,材料搜集的详尽,完备。史文繁简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对材料的取舍。北朝史书格外重视叙事的完备无遗,为此,对史料搜集也有求全求备的要求。但在编撰中,对材料的取舍并无很多的讲究,文辞主于能够充分,完足地表情达意,并不像晋代和南朝,主张史书编撰事增文简。刘知几《史通》提到的几位北朝在叙事方面取得了成就的史家,如崔鸿、李德林、魏澹、王邵、卢彦卿、崔子发,所著之书,都有叙事委备详尽的著述特点。可见善于叙事,内容详密,资料丰富,史事繁多是北朝史学的显著特点。北朝史传都以古朴的散体行文,是一种叙事之文,从文学角度说,这一特点正好也反映了北朝文学重叙事,轻抒情的写作特点。而且北朝史传中那些详尽的史文,还包含有许多文学性强的篇章,诏诰、书檄、奏疏、章表、诗赋等多种文体,都有辑录,在编撰上是存文于史。同时,那些各种体裁的文章,多数是以叙事为宗的记叙文,非关抒情,里面能够将主观情感包含在客观叙述之中,寓论断于叙事。看似琐细小事,却能够反映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文化氛围、时代观念,小中见大。许多重要社会现象,在史书的正文里没有记载,在引用的文章里面却有不少。很多文章表面上看属于文学体裁,实则保存了大量的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能够反映当时的历史实况,这又是文中有史。综合来看,北朝史书乃是一种文学化的历史和历史化的文学,大体的结合方式是以史为本,以文为用,存文于史,史中有文,文中存史。
北朝史籍,现存最完整的大部头著作,唯有《魏书》。表面上看,它是魏收撰的,但魏收以前的数十位史家都参与了北魏国史的撰写,魏收不过是总括其成。其详密完备,注重细节,喜欢铺叙,多载对话,多录诏诰表疏奏状的文体特点,不仅是《魏书》的特点,也是北朝史学的特点,当理解为北朝叙事文的成就。刘师培云:“文章之用有三:一在辩理,一在论事,一在叙事。文章之体亦有三:一为诗赋以外之韵文,碑铭、箴颂、赞诔是也;一为析理议事之文,论说、辨议是也;一为据事直书之文,记传、行状是也。”[8]据此,则北朝发展的是“诗赋以外之韵文”“据事直书之文”,其成就乃在叙事之文上。周一良《魏收之史学》称:“魏收之书,详略得当,近于实录。”篇幅较之南朝诸史,“详略悬殊,而记载大事皆能简当扼要”[9],其说固确,但魏收之书的前身,是北魏国史,此外还有北魏史臣的私撰史书,不是他一人的成果,保留的是北朝史学重叙事,重细节的优点和传统。其史料来源至少包括邓渊《代记》、崔浩《晋后书》、崔览、高谠、邓颖等《国书》、邢峦、崔光、王遵业《孝文起居注》、温子昇《庄帝纪》、元晖业《辨宗室录》,集成了北魏北齐的史学成果,是研究北朝叙事文学的最佳材料。书中尤为重视历史事件的记录,精彩篇幅不少,数十篇名臣传记都有这种笔法,在史传文学中,实属上乘之作。虽拙于写景状物,但叙事详尽,文风质朴,反映生活面广,容量较大,优点突出[9]。而且北朝史官修史之余,还要负责撰写各种应急文字。如邓彦海,道武帝定中原时,擢为著作郎。修史之外,还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崔浩修史之外,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归掌管。李彪在魏孝文帝朝专职修史,著诗颂赋诔章奏杂笔百余篇。北朝文人的文集就是利用职位之便编成的,是在职期间撰写的文字汇编。
北朝修史一事还培养出十多位年轻作家。高祐孝文帝初,拜秘书令,改写国史,著作郎以下有才用者尽取之。高允领著作郎,以年迈,引青年才俊刘模参撰,选为校书郎,毎日同入史阁属述时事,如此五六岁,方成篇卷。崔光拜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参撰国书,为孝文帝所知待,称其才华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4]。崔鸿弱冠便有著述志。以五胡十六国各有国书,未能统一,乃撰《十六国春秋》百卷。此外,傅毗、阳尼、邢产、宋弁、程灵虬等,均以文才见举,参与著述。韩子熙、韩兴宗、韩显宗三人一门修史,其文学皆从史学出。《北史》载:“孝文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著作之任,国书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闻。若欲取况古人,班马之徒,固自辽阔。若求之当世,文学之能,卿等应推崔孝伯。’又谓显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谓程灵虬曰:‘卿与显宗,复有差降,可居下上。’”[10]一国之帝王,竟然以史笔高下来铨衡人才高下,从中可知修史一事的分量轻重。以上所列,均为北朝名家,其得名是缘于修史,而非作文。可见修史是造就文学家的另一重要途径,上述史事,也从事务性质和人才培养上表明了北朝史学对文学的促进作用。
再说,即使就文辞之美而言,北朝史学也是不缺乏的。特别是北齐以后,史学风气转变,一改汉魏古朴之风,变为南朝之雕饰。刘知几《史通》云:“盖史者,当时之文也……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11]表明史书文学化,语言精美化乃是一个大势,南北朝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三)碑志:北朝文学的代表样式
自西晋始,秘书省就置有文史撰述部门著作局,内有著作郎、著作佐郎负责写作文章,在其中任职者,通称史官,实为官方任命的专职作家,其所编撰者乃大臣将相传记,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意图。普通人士的传记则不经著作局,而别属民间,听由人臣私撰,不以为非。北魏建国,继承晋代官制,成立秘书省著作局,专司著述,内有专业人员数十人。这些人平日在秘书省的工作不是校书,而是著述,即编撰书籍,写作文章。碑志因为地位甚高,世人重视,自然也在其掌管范围内。论性质属于记事之文,非关论议,与传记同体,都是记述某人或某个家族、地域人群的一生行实,重在纪实。本来,以今日的学术眼光看,碑志主要是一种历史文献,而不是一种文学性强的文体,史料价值比文学价值要高。但在北朝却不然,是一种最受重视的常用文体,居于文学的主流,地位反而要比诗赋高。身为北朝文士,必须谙熟此体的撰写,方能有地位,有成就。撰写要求也不高,只要把人物的家世、生平记述得完整、清楚、明白,详尽可据,那就是善于叙事。这样的书籍和文章,就等同于高层次的文学,并不是从作品是否优美形象感人来看的。汉晋和刘宋因为立碑过多,叙事不实,风气不正,而遭禁毁。但北朝和隋唐并不禁碑[12],不仅不禁止,还十分提倡,全社会从上到下,对于树碑立传一事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和重视,每有高官、名流去世,必请名家写作碑志,树于道旁,供人诵读。同样是石刻传记,但北朝更加重视竖在路旁的石碑,而不是埋在墓道的墓志,大意以为树碑颂德,唯有以此方式来广而告之,宣传效果才更好。因为这些特点,出自名手的名臣碑志,广泛传播于士林,被当作文学范本来对待。擅长撰碑的文人社会地位特别高,仅仅长于诗赋的则被视为无用之人,世人看不起。从王侯、大臣、妃嫔去世到文武臣僚建功,都要安排专人来撰碑作颂,称为“诏撰”。一般的惯例是委派著作郎或其他史官去负责撰碑铭。以上所述都是官方行为,有政治意图。官制之外的民间的普通人士去世,这方面也有十分强烈和普遍的需要。碑颂的社会地位和文学正宗身份,就是在这种上下一气的认同中自然完成的。
《文心雕龙·诔碑》云:“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13]可见撰碑和修史还很有关系,北朝的碑志作家就多是史官。盖因二者都重在记事,以散笔行文,承担的都是史书的记叙职能,只是文体形式不同,“本同末异”而已。《魏书》中载有大量的实例。例如高遵涉历文史,颇有笔札,进中书侍郞,诣长安,刊《燕宣王庙碑》,进爵安昌子。阳休之在中山及治西兖,有惠政,吏民所怀,去官之后,百姓树碑颂德。表明北朝上下都格外重视碑铭写作,平日留意此事,指派专人负责。魏孝文帝甚至带头树立榜样,亲自写作,《弔比干碑》《郑羲碑》即很有名,其作品实是带文性之史或带史事之文。从文体看,最符合这一特点的就是碑志。因是人物传记,史家往往取以修撰正史列传;但它分明又是文章之一类,为文之一体,自古为文士所掌,文人所长。因为体兼文史,官方和民间都重视,从而成为贯穿于中古文学史的一种大文章,中古士人所看重的“笔”之一,据之可检验人才高下,观察文章流变和文体演变。要考察北朝文学史,碑志是理想的备选对象之一。
多数北朝作家的成名都与撰碑有关,碑志甚至是其文学声誉和政治地位的支撑,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胡方回仕夏国赫连屈丐,为中书侍郎,辞彩可观,所作《统万城铭》《蛇祠碑》诸文,颇行于世。高闾为中书侍郎,奉诏造《鹿野苑颂》《北伐碑》,献文帝善之,位至光禄大夫。卢思道聪爽俊辩。年十六,中山刘松为人作碑铭,以示思道,思道读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后复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邢虬善与人交,作碑颂杂笔三十余篇,号为名手。祖珽词藻遒逸,少驰令誉,世所推重。并州定国寺新成,神武帝谓陈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时称妙绝。今《定国寺碑》,当使谁作词也?”[5]元康因荐祖珽才学,乃给笔札,令起草,二日内成,其文甚丽。温子昇文章清婉。为广阳王元渊门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作《侯山祠堂碑》,常景见而善之,称“温生是大才士”,由是知名。熙平初,召辞人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昇等二十四人为高第,遂补御史,时年二十二,台中文笔,皆子昇为之。成名后,常作碑志,其代表作《寒陵山寺碑》青史垂名,论者称其气势宏大,不乏藻采[9]。萧衍使张皋写子昇文笔传于江外。正光末,为广阳王元渊东北道行台郎中,军国文翰,皆出其手,才名转盛,人称“温郎中才藻可畏”。有文笔三十五卷,其中多数是碑志、表启、奏疏。徐纥除中书舍人,太傅清河王元怿以文翰待之。保定四年,涪陵郡守兰休祖阻兵为乱,诏陆腾讨之,巴蜀悉定,令其撰碑纪功。常景雅好文章。宣武帝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其兄右仆射高肇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简择。光奏:景名位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以上七位北朝文章作者的官位、文誉,就取决于其撰碑的才能。而史书对他们文学业绩的称许,也是以文笔、文翰等关键词来包举,而以碑志为标目,可见其优长所在。
北朝重碑志,承传的是汉魏传统。自东汉起,碑颂的地位就日高,而且碑字往往和颂连用,带有表德纪功,弘扬儒家文化观念的功能。每有后妃、名臣、高官去世,必诏史官树碑颂德。桓彬、崔瑗、李膺、陈寔、杜密、荀淑、蔡邕、戴逵、皇甫规、孔融、服?、张升、张超、孙绰、庾阐都是碑颂能手。刺史郡守擅长撰碑的颇多,本州有重要人物去世,必为上奏请求诏准立碑表墓。北魏把这一套全盘继承下来,帝王亲自提倡,风气愈盛。国家出师献捷,必树碑以记。史官邓颖有文学。太武帝幸漠南,高车数万骑诣行所,诏颖为文铭于漠南以记功德。登国六年九月,道武帝于五原大坡匈奴刘直力鞮,还纽垤川,于棝阳塞北树碑记功。明元密皇后杜氏崩,诏为其别立寝庙,树碑颂德。北朝功臣穆崇卒,孝文帝追思其勋,令著作郎韩显宗撰碑建于白登山。著名道士寇修之卒,太武帝诏秦、雍二州立碑于墓。以上作碑都是帝王授意。由于朝廷提倡,因此文士也重视。今人看到的王褒、庾信、邢邵、魏收、温子昇的碑志就是这么来的。魏收平日为文,就“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视同儿戏”[5],把章表和碑铭看得极重,以为其他文体无法相比。温子昇文名极高,南北公推为河朔文伯,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魏文》(卷五一)存文无几,辑存者唯有碑铭九首,外加诏诰、表疏、奏状数篇。虽为残文,但仍有体气清绮的特点,在辞采清丽方面,跟江左并没无两样[7]。庾信长于撰碑,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埓,自余文人皆不及。庾信之外,其他人的情形也大抵如是。表明章表碑颂为多数北朝名家的专长,擅长此道,就是北人心中的大才士,很受欢迎,容易成名。《宋书》载,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曰:“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不加禁裁,其敝无已。”[14]认为碑志写作须贯彻史家实录精神,是处说是,非处说非,无所避隐,方称实录。这一观念,跟东汉以来去浮华,重质实的文学思想是一致的。从王充《论衡》到裴松之上书,都是反对虚浮伪饰,强调真实可信,足以传世。真实性是史书的生命,也是碑志的生命。碑志的价值首先在于记载的合实,可以凭信,其次才是文章的文学特性。裴松之的话反过来看,则表明北朝社会对碑志的看重。碑志的本职是叙事,重碑志也可解为重叙事。这是北方人士的文学观念,秉承汉魏,经过北朝统治者的提倡,变成一种更加浓厚的社会风尚。直到盛中唐,北方作家擅长碑志的仍多,而江南作家则长于诗赋骈文,在文体崇尚上仍有南北之别,反映出北朝文化的深远影响。
(四)书檄:具有时代特色的北朝实用文体
书檄是军书和檄文的合称,二者乃广义的檄文。这样的文体在和平年代没有用场,战争年代却广受欢迎,大放异彩。魏晋南北朝乃是史上最有名的乱世,战争不断。战事之外,各朝还有为数不少的内乱要勘定。这样的不稳定时局使得北朝社会急需擅长写作书檄的作家,书檄作手应运而生。自东汉末到唐代初,乱世维持了四百年,书檄也流行了四百年。直到唐初天下一统,终结乱局,这类文书才归于消歇,此后也未见起色。故可以说,书檄是魏晋南北朝最富有时代特色的文体,只因多数作品成于军旅战阵,无暇修饰辞藻,止于能够达意,文学性贫弱,加以成文于千余年前,文献保存不好,故今人不了解。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些名文,而且还不是全篇,断简残章居多。其中的精彩部分,被历代正史、类书、总集节录,其余则被删除,难窥全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魏晋南北朝檄文多达47篇,表面上看蔚为大观,实则所得有限,据估计,应为当时所写的极小一部分[15]。《艺文类聚》卷五八引《东观汉记》载:光武帝数召诸将置酒赏赐,坐席之间,公孙述、隗嚣所发之檄,日以百数,忧不可胜。又《隋书·李德林传》:“未几而三方构乱,指授兵略,皆与之参详。军书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动逾百数。或机速竞发,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6]这里所举仅是两个普通例子,一天之内,写出书檄就数以百计。据此估算,历代累加,总量之大,可想而知。这样的实例也说明,书檄是一种发布政令,号令天下的应用文,性质跟诏书相近,但比起诏书更有号召力和应急色彩。乱世军兴,写得最多的就是这种文体。大都成于易代之际的政权更迭,内部叛乱或外族入侵,事态紧急之际,每到这些时候,都最需要檄文来发动群众,打击敌人。这时候,书檄就成为一种特殊武器,不仅有很强的号召力、战斗性,还有舆论宣传功效,语言上具有攻击性、煽动性,特别能够耸动人心,激发士气。类似特点和作用,是其他文体所无法相比的。北朝因为地属中原,长期战乱,故书檄的写作较之南朝更加突出,长于此道的多达数十位。单北魏一朝就有多位。如高允,自文成帝至献文帝,军国书檄,多其所作,直到晚年方荐高闾自代。崔玄伯作文有选择,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胡叟高宗时,奉召与宗舒并作《檄刘骏蠕蠕文》,以文劣于叟,遂归家。高闾文章富逸,为献文帝所知,数见引接。永明初,为中书令,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之,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崔?有辞藻,自中兴立后迄于武帝,诏诰表檄,多其所为。孙搴以文才著称,太保崔光引修国史。高祖西讨,登风陵,命李义深、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辞,以搴自代。高祖引搴入账,吹火促之,搴援笔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悦,即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大见赏重。李绘有文才,齐王萧宝夤引为主簿记室,专管表檄,待以宾友。杨愔转大行台右丞。于时霸图草创,军国务广,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出。魏收文笔清壮,才思敏捷。侯景叛魏入梁,率兵伐魏,文襄帝在晋阳,令收为檄文,凡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执笔,三更便成,文过七纸,文襄壮之,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采。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子才、子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5]祖君彦少有才学。隋大业中,为李密所得,署为记室,军书羽檄皆成其手。以上所举,皆为北朝书檄的著名作手。
至于书檄的写作特点及时代背景,则《周书》卷四一有很好的概括:“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其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往往而间出矣。若乃鲁徽、杜广、徐光、尹弼之俦,知名于二赵。宋谚、封奕、朱彤、梁谠之属,见重于燕秦。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争,竞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16]引文中的符檄指广义的檄文,与军书义近。但前者能切时用,后者不乏文采,故受欢迎。《北齐书·赵彦深传》:“徵补大丞相功曹参军,专掌机密,文翰多出其手,称为敏给。”[5]这里的文翰就不是泛指,是指檄文之类的事关机密的文书。《文苑英华》卷六四五檄文类所收七篇檄文,就非常有名,文学性强。计有孔休先《为彭城王檄征镇文》、佚名《为太祖檄齐神武高欢文》(西魏永熙三年作)、杜弼(《艺文类聚》卷五八作魏收)《为东魏檄梁文》、佚名《为行军元帅郑国公檄陈文》(周宣帝大象元年作)、卢思道《为北齐檄陈文》、佚名《为侯莫陈悦檄陈萧摩诃文》《隋檄陈尚书江总文》。卷六五六檄文类,有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房彦藻《为李密檄窦建德文》、孔德绍《为窦建德檄秦王文》、魏征《为李密檄荥阳守郇王庆文》。以上十一篇檄文,均出北朝名士之手,写作目的都是声讨对方,揭露罪恶,宣扬正义,敦促归降。多用骈俪文体写成,写得气势磅礴,理足气盛,充分发挥了骈文文体的优长,大量运用排偶句式,句子齐整,语意凝练,提炼警句,不仅增强了宣传力度,也增强了文章美感,使之更易于传诵,故这些骈文反而广泛流传,反响极大。《东观汉记》载,隗嚣为故宰府掾吏,善为文书,每上书移檄,士大夫莫不讽诵[17]。可见尽管是战争的缝隙写成的,应急性强,文字上不够讲究,但是写得好的檄文,文学性还是不乏,只是今人未见原文,多不了解。今日看来,其文学性在于运用夸张、比喻、排比、虚词修饰的笔法,增强语言的声势和威力,气盛辞刚,中间还有成段的优美描绘和连贯叙述及雄辩的说理,从不同侧面增强了文学特性,应属于北朝散文的重要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