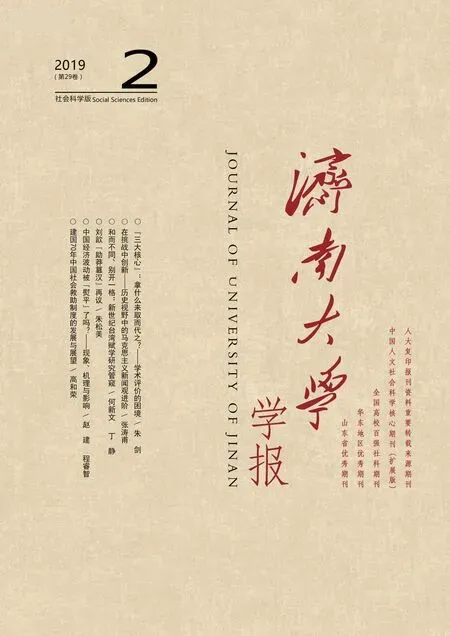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司徒雷登使华
2019-03-05,
,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司徒雷登是近代中美外交关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因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为人们所熟知。司徒氏作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亲历了由美国主导下的一系列国、共和谈。但他是怎么具体贯彻美国对华政策的?他在当时的中美关系,也就是在与国民党、中共等打交道的过程中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目前的相关成果[注]参见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魏楚雄:《美国战后对华经济政策的演变》,《史林》,2006年第2期等等。仍显不足,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和演变,及司徒雷登对其贯彻和反思的视角,就相关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不当之处,恳请教正。
一、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与司徒雷登驻华大使的任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以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对立,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世界冷战格局逐步形成。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思想,都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在此情况下,美国采取除直接武力对抗以外的一切手段,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遏制战略。正如杜鲁门所宣布的那样,“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注][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李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第128页。。其中,中国是除欧洲之外美国推行遏制战略的重要区域。
中国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被纳入世界冷战体系。在美国当局看来,中共成为苏联的工具,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维护美国在亚洲及西太平洋的利益,就要继续执行在二战后期形成的“援蒋反共”政策。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以“援蒋”为核心内容。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在对华政策声明中明确指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美国要以“一切合理的方式”给予帮助[注]③《杜鲁门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1945年12月15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628、629页,第629页。。同时,杜鲁门还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建立联合政府。在使华调处之初,马歇尔向杜鲁门申明:“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注]《美国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770页,转引自《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这一申明获得杜鲁门的理解和支持。这表示,在国共之间,美国政府是明确站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一边的。
美国政府在援蒋的同时鼓励国共协商,以避免内战。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只有改变国民党的“训政”制度,国民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当中国“向和平及团结前进之际”,“则美国准备以一切合理的方式帮助国民政府重建其国家”③。简言之,美国援助国民党的一个前提是,国民党要与中共等党派合作,进行民主化的改革。
可见,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即既要在国共之间宣称保持“中立”,又在实际上偏向国民党政府;既要援蒋,又想迫使蒋介石与中共和谈,停止内战。正是由于这种矛盾,一直在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进行调处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于1945年11月27日发表辞职声明。在此情况下,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使华,继续美国对国民党和中共的调停工作。马歇尔赴华前夕,杜鲁门致信重申,希望国民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尽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注]《杜鲁门总统致总统驻华特使(马歇尔)》(1945年12月15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26页。。
在美国有关方面的调停下,国、共之间展开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根据该协定,1946年1月,国、共和其他方面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决议,宣布要建立和平、民主的现代国家。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企图凭借武力消灭中共,实现中国的统一,导致国、共冲突不断升级,乃至内战的全面爆发。
随着局势的恶化,马歇尔认为,“在调解的努力中,最好能获得一位德高望重并且在中国有长久经验的美国人的帮助”[注]《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第168页。。于是,他便推荐美国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担任驻华大使。1946年7月12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于1876年6月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其于11岁时回美国读书,1904年回到杭州,开始在华传教。1919年1月受聘为燕京大学校长。任校长期间,司徒雷登大力推行中国化、国际化改革,很快使燕大跻身为国内著名高校之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关押,直到1945年获释。司徒雷登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持反对态度,与美国政府一样,对国民党政府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对于驻华大使的人选,蒋介石原属意于一向反共的魏德迈,但蒋常称司徒雷登为“老朋友”,加上司徒雷登在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而非中共,因此从形式上表示欢迎[注]实际上当蒋介石得知司徒雷登将任驻华大使时,并非十分痛快,认为这一任命“于我毫无助益也”(《蒋介石日记》,1946年7月7日)。。中共由于抵制了坚决反共的魏德迈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任命[注]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9-80页。,对于司徒雷登的上任也发表宣言表示欢迎。中共驻上海发言人陈家康指出:“司徒博士为各级共产党员之友人,余坚信彼能与吾人和善共处。”[注]《各方反响·中共之友》,《燕大双周刊》,1946年第17期,第151页。另:“中共代表团代表之一”邓颖超表示,对于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很热烈的欢迎,同时也寄以极大的希望”(《邓颖超同志谈时局》,《群众》第11卷第11期,1946年,第19页)。“第三方面”人士罗隆基认为,司徒雷登“自己就是一个自由思想……一位不左不右的中庸之道的民主主义者”,并以“民主同盟的立场”,对司徒雷登的就任表示欢迎[注]《各方反响·不左不右的民主主义者》,《燕大双周刊》,1946年第17期,第151页。。美国和中国的诸多新闻媒体,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北平的《华北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文汇报》等等,多给予“欢迎”之辞[注]详见《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美国报纸多有好评》,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7月14日,第2版;《各地报纸一片欢迎声》,《燕大双周刊》,1946年第17期,第147-148页;《司徒雷登博士任驻华大使 杜鲁门已正式宣布 我朝野一致表欢迎》,《申报》,1946年7月11日,第1版。。这是“以前来华的使节向所未见的”[注]参见《各地报纸一片欢迎声》,《燕大双周刊》,1946年第17期,第147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徒雷登是在一片欢迎声中走马上任的。
二、司徒雷登使华的主要活动
司徒雷登虽然在一片欢迎声中就任驻华大使,但中国的政局已经是急转直下。国民党部队于1946年4月在东北发动四平街等战役,6月进攻中原解放区,使人们的和平希望愈来愈渺茫。因此,为有效贯彻美国对华政策,司徒雷登认识到,其上任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促成国共双方的和谈”[注]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李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故其上任后,在国共之间积极奔走。
为结束内战,1946年8月1日,司徒雷登在拜访蒋介石时提议,成立一个分别由国共双方各二人或二人以上组成的非正式小组,由司徒氏本人作为中间人,努力促成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在被政协综合小组认可后,召集40人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从而实现此前政协会议达成的建立联合政府的目标,最终结束国共之间的内战,实现人们普遍期望的和平。蒋介石则提出了非正式小组的先决条件:“1.苏北共军撤至陇海路以北;2.共军自胶济路撤退;3.共军自承德及热河省承德以南地区撤出;4.共军须退至东北北部两个半省内地区;5.共军须撤离于6月7日后所占一切地区;6.放弃地方行政尤其是苏北地方行政,但共产党总部可允许保留。”[注]《司徒致国务卿》(1946年8月7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尤存、牛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1990年版,第8页。当司徒雷登带着这些条件同周恩来商谈时,周恩来指出,在这些条件中,国民政府并没有与中共“具有同等义务”,因此这些条件“不符合平等的基本原则”,是“独裁的片面条件”,是“不可能考虑”的。关于与司徒雷登的谈话内容,蒋介石于当日的日记中仅简要记明:“余劝彼(司徒氏)须静观待时,不必急作调解之工作也。”[注]《蒋介石日记》,1946年8月1日。这说明,蒋介石深知中共是不会答应这些具有强迫性的条件的,而之所以提出这些条件,仅是在推脱内战责任而已。通过与蒋介石及周恩来的商谈,使司徒雷登认识到,“国共两党的分歧是多么难以调和”。后来,成立非正式小组的事宜不了了之。这也预示了以后司徒雷登调解国共矛盾的结局。
挑起内战后,对于中共问题,蒋介石主要靠武力来解决。在1946年10月11日攻占中共军事要地张家口后,蒋介石信心大增,单方面宣布召集国民大会。而按照政协决议及有关精神,国民大会须由国民党、中共、民盟等方面一致同意才能召集。因此,中共和民盟等方面拒绝出席由国民党单方面召集的国民大会。但是,国民党一意孤行,拉拢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等小党派,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对此,司徒雷登有明确的认识:“蒋的单方面行为反映了独裁专横倾向”[注]②《司徒致国务卿》(1946年10月15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1页。,“(国民)政府利用现在的拖延采取军事进攻,旨在摧毁共方根据地以削弱共方军事势力”,因此“政府要人应负破裂的大部分责任”②。
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后,中共代表团代表周恩来很快返回延安。返回延安前夕,周恩来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自国民党召开所谓一党国大后,已经把政协决议破坏无遗,政协以来和谈之门已被最后关闭”[注]《周恩来答记者问》(1946年11月16日),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3)增订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3页。。国共和谈破裂后,1947年1月6日,杜鲁门总统命令马歇尔回国,担任国务卿。马歇尔回国,标志着美国调停国、共冲突,推动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受挫。
马歇尔回国之前,就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询问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认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统一、强大的国家,并且为美国民众所接受,与美国关系良好,在太平洋地区有影响力,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如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其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司徒雷登建议,美国政府应采取“一个积极的策略”,即“支持国民政府,尤其是在军事顾问上的援助,帮助他们进行军事上的改革,然后视改革的效果考虑进一步的援助”[注]⑤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144-145页,第146页。。司徒雷登还认为,如果美国的对华策略不能“积极主动”,“不能制止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或是将他们逼到只能战略防御的地步”,仅给国民政府以经济上的援助,结果只能是“徒劳无用的”⑤,因为战争早已使国民政府的预算入不敷出,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体上处于“瘫痪的状态”。
虽然司徒雷登期望美国政府能够确立一个积极的对华政策,对国民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援助,但自马歇尔回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主要原因在:首先,二战后在美国的国际战略格局中,欧洲无疑处于首要的位置,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其次,相较而言,中国处于较次重要的位置,因此,美国不愿进行直接的武力干涉,以免陷入中国内部事务中难以自拔。再次,美国的对华援助,是以国民政府容纳中共等其他党派、进行民主化的改革为前提,但国民党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共问题,导致内战爆发,使得美国对国民政府实行民主化的希望渐成泡影,导致其对华援助迟迟难以兑现。与美国政府的摇摆不定对应,“当时美国对华舆论存在一种普遍不满的状态”[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页。。在此情况下,为对华决策寻找依据,1947年7月22日,美国政府派魏德迈使团访华。但经过在中国一个月的考察,魏德迈向杜鲁门报告,在二战后的中国,“由于政府警察机关的肆虐和压迫,人民的基本自由横遭摧残。苛政与贪污使人民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在实行彻底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前,美援不能完成它的目的”[注]《魏德迈中将致总统杜鲁门的报告》(1947年9月19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782页。。显然,国民政府发动内战,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民主化改革,导致美国政府难以下定决心进行大规模援华。最终,美国的对华援助与国民政府渴望的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全面援助之间的期望相距甚远,且姗姗来迟。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总额为5.7亿美元的援华方案[注]参见《杜鲁门总统致国会咨文提请核准援华方案》(1948年2月18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005-1007页。。但4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的《1948年援华法案》,其中规定的援华总额被削减至4.63亿美元[注]参见《1948年援华法案》(1948年4月3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015-1016页。。而且,根据该法案拨付的援华物资直到该年底才到货。这时,中国的战局已经基本有了结果,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因此,正如司徒雷登所言,这些物资所起的作用“也只是能保证国民党做最后的挣扎了”[注]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李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页。。
虽然司徒雷登一直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积极援华”,甚至还曾“衷心希望”魏德迈使团的访华能够“导致积极援华”[注]《司徒致魏德迈将军》(1947年9月12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125页。,但是,美国政府执行的显然是“有限援华”政策。这对已经“病入膏肓”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此情况下,司徒雷登观察到的是,共产党方面“正稳步地改良组织和训练,官兵同甘共苦,为理想而献身战斗,抛弃一切自私的野心和个人享受”[注]④⑥⑦⑩《司徒致国务卿》(1947年10月29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133-134页,第173页,第249页,第243页,第252页。,而国民党方面“政治与军事的崩溃正接近早已预料的高潮”④。司徒雷登视学生运动为“公众舆论的完全可靠的晴雨表”,但其痛苦地看到,国民党政权“倾向依靠武力镇压”[注]国民党在走向崩溃的过程中,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是全局性的、制度性的。参见《教育部通饬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查明中共及爱国学生立即开除学籍等严惩密代电》(1948年6月26日)、《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秘书处请饬特刑庭不得保释被捕学生代电》(1948年11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182页。,体现的是一种“愚昧态度”,并不断加重“局势的悲剧”。
三、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与司徒雷登离华
在国民政府走向崩溃的过程中,司徒雷登发现美国的对华政策“进退维谷”。因为美国在华援助的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倘若目前能够组织有识之士举行投票选举,结果也许是100%的反对现政府”⑥。而如果“支持一个不代表人民意愿的独裁统治”,就“违反了自决权力这项民主原则”,不符合美国对华政策的初衷。在此情况下,司徒雷登与其他美国在华同仁发生了分歧。
他的一部分同仁认为,随着国民政府的崩溃不可避免,而在联合政府中将有利于中共获得全国政权,因此建议“美国应谋阻止联合政府之组成”⑦。但司徒雷登仍然希望国共双方的矛盾能通过和谈来解决,并产生“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美国政府在考虑了这两种观点后,于1948年8月12日指示美国大使馆:“不可做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表示,以支持、鼓励或接受有共产党参加的中国联合政府。”[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22页。这说明,美国政府改变了之前希望建立包括国民党和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政策,而改为全力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美国改变对华政策,除美苏对抗的全球背景外,美国国内政治态势的变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在194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取得胜利,其取胜的手段之一,就是攻击共产党人渗入了此前民主党占多数的美国政府。因此,杜鲁门为表明反共立场,于1947年春颁布《联邦雇员忠诚法》。根据该法案,任何与共产党有瓜葛或涉嫌的人员都被认为是联邦政府的“不忠诚分子”,从而被清除。于是,“反共立场已成为担任政府公职的必要条件”[注]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自然难以在中国支持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不断溃败,到1948年下半年时,司徒雷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的有效工具了”[注]《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10月16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页。,而且国民党只有得到中共的支持,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此情况下,虽然美国政府已经明确反对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但为有效维护美国的利益,司徒雷登认为,美国“应准备对付任何形式的联合”。在他看来,毕竟“国民党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谴责的弊端,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具有很多值得称赞的造福于民的优点”。鉴于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极大可能性,他还指出,美国政府不应过早地宣布对共产主义的否定性观点,以免不利于美国在华现存利益,或者是在将来处于“难堪的境地”。因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共即将建立的新政权采取“模棱两可的灵活方针”[注]②③《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10月16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53页,256页,第287页。,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利益。虽然司徒雷登支持国民党与中共建立联合政权,但这并不表明他对共产主义不再持否定性态度。司徒雷登强调,“一旦出现联合政府,我们即应全力以赴地支持尚存的非共产党势力,以毫不含糊地表明美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绝不向共产党控制下的政府中的共产党势力提供任何援助”②。
正是由于主张对中共新政权采取“模棱两可的灵活方针”,司徒雷登在中共部队攻占南京之前,就向美国政府请求授权“与中共高级领导会谈”,以至少探明对中共“应该采取的措施的程度”③。在中共部队攻占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后,司徒雷登并没有带领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南迁,而是向美国政府提出大使馆继续逗留南京的意见。两天后,司徒雷登即接到了美国政府的同意意见。司徒雷登之所以提出继续逗留南京,显然是为了与中共政权近距离接触,“以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并和他们讨论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注]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李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页。。
对于司徒雷登,中共方面并不陌生[注]如1945年9月19日,在燕大校友龚维航和其丈夫乔冠华的安排下,毛泽东、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共进午餐。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陈礼颂译,付泾波校订,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0页。,并做了相关准备。为便于与司徒雷登接触,中共方面派曾在燕京大学求学、与司徒雷登相识的黄华负责南京外事处的工作。周恩来明确交代黄华,“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注]⑨黄华:《司徒雷登离华真相》,《燕大校友通讯》,1994年第18期。。周的言外之意,自然是要求黄遇重大事项时,向上级请示。关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毛泽东明确指示黄华,美国政府如果要和中共方面建立外交关系,就应“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注]毛泽东:《黄华与司徒雷登谈话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司徒雷登对与中共的接触持积极态度。他把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看作是美国政府朝着承认中共政权方向跨出的“第一步”。他于1949年4月27日起草了美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的备忘录,其主要包含两点内容:“与非苏维埃国家联合行动;联合国方面须坚持人权保证。”[注]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陈礼颂译,付泾波校订,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22页。5月13日,司徒雷登与黄华首次见面,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⑨,但除平等互利的条件外,还需符合“国际惯例”,即“任何得到本国人民明确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可以得到承认”[注]《司徒致国务卿》(1949年5月14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99页。。6月8日,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泾波[注]傅泾波为中国人,满族,与司徒雷登关系极好。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在大多数场合,他毫无疑问地都能代表我本人”,“成了我外交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傅泾波既像是儿子、朋友、助手,也像是工作上的伙伴”。见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230、231页。在与黄华见面时,提出了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及与周恩来会见的意愿[注]黄华:《司徒雷登离华真相》,《燕大校友通讯》,1994年第18期。。黄华汇报此事后,中共方面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注]陆志韦于6月16日致信司徒雷登:“毛泽东已经宣布了你访问燕京的兴趣,我预计政府将会同意你来访。”(Mao Tse Tung has already announced your interest in coming to visit Yenching, and I presume the government will give you consent),见《陆志韦致司徒雷登函的英文原稿》,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6月28日,司徒雷登得黄华告知,“毛、周会诚意欢迎我的”[注]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陈礼颂译,付泾波校订,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48页。。司徒雷登认为,与中共高层的会见至关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美国“朝着承认共产党政权跨出的第二步”[注]《司徒致国务卿》(1949年6月30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07页。,关系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因此,第二日,司徒雷登即就北平之行,请示美国国务院。但7月2日,美国国务院拒绝了司徒雷登的请求,并要求其尽快离华。在此情况下,司徒雷登与8月2日乘飞机离开中国。大约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正式发表。毛泽东在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指出,白皮书的发表是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注]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05页。。从此,中共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由积极接触转为消极对抗,这种态势直到后来基辛格秘密访华才得以改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司徒雷登没有到北平之行,有论者认为,是令司徒雷登“铸成终生追悔的大错”[注]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意即司徒雷登应先设法与中共接触,打开局面,造成既成事实,而后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但笔者认为,考虑到当时国际上美苏对立的态势,特别是当时美国政坛上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一致对共产党持反对态度,如司徒雷登本人所言,“即使美国人民或政府与大陆的中国人民和那里的政府进行直接性的接触,也不会有什么收获”[注]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李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页。。
四、结语
司徒雷登的离华标志着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司徒雷登的使华悲剧,在于随着战后美苏走向对立,美国朝野普遍把中共看作苏联阵营的一方刻意排斥,而把国民党看作自由主义的象征进行扶持。但国民党贪污腐败问题丛生,统治衰朽不堪,美国投入了很大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没能够将其扶植起来。最终,美国的对华政策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终结而失败。因此,司徒雷登的悲剧,可谓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所造成。
就司徒雷登个人来说,他是一位长期生活在中国,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积极改善美中关系的外交家。他与美国政府一致,贯彻自由主义理念,积极援助国民党。但他对国民党的分析,却令自己甚为失望。国民党被他看作是“自己的一方”,刚开始与之接触时,他认为“不必悲观”,“相信美中关系尚有许多潜在希望”[注]②《司徒致国务卿》(1949年11月13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4页,第117页。。但不久他就认识到“情况正在迅速恶化”,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对此,他却自认“一筹莫展”②。他排斥中共和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看到,与国民党腐败衰朽的景象相比,“共产党内部毫无任何的贪污腐败,从军官到士兵都生活朴素,严格遵守军纪”,“从表面来看,共产党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了千百万个他们所需要的人,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和其他文明要花费很长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几个这样的人,拥有这样的素质,包括优秀的组织能力、严格的自我约束能力、将公共事业放在个人和家庭之上、无私服务于人民、充沛的热情和对理想的忠诚。和国民党那些恶习相比,这些成就是如此光彩照人”[注]⑤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197页,第236页。。可悲的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以腐败的国民党为依赖对象,并最终走向失败。
国共内战的结果,显然并非完全如其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说,“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注]《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1页。。这实际上是把中国内战的责任完全归之于国民党,推脱美国的责任。总结美国对华经验,司徒雷登则认为,美国外交策略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合法、道德和正义的基础上”,而不应该是“毫无原则,放弃原本合理的传统,根据凭空才想出来的可能性来作决定,机会主义”。对于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美国人民和政府仍能为中国做很多事”,但与中国打交道,美国应该遵守“黄金定律”,也就是“以己之欲施之于人,我们想要得到他们怎样的对待,就应该怎样去对待他们,反之亦然”。这种认识无疑是一种审视历史后的洞见,有益于美中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实际上,正是后来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才打开了美中关系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