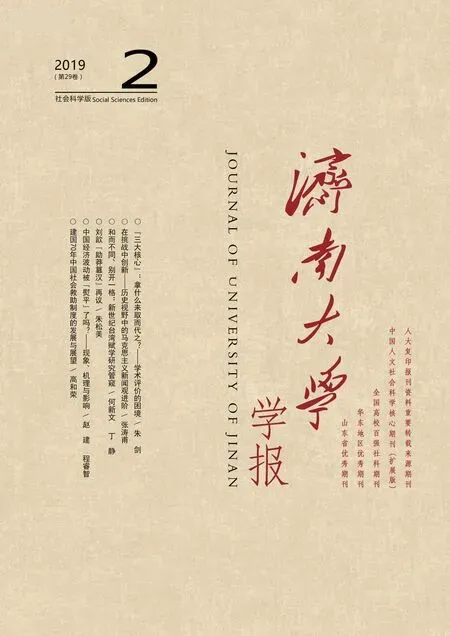刘歆“助莽篡汉”再议
2019-03-05
(济南大学 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刘歆“助莽篡汉”的嫌疑自两晋以来似乎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为“事实”,以至于上升到道德品判的高度而被指称为“行邪”“不孝”“不忠”[注]西晋傅玄评价刘向、歆父子谓:“向才学俗而志忠,歆才学通而行邪。”(傅玄:《傅子》,严可均:《全晋文》卷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40页)洪迈《容斋随笔》称刘歆“不孝”“不忠”(洪迈:《容斋随笔》卷九,《续笔》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239页)清末以降,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继其观点,直指其“伪造古文”、“助莽篡汉”。。其实,当我们深入历史深处,从刘歆的行为、出身及其与王莽的关系入手,对刘歆倡立古文、扼制谶纬、发明五德终始、与王莽的关系演变及其皇族出身与性格养成等进行全面细致地梳理分析之后,便会发现上述指称带有太多主观臆测成份,真正的事实应该是:刘歆“佐莽辅政”是真,“助莽篡汉”是假。
一、扼制“更受命”
君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他们必然为满足贪欲,利用权力巧取豪夺。然而,君主制政权又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巧取豪夺的结果必然造成小农经济的破坏,从而动摇国本,这是君主政治的先天“死结”。这一“死结”伴随君主政治始终,而在西汉统治中率先表现出来。
面对武帝以来日渐加重的社会矛盾与政治危机,政治上层也曾绞尽脑汁寻求自救。元帝时翼奉上书建议迁都:
臣闻昔者盘庚改邑以兴殷道,圣人美之,……必有非常之主,然后能立非常之功。臣愿陛下徙都于成周。[注]班固:《汉书·冀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76页,第3178页。
这种迁都的把戏除了表现出士人的迂阔外,丝毫无益于挽救岌岌可危的西汉统治,就连“易欺而难悟”[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八《汉纪二十·元帝初元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6页。的元帝也对此颇感疑惑:“书奏,天子异其意,答曰:‘问奉:今园庙有七,云东徙,状何如?’”班固:《汉书·冀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76页,第3178页。迂腐的迁都之计就此不了了之。
哀帝继位后,大臣师丹、孔光等又积极推动哀帝下诏限田限奴:
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注]②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42-1143页,第1143页。
与迂腐的迁都之计相比,限田限奴倒真正击中西汉统治要害,这也是后来王莽改革“王田私属”的范本。但这一旨在减轻矛盾、收拾人心的政策遭到外戚丁、傅和宠臣董贤等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结果在哀帝“且须后”②的无奈中搁置下来。西汉统治上层的政治自救运动至此破产。
《左传》云:“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注]《左传·庄公三十二年》,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83页。汉末政治自救失败、社会危机加重,自董仲舒因《灾异之记》获罪后有所收敛的灾异论再度兴起,且更为普及化。社会不同阶层、集团借此表达各自的愿望和理想。从大势上看,主要有三股势力:一是底层百姓。他们利用灾异、假借“神”的力量发泄积怨,希图拯救自身于水火。如哀帝建平四年,关东大旱,饥民浩浩荡荡西入京师长安,借祠西王母,奔走呼号[注]“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班固:《汉书·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2页。);二是熟谙经学的儒者。他们纠结于民生疾苦与政权安危的情感旋涡,既悲悯苍生、痛恨腐朽,却又挣扎于“维系”与“抛弃”政权的矛盾之中;三是以王氏为代表的外戚势力。他们巧妙地借用儒者对政治的抨击,以成就自己颠覆汉政权的目的。
不过,深入来看,上述儒者阶层其实又可细分为两股势力:
一部分是一般儒者。他们饱受经学熏染,原本情感上并不希望看到汉政权的倾覆,所以,眼看社会矛盾日深、政权危机日重,他们承续董仲舒以来《公羊春秋》的传统,借灾异抨击时政,希望执政者从他们的抨击中猛醒,纠正时弊,挽汉朝大厦于将倾。从眭弘借灾异劝昭帝让贤到盖宽饶警示宣帝让位[注]班固:《汉书·盖宽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47、3247、3248、3245、3248页。,再到元帝时贡禹、京房的抨击[注]“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班固:《汉书·贡禹传》,第3072页)“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班固:《汉书·京房传》,第3160、3162页),灾异谏政之风日盛。到成帝时,儒者们对于政治自救显然已由希望转为绝望,于是“汉家天命将终”的舆论开始甚嚣尘上。精于京氏《易》的北地太守谷永以“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警告成帝[注]班固:《汉书·谷永传》,第3467、3468页。,劝成帝传位让贤[注]“白气起东方,贱人将兴之表也。黄浊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夫贱人当起,而京师道微,二者已醜”,“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班固:《汉书·谷永传》,第3452、3453页)。而甘忠可竟直接搞起了“改元易号”的闹剧。
另一部分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刘氏皇族。在汉末灾异论兴起的大环境下,刘向、歆父子也都是灾异论的精通者[注]刘向曾撰《洪范五行传论》,集灾异论之大成。其子刘歆也曾借修订《洪范五行传》重释灾异。。他们与一般儒者相同的是,深受经学熏染,有着与一般儒者相同的政治情感,痛恨政治腐败。因此,面对外戚王氏势力的膨胀和元帝的荒淫,刘向也曾无奈地祭起《公羊传》“天人感应”、“通三统”的大旗,上疏极谏:“物盛必有非当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注]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第1960-1961页。作为儒者,刘向希望借灾异警示统治者,摆脱衰世,再建理想的王道政治,维系汉政权的长期存续。但是,作为宗室,他与一般儒者不同的是,其绝不愿看到汉政权被颠覆。因此,当一般儒者对汉政权由希望转向绝望、由维系转向抛弃的时候,刘向的态度却由与儒者共伍、警告统治转为与一般儒者背道而驰,扼制可能给汉政权的稳固带来隐忧的“更受命”:“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注]②③⑤班固:《汉书·李寻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92页,第3192页,第3193页,第3193页。因为刘向的抵制,甘忠可被“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这场威胁汉室的闹剧总算没有得逞。
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夏贺良再掀“更受命”闹剧。刘歆继其父继续坚决扼制:
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②
建平二年六月,“久寝疾”的哀帝竟接受了夏贺良的建议,发布改元诏书:
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惧焉,战战兢兢,唯恐陵夷。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隆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③
但因“上疾自若”又“卒无嘉应”,且哀帝大概也从中嗅到了“改朝换代”的危险[注]事隔十二年之后(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正是假借“元将”年号上奏太后,为居摄张本:“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藏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班固:《汉书·王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94页),旋即于八月悔诏。夏贺良等先以“背经谊,违圣制,不合时宜”“反道惑众”之罪“下狱”,之后又以“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之罪“伏诛”⑤。刘歆对“改元易号”的反对,表明了其作为皇族,在“维系”还是“抛弃”刘氏政权之间与其父亲相同的立场选择[注]刘向反对易姓授命的立场,另见钱杭:《西汉末年的经学与政治——刘向、歆父子》,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10-313页。。
显然,身为皇族,刘向、歆父子与一般儒者由挽救汉政权到背弃汉政权的态度转变不同,其从警示统治到扼制甘、夏“更受命”的态度变化,显示了他们始终希望通过“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陂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以达到“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注]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46页。的目的,其维护汉政权长期存续的政治目的是始终如一的。
二、倡立古文经
繁苛征敛与土地兼并[注]如武安侯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44页)。造成的自耕农破产,早在所谓“西汉统治最辉煌”的武帝时期就已经相当严重。元帝以后,武帝时对旨在抑制豪强的迁豪政策及所建常平仓的废止,使得官僚、地主、豪强、富商巨贾四位一体的兼并势力趁势崛起,加之上层贪婪与赋敛加重,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豪强大姓,蚕食亡厌”[注]班固:《汉书·鲍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88页。,“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注]班固:《汉书·谷永杜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62页。,“百姓饥馑,流离道路”[注]班固:《汉书·薛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93页。,起义不断[注]如成帝时,在频繁的大旱、洪水、山崩、地震之余,仅见于《汉书·成帝纪》的就有阳朔三年(前22年)颖川铁官徒申屠圣起义;鸿嘉三年(前18年)广汉郑躬起义;永始三年(前14年)尉氏樊并、山阳铁官徒苏令起义(班固:《汉书·成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4、318、323页)。,西汉统治危机日重。
绥和二年(前7年),四十五岁的成帝刘骜在荒淫中暴毙,无嗣,侄子刘欣继位为哀帝。哀帝执政伊始,曾经试图收拾人心、挽救衰政,诏告天下:“制节谨度以防奢淫”[注]班固:《汉书·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6页。,精简机构、限田限奴、抑制兼并。但是,哀帝的自救,在其孱弱、短命与贵族的抵触中破产,西汉统治由病入膏肓走向彻底覆亡已为时不远。不过,这一政治自救引发的新一轮的学术选择,催生了绵延中国两千年的今古文之争,《春秋》学因此再掀波澜。
建平元年(前6年),刘向去世,刘歆代父继续校理宫中藏书。刘歆上任伊始便上书哀帝,将民间献上的《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立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注]⑦⑧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7页,第1970、1971页,第1970页。,遭到今文博士的激烈反对。刘歆为此愤而写了洋洋洒洒千余言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全文大意有三点:一是历数今、古文经典的产生和流传,说明经典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特别是以古文经或出于孔壁、或传于民间的来历,证其可信性与立于学官的重要性;二是抨击今文学者或因循陋学“保残守缺”、“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或“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妬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出于一己狭隘与私利,阻碍经典的广立与流传;三是明确宣示,这次倡立古文经典,原本出于哀帝旨意:“今圣人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发遗”,抵触古文立于学官,实则“违明诏,失圣意”⑦。
按《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述,刘歆倡立古文的目的无非是一介儒者为“思废绝之阙”⑧,“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注]班固:《汉书·儒林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3页。,保存儒家经典、挽救儒经流散,以免“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注]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0页。做出的一般性努力。因为按照常理,通过文化传承拯救国家政治命运,通常是学者最能够有所作为的地方。但倘或把刘歆“大好之”且“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的《左传》的倡立,放到西汉三传轮替的大背景下考量,似乎并没有《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所说的那么简单。
中国两千年经典诠释实践不断验证着一个事实,即:经典诠释虽然一直以回归原义为要旨,但却无可避免地要随时代不同而做出不同诠释,这就是经典诠释的时代性。那么,刘向隐于《上书》背后,倡导《左氏》的政治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结合清末以来“王莽倡立古文究竟是否为助莽篡汉”的问题一并回答。
关于刘歆倡立古文《左传》的目的,清末以来持“刘歆伪造古文《左传》”说的学者都认为:刘歆伪造《左传》、倡立古经是为“助莽篡汉”。先有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比附春秋年月改竄左氏”[注]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二,《续修四库全书》(1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一说,后有康有为《伪经考》“莽文居摄名义亦由歆。即此一言(《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歆之伪作《左氏春秋》书法,以证成莽篡,彰彰明矣”[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的结论。崔适《春秋复始》接康氏之踵,以为刘歆伪造《左》、《谷》二传,是为“破坏《春秋》,为莽饰非。”[注]崔适:《春秋复始》卷一《以春秋为春秋》,《续修四库全书》(131册),第383页。崔适的弟子钱玄同也在《新学伪经考·序》中重申师说。自此以后,刘歆“伪造群经、媚莽助篡”的说法弥漫学术界。对此,钱穆曾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力驳此说。钱穆的考证,理据确凿,极有说服力,“刘歆造伪以助莽篡汉”的说法其实难以成立。
首先,古文《左传》非刘歆伪造,这一点钱穆已有详论[注]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五册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06页。,而《左传》见载于刘歆之前的文献,无疑是驳“刘歆伪造”说最有力的证据。观先秦汉初古籍的确可频见引用《左传》[注]详见刘师培:《周季诸子述左传考》,见刘师培:《左盦集》卷二,《刘师培全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者,说明这期间《左传》一直在民间流传,不待刘歆造伪而成。明显的几例如:《战国策·楚策四》的《客说春申君》篇有荀子曰:“《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围聘于郑,未出竟,闻王病,反问疾,遂以冠缨绞王,杀之,因自立也。齐崔杼之妻美,庄公通之。崔杼帅其君党而攻。庄公请与分国,崔杼不许;欲自刃于庙,崔杼不许。庄公走出,踰于外墙,射中其股,遂杀之,而立其弟景公’”[注]刘向:《战国策·楚策四·客说春申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67页。;《虞卿谓春申君》篇也有:“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注]刘向:《战国策·楚策四·虞卿谓春申君》,第582页。鲍本认为第二例中的“《春秋》”二字是衍文,不确。因为,从所引文看,《战国策》引《春秋》并非一处,且“于安思危”的确见于《左传·襄公十一年》。。上述两段所引三事,分见于《左传·昭公元年》[注]《左传·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伍举为介。”(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19页)、《襄公二十五年》[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春:“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庄公通焉。”(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83页)和《襄公十一年》[注]《左传·襄公十一年》十二月:“《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51页),而今之《春秋》无载。可见,上文均引于《左传》,所谓“《春秋》”即《左氏春秋》简称。另,《吕氏春秋·求人》也有:“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极卑极贱,极远极劳。虞用宫之奇,吴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国者,虽至于今存可也。”[注]《吕氏春秋·求人》,《诸子集成》(6),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2页。上述“宫之奇谏虞公”一事,分见于《左传》之僖公二年、五年,“伍子胥谏吴王”一事,见于《左传》之哀公元年、十一年,全不见于今之《春秋》。除此而外,其余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均证实“至少在战国末期,《左传》已流传甚广”[注]陈鸿超:《〈左传〉先秦传授世系再议》,《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2期。。再者,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而其《说文解字》的著成,就吸纳了包括“《礼》,《周官》、《春秋》,《左氏》”在内的“古文”[注]许慎:《说文解字·叙》,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42-843页。。《史记·吴太伯世家》有:“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之句吴兄弟也。”[注]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75页。《汉书·梅福传》也有:成帝绥和元年“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注]班固:《汉书·梅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27页。的记载。司马迁说的“《春秋》古文”和《梅福传》提到的“《左氏》”即是指《左传》,这是《左传》在西汉武帝到成帝时流行于世的明证。《汉书·儒林传》更是详细记载了《左传》在西汉的传播:“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注]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0页。。班固探本溯源,辨明《左氏》流传自成体系,如刘师培所说:“今之论古文学所以得名,由诸经出于孔壁,写以古文。孔壁既虚,则古文亦伪。夫孔壁而外得古文者尚有河间献王,献王得书在景下之间,然学者之治古文学,则在景武以前。足证秦汉之间,古文之学虽残佚失传,然未尝一日绝也”[注]刘师培:《汉古文学辨诬·论西汉初年学者多治古文学》,《刘师培全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众多文献记载既已证实《左传》自战国至汉初一直流传不辍,足证其存世于刘歆之前,而非待刘歆伪造。至于《汉书》“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注]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7页。的记载,除了证明《左传》存世先于刘歆外,只能说明刘歆在汉末政治衰败的特定环境下,试图借解说《左氏》为匡扶汉室努力。《左传》既非刘歆伪造,那么,他倡导古文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又是否是为“助莽篡汉”呢?从其倡导古文的时间、学术发展和政治环境诸因素综合看,这一结论并不成立。
首先,从刘歆倡立《左传》的时间看。如钱穆分析,刘歆倡立古文时,王莽正处于政治起步和失意期,此时刘歆倡立古文,与“助莽篡汉”根本扯不上关系。王莽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代叔父王根任大司马,次年(前7年)成帝去世,哀帝继位。其时,哀帝外戚傅太后及丁皇后家族得势受宠,王莽卸职离任,隐居于新都,韬光养晦,闭门不出。元寿元年(前2年),哀帝为舆论所迫,召王莽回京侍奉王太后,但并没恢复官职。至元寿二年(前1年)哀帝去世,王氏家族才重新掌权。王莽官复原职,拥立汉平帝登基。其后,王莽的政治野心才逐渐暴露。刘歆倡立《左传》是在哀帝即位的次年,即建平元年(前6年),而在整个哀帝一朝,王莽及其政治后盾——以王政君为代表的王氏家族,一直处于哀帝外戚的排挤之下。在这种局势之下,就连王莽本人是否能官复大司马之职、重掌朝中大权都未可知,刘歆又岂有与其共谋、助其篡汉之想呢?
其次,从学术发展上看。事实上,帝王对于今、古文经的偏好和支持并无固定倾向和一定之规,完全以当时的政治需求以及它们对当下社会政治所能发挥的实际功用为衡量标准。西汉末年以来,章句之学的烦琐僵化,使经学大义淹没于繁言碎辞的繁琐解释之中,降低了维护大一统政治的社会功能,王莽篡政倡立古文就是今文经学在严重社会危机面前失灵的表现。所以,今文经学的烦琐化和谶纬化,使得其自身日渐丧失了立足社会、辅翼政治的能力。
早在西汉末年,刘歆就曾对西汉中叶以来盛极一时的章句之学以尖锐批评:“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注]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0页。“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注]班固:《汉书·艺文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3页。刘歆的批判主要围绕两点:一是指责今文经学的繁琐,使人穷其一生难通其真意,已经完全背离了经学“用日少而畜德多”的教化目的。要求简化经学,求真务实,玩其大体,尽快结束“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烦琐章句学风;二是批评今文经学的教条。家法传授,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安其所习,终以自蔽”,“党同门,妒道真”,狭隘自闭,对于经学的发展遗患无穷,要求冲出师法家法,打破门户之见,广征博纳,今古会综,繁荣经学和学术。刘歆的指责虽然主要站在学术立场上,但针对今文经学却并非局限于今文经学,在更大范围上反映了汉末经学乃至政治领域以复古求革新的新倾向。
最后,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按照刘歆自述和哀帝的说辞,倡立古文只是为了“广道术”而已,即为学术而非政治考量,以致钱穆也相信刘歆:“引传解经”、倡导古文是为“经传比附,用相证切”[注]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五册上编),第164页。。然而,为学术自然无不可,而“非政治考量”却并非尽然。前已有述,西汉末灾异说的兴起,本是针对汉末政治腐朽与戚宦弊政,然而它的延伸与演化,却构成了对汉室的两大威胁:一是自成帝以降的谷永、甘忠可开始,本为警醒统治的灾异论演化为旨在颠覆汉室的“更受命”;二是灾异论的信仰与解说日益广泛化,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不仅成为儒者匡扶政治的工具,也同样成为民间百姓和外戚反抗与颠覆汉室的武器,如杜钦、谷永就是善说灾异的高手。也由此而言,谷永的“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注]班固:《汉书·谷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67页。,与一般儒者的警醒汉室相比,更具有颠覆汉室的色彩。对于灾异之说与政治的关系,顾颉刚曾敏锐地指出:“灾异说已经把汉家的地位在精神上打倒了。”[注]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的确,后来,外戚王莽正是利用了灾异说不仅从“精神”上,也在现实实践中“打倒”了西汉。
而从学术根脉上看,灾异论正是源于《公羊春秋》。刘歆倡立古文《左氏》,意图上正为了通过提倡《左氏》[注]《左传》虽也有大量巫祝及“社稷无常奉”之类的警示,但也不乏“天道远,人道迩”之类的言论。这些言论和《左传》中大量的史事叙述一起,可以通过真象还原适当冲淡、中和对《公羊》的迷信,从而部分校正或拯救时人对汉政权的绝望。,稀释《公羊春秋》灾异说,转移社会舆论对刘氏皇族的攻击焦点[注]比如对于《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刘向、刘歆的解释是:“刘歆以为上阳施不下通,下阴施不上达,故雨,而木为之冰,雰气寒,木不曲直也。刘向以为冰者阴之盛而水滞者也,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协)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9-1320页)刘向、歆的解说,将天降灾异有意从对最高统治者的惩戒转移到臣子身上,以此降低对最高统治的谴责,从而尽全力维护刘姓帝王的权威。,扭转“汉将灭亡”的舆论导向,摆脱对西汉政治的舆论威胁,拯救西汉政治危局。因此,《移让太常博士书》显示,刘歆之为维系汉政权而倡立古文,与哀帝同气相求。因为《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今圣上……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绝不可能是刘歆“伪造皇帝的旨意”[注]吴涛:《“术”、“学”纷争下的西汉〈春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这一结论,还可以在大司空师丹将一顶“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的大帽子扣到刘歆头上时,哀帝一句“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注]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2页。弱弱的袒护,可以证实。
只是,刘歆的这一努力因为哀帝的懦弱、久病和早夭以及缺乏像宣帝倡立《谷梁》时的长期谋划,更因为西汉统治积重难返而归于失败。至于后来王莽推重古文经学作为托古改制的舆论工具,却与刘歆倡立古文经的初衷南辕而北辙。
三、倡导“新五德”
西汉后期,伴随危机日重,谶纬兴起。到汉末元、成、哀、平之际,经学也走上谶纬化。经学谶纬化的社会现实机缘,就是西汉后期的经济、政治危机。
“新五德终始说”就是在汉末谶纬兴起的背景下出现的。关于“新五德终始说”究竟由谁发明,学界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源于刘歆《三统历谱》,为刘歆所造[注]徐栋梁:《〈春秋纬〉与汉代春秋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7页。另见徐栋梁、曹胜高:《〈春秋纬〉成书考》,《济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一种认为刘歆《三统历谱》中的“五德终始”与《春秋纬》中的“五德终始”“二者并行”[注]刘明:《汉代〈春秋纬〉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47页。,因而非由刘歆所造。但无论如何,至少不能否认,刘歆认同并倡导“新五德终始说”。
“新五德终始说”是汉末政治危机下关于德运问题的新论证,而德运问题又是历朝历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重要依据。历史上,从战国邹衍的“旧五德终始说”,到汉初关于“五德终始”的争论,再到董仲舒的“三统论”和汉末刘歆倡导的“新五德终始说”,都是通过德运论证寻找政治合法性依据的努力。
邹衍的“旧五德终始说”最早将五行说运用于政治,用五行相胜解说政权更替。按照邹衍的说法,从黄帝到夏、商、周依次为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按照这一轮转次序推演,代周而起的朝代一定是水德。秦始皇以秦代周,采纳邹衍五德终始理论,以水为德,色尚黑[注]《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律历志》记载了秦始皇对“五德终始说”的推崇。。
汉代建立,同样要面对政治合法性论证问题。因而,对“德运”问题的争论,伴随西汉政权的兴衰,从初期的高祖、文帝到后期的哀、平时期,经历了土德尚黄、水德尚黑和火德尚红的几番轮替。
汉朝初建,一则诸事草创,百废待兴,尤其忙于拯救凋敝不堪的经济;二则起于民间的大臣们对于朝代更替、五德终始的事情不甚明了[注]《史记·封禅书》说:“汉兴……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内、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78页),德运问题也便与其余经济、政治制度一样袭取秦朝[注]《史记·历书》说:“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司马迁:《史记·历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0页)班固《汉书·律历志》也有:“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班固:《汉书·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4页),为水德,尚黑。但是,这里的问题是,汉既代秦而立,若承认秦为水德,按照五行相克的朝代更替理论,土克水,汉代秦,汉应是土德,色尚黄。于是,在文帝时期,朝廷上围绕汉代德运问题兴起了一场争论。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以贾谊和公孙臣为代表,他们认为:汉既代秦,秦为水德,按照五行土克水的理论,汉应为土德[注]《史记·贾生列传》:“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92页)之后,“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81页),尚黄;另一种以丞相张苍为代表,他坚持高祖的主张,以“高祖初起,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杀者赤帝子也。’……因以十月为年首,色上赤”[注]⑧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10页,第1212页,和“汉乃水德之时,河决金堤,其符也”为依据,将尚赤和尚黑结合,“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⑧。因为张苍时任丞相,他的说法不仅继承了高祖的意见,且仔细揣摩,以汉为水德又多少有些蔑视秦的存在、高扬汉政权的意味,因此得到文帝赞同,以“公孙臣言非是,罢之”[注]③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12页,第1212-1213页。。但是,第二年却出现了“黄龙见成纪”[注]《史记·孝文本纪》:“十五年,内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0页)的祥瑞,文帝以为此为上天之符,于是又改变态度,“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③,认同了公孙臣“汉当土德,色尚黄”的说法,“张丞相由此自绌,谢病称老。”[注]司马迁:《史记·张丞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82页。但是,后来因为又发生了赵人新垣平以“言长安东北有神气五采”和“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注]⑥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82-1383页,第1384页。欺诈文帝的事,大概文帝由此产生联想,怀疑公孙臣的“黄龙见成纪”也是欺诈,最终放弃了改正朔的事。公孙臣改正朔的建议受了新垣平的拖累,终究没有成功。
到武帝时,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富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重建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史记·封禅书》记载:“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⑥儒者察言观色、审时度势,急武帝所需,提出了改正朔的事。但因为窦太后作梗暂时受挫,直至武帝亲政后才得以达成。董仲舒在一番“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通以已受之于天”[注]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质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2页。的理论论证下,改邹衍“五德终始”为“三统说”,以夏、商、周分别为黑、白、赤统。三统循环往复,秦朝忽略不计,至汉重为黑统[注]“春秋作新王之事, 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质文》,第247页)。汉武帝采纳了三统说的正朔,却袭用了贾谊和公孙臣的五行土德论的服色: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注]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9页。汉武帝竟通过强行扭合两种本不相融的学说,完成了太初改制。
《汉书·平帝纪》记载: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注]班固:《汉书·平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页;《汉书·王莽传》记载此事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谐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政乖缪,一异说云。”(班固:《汉书·王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69页)对于两次记载时间不同,顾颉刚猜测:“大约此事非一时可办,四年征遣,五年数千人集京师,乃令记说廷中耳。”(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五册下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32页)时正受王莽器重的刘歆自然在这些“异能之士”之中。同年五月,“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注]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2页。《汉书·律历志》也说:“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注]班固:《汉书·律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9页。上述记载一则说明了刘歆“考定律历”而著的《三统历谱》(即《世经》),可能就是当时朝廷大规模征诏“异能之士”,在“钟律”方面取得的成就[注]钱穆考证,在律历方面“刘歆作《钟历书》。又著《三统历谱》”(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五册上编),第188、189页)。;二则交待了刘歆《三统历谱》的写作基础是其父刘向的《五纪论》,《三统历谱》的思想是对其父刘向《五纪论》思想的继承;三则阐明了刘歆所作《三统历谱》为“说《春秋》”提供了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即涵盖了“新五德终始说”。
《汉书·郊祀志》记载了刘歆“新五德终始说”的大致内容:“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庆,顺时宜矣。”[注]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70-1271页。这些内容涵盖了以下几个特点:一、从邹衍“旧五德终始说”的强调五行相胜,开始转向强调五行相生;二、与邹衍的“旧五德终始说”以黄帝开始不同,“新五德终始说”以伏羲(而非黄帝)为开端,伏羲之下依次是共工、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帝舜、伯禹、成汤、周武王、秦、汉,其中共工因“任力而不任德”,帝挚因“立而不知世数”,秦因“任知刑以强”,被刘歆作为闰统排除在正统德运轮转次序之外,剩下的从伏羲为木德开始,以下按照五行相生的次序依次是神农(火)、黄帝(土)、少昊(金)、颛顼(水)、帝喾(木)、帝尧(火)、帝舜(土)、伯禹(金)、成汤(水)、周武王(木)、汉(火)[注]《汉书·律历志》载:“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班固:《汉书·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9页)。;三、从“故高祖始起”的行文推测,在班固看来,刘向父子“新五德终始说”的所谓“汉为火德,尚赤”一说,其实是源于张苍当年坚持的“高祖斩白蛇”的故事;四、从文后“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庆,顺时宜矣”的论证看,刘向倡导“新五德终始说”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论证汉代火德合于五行大统,是为汉政权的长期性和永续性作论证,而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为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注]一部分学者认为刘歆创“新五德终始说”是为王莽篡汉作理论论证。持这一观点的如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五册下编))、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曹婉丰:《“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王莽代汉立新为中心的讨论》(载《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等。。
那么,汉代德运问题在经历汉高祖、文帝的德运之争和董仲舒的“三统”建构后已然尘埃落定,刘向父子为什么还要倡导新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当时社会现实层面找寻答案。
首先,从长远看,这是君主政治已然确立的必然结果。结合时代背景考察不难发现:邹衍的“五行相克”和董仲舒的“三统论”诞生于战国、秦和西汉君主政治体制的确立期。君主政治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战国时期只是在某些国家零星出现,秦始皇一统天下,也只是匆忙搭建起了大致的体制框架,真正的建设期是两汉时期。在武帝以前,这是一个新体制确立的上升期,在这样一个时期,思想理论自然要围绕新体制对旧体制的否定立论。因而,理论与政治相一致,充满着否定旧体制的革命性。邹衍的“五行相克”和董仲舒的“三统论”正是具备了这样的警示性、否定性和革命性特点。然而,到了西汉末,在君主政治体制已然确立的情况下,政权合法性论证便相应地由建国伊始的革命和否定性趋于保守。刘向父子的“新五德终始说”即疏离、淡化邹衍和董仲舒理论中的以新代旧的激进和革命性,转而以“汉为尧后”为依据,从神农——尧——汉德运的循环相生,再论汉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和永续性。
其次,从当下看,这是汉末政权衰落的必然结果。前已有述,自武帝以后,西汉统治转入中衰,特别是元、成、哀、平之世,在外戚专权、政治腐败中,从眭弘到甘忠可、夏贺良,汉运已衰、改元易号的呼声甚嚣尘上。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论证汉代德运的任务变得紧迫起来,作为汉宗室的刘向父子,在一边压制甘忠可等的“更受命”闹剧的同时,也不得不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通过“新五德终始”理论,从汉初政权存在的合法性论证转向汉政权长久存续的合法性论证,给予危机中的汉政权以永续性的新希望。这正是刘向父子倡导新五德终始说的目的所在。这一目的与表现,是与他们的皇族出身及其坚定维护刘姓政权的一贯做法相一致的。至于这一理论初衷被后来的王莽、公孙述等拿来与谶纬结合,经过偷天换日似的改造,成为论证汉代德运已尽的依据,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还可以从《春秋纬》所载“新五德终始说”的内容考察一下其具体功用。
《春秋纬》接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目的就是通过神化孔子和《春秋》,达到进一步神化、警示政治的双重目的。只不过,两者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社会问题已经大不一样了。前者处于君主政治的确立和上升期,后者处于君主政治危机及其调整期。因此,前者的目的重在如何确立巩固政权,而后者的目的则重在度过危机,维系政权的延续。回顾历史,君主政治自秦始皇初立后,因为秦朝的快速灭亡及对这次灭亡教训的总结,才有了西汉政权的建立和汉武帝首次政治调整后西汉政治达到的鼎盛。但是,经过汉武帝的政治调整和完善,以往作为君主政治的根源性弱点——君主政治缺乏有效权力监督的问题,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愈加彰显。正是这一痼疾,致使西汉政权在昭、宣之后很快沦入衰落。面对社会政治危机,士人们能够想到的唯一办法,依然是当年董仲舒举起的那柄用“天人感应”神化和警示政治的双刃剑[注]见朱松美:《国君与庶民同谴 制度与教化并行——董仲舒安民稳政思想要义》,《聊城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但是,面对君主政治江河日下的危局,依然用相同的办法,却再难达到相同的效果。唯一的办法就是神化孔子和《春秋》,通过再诠释,将经典创立者与经典一起神化以提升效果。
首先,进一步神化皇权是稳定人心、维系汉室稳定的必然选择。以孔子秉受天命、为汉制法,强调汉政权的建立是秉承上天旨意。继续假借所谓“天意不可违”的神话,通过君权神授的再强化强化皇权。因而,我们看到《春秋纬》对汉政权的神化无处不在:
有人卯金,兴于丰,击玉鼓,驾六龙。(《春秋纬·演孔图》)
有人卯金丰,击玉鼓,驾六龙。其人日角龙颜,姓卯金刀,含仁义,戴玉英,光中再,仁雄出,日月角。(《春秋纬·演孔图》)
其人日角龙颜,姓卯金,含仁义。(《春秋纬·演孔图》)
有人卯金刀,握天镜。(《春秋纬·演孔图》《春秋纬·孔録法》)
“卯金刀”指的是什么?如果还不明白,那就进一步晓示:
卯金刀,名为劉,中国东南出荆州,赤帝后次代周。(《春秋纬·演孔图》)
劉四百岁之际,褒汉王,辅皇王,以期有名不就。(《春秋纬·演孔图》)
原来这个“卯金刀”是刘的繁体字“劉”的部首拆分。这个秉受天命的刘姓到底是谁呢?
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季,天下服。(《春秋纬·汉含孶》)[注]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2页。
经过如此层层递进的解释不由得你不明白:这个秉天受命、代周而起的王朝就是刘邦建立的汉王朝。这个汉王朝与其它王朝一样,必秉受天意而立:
天子皆五帝精,宾各有题序,次运相据起,必有神灵符纪,诸神扶助,使开阶立遂。(《春秋纬·演孔图》)
强调这一点的目的在于告诉人们一个秉受天命而立的王朝,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取代的。即便社会衰弊、上天示警,只要天命不改,刘姓王朝就依然会继续存在下去。
当然,士人们心里清楚,神化皇权对下安抚百姓,对上则只有借天谏政一条路可走。尽管这一方法经过前期验证效果极差,但除此而外也实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于是,在一方面对下神化皇权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只得选择对上警示统治,以期双管齐下,维系汉朝延续。
辩证地看,上天示警,一方面表明汉代政治现状已经千疮百孔,上天已透露出愤怒和不耐烦,但反过来,又表明上天尚没有打算彻底放弃。不放弃就有拯救的希望,《春秋纬》的作者一方面对下试图通过强化大汉政权秉天而立,以再树天威延续人们对大汉政权的信心;另一方面对上则不得不直面政治衰落的现实,再借天象警示政治,所谓:“凡天象之变异,皆本于人事之所感,故逆气成象,而妖星见焉”,“天人同度,正法相授。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谓之教”[注]《春秋·元命苞》,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654、620页。。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春秋纬》的谏政言论直指汉末弊政[注]总括而言,大体内容有三:一是警示后妃干政,如“专于妻妃,则荧惑辗转轩辕中。”(《文曜钩》)“势集于后族,群妃之党僭,黄云四合,女讹警邦”、“后族专权,地动摇宫”(《运斗枢》)、“后妃专,则日与月并照”(《感精符》);二是警示帝王失德,如“八政不中,则天雨刀”(《演孔图》)、“君失德,则地吐泉,鱼衔兔”(《元命苞》)、“人主自恣,不循古,逆天暴物,祸起,则日蚀”(《运斗枢》);三是警示地方兵乱,如“星孛入北斗,兵大起,将有以外制权,以兵为政者”(《感精符》)、“荧惑入轸中,兵大起”(《文曜钩》)、“日赤足,有兴兵者。日白足,杀诸侯王”(《考邮异》)。统观《春秋纬》全文,其警示统治集中围绕帝王失德、后妃干政、大臣专权、地方叛乱几个方面,而这几个方面也正是汉末政治弊端的突出体现,其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
西汉末年是秦亡以来君主政治面临的首次失政危机,而危机的致因总括来看,无非是帝王失德、朝政腐败、大臣专权、后宫之乱,以及由这一系列内政腐败导致的蛮夷纷起。从前表《春秋》各《纬》的内容看,除了有对传统星占思想的继承外,主要就是围绕汉末导致朝政衰落的上述相关问题提出的警示,其中的针对性是十分明显的。
所以,今天看来,在攸关政权存亡的危急时刻,儒家经典中最关注政治的《春秋纬》的活跃,以及占星家们对彗星变化的重视和失政警示的陡增,甚至以“彗星出,则国枢蹶”(《春秋纬·演孔图》)、“彗星东出,长八丈,天下更政”(《春秋纬·演孔图》)、“彗星守北斗,天帝谋易王”(《春秋纬·演孔图》)[注]上述均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587页。等诸如此类“失政”“易主”的激烈言论相要挟,也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至于这些警示的目的,大多还是希望借助警示使统治者迷途知返,改弦更张,以挽救政治危局。就像哀帝丞相王嘉上疏所说:“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悦而天意得矣”[注]班固:《汉书·息夫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84页。,其中显露出士人对政治衰亡的焦灼与担忧。《春秋纬》正是以神化孔子和《春秋》、建立《春秋纬》的神秘性和可信性为前提,运用“新五德终始说”,在“天人感应”的再强化中实现警示统治、延续汉政权的目的。
可见,刘歆通过《世经》重塑“五德相生”,非但不是如顾颉刚所说是为王莽代汉制造依据,相反,恰恰是在预感西汉行将就木的情况下,“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注]班固:《汉书·平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页。,为刘氏政权合法性延续所做的最后努力。至于本为论证汉室永续的“新五德终始说”,最终演化成“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成为王莽篡政的理论注脚[注]无良文人哀章偷偷置藏有“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某(邦)传予黄帝金策书”的铜匮于高庙,假冒天命,篡夺汉室。王莽借此奏称:“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王莽又在即位诏书中说:“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班固:《汉书·王莽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06、4105页),显然与刘歆倡导“五德终始说”的初衷并不相干。
四、与王莽关系及其演化
可以说,刘歆的一生与汉室衰亡、新莽兴衰相伴生。其与王莽的关系与纠葛可从以下四个环节考察:
一是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王莽受王凤之托,与刘歆同任黄门郎。但不久二人便人各异途:王莽以外戚身份迁官射声校尉,自此一路高升,直至绥和元年(前8年)任大司马;而刘歆一直辅助父亲校理群书。此次共事二人虽交际不深,但开启了二者关系先河。
二是哀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哀帝即位,其时王莽首任大司马不久,为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向哀帝“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注]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7页。,刘歆被荐升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此间,因王莽与哀帝外戚丁、傅矛盾,被迫谪居封地,而刘歆则于光禄大夫任上,整理文献,建议将古文经设于学官,招致弹劾下吏,离开京都,迁任河内、五原、涿郡三郡太守,至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因病返京。
三是平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到王莽摄政时期。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九月,哀帝去世,王莽复任大司马,拥立平帝继位,操纵朝政,“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注]③班固:《汉书·王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45-4046页,第4046页。。刘歆受王莽拔升中垒校尉,包括歆子棻“皆以材能幸于莽”③。期间,王莽于元始元年(公元一年)进号“安汉公”,开启了迈向权力颠峰的第一步。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嫁女平帝,刘歆负责议定婚礼。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设明堂、辟雍,刘歆任羲和、京兆尹,主持兴建事务并因此立功被封红休侯。居摄元年(公元6年),平帝去世,王莽“兄弟不得相为后”为借口,抛开有资格继位者四十多人,“选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子婴,年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注]⑤班固:《汉书·王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8页,第4046页。立为皇太子,王莽向权力颠峰再近一步,以摄皇帝亲理朝政,开始大刀阔斧地改组行政,建构自己的权力核心:“以王舜为太傅、甄丰为太阿右拂,甄邯为太后后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⑤,刘歆为“四少”之一的少阿,位在“四辅”之下。
四是新莽始建国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正式篡夺了大汉政权,称帝。刘歆拜国师,受封嘉新公,以符命为“四辅”[注]班固:《汉书·王莽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19-4120页。。刘歆仕途至此达颠峰。但随着王莽新政的折腾,国内和民族矛盾加深,地方刘氏皇族反抗与边衅不断,在屡次祥瑞嘉应中兴起的新莽王朝在不断的灾难图谶中走向分崩离析。而在王莽政权快速崩塌的当口,种种矛盾机缘聚汇[注]包括新莽上层由甄丰贪权引起的内部矛盾、刘氏皇族与地方的反抗和刘歆二子刘棻、三子刘泳及女刘愔受牵连被杀(事见班固:《汉书·王莽传中》,第4123页)和自杀(事见班固:《汉书·王莽传中》,第4165页)。,促发了地皇四年(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歆与王莽关系由隐到显的实质性转折:“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庐道语星宿,国师不应。后涉特往,对歆涕泣言:‘诚欲与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怒莽杀其三子,又畏大祸至,遂与涉、忠谋,……(事泄)刘歆、王涉自杀。”[注]班固:《汉书·王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85页。
由王莽发迹及其与刘歆关系纠葛演变,应该有以下发见:
由安汉公到假皇帝、摄皇帝,直至篡政,王莽的欲望是在动态过程中步步递进,其篡逆之心其实是在登上权力中心的过程中渐次萌生的。而刘歆对王莽的态度也随这一过程的动态演变发生着变化——由辅佐转向谋叛,其中实质性的转折点应该是王莽篡政建新。班固《汉书》将刘歆生平分为两部分叙述。前一部分列入《楚元王传》附传,仅叙刘歆在汉行迹;“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注]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2页。。班固以王莽篡汉为转折点,将刘歆生平分为两截,在《汉书》编撰体例上属特例,有的学者也敏锐觉察到了这一安排具有的特殊用意,指出:“其中蕴含的特殊原因及展示的独特史观,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注]赵国华:《刘歆谋反事件考论》,《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简单说,蕴含其中的“特殊用意”就是要彰显刘歆在王莽篡政前后对王莽态度的转变:此前,刘歆的一切表现,包括扼制“更受命”、倡立古文、发明五德终始都是积极的,其百般褒扬、附翼、辅佐王莽的目的也是明确的,那就是维系陷入危机之中的汉政权的延续。甚至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毒死平帝成为“摄皇帝”、篡逆野心已然昭彰的情况下,天真的刘歆在居摄三年(公元8年)还借奏议王莽母亲功显君去世礼仪之机,试图通过“诏安汉公居摄践祚,将以成对汉之业”,“受太后之诏居摄践祚,奉汉大宗之后”之类的词句,提醒王莽谨遵“奉汉大宗”的“居摄”之位而不要有僭越之举。
此时的王莽虽已大权在握,并不断致力于铲除同姓和异性异己,收买人心,被王莽拥立的平帝也已形同虚设,但揽权与篡逆尚有天壤之别;另一方面,此时的王莽凭借其高超的政治手段与技巧,以谦恭俭让、礼贤下士的假相骗过了几乎所有朝野大臣而被视为“周公再世”,也便不可奢望出身皇族一介儒者的刘歆能看穿王莽的伪诈伎俩!在哀帝昏庸无能的无奈下,刘歆倾心拥戴王莽,寄希望于其倾心辅佐汉室,挽救刘氏危局,也自符合情理。
伴随王莽从“安汉”、“居摄”到建新,刘歆经历了从倾力辅佐到“内惧”的心理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了刘氏宗室而又一介书生的刘歆面对汉室大厦将倾的内心苦痛。班固洞察到了这一微妙的心理变化:“初,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德,……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桀。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歆内惧而已。”[注]②③班固:《汉书·王莽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23页,第4126页,第4123页。“内惧”二字,十分恰当地反映了作为刘氏皇族、一介书生的刘歆,对王莽由辅政到篡逆的清醒认识与恐惧。与刘歆一同陷入恐惧的还有倍受王莽重用的太师王舜:“太师王舜自莽篡位后病悸,浸剧,死。”②王舜与刘歆的“恐惧”,内容或有不同而结果趋于一致:一个病悸而死,一个谋反自杀。
刘歆平生行迹显示:从表象上看,刘歆的职位虽然并没因王莽篡政而终止,甚至是在王莽篡政后其职位达至顶点,然而细观刘歆之作为,我们不难发现:刘歆整理文献、倡立古文、发明五德以及讲究礼仪、设章建制等积极作为均是在王莽篡政以前,在王莽篡政之后则几乎在政坛上毫无建树,而在始建国二年条下,班固却意味深长地记载了如下信息:“初,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③其下接踵记载了因甄丰贪权导致刘歆的两个儿子受牵连被杀。之后,从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汉书》集中描述新莽统治江河日下,天灾不断、盗贼蜂起,刘歆行迹长久地销声匿迹。直至地皇四年随着更始政权在绿林、赤眉烽火中崛起,新莽政权的分崩离析,班固方于此年条下突然集中叙述刘歆、王涉谋叛。这一叙述,作为刘歆生平以及刘歆与王莽纠葛的终结,以突然的形式爆发式地体现了刘歆对王莽篡政从无奈、隐忍到为“安宗族”而奋起反抗的最后的殊死一搏。
五、皇族出身与士人性格
一个人的作为与其出身、环境及由此决定的性格养成有着密切关系。在西汉衰落的大背景下,一向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自任,为西汉政权的存废倍感焦虑的儒者们,越发强烈渴望参与政治、尽己所能挽救时局,这是儒者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使然。与一般儒者相比,刘歆作为出身皇族的儒者、经学家,对于刘氏政权存亡的焦虑自然更加强烈。从家风渊源看,刘歆的父亲刘向就一心向汉,曾因屡谏元、成二帝[注]参见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而频遭宦官弘恭、石显谗害[注]元帝时,刘向(本名更生)与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侍中金敞“四人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望之、堪、更生议,欲白罢退之。未白而语泄,堪、更生下狱,及望之皆免官。”(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9-1930页)。其《列女传》的写作,正是直接针对元帝时期的外戚宦官专权和成帝的淫乱[注]“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踰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採《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顾家可法则,及孼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57页),希望通过“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注]曾巩:《列女传目录序》,《曾巩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9页。,以古为鉴,讽谏政治,以保江山永固。所谓:“向每召见,数言……方今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社稷,安固后嗣也。”“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注]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6页。。
刘歆生活于西汉政权江河日下的元、成、哀时期,其命运跌宕和政治焦虑自然甚于其父。据班固《汉书》本传载,因《移让太常博士书》“其言甚切,……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注]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2页。有学者怀疑《汉书》的说法,以为:刘歆被贬外放于建平非因儒者反对,而是因为王莽受外戚丁、傅排挤而遭免官,“刘歆牵连其中”(徐华:《刘歆〈遂初赋〉的创作背景与赋史价值》,《文史遗产》,2013年第3期)。。于哀帝建平初年[注]有学者考证,刘歆被贬外放时间为哀帝建平二年,《遂初赋》写成于守河内、游五原之后的建平三年(徐华:《刘歆〈遂初赋〉的创作背景与赋史价值》,《文史遗产》,2013年第3期)。外放五原,一路有感而发写了《遂初赋》[注]有学者考证刘歆遭贬的原因是因为哀帝继位后支持外戚丁、傅,王莽遭抑制,受王莽重用的刘歆受王莽牵连遭外放,可作一说(徐华:《刘歆〈遂初赋〉的创作背景与赋史价值》,《文史遗产》,2013年第3期)以“感今思古”,“而寄己意”[注]《遂初赋·序》,《古文苑》卷五,《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6页。。《遂初赋》以山西古晋国为历史地理背景,以颇具开拓性的现实主义手法,怀古吊今,因史鉴今,借两周兴衰,由晋不护周与晋强卿政治导致西周和晋国衰亡,暗讽西汉末刘姓宗室羸弱、枝叶不茂与外戚强大下的政治衰相。此赋无疑是审视两汉之际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刘歆其人的重要材料:
过下虒而叹息兮,悲平公之作台。背宗周而不恤兮,苟偷乐而惰怠。枝叶落而不省兮,公族阒其无人。日不悛而俞甚兮,政委弃于家门。
始建衰而造乱兮,公室由此遂卑。怜后君之寄寓兮,唁靖公于铜鞮。越侯甲而长驱兮,释叔向之飞患。悦善人之有救兮,劳祁奚于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为群邪之所恶。赖祁子之一言兮,几不免乎徂落。[注]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六十·刘歆》,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45页。
全文充斥了面对汉末政治衰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与茫然,表达了对刘氏皇族及其政权存续的无限忧虑,倾诉了对自己遭遇不公的无比愤慨,所悲所叹无不显露出其由皇族出身与士人性格所决定的心系汉室的政治倾向。
一个人的性格表现受制于先天出身与后天经历。出身皇族又蒙受经学熏陶的刘歆,自然免不了兼具皇族、学者的风骨与傲慢。这一点,我们从他对同为经学大家的父亲曾屡有发难:“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注]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7页。可以发见。东汉贾逵也曾有“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致使“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仇”[注]范晔:《后汉书·贾逵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7页。的评价。以渴望汉政权有“百世之基”的皇族立场,兼以如此高傲的士人秉性,岂是为感恩王莽举荐为官,便肯轻易背弃皇族荣耀与刘氏政权根基,摒弃梗直忠贞的家风而趋炎附势、助莽篡汉的利禄之徒和蝇苟之辈!
上述分析可见,作为大汉宗室、一介儒者的刘歆,绝不可能甘愿为一己之私蝇营狗苟,助莽篡逆。相反,其为维系汉政权苟延残喘的良苦用心于此可见一斑。
真实的历史往往是复杂的,客观上看,刘歆包括倡导古文、发明五德等所有辅莽行为,在客观上的确对王莽篡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或成为王莽篡政的助力。然而,也应同时看到,这并不是刘歆倡导古文经学的主观目的。从上述刘歆对刘氏政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却又忠于刘汉历久不衰的表现可以看出,刘歆对王莽的配合,是基于王莽辅助刘汉政权的前提之下的。王莽的篡政,并非刘歆的主观愿望。这一点,班固已经看得很明白。钱穆的考证也指出了这一点:“按:歆在当时,名位尚非甚显。同时在朝出歆右者多矣,谓莽尊信歆,推行其伪学,若其时惟歆与莽沆瀣一气,同谋篡业,此非史实。”[注]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五册上编),第187页。所以,需要明确的是,即便刘歆的倡立古文客观上助推了王莽篡汉,但辅莽“安汉”始终是刘歆的主观本意,从当刘歆觉察到王莽“居摄”而“内惧”并从辅莽转向反莽的表现足以证明[注]不仅刘歆在王莽篡逆后从支持他走向反面,即曾为王莽座上宾并因辅佐王莽走上“安汉公”之位而号称“四辅”之一的甄丰,也在“莽篡位后,丰意不平,卒以诛死。”(范晔:《后汉书·彭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03页),所以钱穆有所区别地下结论说:“莽之篡汉,歆、舜之徒以革新政考相翼,而愚人争言符命,则甘、夏之流也。”[注]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五册上编),第171页。而主观上“助其篡逆”与客观上为支持王莽辅佐汉室而“助推了其篡逆”,是有着“故意”与“非故意”的本质区别的。